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ID:Neugeist),作者:Joseph Epstein(美国作家),译者:宴梁,审校:杨银烛,编辑:杨银烛,原文标题:《从达芬奇到桑塔格,博识者会成为时代的眼泪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认识论是一门关于知识以及如何获取知识的学问,但就博识者(polymath,知识面极广的人)这一话题而言,当今的认识论却无话可说。它也无法告诉人们满足什么标准才可称得上博学、甚至称得上受过教育。一个没有学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不懂音乐、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可以自称为博识者吗?而说到教育,鉴于当今大学所包含的远远不止科研院系的现状,所以,没有任何一人可以因其大学毕业而自称受过教育。问题在于,信息和知识有什么区别,以及知识和智慧有什么区别。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论正如一片肥沃而尚未被开垦过的土地。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是一位英国的文化历史学家,也是新书《博识者》(The Polymath)的作者。他把自己的研究主题定义为“有兴趣学习多门学科的人”。而要想配得上这个头衔,就必须表现出对几门学科有相当程度的精通,这通常由其发表的作品或发明来证明。真正博识者的目标是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热衷于掌握尽可能广的知识面。在历史上,“博识者”一词还可以被其他称谓所替代,包括博学者(polyhistor)、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通才(generalist)、文人(man of letters)等。大多数博识者所寻求的目标,常常是不言而喻却甚少实现的大智(pansophia),或称普世智慧(universal wisdom)。对学习和智慧之间区别的探讨,也正是《博识者》的主线之一。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段从列奥纳多·达·芬奇到苏珊·桑塔格的文化史》,这个标题暗示着博识者在历史进程中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坡路。但在此过程中,知识领域在不考虑深度的情况下极大地扩大了其研究广度。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目标本身在很长时间里被看作是愚蠢和哗众取宠的。早在18世纪中叶,狄德罗和达朗伯的百科全书仍然将“博识(polymathy)”定义为“通常只是一堆混乱而无用的知识,用作‘表演’之用罢了”。

究竟为何会有人想要成为一名博识者?宽泛而无休无止的好奇心是一方面,智力上的好胜心和虚荣心则可能是另一方面。第三个,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对发现所有知识之统一性的强烈驱动(如果确实存这种知识统一性的话)。
伯克列出了成为一名博识者所需要的品质:高度的专注、强大的记忆力、知觉速度、想象、精力、好胜心等。他也将自己研究的博识者们以被动型(passive)、集中型(clustered)和连续型(serial)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库斯关于刺猬和狐狸的二分法——“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也是贯穿伯克这本书的另一主题。(译者注:被动型指只获取知识,而不产出作品;集中型指专于某一系列相关学科内,如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连续型指连续跨域于不同学科的人。)
能写出《博识者》这样的书本身就是身为博识者的一种表现。伯克从人类历史中选取了上百位博识者,为这些与众不同的人撰写了精炼的传记。伊本·卡尔敦、伊拉斯莫、牛顿、培根、莱布尼兹、维柯、孟德斯鸠、布丰、勒南、杰曼·德·斯戴尔、冯·洪堡兄弟、孔德、乔治·艾略特、马克斯·韦伯、威廉·詹姆斯、帕特里克·格迪斯、罗曼·雅各布森、詹姆斯·弗雷泽、李约瑟、刘易斯·芒福德,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极富才智的人都被列举在了这本书中。伯克欣赏这些人,同时也了解他们的缺点。
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列举了500个他认为称得上博识者的人。但他所列举的人越接近今天这个时代,也就越有争议:大卫·理斯曼、罗纳德·德沃金、雅克·德里达,这些是博识者吗?我不认同。还有,他为什么忽略了罗伯特·奥本海默?

在关于“犹太人博识者”的一节中,彼得·伯克引用了托斯丹·凡勃伦的文章《犹太人的智力优势》,并且他也指出,他名单中的犹太人直到19世纪中期之后才频繁出现,大约是伴随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一项向犹太人介绍西方世俗学问和文化中的运动)而开始的。在犹太人博识者中,最著名的犹太人包括著有《论犹太人问题》的卡尔·马克思。在伯克所列的500人的名单里,出生在1817年后的“250人中有55人是犹太人”。
博识的兴盛主要在17世纪,伯克认为在这个时期,“欧洲人度过了一段延长的自由时光,一方面传统对好奇心的怀疑与压制逐渐式微,另一方面智力的劳动分工方兴未艾”。新世界已经被打开,而“新的知识正在不断涌来,撩拨着学者们的好奇心,却又不至于吞没他们”。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富于才智的犹太人仍然主要关注在《塔木德》和其他更严格的犹太教经典中。巴尔·谢姆·托夫、维尔纳·加翁以及他们的信徒关心着那些他们认为远比博识重要得多的东西。
然后就出现了我认为的智力怪胎。其中大部分人我在读这本书之前都不了解。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据说了解不下30种语言。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全才”,他是一名物理学家,会西伯拉语、叙利亚语、撒玛里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发表过人身保险、声学、光学等主题的论文。
贝尼托·赫罗尼莫·费伊豪(Benito Jerónimo Feijoo,1676~1764)是一名被描述为“学习怪人”(a monster of learning)的本笃会僧侣,他写过“神学、哲学、语文学、历史学、医学、自然史、炼金术、占星学、数学、地理、法律、政治经济学、农学、文学、水文学”方面的内容。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是一名杰出的数学家,兴趣涵盖光学、化学、摄影、天文学、词源学,以及对翻译可靠性的研究,而在此之外他仍尚有精力担任威尔特郡奇彭纳姆的议员。
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是一名科学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还是国际图形字体教育体系ISOTYPE这一视觉语言系统的发明者,据说他一天读两本书。光是阅读这些人的故事就已经让人感到脑力枯竭了。这些人和书里刻画的其他博识者们,令歌德(他本身也是一名天才的博识者)都相形见绌了。
据伯克所说,最好的博识者能够“看到那些宏大的图景,并指出其中专家们所忽视了的联系”。很多博识者们都长年对知识统一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伯克书中的另一名博识者,雅克布·布洛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1908~1974)写道,“我所写的一切,尽管千差万别,但它们都在接近同一个母题,那就是人类的独特性,通过其奋斗(和天赋)来理解自然和自身的过程所产生的独特性”。迄今为止,博识者们在前者方面(理解自然)比后者(理解自己)做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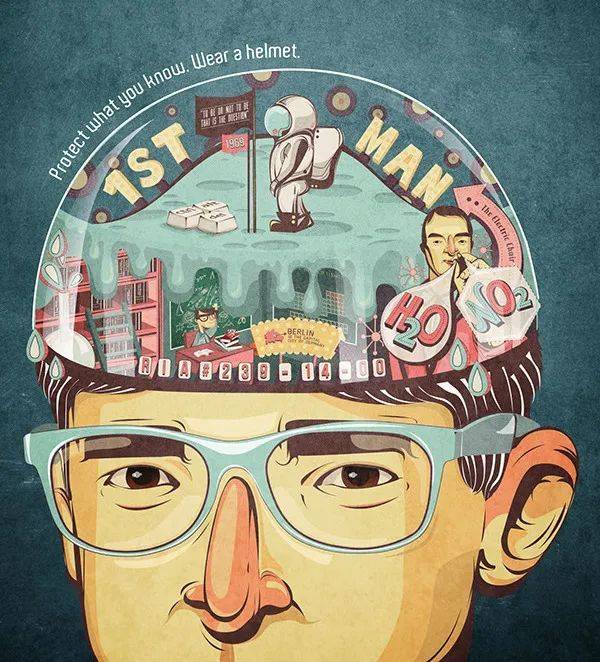
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特别是由现代大学院系和专业的划分,都是在排斥博识者。然而,像伊曼努尔·康德、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这样的人物(后面两个还是伯克名单中的博识者)都表达了对专业化的赞誉。斯密认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越是精通,就会有越多的贡献被添加到人类对整体的认识中,而科学也因此得以增长。”一个世纪后,韦伯补充道,“摒弃浮士德式的知识统一目标,而将工作限制在专业分工内,是现代世界中任何有价值的工作所必要的条件”。
博识者也可能会因其浅薄和业余而受到批评,特别是来自专家们的批评,更甚者被指为纯粹的骗子。对此,可以想一下以赛亚·伯林对乔治·斯坦纳(也是名单中的博识者之一)的描述,“非常罕见的家伙,一个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伯林也对雅克·德里达发表了类似的评论。不过伯林本人也出现在了伯克的名单中,我很怀疑当他在名单里发现自己时是否会高兴。
伯克将这一问题称为列奥纳多综合征,也就是“由于兴趣分散,博识者们经常在写书、做研究和发现时,进行不下去”。他补充道,“很多博识者没能完成工作计划就是由于其过于分散的兴趣和精力”。在这些博识者中,最伟大的或许是达·芬奇,而他因为自己兴趣过于宽泛,不免留下了很多有用的工作没有完成。伯克写道,“(达·芬奇所设计的)巨弩实际上并不实用,他‘化圆为方’(也就是求π)的企图也落空了,还有《最后的晚餐》那糟糕的保存情况(在几年后已经可见端倪),则是由于他在化学实验上的失败所导致的。”
如果一个人在智力上有丝毫的自负,那么他读过《博识者》这本书之后,很难不去思考自己在博识者们当中的位置。
在我自己相当自负的一段时期里,我被称作是文艺复兴人和文人,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动机在背后推动我去成为一名博识者。必须补充的是,我也从没有感受到任何促使我成为专家的驱动。嗟乎!我就是这样乏味的一个人,仅仅满足于去学习自己感兴趣、或者是能从阅读和思考中获得乐趣的东西。
除此之外,因为任何不对科学有严肃兴趣的人都是不能称之为博识者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因为缺乏天赋和兴趣而被取消了资格——但我还是很感激应用科学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我满足于自己可以仅仅生活在这个宇宙中,而把对宇宙的描述留给其他人,从分子层次到行星水平。
即便如此,我还挺热衷于去关注科学本身有多么常犯错,就像伪科学那样,而且有时候还是非常严肃的错误。例如在1949年,一个叫做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的葡萄牙神经学家因为发明了脑前额叶切除术而摘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在弗洛伊德的错误学说所统治的约75年间,谁又能说它对人类造成了多少损害呢?关于意识,大脑最基本和最有趣的功能,那些被大肆鼓吹的脑科学新领域却尚未告诉我们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塞缪尔·约翰逊说过,“知识之海太广,哪怕是最积极最勤奋的智者也不能探索尽它”。这句话曾缓和了我的好奇心,使之从未驱使我离开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我不能用爪哇语做梦、用西里尔文字写作、或根据《爱经》的指示来做爱,但我不会因此而感到不满足。而对于从海草中提取碘或是学习海豚的语言,我则毫无兴趣。
伯克写道,17世纪时的百科全书是由单个作者撰写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知识之圆(circle of knowledge)*,暗指如圆一般完满的知识,或是所有可触及的知识。当然在后来,百科全书就由很多人一同来完成了。
我曾在《大英百科全书》做过几年编辑,当时由莫提默·艾德勒重新组织编撰。
艾德勒不在伯克的名单里,他也没有在《博识者》这本书里出现,但他本人完全可以称得上博识。他智商极高(我开始相信智商主要衡量的是一个人的抽象处理能力),与之相映成趣的则是他极度缺乏常识。(艾德勒想在他的湖滨大道公寓挂一幅画,但他发现自己没有锤子,所以他去了附近的登喜路。但那里不卖锤子!所以他买了一个黄金做的花洒,然后回到家用它把钉子敲进墙里。)
我参加过很多会议,艾德勒在这些会议上极富智慧并且精力充沛,他试图把所有知识分为九类(主要是为了减少《大英百科全书》早期版本的工作量)。但事实证明,知识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有可塑性。(译者注:encyclopedia可被分解为en-cyclo-pedia,其中cyclo对应圆,pedia对应知识。)

这在被称作数字时代的今天,似乎变得更加不可能了。互联网中充斥着海量的信息,其中有些信息是真的,大部分则是假的;一些只是有所成见,而相当多的则充满恶意;绝大多数都是刻薄而非和善的。在数字时代里,维基百科代替了《大英百科全书》和谷歌黄页,几乎每个有手机的人都在口袋里装入了一座图书馆。还有谁会想要试图统一全部的知识领域呢?
彼得·伯克也清楚数字时代为博识者们设下的障碍。伯克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出生在互联网问世之前。他指出,过去很多帮助到博识者们的工作都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例如像图书馆管理员、书店老板和员工、博物馆馆长等。而如今强调知识分科和政治正确的大学,也没能为博识者们提供其所需要的自由学习环境。
相反,数字时代提供了过量的信息。托马斯·杰斐逊写道,“消息灵通的公民是对暴政最好的防御”。但如此多自由传播的信息,难道不正在以某种方式塑造一种新的暴政吗?人们可能会认为,信息的过量同时也伴随着人才的减少。
爱德华·萨义德、苏珊·桑塔格、斯蒂芬·杰·古尔德,这些人都在伯克的名单上,但他们真的是博识者吗?
萨义德发表过一部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关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书,写过一些音乐评论;桑塔格读过哲学,从学术角度写过关于摄影和低俗文化的书;古尔德写过科普。这些人与莱布尼茨、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培根这些早期的博识者相比如何呢?弗如远甚。
不过,《博识者》一书并未提及博识者显然的式微。在书的末尾,伯克仍然抱持博识者复兴的愿望,他引用莱布尼兹的话,“能够联结万物的一个人要胜过十个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里,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这样的人”。然而真的如此吗?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joseph-epstein/polymath-know-it-all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ID:Neugeist),作者:Joseph Epstein(美国作家),译者:宴梁,审校:杨银烛,编辑:杨银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