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作者:毒Sir,头图来自:《过把瘾》截图
你信不信爱情?
不信?你不是经历少了,就是看片少了。
信?那是你看片多了,看八卦少了。
你看赵丽颖,从2018年官宣结婚到离婚不到3年。结婚时有结婚的祝福,分开时有分开的祝福, 你信哪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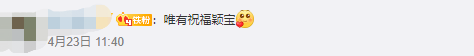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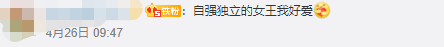
这个提倡独立的年代,后一种祝福显得更应景。
“神仙般的爱情”好似最套路的电影营销噱头,高潮戏让观众云里雾里,下了票房就烟消云散。如果不散,一定是因为撕逼,比如张恒还在孜孜不倦地撕郑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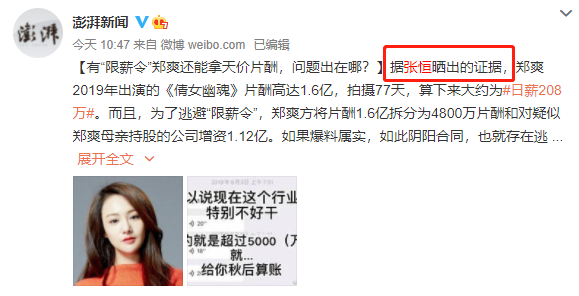

好你问了,那Sir你信不信爱情?
我信!但不是因为看现在的影视相信的,而是因为当年的我看过、信过王朔的那本,赵宝刚的那部——《过把瘾》。

海报像素感人,谅解一下,这是1994年的国剧,但除了像素感人,其余的都感人,是真的感人。它是纯爱剧,在当时太稀罕,也当然击中了纯纯的少年Sir。我模仿过王志文走路,那种标志性的甩手,微罗圈的腿,还学他撩人时的贫,愤怒时的人狠话不多。

我喜欢上了江珊那种卷发女生,爱屋及乌喜欢上了护士群体。

我开始向往未来也能有一个爱吧唧嘴喝茶的讨厌上司,有一个小破工作,只因为片中当个反抗的愤青好像挺酷……

以及,我开始过早向往爱情,并且当时班上,肯定不止我一个。所以现在Sir能理直气壮地给《过把瘾》下个定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聚焦都市男女爱情的电视剧。
导演赵宝刚,找到了文艺不羁的王志文,以及貌似任性娇憨的江姗,饰演一对北京恋人,找到了刘蓓和赵亮(剧中饰演潘佑军潘胖子)给他们搭戏。


这四人搭戏,绝了。以至于Sir后来再看到《鬼吹灯》《盗墓笔记》里的胖子角色,都觉得是从“潘胖子”来的。
《过把瘾》融合改编自王朔的三部小说,《过把瘾就死》《无人喝彩》和《永失我爱》,讲述了文化馆职员方言(王志文 饰)和护士杜梅(江姗 饰)之间的爱情纠葛。

现在看来,它当然也规避了些什么,比如“就死”两个字就没了。从流行文化产品的角度看,“过把瘾”三个字也确实具备更主流的传播效果。
但它当然不是一部心机剧,没有挂羊头卖狗肉,没有灌水。因为那个年代一点不需要水,它只要拍出来就是对的,哪怕只有八集,因为那时就缺它。
对,《过把瘾》就八集。八集,需要高度对故事进行提纯,把三部小说主要情节讲完,进展之快,起伏之大,真过瘾(对于王朔铁杆粉来说也未必)。
再问一个,《过把瘾》当年有多火?它让王志文和江姗一跃成为当年最火的荧幕偶像,合唱的主题曲《糊涂的爱》红遍大江南北。

爱是歌的主旨,而糊涂是爱的方式。
多年后,演员在节目重聚,还说起当年剧组去天津,如何被热情的观众堵在百货大楼,以至于赵宝刚非得跳窗才能摆脱……然后他还跳伤了。
“就是天津市百货大楼,然后观众都拥去了,一步步的堵堵堵,堵到了四楼,最高的一层,然后我们就下不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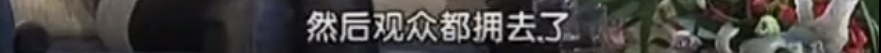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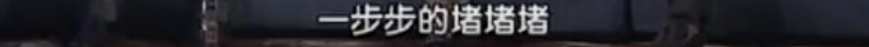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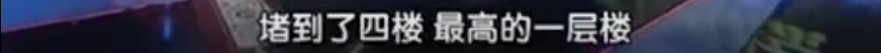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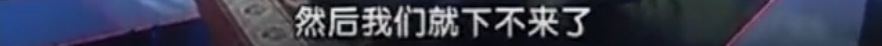
不,其实90年代的人爱得不糊涂。
彼时,全国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都有王朔的大部头摆放。那还不是穷青年寻找王朔的地方,口袋里只有五毛一块的初高中学生,放学了纷纷涌向地摊,因为那儿有更破旧的王朔全集,租一本一毛二毛,有明显盗版嫌疑,油墨脏,字小而挤,摸几页手就黑……
当时的文学,就是如今的网游如今的Switch。哪怕对文学二字无感的少年,也会想听王朔侃侃北京的街头爱情和地下江湖,听苏童扯扯南方的城北地痞和车站流氓。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不缺小说,不缺故事,只缺剧。你说胡扯,他们不缺。对,90年代不缺普通的剧。但你仔细想想吧,《渴望》那一类命中心灵的剧只属于90年代中年人。

而90年代的青年,他们从《西游记》的童年走来,从《我爱我家》和《包青天》的少年走来,他们刚刚觉得自己懂事了,以前的那些不够了,需要把王朔、苏童用劣质油墨给予他们关于真实生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剧里的、一张张活人的脸。
所以90年代的青年传统,也不传统。比起现在,他们当年对爱的追求,更有一种动物般的凶猛。他们想看见更极致的爱情与反抗,用来自黑自嘲,用来对照自己过于平庸守旧的学业、工作和感情。
他们不会像我们,让自己过度分神于社交话题,被太多政治正确的讨论耽误和绑架。他们喜欢《过把瘾》,因为它既小心,又大胆。所谓小心,是它不屑于用人设标签去盖棺定论,反而会拧着观众的头,让他们直面爱情的复杂、伤害与不完美。
等他们终于看见爱情婚姻的另一面,它才会大胆问出一些貌似“不正确”的问题,都是些什么问题呢?
放现在,你未必答得出来。
01
故事,始于方言好友潘佑军和石静的婚姻之死。这是剧里起初的一对影子夫妻,从一开始就给主人公方言和杜梅的爱情,加诸了不祥的阴影。潘胖子与石静这一对90年代小夫妻,从热恋到结婚,到横眉冷对,到彼此厌恶,只经历了几个月。
胖子对方言抱怨说,“我发现我现在都不会笑了。”
胖子说,“石静就是精神暴君。”
胖子还说,“我这比监狱还惨,监狱刑满释放,有个盼头。我这倒好,白头到老,终身死囚。”

那边的石静会说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也就是在这个丈夫,潘胖子惯常逃避回家的某个夜晚。石静给自己化了一个精致妆容,换了一套漂亮干净的衣服,打开音乐,喝了好几杯红酒。最后一杯,泼到了两人的结婚照上。

然后转身,从阳台一跃而下。
这一刻胖子的嘴还没闲着……直到他看到了那个影子掉下来,整个人才傻了。

所以婚姻是什么,是悲剧吗,是爱情的坟墓吗?问得有些矫情,可这其实不止于一个文艺话题,而是90年代很多观众心里默默思考过的真问题。
改革开放打开一片新天,也动摇了小市民阶层的传统和安稳。是留在单位还是跳槽,是留在籍贯还是去沿海碰运气,是拿死工资还是拼个万元户,是做个全职老婆还是上班……人们诸如此类对未来的想象反复碰撞着,生存观、价值观难免就动摇了传统的婚姻观,但生活总要继续,思考不能打断它继续。
来,既然是故事,那让我们再做一次实验——
因为石静的死,方言和杜梅第一次在葬礼上见面。还没等观众从悲剧中缓过神,新的爱情又悄悄萌发。
男人套瓷说:“你一般中午吃饭吗?”
女人飒飒回答:“瞧这话问的,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于是男人直接了:“其实我挺想请你吃饭的。”
女人给面儿了:“这不难实现。”

“干柴烈火”这个词会侮辱这段爱情,虽然每段爱情总有干柴烈火的时刻。
在书中,方言和杜梅你来我往也有好几个回合,可因为剧只有八集,看起来就像是短暂地试探,然后迅速也合理地相爱了。

然后趁着火焰的余热,他们领证了,结婚了。方言忘记了潘胖子的叮嘱,杜梅也丢掉了关于石静跳楼那段不好的记忆。因为爱情是如此私人的体验,私人到,从不会虚心借鉴他人的经验。

好的故事,总会悄悄埋线。
刚走出民政局,杜梅和方言就吵了架。原因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谎言,反而是因为真话。男人对新妻子,感叹了一把结婚的简单。女人翻脸了:“敢情结婚就这样。”
“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后悔了还来得及。”

现在的人看来,会觉得这两人太年轻,不圆滑,没搞懂婚姻是什么,相处是什么,但这是现在的看法,可从前的婚姻没现在复杂。从前只要有了爱情,婚姻就是幸福的,就会有下面一些顺理成章的词,比如理解、迁就、磨合……
但现在有爱情,婚姻也未必幸福,因为婚姻不再是第一顺位,它下面,不,它前面还会顺理成章地排列着权利、空间、自由……
所以,真不一样。
也有一样的。一样的是不管过去现在,刚结婚就拌嘴,刚买房就吵架,刚生孩子就分居,都不像好兆头。这是他们第一次吵架。虽然只吵了几句便和好,但也成了伏笔。

又必须扔出一个中国夫妻最熟悉的词:性格不合。方言和杜梅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之间,会从第一次几句小拌嘴,发展到后来砸东西,烧屋子……



客观一点我们说:呃,这是一个性格不合,导致两人水火不容的悲情故事。但主观一点,回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你还愿意只聊这个?
你不想问得更深一点?比如,像潘胖子那么问:“谁能永远保持新婚和热恋的温度呢?你能吗?”

02
石静死后,潘佑军曾这样困惑地问方言。他困惑了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也曾想保持、想维护。所以为什么两个都想维护爱情的人,最终会维护不了婚姻?
这一句,也是整部剧的探讨核心。
同样在1994年,王家卫在《重庆森林》里,也问出了类似一句:“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方言和杜梅之间的爱情来势汹汹,维系却举步维艰。越相爱,越靠近,越痛苦。
方言是一只怎么样的刺猬,不,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整日闲散无事的文化馆员工,没什么追求,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嘴贫,带着一种洒脱不羁的痞气。在他告诉潘胖子自己要结婚时,对方相当难以置信:“你敢说“爱情”俩字吗?你在乎过什么呀?”
方言,是王朔笔下具有代表性的“无能浪子”形象,别说你不喜欢,当年很多人喜欢。也别说当年那些人是“糊涂着喜欢”,当年是当年,你不在当年(当年的喜欢,也是对自我无能境遇的一种心照)。
说公道一点,“喜欢一个人”和“这个人没毛病”,是两回事。
一个啥都不在乎的人,其实肯定在乎一个人或一件事。对方言来说,就是这个好不容易遇到的杜梅。所以方言貌似满不在乎,貌似打开了人性宽容的最大极限。但这种人,一旦两脚踏进了婚姻,就处处被动。
他不愿看清婚姻的真相,因为他更信奉“无能的力量”。他觉得有了爱情,其他算什么呢,他轻视生活的本质,轻视相处之道,轻视环境与舆论的阻力。可爱情与维系恰恰离不开这些,所以他进而轻视的,就是婚姻本身。
是的,这是一个不在乎生活瑕疵的人,所以,也就不研究瑕疵,无力解决瑕疵,进而会累积瑕疵。 瑕疵累积久了,婚姻会变成什么?
牢笼。
再看杜梅。王朔在原著里形容她: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老爷手中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

这话听岔了,你会以为这女人是悍妇。但,当然不是这意思。
杜梅是大刀,这是对她敢爱敢恨的比喻。杜梅锋利无比,因为她只要极致的浪漫,只要永远激情的爱,但杜梅并不只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她从小就孤单,因为父母也有婚姻悲剧,她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她对婚姻,反而有着最低门槛的接受度。
结婚时她对方言说:“只有你爱我,有张床就够了。”因为条件有限,他们的婚房是教室,教室黑板上,被她大大小小写满了“爱”字。


所以你发现没有?
“性格不合”恰恰不适用于这一对情侣,因为他俩其实是一种人。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杜梅是一个对一切(除了爱情)都不在乎的人。但婚姻的失败,恰恰因为她的“各种在乎”,几乎形成了对方言的禁锢,这又是为啥?
来,问一个问题吧。
如果你是个穷人,口袋里只有一件让你珍视的东西,你会怎样?你会时不时查看它,对不?你会害怕它丢掉。
杜梅也是这样。因为方言的爱是她唯一珍视的东西,她才会穷追不舍,天天确认方言爱不爱自己。确认一遍不够,也并不因为杜梅无脑,恰恰因为她心理也对爱情的本质有所担忧和怀疑。这是不是那件,容易过期的东西?
新婚之夜,她追问方言:
杜:石静呢?(你喜欢石静吗?)
方:她已经死了。
杜:如果她不死呢?
方:她是潘佑军的媳妇。
杜:如果他们离婚了呢?
方:你不是说她不喜欢我吗?
杜:如果她又喜欢上你呢?
方:……
杜:问住了吧!

假设都伤人,这还只是假设,生活不止有假设。一旦看见方言和别的女人走在一起,她会更痛苦;方言如果表现得蛮不在乎,她会更愤怒。所以,方言的不在乎纵容了瑕疵的存在;而她每一次在乎的查看,都会放大每一个瑕疵。久了,婚姻会变成什么?
还是牢笼。
现在我们知道了,牢笼,是我们对情感绑架的最好比喻。
都是现代人了,你在婚姻原本第一顺位的序列前排列的每一个词,现在都比婚姻重了。独立、空间、自由,这些词你一个都不会忘,因为它们是时代精神,是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顶端最美丽的宝石。
可是,当这些词开始绽放光芒,婚姻会显得多么不堪。它是曾经方言憋在肚子里不好意思出口的话;它是后来在杜梅穷追猛打下,方言才勉强吐出的“爱”字。

它是初识时,方言会主动帮杜梅撇开的烟;后来成了婚姻冷战时,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雾。


它是曾经如胶似漆的两人,为了永远把对方嵌进身体,最终抵达的彼岸;现在,是轻轻触碰便抽回的手,是掉到沙发下谁也不会去捡的廉价打火机。



所以放过爱情,我们谈电影吧。
仅仅从影视角度说,今天爱情剧只敢发糖的原因,离不开“正确”。把《过把瘾》从90年代故剧堆里扯出来聊,也是为了这个——它是足够真诚的。但把它放到今天,又会有多少存活率呢?
潘胖子在前妻自杀后没多久就有了新欢,试想如果在今天,一场关于他的社会话题审判,肯定会让《过把瘾》大火。但是不是,也同时造成了《过把瘾》的命题性死亡?
我们还会、还敢真诚地思考爱情吗?下一个编剧,又该怎么编才保得住小命呢?

杜梅因在乎而产生的“感情绑架”,方言因不在乎而出现的“不负责任”,用如今的创作眼光看,都是危险人设。
两人离婚后还为了赌气,各自理直气壮地“养备胎”,难道不是典型的“渣男渣女”?如果审判这些,肯定能让《过把瘾》大火,但又有哪个演员敢演?他或她,怕不怕社会性死亡呢?


为了正确,为了讨喜,我们再看不到爱情完整的样子。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糖霜,真实的连一半都没有,哪怕它符合世界、符合熵增、符合人性、符合时势都不行。
所以Sir想说,《过把瘾》和如今发糖剧的距离,就是“正确”和真诚之间的距离。“正确”我们只会挂嘴上,用来站队和被站队;真诚,才让我们行动,真的去改变自己、改善现状和世界。
就像前面说的,90年代的人看剧,即使结局不那么令人开心,不那么让人感到安全,可他们反而会更审慎地面对。没人会反对吧,30年前的婚姻更有韧性,当然不是因为那时婚姻法更强势,而是因为人们更有智慧和技巧去面对婚姻的瑕疵,生活的瑕疵。
当然反过来说,也不会因为它更有“韧性”,它就属于美德。韧性之下也有别的可能性,那都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
而今天呢?当《过把瘾》里不完美的男男女女,在爱情剧中绝迹。当我们获得所谓的“正确”,假装看不见真实存在的瑕疵和不完美,我们就完美了?当男主和女主的人设修改到毫无“瑕疵”,一点毛病没有,为什么我们反而觉得他们作妖呢?
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因为这是一场彼此的捆绑,编剧和观众,市场和故事。谁都不敢放手,谁都在等着今晚票圈里“正确”一下你,或者被你“正确”。
如果什么东西吃反胃,我们才会呕吐。那我只能期待这一场呕吐来得快一点。也真诚的把这部好剧,推荐给错过它的年轻人。
它只有8集,看完别急着发言,别急着评判。
过把瘾,但是别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作者:毒S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