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高一然,头图来自:《山河令》剧照
上周,耽改剧《山河令》大结局。
温客行(男主之一)为周子舒(另一男主)一夜白头的剧情,让#山河令#再次登上了微博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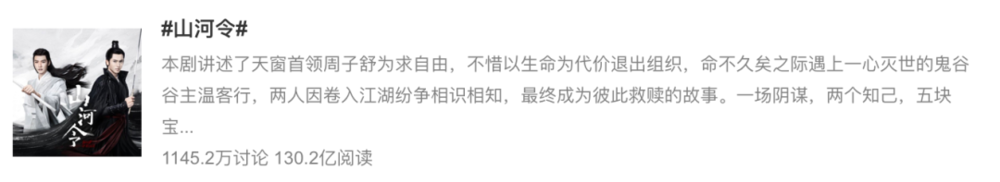
随着这部剧的完结,传说中的“耽改101”才刚刚拉开帷幕。

2018年的《镇魂》捧红了白宇和朱一龙,2019年的《陈情令》创造了“双顶流”肖战王一博,直到今年的《山河令》,“要想红,演耽美”似乎成了一条娱乐圈定律。
而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即便你不是耽美圈中人,也应该在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中,了解了什么是“攻受”,什么是“腐女”。
甚至看过许多对耽美作品性别隐喻的讨论。
有人说,耽美作品的爆红是一种“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也有人说,它不过是一种“隐藏得更深的厌女思潮”。
如此两极化的描述让“耽美”显得更加神秘。
男男之间的爱情,究竟对女性有什么样的魔力?
不如让我们回到耽美的最初,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被塑造的。
女性书写的“男男之恋”
耽美一词,最早出自日语たんび(读音TANBI),其本义是“唯美”之意。
它是日本近代文学“唯美派”的一个分支,崇尚完全纯粹的、超乎现实生活的美。
之后在1960~1970年代,日本的少女漫画为了追求至诚至纯的“美”,开始在作品中加入男男同性恋情,“耽美”才正式指代了“美少年男男恋情”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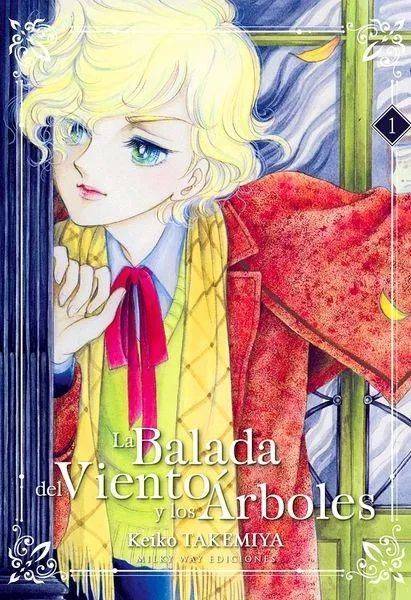
中文语境的“耽美”与日语中的“TANBI”并不直接对译,而是有着中国独特的古典韵味。
“耽”,出自《诗经·卫风·氓》:“士之耽兮,尤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耽的本意是“过乐,酷嗜”,美则包含了“官能美、文学美”。
古风耽美,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耽美文学类型之一,《山河令》的两位男主亦正亦邪,便颇有几分武侠色彩。

总之,这种不顾一切、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达到的唯美主义艺术目标,在日本和中国的耽美文学作品中均有展现。
也正因如此,耽美文学与同性恋文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在耽美文学的世界里,主角也会经历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恐慌,经历亲人的不理解和阻拦,但这些情节只为了突显同性之间爱情的坚韧,并不影响他们实际的生活状况。

相比而言,同性恋文学并不强调主人公之间的“唯美爱情”,作者更多关注同性恋的现实困境。
例如白先勇先生的《孽子》,主人公小青被父亲赶出家门,“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这样的描写几乎不可能出现在耽美文学之中。

那么,如果耽美文学并不根植于同性恋文学,它又为何以同性恋情为核心主题呢?
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在BL(Boy's Love)盛行的同时,GL(Girl's Love)的作品却少之又少?
事实上,耽美的本意不限于男女,但在日本产生之初,就是一群女性作者描写男性的故事(Boy's Love)。
中国的耽美文学也是如此。
目前被学者认为是中国“耽美小说之祖”的《凤双飞》,是晚清女作家程蕙英的弹词小说。
所谓“双凤”,指的就是两位男性。

小说第一回的开头:“有节概弱女能为豪杰事,没检束美男反效妇人颦。奇奇变变浑难测,正正邪邪总绝伦。”
这几句话,既表明了作者 “对性别颠倒与正反价值杂错的兴趣”,也说明了她之所以要描写两位男性之间情谊的原因。
女性借助耽美小说,从几千年来的“被看”转为“看客”。
一方面挑战性别伦理,一方面在文学作品中实现对传统两性关系的重构。
也就是说,耽美文学在产生之初,它的人物形象、情节设计就是从女性视角进行书写的。它的叙事性别就是女性的。
意识的觉醒,还是变相的顺从?
早年晋江文学城的耽美小说,会直接把“攻受”人设打在网站“公屏”上。
例如动画上线不久、马上就要进入影视选角的《天官赐福》。
晋江简介中就写明了两位男主的人设:“上天入地小妖精攻×仙风道骨收破烂受”,有内味了。

风靡了2019年的《陈情令》(原著《魔道祖师》),也因为“面瘫高冷攻×风流嘴欠受”的CP设定,让观众磕到上头。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提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
而耽美作品,在这种坚固的“男性凝视”中撕开了一道口子。
男性作为被观看、被解释、被定义的客体,呈现在了广大女性受众面前,女性的凝视欲望有了极大幅度的释放。

另一方面,耽美文学作品中的“攻受”,都是“搞事业搞得风生水起”的角色。
《山河令》的两位男主,一位是刺客组织的首领“天窗之主”,一位是江湖反派的头头“鬼谷谷主”,两个人平地里暗戳戳地武力对决相当有“糖分”。

传统的言情小说中,男性相比女性在个人成就上占尽优势;到了耽美世界,两位主角能够平起平坐,谈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
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欧美研究者,会将耽美小说定义成“女性主义的色情作品”。
因为它们是“女性表达她们对于双方平等的恋爱关系的渴望”。

但近年来,很多研究者对耽美的“女性主义色彩”打了一个问号?
1)从攻受设定来看,攻受这种固定性关系非常类似于男女关系。
《陈情令》中,禁欲系男主蓝忘机有一句难得的表白:“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一个男性渴望保护另一个男性,渴望将他带回家、藏起来,这种表达,打动的实际上是沉浸于戏中的女性观众。

耽美文学中很多“糖分超标”“甜宠”的剧情,本质上仍然遵循了“男强女弱”的异性霸权逻辑。
2)从女性角色来看,耽美文学的一大特征是女性角色的缺席。
女性的缺席,不是指小说文本中缺乏女性角色的描写,而是指它塑造的真实饱满的女性形象非常稀少。
耽美小说中的女性,通常不是“情敌”,就是“助攻”。
这些角色大多扁平而模糊,在耽美文学创作和讨论的过程中,她们被针对性弱化,甚至选择性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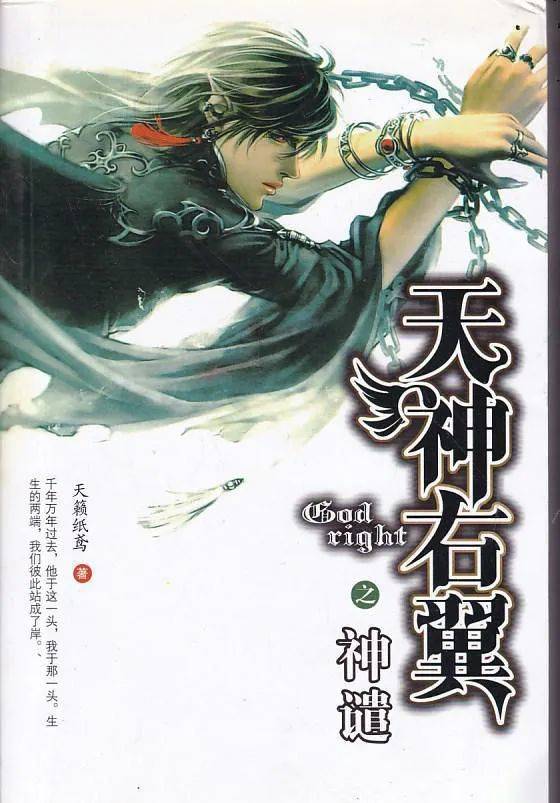
在目前的耽美框架内,我们既能看到女性自我的诉求,也能感受到其文本内容与女性主义的冲突和矛盾。
耽美之美,一场“去性别”的虚拟实验
耽美之美,能走多远?
随着耽美文化逐渐破圈,耽美作品自身也在不断尝试着打破框架。
有学者称,“酷儿理论”能够为耽美文学的存在和受欢迎提供理论支持。
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她用酷儿理论代替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提法,成为一种“反对二元性取向”的理论。

研究者认为,随着耽美文学的发展,耽美作品中开始涉及到模糊的性别、易装的男性等,尤其是“美攻强受”的出现。
以刚刚完结的《山河令》为例,作品设定的攻(温客行),是一个美若天仙的“疯批美人”;受(周子舒),则是一个武力超群的“易容糙汉”。

甚至很多观众已经无法区别《山河令》中的“攻受”属性。
这种CP模式中,“受”的男性气质可以被理解,“攻”的女性气质拥有正当性,真正实现了对性别二元划分的反写,使之成为一种“非固定的流动的性别气质”。

虽然这只是对耽美小说的一种文本解读。
但它把耽美文学当作一场“去性别”的虚拟实验,的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因为性别权力体系的顽固,女性在耽美作品中的性别诉求又如此明显。
这个特殊“实验室”里的作者和读者,他们的性别意识,才能够通过人物匹配和行动模式进行感知。
可惜的是,当越来越多的耽美作品要么被强行塞糖,要么被舆论击垮,创作者自身也缺乏关于女性审美和女性表达的思考。
耽美文学中那一丝异性恋霸权世界的反抗之声,也终于被满屏的“磕到了”就地掩埋。
参考资料:
周杰. 耽美的世界——中国大陆耽美文学研究[D]. 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刘雪平. 文本重构与性别叙事——中国大陆网络耽美同人小说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赵媛. 耽美同人群体的性别文化研究[D].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王艳萍. 网络原创耽美小说的叙事转向研究——以2008-2018年的“晋江文学城”为中心[D].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
Zhang,C. (2016). Loving boys twice as much: Chinese women’s paradoxical fandom of “boys’ love” fiction.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39(3), 249-26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ID:janelee1231),作者:高一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