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读书》2021年4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作者:韦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产、消费和交往方式,乃至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逐行为,也都在发生变化,各国的经济表现产生了极大差异。这些变化是巨大的,但也是渐进的,以致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都对此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还在自己的已有理论知识框架中来解释世界经济的变局和各国的经济增长。
近几年,由美国两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本经济学著作,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洞见和观点。这三本书分别是:二〇一六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的著作The Curse of Cash(《纸币的诅咒》),以及由同一家出版社于二〇一八年出版的两位英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合著的著作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崛起》),以及二〇一六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穆哈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所撰写的The only Game in Town:Central Bank,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城中唯一的游戏:中央银行、不稳定以及避免下次崩溃》)。
这三本书目前都有中译本。笔者把这三本书的英文原文放在一起读,希望能整合出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变局的一个大致清晰的理论图景。
一、无纸币社会即将来临?
按照罗格夫的说法,现在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less-cash societies”(少现金社会),正在向“cash-less societies”(无现金社会)转变。尤其是北欧国家,已开始进入无现金社会。他给出的数据是,二〇一五年,挪威、瑞典等国家,现金与GDP之比不到2%,加拿大这一比例也只有3.4%,英国4.07%,美国7.38%,中国9.34%。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数据,二〇一五年左右,西方发达国家M0即现钞占广义货币(M2、M3甚至M4)的比重平均都不到5%,当然在北欧国家这一比例更低。实际上,现金存量与GDP之比这一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纸币现钞交易在当今世界各国交易中的实际运用。
因为,正如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大量大面额的现金钞票都不知道被人们贮存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管人们现实生活中进行实物和劳务消费,如购物、旅游和住宿等,还是在商业支付和国际贸易中,都是通过信用卡、银行卡、智能手机和银行转账支付来完成。现实中在欧洲、美国,尤其是在北欧国家,人们使用现金纸钞越来越少了。到二十一世纪后,中国也迅速进入了“少现金社会”阶段,也正在迅速向“无现金社会”的银行账户数字货币制度转变。截至二〇二〇年十月,中国的M0只有8.1万亿左右,占215万亿广义货币量的比例仅为3.8%,占GDP比例降到了8%以下。尤其是从二〇二〇年十月起,中国央行开始在世界上首先推出数字人民币(DC/EP,其中DC为Digital Currency的缩写,即数字货币;而EP是Electronic Payment,意指电子支付),未来中国的货币非纸币化进程将会加速,并将领先其他国家。
尽管世界各国均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纸币交易减少的大趋势,但罗格夫还是指出:“如果有人认为,借记卡、手机支付以及虚拟货币的发展,正在逐步淘汰现金的使用,那就大错特错了。过去二十年里,多数发达国家对纸币的需求在稳步上升。”(p. 3)
罗格夫发现,尽管从大趋势上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纸币会减少,从而进入少现金社会乃至无现金社会,但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国家,目前人们还存有大量现金,且近几年现金与GDP的比例在主要发达国家均出现回升的趋势。譬如,按照罗格夫在《纸币的诅咒》后记中的数据更新,到二〇一六年底,美国流通中的现金已经从二〇一五年的人均4200美元上升到4400美元,现金与GDP的比例也从二〇一五年的7.4%升至7.9%(如果考虑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迅速超发货币,尤其是大量印发美元现钞,这个数字更加恐怖。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美国的M0即流通中的现金达到5.093万亿美元,人均按二〇一九年底美国人口和GDP计算,也迅速回升到15433美元,与美国GDP之比回升到23.8%)。
在欧洲,二〇一六年底人均持有欧元3300欧元,欧元区现金总额与GDP之比也回升到10.6%。在日本,纸币总额占GDP的比例由二〇一五年底的19.2%升至2016年底的21.2%。按二〇一六年底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计算,目前日本每个国民平均拥有现金7300美元。而按照目前中国的M0即流通中的现金8.1万亿元来计算,中国的M0/GDP的比例大约为8%,并没有多少回升;但中国人均流通中的现金为58909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纸币拥有量约为9063美元,比日本还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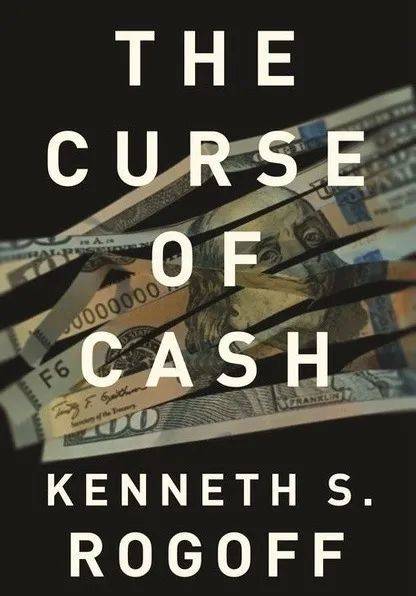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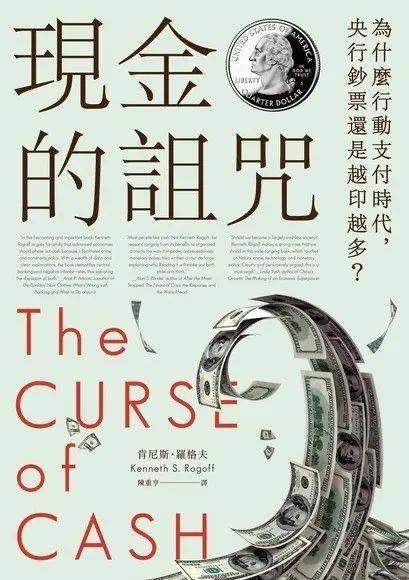
在《纸币的诅咒》中,罗格夫还发现两点:一是各国的大部分现钞是以大面值纸币的形式存在,如100美元、500欧元和1000瑞士法郎;二是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都遵循惯例发行了大量大面值货币,但是没人真正知道这些大面值货币都到哪里去了,也不晓得都被用在什么地方(一个贪官赖小民,就在一个自己私家的号称“超市”的别墅中藏了两亿人民币现金),而只知道很少一部分现金存放在收银机和银行的金库中。他还发现,在全部美元纸币中,约有40~50%为境外人士所持有,这也导致“任何大面额纸币的突然废钞行为,都是一种对外美元持有者的违约行为”。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用计算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进行货币支付和转账都非常方便和快捷,这种无现金支付又能节省纸币和少量小额金属铸币的印制和铸造成本(按照美联储的数据,生产100美元纸币的成本为12.3美分,生产1美元的纸币成本是4.9美分。p.81),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还要保留一定量的现金纸钞和少量小额金属铸币呢?而且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的纸币占GDP的比例还在上升?在这本书中,罗格夫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纸币流通制度的坏处、好处。
从纸币流通的坏的方面看,罗格夫发现,到目前为止,大面额纸币占据了全球硬通货供应量的80%—90%,且大部分都是在地下经济中流通,从而助长了各国的逃税、犯罪和腐败,并且规模巨大。他举例道,在美国,各种层面的逃税总额加起来超过GDP的3%,而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可能更高。而犯罪活动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可能比逃税更重要。由此罗格夫认为,如果消除大面额货币,大部分市场交易都由银行转账和移动网络支付完成,那显然可以减少犯罪、逃税漏税和腐败献金。
在《纸币的诅咒》一书中,罗格夫也给出社会上支持保留纸币的几点意见:首先,即使到了没有贵金属实物储备来支持的纯政府法币制度(fiat money regime)时代,纸币现金交易仍具有匿名性,可以保护个人隐私,即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所说的那样,纸币是“被铸造出来的自由”(coined liberty)。反过来,如果将来消灭了纸币,完全采用央行发出的电子数字货币(CBDC,即,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如在中国已经开始试行的 “DC/EP”),或完全采用银行的数字转账支付或银行存款账户内的数字形式,那就会失去货币的匿名性,理论上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和执法机构进行监督,乃至进行控制。
其次,纸币交易还不受停电和其他网络中断的影响,可以瞬间完成交易清算,又可以免受网络犯罪之害,还可以为没有银行账户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交易的媒介(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调查数据,到二〇一三年美国有超过8%的家庭仍然没有银行账户,超过25%的美国成年人没有借记卡,p.98)。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民众的用钱和花钱的习惯和习俗问题,即一些民众还是习惯用现金来支付等。
除了上述种种理由外,近些年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货币交易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媒介来完成,银行借记卡、信用卡和智能手机均是不同形式的物理载体,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银行记账货币的时代,对银行账户内所持有的数字货币支付负利率是完全可行的,而且自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许多央行和商业银行都这么做了。
在这种新世纪新的货币金融制度下,如果实行负利率,那人们就会把国债变现转而持有大面额的纸币贮存起来,甚至把银行存款提取出来而存贮大面额的现金纸币。这也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美国和日本纸币/GDP的比例不降反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欧盟国家则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后才开始这一比例回升)。到了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风暴后,西方各国央行普遍大水漫灌式地猛增基础货币,且普遍进入了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时代,随之,西方国家的非纸币化进程停滞并逆转,纸币/GDP的比例开始大幅回升,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尽管如此,罗格夫在该书中还是认为:“对发达国家的政府而言,逐步取消纸币(现金)和硬币,或者只保留硬币即小面额纸币的时代是否已经来临?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涉及经济、金融、哲学乃至道德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总体而论,我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为‘是’。”(p. 1)这本书受到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S.Bernanke)的称赞和推荐阅读:“这本书引人入胜,所论述的观点也意义重大。罗格夫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用大量的理论和数据来说明:经济必须摆脱纸币的禁锢。”
无论在宏观经济学还是在货币理论中,伯南克均是大家。作为连任两届八年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经历了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具体领导了美联储应对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复苏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伯南克如此称赞罗格夫的这本《纸币的诅咒》,自有他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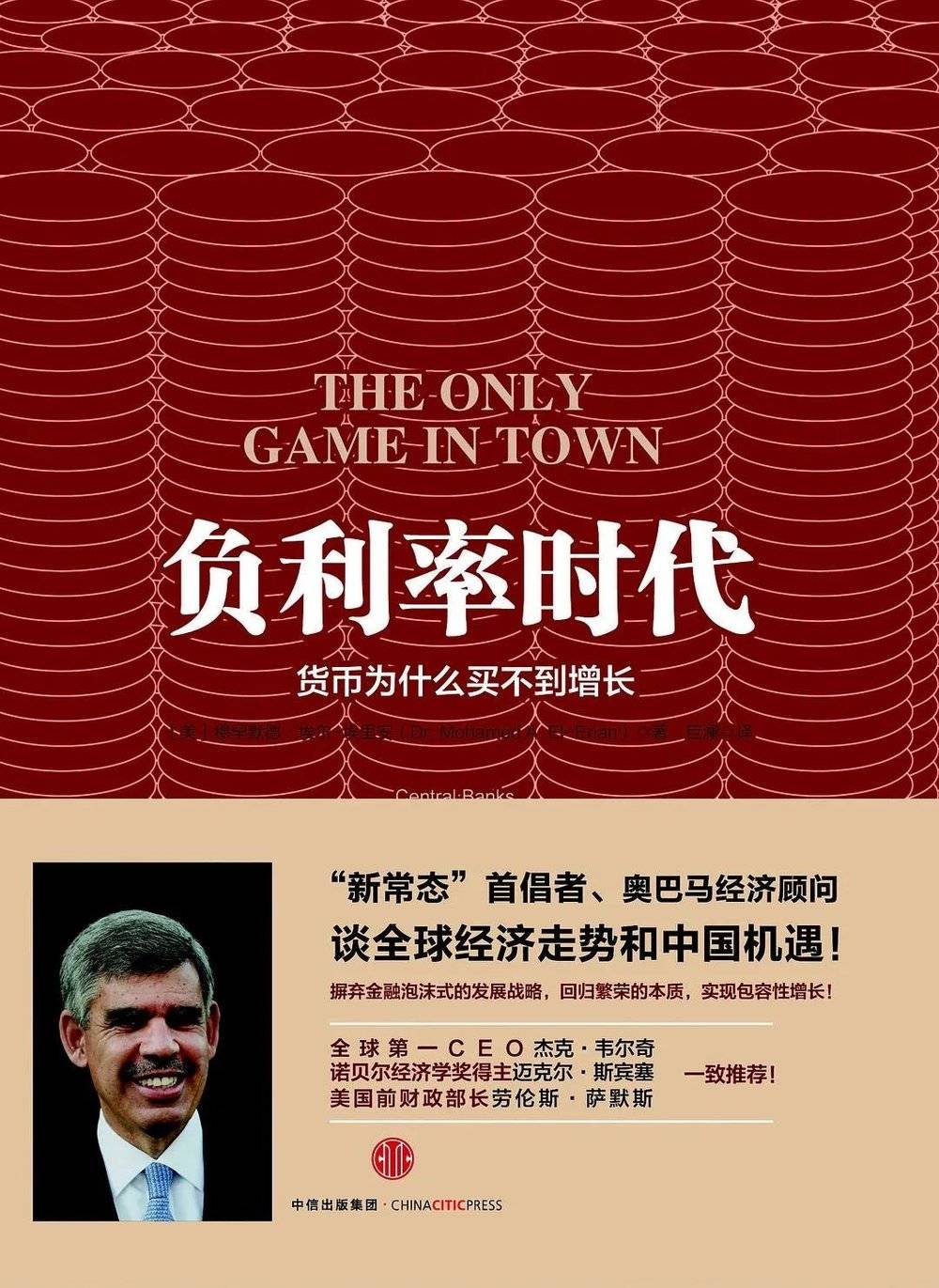
这本书关心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他的话题自然是从那场危机开始:“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对每一个国家、政府和家庭都产生了冲击。尽管央行已经出台了大量干预政策,也进行了转型创新,但随之而来的是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收入不平等拉大、政府职能紊乱,以及社会紧张等等。”(p. XV)
埃尔-埃里安还认为“全球经济正在接近一个三岔路口,更精确地说,即英国人所说的T字形路口。经济发展道路将很快走到尽头,与此同时将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更好世界的物质状态或一个更糟糕的物质状态。”(p. 176)他还认为,对现在和未来几代人来说,现在的选择至关重要。
全球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T字路口的?这得从二十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低通胀、高增长且通胀和增长的波动幅度都很小而被称为“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说起。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总统第二任执政起,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长达二十多年经济波动很小的“大缓和”时期。从统计学上来看,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二年,美国经济22%的时间里处于衰退期;但从一九八二年到二〇〇八年,美国只有5%的时间处于衰退时期,且经济波动很小。这一现象曾导致当代经济学中两大巨擘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和伯南克在二〇〇四年先后声称,经济危机以后大致会从人类社会历史上消失。没想到他们二人这话讲了没几年,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就发生了一场全球金融风暴,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让世界各国政府几乎全慌了手脚,纷纷推出了救市政策。但按照埃尔-埃里安的看法,在应对这场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上,实际上只有各国央行在忙乱中自个儿在干活:“面对眼前的混乱局面以及可能到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各国中央银行从自由放任模式转变为‘不惜一切代价’的高度干预模式。”“印钞机开始超速运转,无数应急资金窗口打开,大量现金从四面八方注入金融系统;主权借贷和信用担保全面开放,直接公共资金被发放到美国主要银行和无数中小银行。”“这就像你拼命往墙上扔东西一样,有什么就扔什么,并希望总有什么可以贴在上面。在经历了一个危险阶段之后,作用终于显现了。”(pp. 48~49)也正是考虑到各国央行成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唯一玩家,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书名 The only Game in Town 。
埃尔-埃里安还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乃至在大多数时间里,央行都是主要且唯一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尤其是在二〇〇八年及其随后的时间里,“央行挺身而出来拯救全球经济,并负起了更大的政策责任”。因此,“我们都欠央行一个大大的感谢。多亏(各国)央行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胆的创新行动,整个世界才免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失误,包括放任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庭和公司把一些不负责任的风险堆在他人头上”(pp. 252~253)。
在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之后,央行的积极干预已成功地纠正了市场的不正常状况,平息了让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金融危机,其功劳是很大的。
但是,之后央行干预经济的积极性并没有消失。原因在于:“它们发现,危机过后,没人可以接手将全球经济复苏带入下一段的工作。因此,它们别无选择,只好承担起了宏观经济方面前所未有的重任。”(p. 253)这并不是各国央行执意要争夺权力,相反,政治的失灵让其他决策者无法提供有效的工具,使央行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伦理责任上都觉得应尽自己的一份力去争取时间,让私营部门恢复元气,让政治体系重新集中起来,来承担起经济治理的职责。
然而,这场央行救世的唯一游戏越来越无效。正如埃尔-埃里安在序言中所引用的美国政府前财长、曾任哈佛大学前校长的拉瑞·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在当今世界,靠中央银行的应急措施来作为增长策略的空间已经穷尽。”萨默斯的这句话,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而萨默斯所说的这种增长策略,就是埃尔-埃里安说的“流动性辅助增长”(liquidity-assisted growth)操作模式,即“由于特殊的流动性注入而带来的金融市场的繁荣所驱动的经济增长”(p. 13)。
这种流动性辅助增长,看起来似乎神神秘秘,实际上很简单,即各国央行从它们的魔术师帽子里掏出来的不是一只只兔子,而是不停地印钞,即拼命地进行量化宽松。所谓央行的印钞,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向实体经济投放基础货币,其主要渠道,是在二级市场购买资产,主要是购买国债、机构债券和MBS,以及少量高信用等级公司债券等。
比如,二〇〇八年一月至二〇二〇年八月,美、欧盟、日、英四个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684.5%、326%、513.6%和987%。四大央行合计扩张资产负债表近20万亿美元。如果换成各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总量,更能看出各国央行的魔术师们无中生有地从它们的魔术帽子掏出来的这一只只“肥兔”会长得多快、变得多大了:一九七〇年,全球央行的基础货币总量(央行资产规模),不到1000亿美元;一九八〇年,这个数字大约是3500亿美元;一九九〇年,大约是7000亿美元;二〇〇〇年,大约是1.5万亿美元;二〇〇八年,变成了4万亿美元;二〇二〇年,加上中国,变成了33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中、美、欧盟、日四个经济体的央行总资产加起来,就有20万亿美元。这样一算,二〇二〇年全球央行的资产(反过来也是负债)是二〇〇〇年的22倍,二〇〇八年的8.25倍!这些年,各国央行干了多大的事(且不说好事坏事),以上这些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了。
各国央行从它们的魔术师帽子里掏出来的第二种有点令人吃惊的东西,不是一只只越来越大、越来越肥的鸽子,而是越来越低的利率。在货币不断宽松的背景下,各国的利率不但降到了1%以下,最后竟到了负利率。曾几何时,世界各国的商业银行间还在为争夺客户存款而斗得头破血流,吸储手段五花八门,从免费赠烤面包机和各种礼品,到直接返还现金。然而,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士乃至全世界,央行和商业银行似乎都不再欢迎客户存款了,而是努力阻止人们来存钱。到近几年,欧洲大量的政府债券的实际交易利率比市场上的名义利率还低,乃至最后到了债券本身的利率都变成了负的。政府债券的负利率,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向投资者借钱,投资者却为这种借钱的机会埋单”(p. 6)。
不但政府债券的利率为负的了,在欧洲,甚至商业银行的存款利息都为零,以至为负。在二〇〇九年七月,瑞典央行首次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至-0.25%。二〇一二年,丹麦央行利率破零。令许多人惊讶的是,负利率并没有给当时的金融体系带来压力。随后,欧洲央行(ECB)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1%。另外根据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惠誉(Fitch)的数据,在此之后,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都选择了负利率。到二〇一七年,全球就有9.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出现负收益。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央行拼命印钞,并把利率压低到零乃至负,是史无前例的。但这好像有它们的道理。因为,在各国央行都在大肆放水的当今世界,世界上似乎到处都不缺钱;而另一方面是政府、企业和家庭负债累累。既然不缺钱,银行的钱贷不出去,那也只有降低利率了。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才能让负债累累的政府继续运转,让企业存活下来,让金融和银行系统不崩溃。
正如应对金融危机的专家、曾任美国奥巴马政府财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E. Geithner)在二〇一四年的《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总统知道,如果不首先修复金融系统,就无法修复整个经济。银行就如经济的循环系统,像电网一样为日常的经济运行提供活力。离开一个正常运转的金融系统,任何经济都不能增长。”(pp. 55~56)
然而,当今世界的问题是,当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被修复之后,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仍然停滞不前。不但如此,还出现了书中所描述的十个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第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且不平衡,遇到了周期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长阻力,也就是拉瑞·萨默斯所说的发达国家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从而使埃尔-埃里安所说的“新常态”,也随之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所说的“新平庸”(new mediocre)。
第二,许多发达国家失业率仍然很高,如欧洲的失业率曾超过10%(现在仍然很高,二〇二〇年欧元区失业率的平均值为8.3%),希腊的失业率超过25%,青年失业率甚至超过50%。
第三,居民家庭收入和财富拥有的不平等在迅速恶化。
第四,机构公信力丧失导致了对政治家乃至整个“制度”信任的侵蚀,民怨爆发,美联储、IMF、欧洲央行、政府乃至伯南克本人都被呼吁要被问责。
第五,国家政治的失灵。在美国,两个政党之间很难就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政策达成一致。在欧洲,这个问题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出现在国与国之间。
第六,由于国家功能的失调对全球政策性协调造成了破坏,使传统的核心/外围关系变得十分脆弱,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逐步升级。
第七,在系统性风险从银行向非银行机构转移和变形的过程中,如何占领先机,如何应对未来的问题,向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八,当市场范式发生了变化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重新配置资产组合的意愿会远远超过整个系统可以有序容纳的空间和范围。
第九,在经济、金融、制度、地缘政治、政治和社会的不确定性面前,应该有更大的金融市场的波动。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波动性却一直很低,金融市场一直在持续地膨胀。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与基本面的鸿沟却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弥合。结果,自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增发出来的货币,并没有注入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基本面的增长,而各国似乎都玩起了“钱生钱”的游戏,导致全球虚拟财富像吹气球一样地迅速膨胀(这一点是埃尔-埃里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注意到却没有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现象)。
第十,所有这一切问题,给管理好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阻力。(未完待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