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次元研究(ID:ciyuanpotato),作者:MacroKuo,原文标题:《为什么动漫<BEASTARS>是哲学家,<疯狂动物城>只能算“傻白甜”?》,头图来自:《BEASTARS》豆瓣剧照
多元文化主义原本的目的是去实现更好的世界,然而,当她逐渐脱离这一目的,转而去搜寻和攻击所谓“不正确”的存在时,多元文化主义也就跟暴走的警察权力并无二致了。
漫画《BEASTARS》从2016年起连载于《周刊少年Champion》,并于2020年10月完结。2019年第一季播出后,2021年1月网飞平台上动画版的第二季的播映也已开始。故事发生在被拟人化了的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共存的世界。主人公是就读于名门高中切里顿学园的大灰狼雷格西,他在学校里担当戏剧社的灯光负责人。某天,戏剧社的社员羊驼被杀害吃掉的“食杀事件”发生了……

从《BEASTARS》的故事,我们不难联想起同样问世于2016年、也同样以拟人化的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共存为主题的皮克斯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可以说,讲述了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之间的对立和融合的这两部作品所讨论的,就是全球化进程下当代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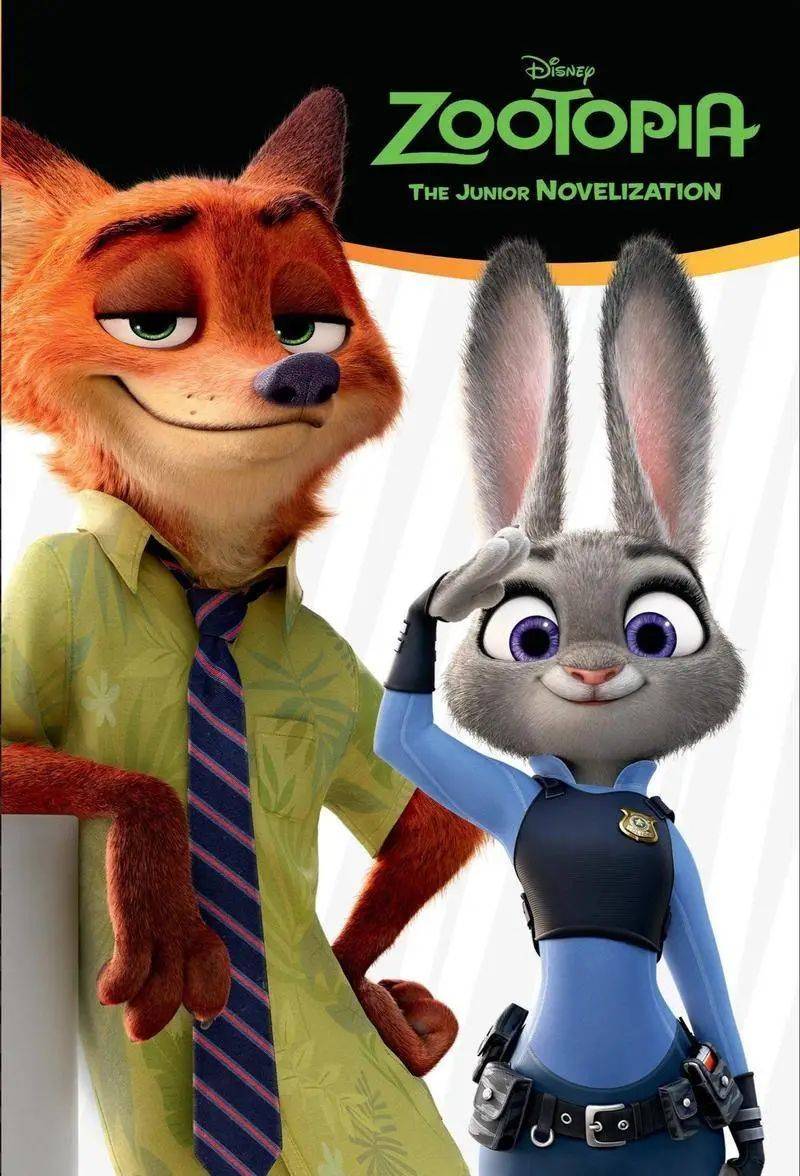
正如家喻户晓的《动物庄园》是一部反乌托邦政治讽喻寓言,这两部作品也承载着各自的讯息。只有解读出这些讯息,我们才会发现,包裹着相似主题的两部作品,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内里——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疯狂动物城》和《BEASTARS》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疯狂动物城》中女兔子朱迪成为代表“正义”的警察的故事讴歌的是电影中那句“Anyone can be anything!”所象征的多元文化主义。
然而,在这种弱者和强者和平共处的自由主义式多元文化下,难免被贴上“政治不正确”标签的肉食动物们就沦为了“新弱者”。而通过男性视角的雷格西的故事,《BEASTARS》探讨了该如何去宽容和理解这种“新弱者”们的过程。《BEASTARS》所揭示的多元文化主义陷入的陷阱,也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新的启示。
从“加害者”的立场思考
当今已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诞生于这个时代的虚构作品也难免会对这一现实议题有所涉及,《BEASTARS》也不例外。然而,《BEASTARS》跟大多数虚构作品对这一议题的涉及角度却是截然不同的。
何谓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人,多元文化主义劝诫我们不要去歧视与“我们”有着不同身份的“他者”,这里的他者往往是没有得到足够尊重的少数群体。当某一行为尊重了这样少数的他者时,这一行为就是“政治正确”的。《BEASTARS》就将这种现实存在的人种、宗教、信仰等身份间的多元文化主义转换为了动物种群间的生物学差异。
尽管将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设为了前提,《BEASTARS》却不会去号召“尊重他人”,而是将视线转向了身为强者的肉食动物和身为弱者的草食动物间存在的绝对的不平等。有趣的是,故事还把主人公雷格西设置为了“大型、肉食、雄性动物”这一动物界最强的存在。然而,正是通过这种传统动物界“加害者”的身份,我们才能在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普及的今天重新发现其中容易忽视的问题。
“政治正确”能带来幸福么?
《疯狂动物城》的主人公是女兔子朱迪和男狐狸尼克。肉食草食动物和睦相处的动物城里,突然发生了野生化、狂暴化的肉食动物攻击其他动物的怪事件。作品就讲述了朱迪和尼克解决这一事件的过程。故事中,朱迪和尼克在受到“兔子太弱了没法当好警官”、“狐狸太狡猾了没法信任”等偏见的同时,也时不时沦为施加偏见的一方。正是通过对这些偏见的批判、反省和解消——也就是实现政治正确,这部电影才迎来了完美的结局。
通过这个故事,《疯狂动物城》就发出了这样的讯息:“谁都可以成为多元文化主义者,这样世界就能变得更加和平和幸福”。作为典型的寓教于乐的影视作品,《疯狂动物城》的完成度可以说无可厚非。然而,将它与《BEASTARS》相比较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主人公们是在判明“草食动物也会凶暴化”这一事实后,才解决了肉食动物的凶暴化这一事件。也就是说,这部电影通过一种"Anyone can be anything!"的自由口吻,将暴力的可能性公平分配给了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从而掩盖了动物界真实存在的“肉食动物单方面捕杀草食动物”的这种不平等。
与此相对,《BEASTARS》就将这一不平等放在了作品主题的中心。在这部作品里,草食动物在日常接触中总是处于随时会被肉食动物捕杀的脆弱境地,而被“想要捕杀草食动物”这一食欲的本能所驱使、因此被赋予了健壮身躯的肉食动物也总是游走在犯罪的边缘。

通过导入这种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的不平等,《BEASTARS》某种意义上就描绘出了一个从生物学上无法实现多元文化主义的世界。对于《疯狂动物城》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和平”这个主题进行重新审视,这种自由主义问题意识甚至会显得有些激进。
本作所探讨的“肉食和草食是否能共存”这个问题是如此困难,我们永远无法给予一个简单明快的答案——就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永远没有单纯的正确答案。《BEASTARS》的自由主义并不会带来圆满的结局。如果说其世界观与《疯狂动物城》相比较为难懂,那大概是因为这就是对于现实所拥有的复杂性最为忠实的再现。
重新认识“非善即恶”
让我们细看《BEASTARS》的故事。从“食杀事件”发生到雷格西发现事件真相可以算是作品的第一幕。然而,不同于《疯狂动物城》,这一幕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惩恶扬善的故事。漫画第三话,为了替明知违反校规还在夜间排练的戏剧社员放风的雷格西突然闻到了一股草食动物的气味。发现各自的双方胶着了一阵之后,就在草食动物想要逃走的瞬间,雷格西下意识地将对方扣在了自己的爪中。

在经历了一阵与理性的纠葛之后,雷格西终于还是对这只之后会成为自己恋爱对象的女兔子春萌发了杀意。然而,就在爪子刺进春的手腕时,听到正在排练中的伙伴的呼唤的雷格西就从杀意中回过神来,春也因此得以逃脱。可以说,故事的一开始,作为主人公的雷格西就败给了自己的狩猎本能。在这一瞬间,他的行为不受自己意志的控制。
苦恼于自己生为肉食动物的罪恶感,一直行事低调的雷格西某种程度上,也是坚持“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政治正确的大灰狼。因此,本作中的本能就是将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效化的装置。在这个意义上,不论肉食动物被灌输了多少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都无法摆脱成为加害者的风险。
《BEASTARS》会选择雷格西作为主人公的意义也就在于:读者并不是从与这个动物的世界无关的视角去观察他,也不是作为被害者,而是与作为加害者的这只肉食动物的视线实现了统一。作品就成为了一个思考多元文化主义者内部所隐藏的“非正义”的实验。此时,歧视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的之间的区别不复存在。从此,作品的真实度骤增,愈发催人自省。
最弱的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第八话里,雷格西偶然与园艺社的春再会。雷格西发现眼前的春就是曾经差点被自己杀死的兔子,生怕自己败露身份。然而,若有所查的春却表示自己“记忆模糊”,缓解了这种紧张的氛围。之后,在帮助春的过程中,雷格西渐渐对春产生了爱慕之情。

园艺社的工作结束后,春突然开始宽衣解带,甚至还脱起了雷格西的衣服。原来她是学院里知名的荡妇。然而,还是处男的雷格西见到这一幕,只是将床单披在了春身上后,就不知所措地逃离了现场。与春从雷格西手中逃走的场面相反,这次,是雷格西从春的“手中”逃走。作品中出现的荡妇(bitch)/童贞这一组词语很有象征意义:原本意指“母犬”的bitch这个词就是用来指代狗或者狼的,而雷格西也是当今日本消极的草食系男子的完美写照——恋爱关系中,雷格西和春的肉食草食关系就得到了反转。
肉食系女子春是恋爱中的强者。我们甚至能在作品中发现她如凶暴的肉食动物一样“遍历”学院中的男生的“事迹”。也就是说,原本作为草食动物的她在恋爱这个领域则占据了加害者的地位。春的这种“最弱的被害者也是加害者”的两面性在雷格西身上也会得到反转。由于自己大型肉食动物的身份,雷格西平时受到了无心的歧视。此时,最强的加害者往往也是被害者——这是作品中许多肉食动物都曾经历过的。
在这个意义上,《BEASTARS》的主要角色们就都同时具有了作为被害者和作为加害者的一面。在某个场景里是强者,到另一个状况里很可能就会化为弱者。就像现实中,同样的人,有时会是多元文化主义者,有时候又会化身歧视主义者。
应该说,弱者、加害者、多元文化主义者,这些分类都是一时的、流动的,并非是一种固化的身份属性(identity)。当今社会中,比起自觉的歧视者,自认为信奉多元文化主义者的人,才往往缺乏这种理解。无论谁都有多个身份,无论哪种生物都有弱点。重要的并不是安于自由的状态,而是需要为了在不经意间成为加害者的下一个瞬间而思考和反省——《BEASTARS》如是说。
不是只排除暴力
雷格西所属的戏剧社社长是欧洲马鹿路易。他在社内实行独裁的同时,也因自己的声望而受到了支持。如果说春是恋爱的强者,路易就是政治的强者。在戏剧社受到学园荣誉赏表彰后,为了洗去因“食杀事件”导致的污名,路易在众人面前就肉食和草食的共存和共荣做出了宣誓。

原本这里的戏剧就是将现实中草食和肉食动物 “共存和共荣”这个表面上“正确”的理想以虚构的形式进行提供的装置。也因此,剧目中草食动物的路易才会去打倒肉食动物所扮演反派,实现了剧里剧外不同次元间的呼应。
由于总是憎恨自己与生俱来的弱小,路易才一直刻意保持坚强,最终成为了一只唯我独尊的草食动物。也因此,他才会去批判为自己的强大感到耻辱的雷格西:“鬼鬼祟祟的”、“为什么你不能为自己的强大而负责呢?”想要变弱的肉食动物和想要变得强大的草食动物——路易和雷格西也再次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
面对路易的谴责,雷格西解释道:狼的强大中不存在希望,所以才得“鬼鬼祟祟”的,观众所期待的都是路易的“正确的强大”。于是,雷格西在戏剧社里不是担任演员,而是担任照亮他人的灯光师也可以说很适合他的想法。拥有与生俱来的强大的他就这样选择了身处幕后,而将光线投射到了这个“政治正确”的舞台。
然而事与愿违,公演第一天路易骨折后,路易的角色由老虎比尔顶替,而比尔原来扮演的角色又换成了雷格西。鼻子灵敏的雷格西在正式演出前察觉出比尔喝了兔子的血当作兴奋剂,因此暴怒的他就在演出中放弃演技,开始猛揍比尔——主人公就这样用残酷的现实破坏了戏剧的虚构。

多亏路易的乱入,现场的混乱得以一时平息,然而雷格西的暴行却留下了决定性的影响。公演结束后路易在训斥雷格西和比尔这两个后辈的时候,受到了记者采访。这位社长就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困难,做出了如下发言:
对于后辈们,这次公演也有绝大的意义。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十分复杂。大家都在隐藏着、忍受着某种东西,在各种思绪的交融和冲突中拼命活着。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所谓正确或不正确。只要有着坚实的信念,就值得这舞台的光线。就算是有点暴躁粗鲁、或是有点稚嫩、只要存在信念——我想我的后辈们就将这种讯息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这番话是路易站在舞台上说出来的。然而,他却不会为了守护舞台上政治正确的和平“叙事”而去排除雷格西的暴力。路易就将“不存在所谓正确或不正确”这种现实伦理代入了舞台,某种程度上也拥护了雷格西的暴力。
因为路易知道冠冕堂皇所隐藏的真正“不正确”的现实,只有将肉食动物的暴力这一现实融入这个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存和共荣”。他也知道,歧视背后往往存在更为深邃的原因,无视这些内部的原因,一味强调多元文化平等的自由主义毫无意义。
此后故事中戏剧很少再有登场——因为现实已经成为了新的舞台。雷格西和路易作为BEASTARS所要努力的,就是在这个现实当中实现真正的“共存和共荣”。
“正义”只是一种偶然
雷格西在学园祭的准备期间与肉食动物们一起外出的时候,误入了贩卖动物肉的黑市。实在看不下去的雷格西与想要买肉的同学分道扬镳之后,却因为眼前卖的肉失去了自我,变得口水直流不能自已。就在这时,他被熊猫刚兵给抓住了。

刚兵是帮助触犯了吃肉禁忌的肉食动物改过自新的江湖医生。听闻了雷格西的经历后,他把有袭击草食动物“前科”的雷格西对于春所怀有的感情称作“歪曲的狩猎本能所带来的恋爱感情”,并命令他跟春断绝关系。
刚兵在作为拥有肉食动物最强力量的熊科的同时,也是只吃竹子的食草动物。在这一点上,他就也是体现了《BEASTARS》中肉食草食之间扭曲关系的角色。不久之后,雷格西就成为了刚兵的弟子。
作为年长者,刚兵的伦理观对雷格西起到了重要的指南作用。然而,他在治疗触犯了“食肉”这一终极禁忌的患者的同时,也是在藏匿罪犯,所以按理说都是违法的。认识到这一点的雷格西问道这会不会不妥的时候,刚兵如此答道:
我是熊科动物,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宏大理想妄图通过惩罚肉食动物来维护正道。只不过偶然生为熊猫,才不会想吃肉,如果因为这样就占据优势地位,那也太奇怪了。所以我才会直接面对这些家伙,在与他们对峙中贯彻我自己的正义。这个世界没有单纯到通过惩罚就能变得和平。作为精神科医生,我觉得无论是怎样的食肉动物,只要当事人有意愿就一定能改变,我也想替他们的改变助上一臂之力。
刚兵在这里提到,自己避免成为加害者的原因只不过是偶然生为了一只草食动物。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动物的原因只不过是出于生物学上的偶然性。相对的,“食杀”这种行为也只不过是这种生物学式偶然的产物。这句话可以说就触动到了偶然回避了食杀行为的雷格西。
因此,与其说刚兵是某种意义上加害者的同伴,不如说他是这种暴力性的敌人。他的那句“这个世界没有单纯到通过惩罚就能变得和平”就和路易的“不存在所谓正确或不正确”是同源的。刚兵也是单纯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者。
之后雷格西也继承了刚兵的这一精神。当雷格西发现戏剧社的食杀犯后,因为自己也有“差点吃掉食草动物的经历”,他没有选择报警去单纯惩罚这种行为,而是选择了直接面对犯人,向对方提起了决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死斗。这种暴力行为对于社会来说真的有益么?这又是“正确”的么?《BEASTARS》就开辟了一条被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所忽略的野性昏暗之路。
通向“正义”所无法抵达的地方
犯下食杀罪的犯人,是棕熊里滋。身材比雷格西还要大上许多的里滋也有因作为大型肉食动物而被歧视的过去,此外,他也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才犯下食杀,吃掉了自己作为食草动物的朋友提姆。在这一点上,里滋与提姆的关系就与雷格西和春的关系近乎一致。

就像刚兵一样,通过与里滋对峙,雷格西并不是想要惩恶扬善。对于雷格西来说,与里滋的决斗某种程度上作为对于险些犯下同样罪行的自我的批判,也是一种理解对方的表现,他的目的是要救赎里滋。因此,在决斗过程中,雷格西也表明了这种对于里滋的理解和共感。
此时,雷格西曾经伸向春的代表“歪曲的狩猎本能所带来的恋爱感情”的爪子在这里就转而握住了里滋的爪子,见证了两头食肉动物间的惺惺相惜。就这样,两头“非正义”的动物通过这种“非正义”的暴力,最终实现了相互理解。
当然,熊还是比狼要强。决斗到一半,雷格西已经奄奄一息。多亏了路易赶到,这场决斗才得以一时中止。此时,路易的那段演讲再次出现在回忆当中。
在这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里,雷格西通过“与对方对峙到最后”,履行了自己作为“强大”存在的责任。这里的“对方”不仅是“里滋”这个个体,更是里滋和雷格西所共有的一种捕食的本能,也就是一种“怪物化”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继续决斗下去,雷格西很可能会战死。路易也知道雷格西一根筋的性格很有可能会让他就此丧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让雷格西吃自己的脚——

路易会提出如此要求,并不只是为了补充雷格西的体力。路易的这一行为是在宣布:现实中为了解开“正义”的谜,并不能缺少草食动物的参与。曾经将肉食动物的“不正义”搬上舞台的他,现在却又将“被害者”草食动物作为主体要素放进了现实。也因此他会对不知所措的雷格西说道:我是在“逼”你吃,所以你才是“被害者”。可以说,路易在这里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
最终为这场死斗画上句号的,并不是力量的孰优孰劣,而是里滋的主动投降。在见证了自己所梦想的“食杀和友情的统一”这个奇迹后,无意识地杀死了自己的挚友的里滋就这么认输了。草食动物路易的参与,就这样将肉食动物间野蛮的死斗驯化为了理性的对话。
就这样,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抗争的《BEASTARS》就通过这个极为政治不正确的“食杀”,导出了一个“正义”所无法实现的解答。看到这个结局,多元文化主义者们还能说将里滋交给警察才是“正确”的选择么?
自由主义所陷入的“本质主义陷阱”
治安可以说是《BEASTARS》中隐藏的主题。刚兵、现任Beastar的雅付亚、雷格西的爷爷、雷格西和路易——这部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大都为了实现困难重重的“共存和共荣”,而参与了某种“不合法”的治安活动。
这点也与《疯狂动物城》形成了对比。这部以警官为主人公的电影讲述的是朱迪从开停车罚单到解决歧视问题,事无巨细地更正各种“不正确”,最终将世界导向“正确”的故事。就像“诈骗师尼克会成为警官”这个故事结局所象征的那样,故事的圆满结局也是法律的胜利。
而在警察没能起到作用的《BEASTARS》中,治安活动都是在法律的外部完成的。这部作品仿佛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悖论:在“不正确”的地方,保障“正确”,法外之徒(out-law)才真正支撑了法(law)的存在。就像美国的BLM运动所显现的那样,在警察和民众的对立频繁上演的当今世界,警察所守护的是国家而不是市民这一不争的事实再次得到了历史的验证。那么在这样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去解读《BEASTARS》中的这一事实呢?
近半个世纪的人文学科告诉我们,身份(identity)是构造性的存在。也就是说“狐狸就应该是狡猾的”这一认知只不过是社会所制造出来的意象,而将这种意象总是当成真理进行主张的态度,就被称作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很明显,这种本质主义是存在偏见的。
就像《BEASTARS》所显示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政治正确”现在也开始被视作了一种身份。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原本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世界本不存在所谓“多元文化主义者”。这恰恰就是一种反转了的本质主义,一种自由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
刚兵的那句“并不能因为生为草食动物就有了优势地位”中,就浓缩了这种问题意识。当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时,多元文化主义者们往往会化身成为“正义”的代言人,对于“政治不那么正确”的存在,行使某种有形或无形的暴力。比如,许多不理解御宅文化的声音对于宅文化的“一刀切”的批评就是这种暴力的一种。
“这个世界没有单纯到通过惩罚就能变得和平”——刚兵在这里想说的就是,纠察“不正确”的行为其实是与和平无关的。多元文化主义原本的目的是去实现更好的世界,然而,当她逐渐脱离这一目的,转而去搜寻和攻击所谓“不正确”的存在时,多元文化主义也就跟暴走的警察权力并无二致了。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那就是“宽容”。《BEASTARS》教给我们的宽容,并不是一种放任不管的态度。我们谁都可能会处于“不正确”的位置,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去理解这种“不正确”,才能在这种理解上对其实现真正的批评——雷格西面对里滋的这种态度,才是真正通往“正确”的态度。
本质主义不会接受别的声音。也因此,自由主义至上最为忌讳的,就是自身“不正确”的可能性。然而,不去像雷格西一样将这种阴暗一面照射出来,我们就无法对“不正确”进行建设性的批判。毕竟,只有不断的自我批判,才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
《BEASTARS》从动物界这一外部将“不正确”回归暴力,打破人类社会已经逐渐变味的 “正确”,就是在向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这个多元文化主义环境投以新的质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次元研究(ID:ciyuanpotato),作者:MacroK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