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是个比较未雨绸缪的人,开手动挡是以防世界末日需要开大巴车逃生,跑长跑是为了世界大战有力气逃跑,练习左手画画是怕右手断掉(总有一天我会开始练习用脚画画)……作为动态视觉艺术工作者,我还有一个并不多余的担心,如果有一天我失明了,我怎么看动画和电影呢?
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电影就是通过 “看”,让你感受到一个故事,那我们凭什么不可以跳过 “看” 这个步骤,直接感受到故事?


体验的朋友说她感受到了
我做到了 —— 通过把电影转译成一场按摩,毫不夸张的说,虽然被蒙着眼,但整个过程比你坐在山寨景区 17D 影院的震动喷水椅上所体验到的要身临其境多了,试过的人反馈:就像被打了一顿,对故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目前,我的按摩剧场还只有一个剧目:哪吒闹海,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古老的 IP 足够脍炙人口,且包含很多能用按摩手法还原的激烈武打场面。作为一名实验动画作者,我很清楚自己在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 “材料”:电影是视觉的,被剥夺了视觉就像被废了九成武功,所能做的就是讲好一个简单的故事。

最开始的编排非常迷茫,我决定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录好一段声音,然后根据声音所表现的画面设计按摩的动作。
比如这句旁白:“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陈塘关,有一个将军叫李靖,他的妻子怀孕了,但是她花了六年才生出来”,为了表现整个怀孕过程,我在参与者的手上放一个气球,然后慢慢把气球吹大。
参与者在气球即将破裂的紧张中感受到了哪吒他妈难产时要生不生的痛苦,紧接着,“啪” 一声,气球被戳破,哪吒他妈生了!一般人到这里都会被吓一跳,观众情绪和戏剧情节百分百同步地到达了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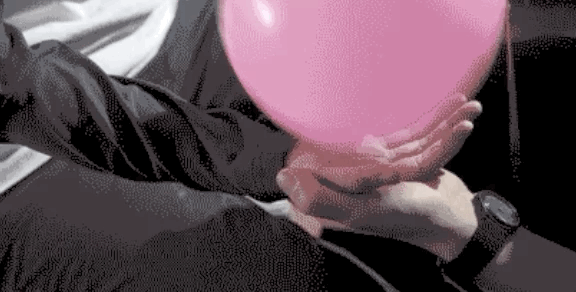
跟电影一样,在我的按摩中,参与者的视点也是可以不断变化、游荡的,他有时是故事的旁观者,有时会沉浸式地成为故事中的某个角色。
哪吒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粉色的肉球,其父李靖认定他是带来凶兆的怪物,要杀了他,这时,我把一柄锅铲塞到体验者手中,体验者扮演了持剑的李靖。

话音未落,肉球裂开,里面蹦出来一个小男孩,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出现,认定小男孩前途无量,旁白变成了太乙真人对哪吒的叮嘱:“你是一颗灵种,是个做神仙的料,我愿收你为徒……你切记要惩恶扬善啊。”
这时,我会语重心长地拍拍体验者的头和肩膀,然后把 “乾坤圈” 和 “混天绫” 塞到对方手里 —— 体验者顺理成章地成了哪吒。

委以重任!语重心长!后面的毛是要模拟一阵仙气将太乙真人的云朵座驾拂到你脑袋后面的体验


这是乾坤圈!这是混天绫! 接着,哪吒在跟龙王三太子的鏖战中将其杀死,龙王得知后大怒,找来哪吒他爸李靖对峙,并以水淹陈塘关相要挟,要李靖交出哪吒。一边是陈塘关子民,一边是亲生骨肉,李靖无法抉择,于是,东海波浪滔天、狂风大作。
放到电影里,此情此景也是需要集中燃烧经费的大场面,但我们轻轻松松地用环绕式喷雾、吹风机和疯狂在你背上摩擦的破编织袋让你成为在现场围观而被浇了一头雨的陈塘关市民。

对于电影的空间感,我也在按摩中有效地重现了。人的背部没那么敏感,可以用来展现远景,比如,我用搓背的方式让体验者感受远处翻滚的海浪,而肩膀或者手臂可以作为中景的舞台。

当哪吒和朋友在海边玩耍时,我和助手一人拿一个玩偶在体验者的肩头跳动,体验者虽然看不到,但他的感受也是遵循了透视原理的,玩偶越小,他便认为 “镜头拉的越远”。
最开始的版本是单人的,但因为道具太多,我几乎忙出重影,在正式面对公众表演前,我特地招募了助手,将按摩优化成了双人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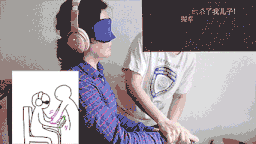
一个人按摩令我手忙脚乱
在演化成双人版本的过程中也诞生了新的花样,哪吒重生了之后得到了三头六臂,我们和助手一起两个人分别勾住参与者的两只手,就是 “真·三头六臂” 了。

真·三头六臂,一起表演的是好朋友叶雅欣和鱿鱼

这是我给我用到的所有道具拍的一张合照。中间的铁铲子是李靖的 “剑”,那条丝巾是混天绫,水管做成的圈是乾坤圈,毛茸茸的白带子是太乙真人的云朵座驾,最左边的珠帘是用来在体验者背上划过,以体现海浪特效的道具之一。

对了,我从布料市场发现的一种神奇弹性面料,后来成了龙王三太子的 “龙筋”。

哪吒:“我要扒了你的筋,给我爹爹做腰带!”
至于这个无法描述的塑胶肉虫,便是龙王三太子的真身。他的皮肤是用洗碗用的塑胶手套制作成的(足足耗费两双手套)。每当我拿着三太子在参与者的脖子上绕圈时,总能吓得他们肩膀一耸。


三太子出洞场景
有意思的地方是,虽然《哪吒闹海》理论上是个动作片,有的人却意外地放松,声称真有 “按摩” 效果。我得到的最有意思的评价来自我的同学。她认为这是她见过的 “最反映电影本质” 的作品:一些人废了老鼻子劲儿制造一些幻象,然后来撩拨你的感官。
第一次正式表演是在北京费那奇动画周上,不知道为什么,本人精心布置的摊位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非法气质。

可能是因为灯牌吧
在费那奇动画周出道后,某个在高端商场举办的艺术市集想要邀请我们去表演,结果过了几周,又嫌我们的外观 “太土”,要求我们整得更 “上档次” 一点。
我果断拒绝了。城市化的面子工程是本人所不屑的,我的按摩影院是街边摊的隔空叫卖,是从吉普赛人的帐篷里面飞出的魔法,是不掀开门帘就不知道里面正在上演着什么的异人马戏团,它能给你实打实的快乐和新鲜感,让你摘下眼罩那一刻便发现:其貌不扬的日常物品也可以给你近乎奇异的体验 —— 就像触觉本来就是五感之首,到头来它却成了最被忽视的神经。
以前学动画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练习。学生两两一组,一个人蒙上眼睛,另一个人带着 TA 上街去。当我被蒙上眼睛到处走的时候,感觉周遭的一切声音和气氛都放大了 —— 直到走进了美术馆。
寂静、不透风的感觉让我立刻知道它是美术馆,在那一刻,所有的一切不再与你有关,就像一群小朋友在讨论你不了解的游戏,你就只能坐冷板凳一样。平时如空气般呼吸着的艺术,在此刻就变得如此不近人情 —— 我以自己受过几年教育的 “艺术之眼” 洋洋得意,而这种 “尊严” 竟然可以这样轻松地土崩瓦解 —— 只要你看不见。
仔细想想,在艺术里面,视觉和听觉是占着 “垄断” 地位的。触觉在艺术馆里唯一会出现的场合,就是展品前那个 “禁止触摸” 的牌子。
视觉障碍者在绝大多数的艺术前,都无法找到入口。

说回来,在疫情的时代里,触摸变成了一种禁忌,一种奢侈。但我觉得正是在这种人人都触摸饥渴、事事都线上虚构的时候,触觉的艺术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身体的知觉才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我们在费那奇动画周的表演摊位,图中另外两位是一起表演的蔡菜和兰馨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