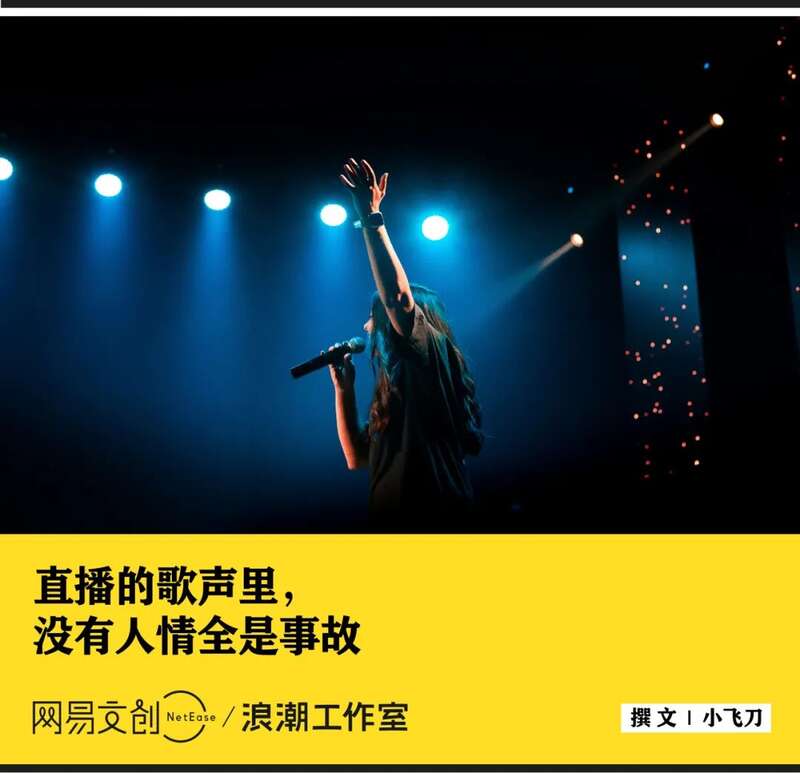
最大卖点为全程直播的《歌手2024》,又名“内娱歌坛扑街会”,成为近期热梗聚集地。
来自美国的香缇·莫(Chanté Moore)是德艺双馨老艺术家;加拿大零零后凡希亚(Faouzia)一张嘴,那英直接慌出表情包;亚当·兰伯特(Adam Lambert)的加入,更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外实力唱将们用行走歌坛的硬通货——唱功,彻底戳破国内歌坛的虚假繁荣。节目前采里,众多音乐圈专家也说出了观众的心声:国内乐坛太好混了。
与此同时,这档节目引发了观众的疑问:为什么国内外歌手的唱功差距如此巨大?这种差距到底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发声基础的差距,
让中国歌手不占优势
有人开口就跑调,有人高音如破锣,还有人即使倒吊着做体操,也能声声丝滑、句句到位。
无论优秀还是拉垮,支撑唱功的基础与根本,都是呼吸、振动、共鸣和造字四大发声器官的协调运作[1]。
从肺部呼出的气流使声带振动形成声波,这些声波通过在喉、咽、口、鼻的共鸣得以扩大和美化,造字器官又为我们提供了唱出歌曲中复合词的发音条件[1][2]。
呼吸是唱歌的动力,肺活量的大小影响着吸气与呼气的总量,也是影响歌者音域、音区、音量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1][3]。
肺活量大,意味着歌手具备吸入更多空气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控制呼气来调节音调和音量,稳定充足的气流还能维持音质、延长连续演唱时间[1]。

 针对纽约歌剧院演员呼吸习惯的研究发现,活泼好动的歌者比一般人的肺活量高出20%以上[4] / Unsplash
针对纽约歌剧院演员呼吸习惯的研究发现,活泼好动的歌者比一般人的肺活量高出20%以上[4] / Unsplash《歌手》第三期节目里,凡希亚在《沙漠玫瑰》的表演中动辄就十几秒的转音,如果没有强大肺活量的支撑,很可能就会变成“灾难现场”。
但肺活量这个事,中国人还真不占优势。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数据,巅峰期中国男性肺活量为3751ml,女性为2557ml[5];而美国健康成年人的肺活量约是男性4800ml,女性3100ml[6]。
这一差异和生理结构有关。研究者在对比不同种族男性的肺功能后发现,白种人具有更大的胸腔和更多的肺泡数量[7]。在呼吸这个重要的技术指标上,中国歌手大概率要稍显逊色。
气流从肺部到达喉部后,使固定在喉头中的声带震动,而喉头的位置直接关系着嗓音质量[1]。
声乐教育家潘乃宪曾谈到,欧美歌手唱歌时习惯放下喉头,而中国人是高喉位[8]。具体而言,欧美歌手唱歌时,声带闭合紧密、喉头位置低,听众会觉得声音更加厚实、充满力量感;华语歌手喉头上提会让声音听起来扁而轻飘, 嗓音则相对细腻;一旦定型,想要扭转也要花费很大的功夫[3]。

 高喉位配合头腔共鸣的唱法,让天后王菲的声音听起来轻盈、细腻且具有穿透力 / Wikimedia Commons
高喉位配合头腔共鸣的唱法,让天后王菲的声音听起来轻盈、细腻且具有穿透力 / Wikimedia Commons咬字习惯的不同也是导致中国歌手听感不如欧美歌手的原因之一。唱歌时,咬字如果过扁过紧,会影响发音质量;唇齿舌放松,歌者就更容易发出饱满的声音。
普通话的发声部位多在口腔前半部,大部分声乐教学讲究字正腔圆,这些都会造成口腔的紧张;但英语咬字相对松弛,口腔会自然而然变得成圆润,也就为歌者创造了良好的发声条件[9]。
不仅如此,中国歌手唱歌时声母需要清晰发音,但美声唱法则要求辅音作为连续和顺畅的音乐线的一部分来演唱,听感流畅性上的差异就额外明显[10]。
在声音形成的每一个环节,欧美歌手似乎都具备更好的基础;演唱过程中共鸣腔的使用,则让歌手们在舞台上暴露出更加明显的区分度。
国内的气声唱法,
在比赛中难获观众共鸣
当竞技曲目为流行歌曲时,凡希亚和亚当会把话筒举过头顶,用鼻腔和头腔共鸣狂飙高音转音;国内歌手则更多采用平缓的演唱方式,共鸣区集中在喉、咽和口部[3]。
同样的流行唱法,欧美和国内歌手在共鸣技巧上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这还要追溯到唱法诞生之初。
蓝调作为欧美唱法的渊源[8],最初几乎都是由黑人游吟歌手在大型帐篷、教堂大厅进行无麦克风表演[11];扩音设备不存在,歌手们就会更加关注声音本身;他们除了要想办法唱得又远又响亮,还需要用原始、粗糙的音色来传递情感。
与蓝调发展类似,早期的福音歌手在大型教堂唱诗班演唱,同样面临着缺乏音响的现状。自然而然地,他们需要通过饱满有力的发声来解决这一问题。有些福音歌手甚至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肌肉力量,才能支撑得起呼喊性和哀鸣式的高音[11]。

 合唱团成员一般利用头腔、口腔和胸腔共鸣,提高声音的穿透力和音量 / Wikimedia Commons
合唱团成员一般利用头腔、口腔和胸腔共鸣,提高声音的穿透力和音量 / Wikimedia Commons将蓝调、福音、乡村等风格融为一炉的欧美流行,也继承了相应的发声和共鸣特色,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常态化厚声带和带式音[11]。
演唱者的声带保持厚实,从胸腔处发出流畅且饱满有力的声音[11]。在凡希亚、香缇·莫和亚当频繁使用高音转音的演唱中,观众也能明显感受到这种传统的延续。第五期揭榜成功的张钰琪,在伯克利音乐学院接受过欧美唱法的训练,也以这一唱法饱受好评。
国内的通俗(流行)唱法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12],从一开始就是“半路出家”。黄霑在博士论文中多次提到,中国流行乐从发展之初就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而是吸收了多国的音乐风格[13]。
虽然它融合了不同的声乐技巧,但当时城市生活丰富,扩音设备的发展已较为完善,这就从源头上造成了与欧美唱法的差异。对音响系统的依赖让国内歌手不必担心声音不被听到[3],自然也就不像欧美歌手那样重视共鸣和高音。
在国内通俗唱法中,大量使用的是气声。三十年代的歌星周璇,就是中国流行乐坛气声唱法的探索者[12]。

 百老汇音乐、好莱坞的歌舞片大量涌入中国,一大批流行歌星涌现,“金嗓子”周璇的凭借甜美的嗓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代表性人物 / 图虫创意
百老汇音乐、好莱坞的歌舞片大量涌入中国,一大批流行歌星涌现,“金嗓子”周璇的凭借甜美的嗓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代表性人物 / 图虫创意由于声带刻意不完全闭合,气流通过未完全振动的声带发声,气声唱法与欧美常用的发声方式相比,音量较小,听起来柔婉暗淡,甚至略显沙哑[3]。
尽管两种不同的声乐体系都不乏优秀的歌者,但《歌手》本质是一档音乐竞技类节目,评委和观众更容易被声音强度高、演唱技巧多样和自信外放的表演打动[14]。
香缇·莫和凡希亚的唱法,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具特色和难度的声乐技巧展示出来,在高音、转音和海豚音的冲击下,国内歌手平淡叙述式的气声唱法就不怎么占优势了。
好唱功的背后,
是科学且持久的训练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国内还是欧美乐坛,歌手从基础发声到形成风格,都需要科学系统的训练。
以伯克利音乐学院四年制的声乐表演专业为例,学生在前两年可以掌握听音和声等基本声乐技能,但需要用四年的时间,才能熟练运用气息共鸣和不同语言的声乐技巧,并将这些技巧融入音乐内涵,生动地演绎歌曲中的故事[15][16]。
系统的培训能够有效提升歌者的综合声乐能力。研究者使用音谱图测定了肯特州立大学不同群体的声音表现,发现与没有声乐训练经历的学生相比,有声乐训练经验的学生具备更广阔的音域,更强大的高低音控制技巧[17][18]。
同样一首《灿烂的你》,经过扎实的共鸣、声带和咬字训练的同学能够唱出更厚实有力和清晰饱满的声音;业余爱好者唱到“那渺小的坚强的怒放的才是真正灿烂的你”这句时,极有可能闹出气息不够用、声音干瘪、咬字不清的笑话,第二天睡醒甚至会发现自己意外获得了“宝娟嗓”,声音变得疲劳与嘶哑[19]。

 唱K时使用错误的发声方法,如用喉咙发声而不是用腹部或胸部支持发声,会增加声带的负担 / 图虫创意
唱K时使用错误的发声方法,如用喉咙发声而不是用腹部或胸部支持发声,会增加声带的负担 / 图虫创意科学系统的训练不仅为歌者打下坚实基础,持续的练声更是歌手精进唱功的关键。
纽约声音动力学实验室的研究者对比了职业歌手、声乐学生和未受训者的肺功能指标,发现与只训练5年的声乐学生相比,平均训练14年的职业歌手具有更强的呼吸能力,因此能更好地运用头声等高音域[20]。
也有研究者连续四个学期记录声乐专业学生的声音参数,结果表明,持续性的训练显著扩展了他们高低音的演唱范围,提高了声压[21]。
歌曲《Hello》编曲精细,层次分明,由钢琴、弦乐和电子元素组成的伴奏层层叠加,形成一种推进效果;原唱阿黛尔(Adele)在主歌部分声音轻柔安静,到了副歌声音极具力量和厚度;听歌听出一身鸡皮疙瘩的我们,被这位经验丰富歌者的“音墙”包围,完全共鸣在私人的情感、回忆和遗憾中。

 阿黛尔不仅拥有出色的技术能力,还能够通过音乐传达深刻的情感,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 / Wikimedia Commons
阿黛尔不仅拥有出色的技术能力,还能够通过音乐传达深刻的情感,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 / Wikimedia Commons对于优秀的歌手而言,准确的技巧只是基本要求,而能否动情演绎歌曲,更需要他们花心思。
研究人员分析了多伦多表演经验为3至15年的歌者的声音数据,结果显示,经验丰富的歌手有意地在表演中使用更多不准确的音和明显的声带抖动,听众在这些看似“失误”的声音中感受到了情感的流动[22]。
《Hello》曲终,一句“it clearly doesn't tear you apart anymore(不会再有人让你悲痛欲绝)”把所有情绪收束, “anymore”被唱成“any-mow-ow”,歌迷们意识到,唱功强大如阿黛尔,也会有格外纯粹真切的感性时刻。
反观国内的音乐节目,现场修音混音,台下掌声雷动,事后好评如潮。实力和名气不匹配的歌手们即使随意对待舞台,但台上台下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不断给他们唱得很好的错觉。
直到在全程不修音的节目中,“皇帝的新衣”再也不能成为遮羞布,落花流水的歌手们自以为用歌声传递了真诚,实则只是为观众带去了笑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