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意的故事,没有逆风翻盘的爽文情节,只有一个抗压能力平平的女孩,面对不如意的生活,被迫探索人生新的价值感的经历。
对于那些躺也躺不平,卷又卷不动,有过三两件后悔不甘的过去,还被时间追着跑的人。她的探索,或许,也可以是你的探索。
我一直在追逐一朵“小红花”
2020年,三联发表过一篇《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笔者徐菁菁在里面写道:
“从前,人们觉得中国有一批好大学,考上它们的学生都有光明的前途。而现在,很多专业小镇做题家非清北不上,这就是符号效应。”
在三联的这篇文章中,有一个与我同级的采访对象,提到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小红花”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表现物。他说,从小到大,大家都在追求“小红花”,但其实它本身不蕴含任何价值,只是象征自己胜过他人的符号。然而进入大学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小红花贬值了,接着,你发现你再也无法通过不断地获得小红花来维持自己学习的意义感。

中国的重点高中,很多人都有被老师划归三六九等的经历,我也不例外。
高一的理科实验班,班主任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南大以下的学生我看都不看”。高三通过自主招生初试后,因为复旦和清华复试时间冲突,班主任立刻找我谈话,让我放弃复旦,即便从项目匹配度来说,复旦显然更适合我。
身处这种环境中心的我,眼里几乎只有清北复交人浙南这七所高校,而被它们录取,就是我心目中渴望的、证明自己超过别人的“小红花”。所谓“一二三流”的学生分别能进入哪所,我在心里分得明明白白。
从小被深植于心的有色眼镜,让我向内用等级约束自己,向外用等级鄙薄他人。而最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是无意识中完成的,是潜移默化的,是无法自控的。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人生的核心价值只有学业。而学业的根本意义在于对外展示:如果说本硕博的学历像三张卡牌,我唯一的追求是一出手就是三个漂亮的S——他们象征着我的稀有性,代表我在竞争中胜过了大部分人。
但高考就像甩在我脸上的一巴掌,北师大成了我打出的第一张“烂牌”——它不是S,不是A,甚至也算不上B。倏尔之间,我手里的牌全都失去价值:开局拿到C,即使我逆风翻盘,也无法再和拥有完美牌阵的人一争高下。
这不仅意味着我失去了长久伴随自己的优越感,还意味着“打出漂亮的牌以获得自我价值感”这种生存方式被强行推翻了。成长到十八岁,我依靠的都是对这种生存方式的认可,它的破灭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戴着我的灰色滤镜,在大学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每每看到身边同学对其跻身顶尖高校的同窗表现出羡慕、钦佩,我都感到格外痛苦。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从与之比肩,变为了仰望。
不甘让我游离在大学生活之外——我独来独往,加入后又退出所有社团。除了心不在焉地上课、考试,以及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以外,我仿佛和学校全无关系,也和“大学生”这个身份全无关系。
幸运的是,时间是仁慈的。即使是对挫折消化困难的我,在两年后也走出了痛苦期,生活重归彩色,我那被从小培植的“必须自我成长”的底层逻辑又开始正常运转,它让我“被迫”重新努力向前走。
我没得到我的“小红花”,也失去了我从小就被灌输,一直都希冀得到的完美的符号价值带来的优越感。我跌入矿洞,渴望自救,却又频频回头。
走出矿洞,并不容易
我经常自我调侃,也感到万般无奈的一点是,父母不计成本的教育投资,使得出身工薪家庭的我,养成了一身中产的毛病——比如,追求个人志趣,按照喜好选择专业。
这一点,并没有因为高考落马改变。我填报的志愿依然清一色外文、中文系。至今记得高考后和少年时喜欢的男生聊天,他问我,你怎么选的这个专业,被调剂的吧?我说不是,是我第一志愿。然后双方同时陷入沉默。
被逆境打垮、接连摆烂的现实,也没有减少我的“任性”,我依然在努力挖掘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我几乎从来不选高分水课,所有课都是在试探我的兴趣所在。
大三我主动参加了workshop,开始求索:我究竟想做什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更有效地确认这个想法?留学这件事情,能怎样帮到我?
答案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动起来,去探索。
我对艺术管理专业动心,所以去了北大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做助理;我想更了解新媒体写作,所以我在新锐出品方的公号做内容实习;曾经我对爱丁堡的Intermediality(媒介间性)项目感兴趣,所以毕业论文我做的是音乐与文学的媒介间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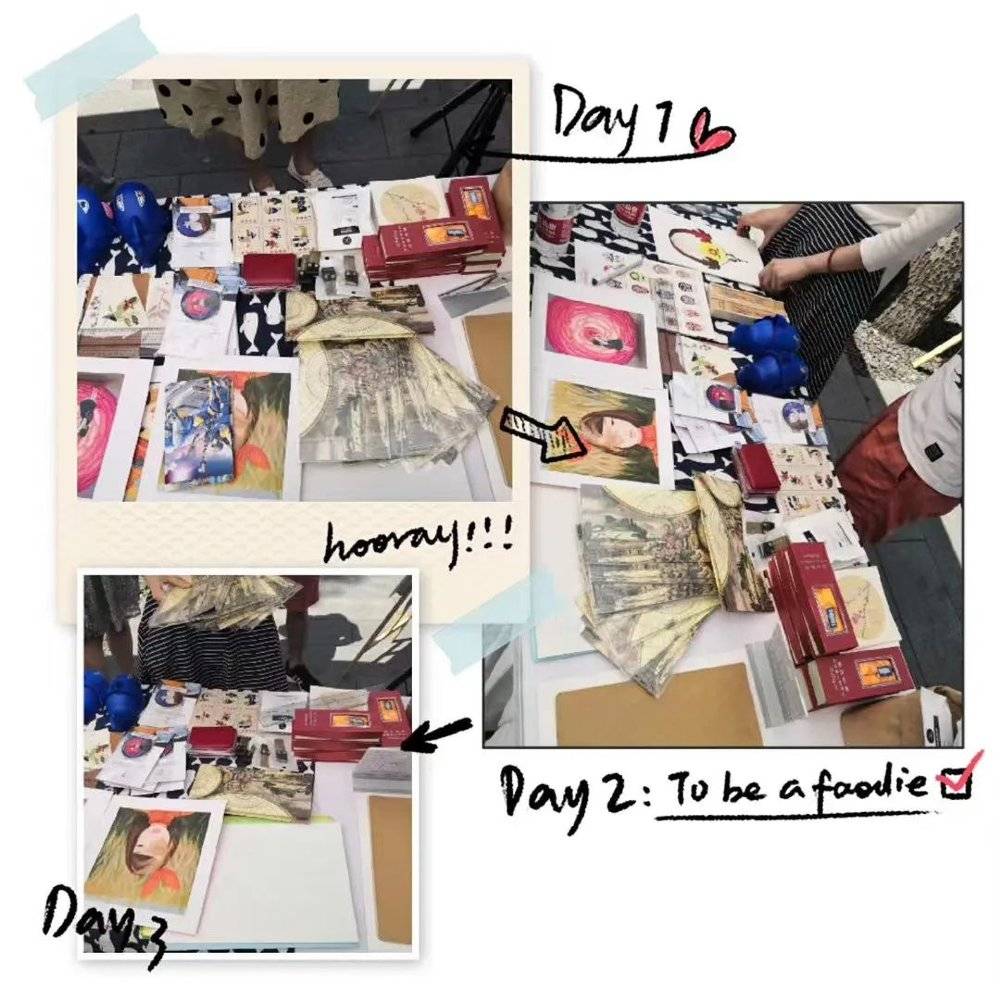
▲实习时候的文化市集
排雷、试错,全情投入地探索,然后我就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我感兴趣的不是文本研究,而是文化研究,这也是我在硕士时选择数字文化与社会专业的原因——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它可以满足我将文化与社会现状联结的渴望。
入读后,我幸运地发现,课程内容和预想一样,研究电子时代的亲密关系和社交平台上的心理身份这类话题让我满足。
然而,学术生活并非全然快乐,它是孤苦的,充满不可言说的寂寞。过去少做的积累使得理论框架不完整,一年多的时间不够我汲取足够的养分;论文写作是痛苦的,翻来覆去修改,上交成品的那刻,我无比厌倦论题本身;学校的名头依然不够“漂亮”,也常常使我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同时,因为退出了过去的评价体系,我又感到无比的自由。
过去的我们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认知——你是哪儿人,多大了,什么学校的?然后答案被迅速与入学考试、国内的地域相联系,带着一套既定的社会规范开始互动。
在国外,没有人会这样认识你。
你们可能在大英博物馆的某个展品前相遇,聊了聊对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见解,然后去泰晤士河边喝了杯咖啡。对方或许会对你的文化背景感兴趣,但你们聊起泡酒、聊火锅和牧羊人派,聊奇幻文学和俗气的爱情电影、聊在欧洲的旅行见闻,甚至聊到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聊到对方对于中国政治的误解,却不会聊到高考报志愿。
因为对方没有认识这段过去的渠道,你的过去就这样沉寂了。消失的过去让我短暂地忘记了我失去的“小红花”,也让我在与陌生人的交流中,获知更多我身上除了成绩以外的价值。
我并不是主动放下了过去,我只是必须选择一条路继续向前走。但我也相信,如果成长是不断接纳更多更新的逻辑的过程,我总能等到足以忽略他们的那一天。
我要真正走进一片新的旷野
我寻找机会重建,尽管也走了一些弯路。
在新锐出品方的公号做内容实习的那段经历,让我对未来感到怀疑。我喜欢慢吞吞的纸媒,喜欢反复打磨后更具深度的内容,但新媒体日更的节奏让我觉得力不从心。
我曾坚信内容对人的影响,以及产出内容本身的价值。但新媒体编辑的工作让我对这一切都产生了质疑:这些我们精心策划的、在有限时间内反复打磨的东西,和那些营销号复制粘贴驴头不对马嘴的文章,究竟有什么区别?
和电子时代所有的消遣一样,这些阅后即焚的速朽的文章,似乎都会在一瞬间就变成赛博垃圾。我难道真的,还非走这条路不可吗?
这份迷茫持续到了留学后。对于大部分留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高开高走,绝不浪费“留学生”的身份,不浪费自己手头的资源。英国对于专业背景的包容,使得留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可能。
在国内,圈内人卷到卷不动的咨询行业,在英国却是可以属于我们这些“圈外人”的。于是,很多选择留在英国和美国的朋友劝我先别追求不着边际的理想,而应该进大厂进咨询公司,用手里的牌在最好的平台赚更多的钱,安身立命后再逐梦。

▲阴雨天的泰特,我也想过留在英国
我对此建议动过心,尝试投快消和奢侈品行业的管培生。然而写cover letter时却发现落笔困难——如果我有两三分的喜欢,夸大成七八分是能做到的;但如果对它的喜欢小于等于零,那我是真的一句话都写不出来。我没法表达我对这个岗位的热爱,因为我根本不爱。
所以,我还是没忍住尝试了英国繁荣的出版业。虽然我语言竞争力弱,对本土文化和市场的了解不够多,但求职的两个多月里,我最诚实的时刻就是面试杂志和出版业——我能立刻回答出留学前PS里写下的职业规划,并明确感受到,这依然是我长久所想的、无法逃避的、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
最终,瞻前顾后的我回国了,但这次,我依然把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选择了心仪的杂志。
快过年了,我却又回到北京入职,万般不情愿地成了一个为爱发电的新北漂。落脚之前,其实我非常害怕。然后我告诉自己——没关系,如果因为大环境不好,我失业了,我就去申请新西兰的打工签证,做体力活儿享受一年working holiday;如果申请不上,我就去大理学习做咖啡,去西藏当编织毯女工;如果我最终发现喜欢只是一种错觉,我就换去公关行业,如果换行也不成,我就蹲在家里养猫,申请欧洲的岗位制博士……

▲生活中有很多美好,我到现在才学会挖掘
回头一看,抓了一手“烂牌”,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我学会了与烂牌和平共处,我学会了牌臭的时候依然认真思考最机灵的打法,我还学会了——牌面赢不赢又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打牌的人的体验。
当然,我必须要说明,这一切终归是要感谢我的家庭。不管家境如何,我的家人愿意给我他们能够提供的经济保护和支持,不干涉我对于专业和职业的选择。正因如此,我才敢于抛开更多“世俗”的压力,在可能会失败的情况下依然去探索自己所想的职业和生活。这本身也算是一种privilege,无法完全普世化,所以需要好好感恩。
我不勇敢,相反,我很怯懦,有很多恐惧。恐惧意味着面对未知,但未知意味着新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性”本身,让我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对看到这里的你们,我想说,不要害怕,你可以努力创造新的可能性,但也记得随遇而安。你可能犯过很多错,掉过很多马,但是只要你向前走,生活总会给你提供落脚的地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eBeyond(ID:BeBeyondG),作者:BeBeyo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