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说谎者的惩罚,不是没有人信任他,而是他不再信任任何人。”——萧伯纳
“棍棒之下出孝子”,这曾经被传统中国人奉为圭臬。
农村出来的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如果不是家里的独子(包括有姐妹的情况),很少没有挨过长辈打的。挨揍是传统社会男孩子的日常生活。
小时候我挨亲娘(祖母)打最多——其实也没被打过几次——我记得很清楚,她老人家总是举着扫帚,迈着半路解放的小脚,在后面追赶我们兄弟,当然总是追不上。村里人给她老人家起了个外号:“笤帚婆”,其实就是亲娘教训我们兄弟时的情景。
不过,我的父母亲很少打我们,母亲没有打过我,而挨父亲打,我的记忆和父亲的记忆是一致的:两次。
有一次我在武力教育女儿时,父亲曾经规劝过我,最好别打孩子。父亲说,我记得也就打过你两次。是的,父亲说的打过我两次,我都记忆清晰。而父亲打我们兄弟,不是因为他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是怕我们兄弟不走正道,走了歧路、歪路。
一
我记得第一次挨父亲打,应该是6岁左右。
当时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组织劳动,家里大人下田干活的时候,我们这些无人照料的孩子会跟着,放在田间地头,自个儿玩草、玩泥巴,大人时不时可以直身察看照顾。
当时我母亲在镇上的社办厂工作,不能带我们,而父亲是壮劳力,要干重活也不能带孩子。所以,平常都是我祖父母带我们兄弟仨下地。但即使跟着大人下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作为老大,得在地头看管两个弟弟。
几年前微博曾有一张照片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小孩被用绳子拴在煤堆附近,任由她自己玩,大人们在远处干活。其实类似的事我也干过,我曾经用绳子系在弟弟腰间,另一头拴在桌子腿上,自己偷偷跑出去玩。这一幕被回来的堂姑撞破,后来堂姑一边跟祖父夸我聪明,一边也有担心。那次我没挨打,也就挨说了几句。
那一个夏天,我照例和弟弟们跟着祖母下地。就在今天我们村西浜头西南角的地里,离我家老宅不到两百米。快接近中午的时候,我跟祖母说,要回家喝水。
夏天下地干活的大人,通常都会带着水,但那次就在村子附近的地里,没带水。祖母经不起我折腾,放我回家喝水,临走再三交代,喝完水赶紧回来,尤其提醒不要乱走,不要去河边埠头上。
得到许可的我兴高采烈,就像出笼的小鸟,拎着一根当枪玩的葵花棒,光着脚一路颠跑着回了家,我家的小狗紧跟在我屁股后。不过,我没有像跟祖母求告那样是回家喝水,而是直接去了西浜头的埠头上,埠头离我家旧宅最近,也就十多米。
西浜头当年的埠头,青石板拾阶而下,隐在河面下还有好几个台阶,夏天跟着大人上埠头,我会趴在水里的台阶上玩水。石阶边上还横架着一块长条青石板,可以容纳好几个人同时淘米洗菜的。父亲后来跟我说过,这青石条是当年村里祠堂拆下的。
我先在水里的石阶上洗了脚,然后返转站到长条青石板上。虽然几乎天天跟着大人跑河埠头,但我那时还小,不知道河的深浅。一时起了好奇心,拎起葵花棒,想探探河有多深。
多深?站在青石条上,我用葵花棒往水里一戳,没想到葵花棒短,一戳,没够到底,我顺势被带着栽落进了水里!
那时我还不会游泳,虽然边上青石板触手可及,但根本没有意识,惊恐之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双手使劲乱拍水,身体在水里扑腾,或浮或沉,浮起时便喊救命,呛水之后,连救命也要喊不出了。
我家的小狗见我落水,在埠头上朝着河里狂叫,声音凄厉。村里一位同宗兄长本来回家换衣服要去走亲戚,听狗叫凄惶,不知何事,跑来一看,发现是我落水了,赶紧跳进水里把我捞了出来。
兄长一边给我控水,一边叫村里赶来的其他小孩去地里叫我祖父母。祖父母赶回时,我已经躺在家里的竹床上哭,看我那害怕的样,祖父母又生气又心疼。父亲随后也赶了回来。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毫不怜惜地把我从床上拎了起来,使劲打我屁股,一边打一边责骂我,我又疼又委屈,哇哇大哭。
这是父亲第一次暴打我。多年后我成了“中举的范进”,曾就此事问父亲,为何当时这么“凶狠”地打我。父亲淡淡地说,一来我不听话,跑去玩水;二来竟还撒谎骗家里人,小小年纪如此,长大了如何了得。我哑然。
《儒林外史》里,胡屠户打发了疯癫的范进耳光,打的手掌作疼,觉得天上的文曲星果然是打不得的。这个时候的范进,已经不只是他的穷姑爷范进,而是天上的文曲星。而我父亲打我的时候,我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小屁孩,父亲打我自然毫无忌惮,手不留情。
父亲第二次暴打我,也是因为我撒谎。
那时我已上小学,记得是某一年的农历七月半前——我记得在回家路上遇见邻居家过七月半的亲戚。那天上午,我自告奋勇代父亲去街上卖甲鱼壳,当时是去走马塘街上卖的,卖了多少钱记不得了。但当时我卖完甲鱼壳后,偷偷拿出其中两毛钱,在供销社买了本小人书,书名叫《桑椹红了》,是讲抗日小英雄的。
父亲是老法师,自然知道甲鱼壳能卖多少钱。我回家把钱交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发现少了两毛钱,我告诉父亲说,可能是路上掉了2毛钱。父亲也没追究,提醒我以后注意。
但是,父亲后来在我枕头下发现了小人书,还是新的,一看定价,正好是两毛钱。立刻把我揪住审问,我看蒙混不过,只能怯怯地承认小人书是拿了两毛钱买的。
父亲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更狠,用上了器械,用的是担绳,就是家里用来捆扎稻麦用的粗绳。当时父亲打我的时候,大概率嘴里会嚷嚷着“叫你说鬼话”。鬼话,就是谎话。
按父亲的说法,这叫吃记性,让我以后不说谎。父亲痛恨自己的孩子说谎话,不学好。这是一个严父的朴实信念。
二
我的长辈都是普通农民,在自己的世界里有自己的生活信条,不说谎,是重要的一条。过去我的尊长对我们兄弟的日常伦理教育中,都会通过民间流传的宗教故事,跟我们讲述不说谎的重要性。
我和父亲的母校朱家桥小学,前身是东岳庙,这东岳庙里的泥塑被推倒改建新式学校之前,据说非常有名。
我的祖父母、父亲都给我们讲过当年庙里的上刀山下油锅之类的塑像毕肖,包括说谎拔舌的泥塑。亲娘给我们讲故事,总是会讲到说鬼话骗人,会被阎罗王捉去打入地狱,小鬼来掰开你的嘴,用铁钳夹住舌头,生生拔下你的舌头……小时候听了这样的故事,总是不寒而栗。
老人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因为这也是他们相信的。但当我在朱家桥小学读到木偶匹诺曹的故事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并不真的认为说谎鼻子就会长长。
但是,现实生活中,说谎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拥有某种信仰的人,即使明知道说谎不好,也难免仍会撒谎。
在世俗生活中,有时候撒谎可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大致而言,普通人撒谎的原因,或为谋利,撒谎能带来直接的诸如权力地位和经济方面利益,这是世俗生活最大的诱惑,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撒谎的最大动力,为此,一些人甚至可以背弃宗教信仰道德信念;或为自我保护,保护自己和亲善之人的利益和隐私,以防止受损,也很容易撒谎;或为掩盖真相,掩盖真相的谎言,既有利益关联,也可能是因为善意,当然也不乏栽赃;或因面子,避免尴尬,或者站队避免被孤立的社会压力;甚至,还有因为游戏心态的好玩……
撒谎是人类古老的传统,通常人们撒谎是为了具体的利益,即使满口谎言,也知道自己在撒谎,连小孩也知道。
我的第二次撒谎——偷买小人书,既为掩盖真相,也为自保,因为我那个年龄已经很清楚偷买小人书行为的后果。
至于我的第一次谎言,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与权力地位财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有着类似的逻辑:如果不撒谎,亲娘很可能不会允许我回家,不回家就不可能有放纵的自由……
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很容易被戳破,比如我的那两个谎言。一旦戳破,撒谎者也自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人世间最大的谎言,其实在政治生活中。政治生活中,即使谁都知道是谎言,也很少受到惩罚,除非政治生活发生革命。
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并非仅是童话那么简单;一如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的《法西斯谎言简史》中所描述的那些谎言和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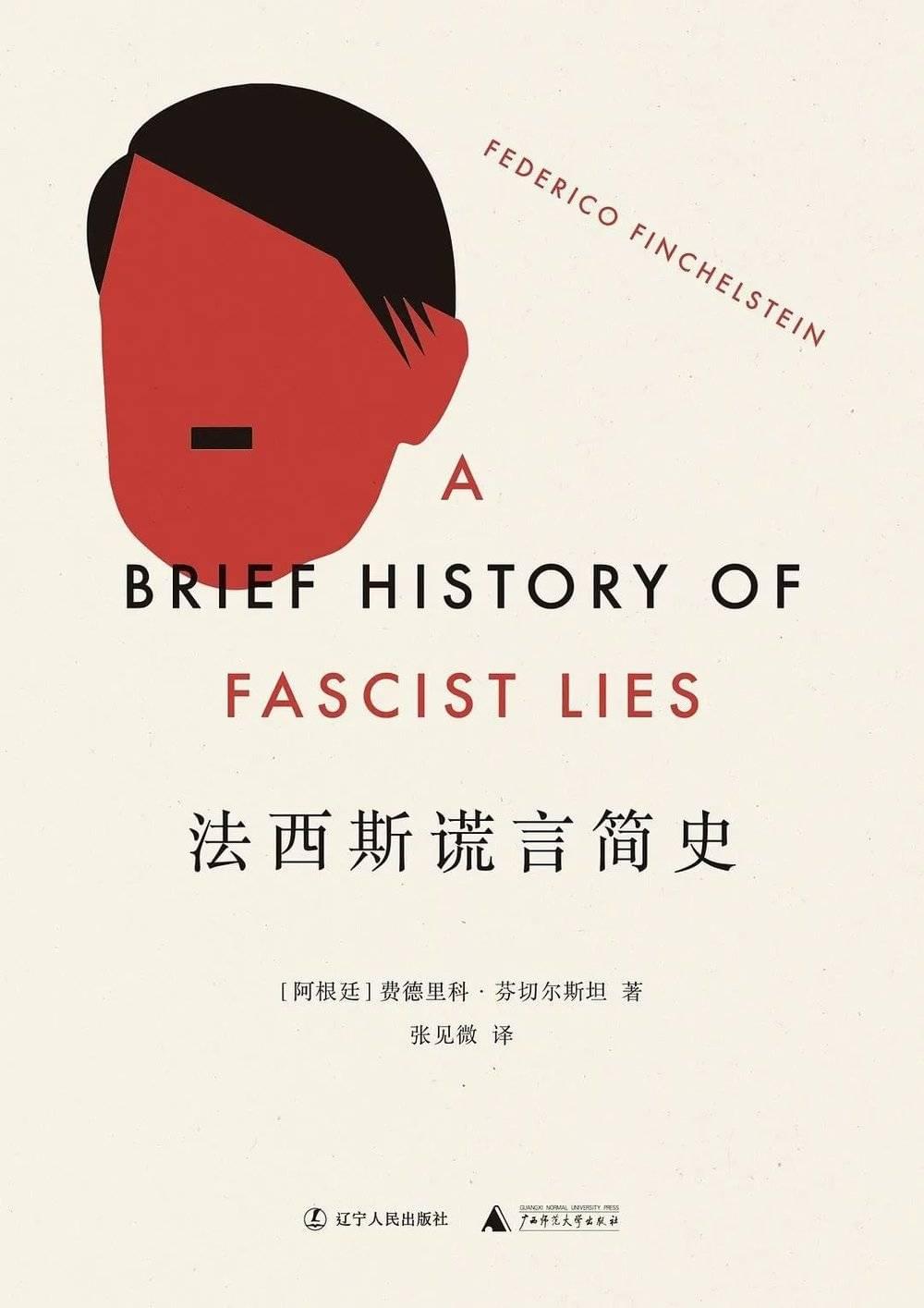
《法西斯谎言简史》
[阿根廷] 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 | 著
张见微 | 译
一頁丨辽宁人民出版社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20世纪著名的法西斯主义领袖,无论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都视谎言为真理,视自己为真理的化身,而在他们的信徒那里,只有领袖才能成为真相的来源。“墨索里尼永远是对的”,谎言说多了,连自己也信了,没有人相信匹诺曹的故事。这是20世纪法西斯统治下体面人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一个人意识的真实历史,往往始自他撒的第一个谎。”
布罗茨基在他的名作《小于一》中写道。布罗茨基记得自己撒的第一个谎,是7岁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填写借书申请表,要填写“民族”一栏。布罗茨基已经清楚地记得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对管理员说不知道。犹太人过去在俄罗斯的命运很是不济,反犹主义曾经很盛行,犹太人常遭歧视。所以布罗茨基说,自己撒的第一个谎与自己的出身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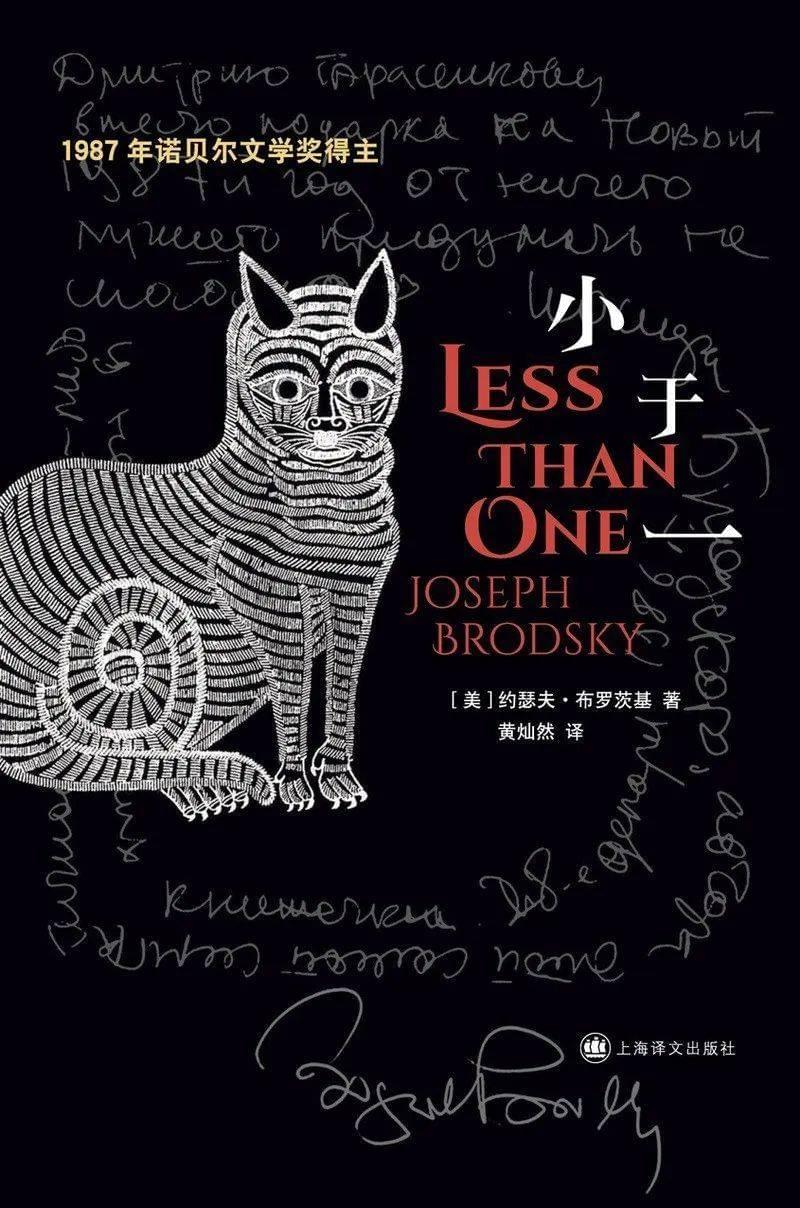
《小于一》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 著
黄灿然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自己撒第一个谎言时的年龄,应该比布罗茨基还小,但我读到布罗茨基这句话时,却让我陷入了思考。我的谎言与出身无关,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文化冲突都无关。
6岁多那年,我跟亲娘说要回家喝水,并非一开始就是撒谎的目的,去河边玩,大概率是顽童即兴发挥。而我所以记得,也是因为撒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屁股挨了父亲好几巴掌,也因此有了记忆,也有了自己意识到的真实历史。
第二次偷买小人书撒谎,则与布罗茨基一样,已经完全有了一种自我意识——撒谎是为了掩盖真相,掩盖真相是为了避免做了错事受到惩罚,知道做错事会受到惩罚,前提是知道了对错,知道了被惩罚的痛苦,而这些来自生活的经验家人的言传身教……
在《小于一》中,布罗茨基说,一个男孩同迫近的命运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脱离轨道。撒谎是脱离常态轨道的一种方法。谎言一旦得利而说谎者未受惩罚,撒谎就会上瘾,就像《奥德赛》中塞壬的歌声一样难以抗拒。天纵英才如奥德修斯,也得将水手的耳朵弄聋,让他们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才能躲过成为塞壬腹中餐的命运。
不过,我这个试图脱离轨道的尝试,在一次被父亲打了屁股之后,又一次尝试时,遭遇了父亲更暴烈地抽打,父亲打在我屁股上的巴掌和抽在我身上的麻绳,就像绑住奥德修斯抵御塞壬歌声的绳索。我尝试通过撒谎脱离传统生活轨道的路径被堵住了,没有养成撒谎的习惯。
人生的历练后来告诉我,如果撒谎的习惯没有被遏制住,我的人生可能变成一种不堪设想的生活——或者可能被收监,或者成为自己今天所鄙视的那些人,甚至还不自知,可能还洋洋自得……
没有养成撒谎的习惯,其实就是一种“同迫近的命运斗争”的极其重要的方式,是一种最罕见的脱离日常生活轨道的方式——因为几乎人人都会说谎,包括纯粹恭维的好话。
鲁迅在《立论》中的表达很是经典: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事实上,几句好话能改运?
因撒谎挨过父亲揍后,我在生活中并非没有再撒过谎。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不顺心的时候,我也会跟父母家人撒着善意的谎言,以免他们担心。
但我后来在日常工作的那些谎言,大多无非是形格势禁下鹦鹉学舌的空话、套话、瞎话,非出本心,于己自是鬼话谎言,这些多与为己谋利、掩盖真相、栽赃陷害无关,目的在为了更好地完成自认的更高的职业理想和道德责任。
但是,本来为了达致一种理想而在过程中与各方力量妥协低头,有时也难免有瞎话——最后可能忘了妥协的初衷,只剩下妥协。
这也就是布罗茨基说的,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就一定要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关系……”
但如同布罗茨基所说,这个人所编织的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自己,这便是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到有罪。”
“谎言更多的是对自身而不是对他人义务的侵犯”,违反对自己的义务(说谎)就是抛弃自己的人性。康德这样说过。
夜深人静写日记的时候,我有时还会想起父亲当年的巴掌和担绳,为自己曾经的谎言感到羞愧,为自己曾经挨过的揍感到庆幸——它让我的人生保持了基本的人的体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朱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