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八角钟楼静静伫立于如今的雅典,在空旷的罗马广场之上,它敦实如一支消音器。晴天时,它是日晷,以阴影测度着时间;夜晚,或阴雨绵绵之际,塔内的水钟便会派上用场,滴漏的声音使人感受到时间的存在,那细密的噪音几乎可以渗入你的皮肤,让你恐惧。
在这座古城中,时间的流速是不一样的,生者与死者分享同样茂盛的阴影。后者,那些雅典黄金时代的古人,因他们的死亡而不朽,反比速朽的我们拥有更热烈的生命。你可以在雅典的街巷中找到他们的刻痕。就譬如这座钟楼,它被称为“风之塔”,又名基尔斯托斯钟楼。据传,它是在公元前1世纪由马其顿天文学家安德罗尼库斯建造。在众多雅典旅游手册中,它又被称为“苏格拉底之墓”。
实际上,这位哲学家并未埋骨于此。甚至,在公元前399年的那次著名的审判中,水钟也应被视为谋害苏格拉底的凶手之一。在法庭上,苏格拉底必须在水钟漏完之前完成自己的辩护,因此,他的生命便系于这一只陶罐的容积。他对此表示不解,如果拥有更多时间让他的言辞发酵,人们便会更充分地考虑这场死刑判决。
生活在2400年前,习惯那以节日和仪式编织成的乡村历法的苏格拉底,并不熟悉现代意义上的时间。古希腊语中的“hora”直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才拥有了“小时”的含义,在此之前,它可以指代一个季度,也可以表示某一段指定长度的时间。
在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能说,苏格拉底所生活的时代,是时间开始的时代,而他正是这个时代的刻度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刻度。
雅典民主的诞生
一本简明扼要的评传,譬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以下简称《苏格拉底》),将导引我们进入苏格拉底的雅典。

《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
作者:[英] 保罗·约翰逊
译者:郝苑
出版社:大学问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这位哲学家亲历了雅典民主制的盛极而衰的过程。他人生中大部分光阴,雅典都处在伯里克利统治之下。作为彼时雅典的立法者,伯里克利如同他的先行者梭伦与克里斯提尼,将城邦视为一块未经修整的大理石原石,而政治之于城邦,就像雕塑艺术之于大理石,它让一种本质性的思想从空白中涌现。
透过伯里克利的努力,公共空间于焉兴起。雅典的街道成为容纳思考的场所,或清澈或浑浊,言辞之流在毛细血管般的街巷中涌动,冲刷出文明的卵石。
这便是为何,当雅典法庭以微弱多数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他宁愿接受死亡,也不愿选择流放:只有在雅典,他才能够在街道与广场之上,在大众之中思考,在对话与反驳之中,不断确证自身的有限性。
雅典民主体制的最终形态,即是一种近乎纯粹的大众政治,人本身成为尺度,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如此充分的主体性。
《苏格拉底》一书给出了某种描绘苏格拉底人生的范式,即把苏格拉底视作雅典黄金时代的精神表征。似乎,书写苏格拉底就像在用史料编织一个甜甜圈,作为旁证的材料堆砌着,被各种史观烘焙成某种宏大叙事,但这叙事的核心却是一片空洞:
色诺芬在回忆录中几乎逐字记述了苏格拉底的一些言论,在保罗·约翰逊看来,这位《长征记》的作者或许是一位杰出的军旅纪实作者,但他却无法理解苏格拉底心灵的“坚强、敏锐和轻快”;
柏拉图的著作是我们了解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途径,不过阿加德米学园的创始人毕竟不同于在公众中生活、思考的苏格拉底,尽管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仍相当忠实于苏格拉底言说的原貌,中后期的柏拉图却愈发倾向于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成为传达他学说的人格化面具。
保罗·约翰逊写道:“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柏拉图开始阐述他自己的理念。作为一个学者,他迅速将这些理念融入一个体系之中。作为一名教师,他不仅用苏格拉底来传播他的理念,而且还用苏格拉底来让这些理念永存。”
在他看来,柏拉图的做法,不啻于对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谋杀。故而,我们只能透过这些旁证去接近那个名为苏格拉底的空洞,透过对雅典黄金时代主流意识的勾勒去找寻苏格拉底哲学的原点。
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雅典的政体,确立了财产等级制及议事会制度,寡头的权力被限制。由于梭伦并非民主派,真正意义上的雅典民主制要到梭伦改革90年后才出现。当时,雅典城内亲斯巴达的伊萨格拉斯与平民派的克里斯提尼爆发冲突。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五卷中记载,当伊萨格拉斯处于下风时,他请求他的旧日好友斯巴达国王克琉墨涅斯出兵雅典,将克里斯提尼一派作为“受诅咒者”放逐。
碍于斯巴达的武力威胁,克里斯提尼暂时离开雅典,斯巴达国王和他的一支卫队进入雅典卫城,试图解散议事会,于是,在公元前508年,支持议事会的雅典人围攻了占据卫城的斯巴达人,3天后,斯巴达人被迫与之休战,克里斯提尼一派在雅典人的邀请下回归,来到了这座陷入政治真空的城邦。在克里斯提尼手中,“demos-kratia”诞生了,在古希腊语中,这是一个复合词,意为“人民的统治”。
黄金时代的哲人
在苏格拉底活跃的时代,雅典抵达了它的巅峰。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同样生活在这个时代,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叙了所谓“雅典帝国”的兴亡,在这部史学名著的第二卷,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说道:
“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这些并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的一种空自吹嘘,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城邦的势力就是靠这些品质获得的。”
这篇经修昔底德之手编辑的演说词,本是为悼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牺牲的雅典将士,如今已成为论述雅典民主制度的经典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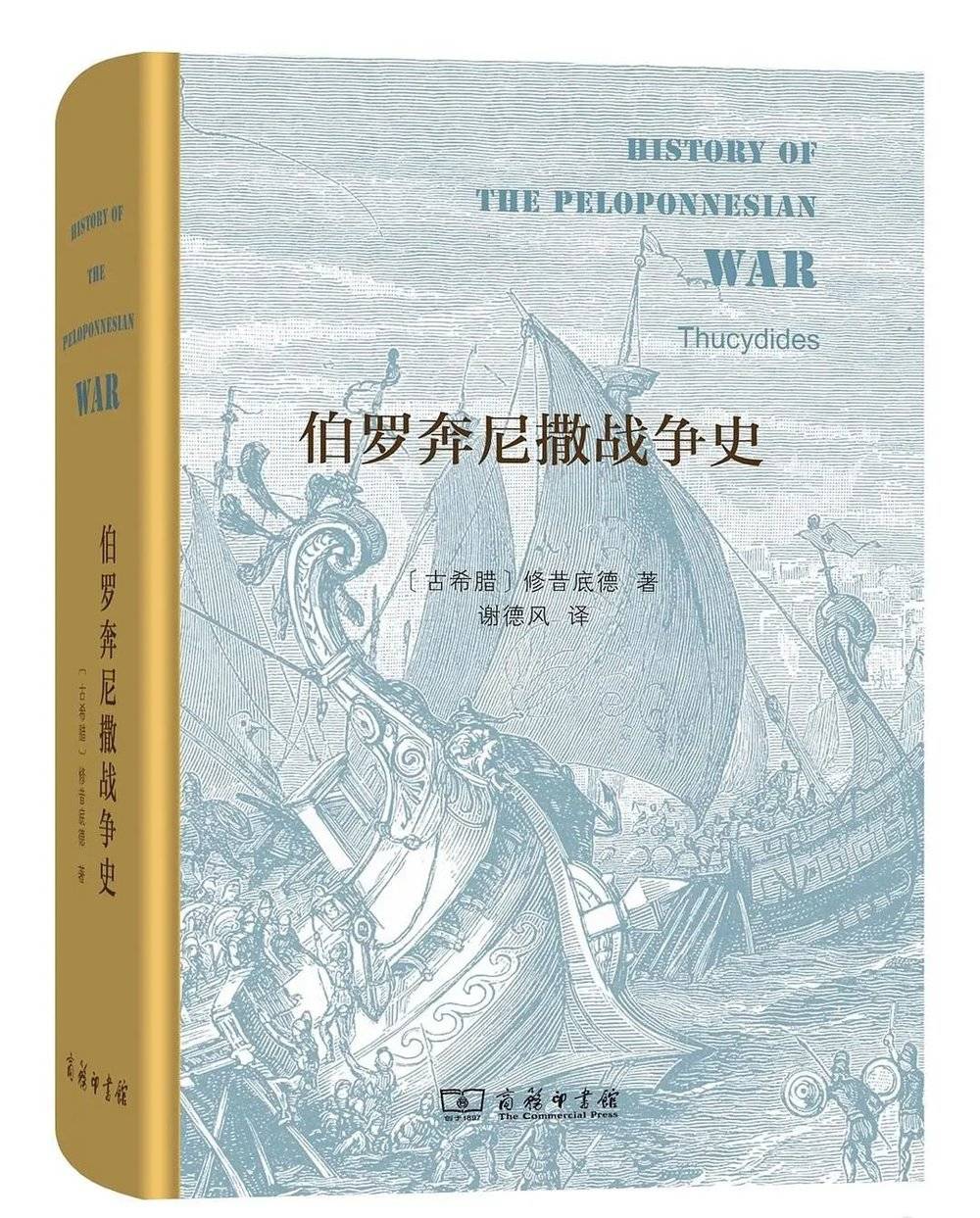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作者:[古希腊] 修昔底德
译者:谢德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从中,我们可以管窥支撑这一制度的社会心态,保罗·约翰逊在《苏格拉底》一书中称之为雅典的乐观主义。修昔底德提到,正是雅典人的祖先,在波斯的入侵下保卫了希腊,一个以雅典为核心的海权帝国才得以建立。苏格拉底出生时,恰逢希波战争落幕,雅典人开始在一片瓦砾中重建家园,旧城的碎片被砌入长墙之中,仿佛雅典人有意让这段悲惨的过去守卫他们的城市。苏格拉底的父亲索福洛尼克斯就是雅典城中的一名石匠,他与来自泛希腊的石匠共同构筑了雅典外在的庄严。而这座城市内在的高贵,则由哲人、诗人与公民一同维系。
战火一度摧毁雅典城,却为雅典人留下3份赠礼,一是在雅典周遭意外发现的储量丰富的银矿;二是仰赖银矿的开采,在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导下,雅典人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强大且有实战经验的海军,这支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传奇般地击败数倍于己的波斯海军;最后则是,基于希波战争胜利带来的威望,雅典成为提洛同盟的盟主,并且透过对同盟共有金库的控制,一步步将同盟转化为以雅典为核心的帝国。利用金库中盟友的贡金,伯里克利将雅典打造成一座充满奇观的大理石之城。“这些巨大的建筑物”,伯里克利说道,“不但让当代人,也让后世对我们表示赞叹。”
根据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记载,伯里克利曾师从智者学派的达蒙、芝诺与阿那克萨戈拉,他们分别教授他政治学、辩论术与伦理学。这些哲人共同引发了一场智识上的变革,使人们从关注神明,转向关注尘世。
苏格拉底两岁时,有一枚陨石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坠落。英国历史学家贝塔妮·休斯在《毒堇之杯:苏格拉底、希腊黄金时代与正当的生活》一书中写到:
“出人意料的是,并不是所有希腊人都在哀叹这是众神的怒火。不久,雅典娜之城的一位古怪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就用一种疯癫的理论逗乐了别人,他认为恒星和行星并不是什么天上的生灵,而只是一些滚烫的岩块。他的信念似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那块天降陨石的证明。”
雅典黄金时代的哲人,逐渐补缀出早期人本主义的图景。正是他们制造出所谓“新神”。苏格拉底日后被指控的渎神罪行,其雏型就掩藏在彼时希腊的智识世界中。
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最强劲的对手,被后世广泛视为希腊哲学中人本主义的代表。他将对人自身的信仰,提升到近乎绝对的地步。人成为万物的尺度,这意味着,一切真理都可以在言辞的透镜之下,被灼烧成泛着焦糊味的立场。在他面前,即使苏格拉底惯用的反讽也显得笨拙。
普罗泰戈拉和所谓智术师们,显然明了言语的力量,他们贩卖这种力量以求得财富,这正是苏格拉底忧虑的地方,诡辩会腐蚀城邦的根基,智识上的自满亦将使城邦裹足不前。
与智术师不同,苏格拉底从不向他的门徒教授操纵人心的修辞术,而是催促他们去认识自身的有限性。“无知”——这便是苏格拉底哲学中的核心悖论。正是由于苏格拉底坦言自己的无知,他才是神谕中那位“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非政治的先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城邦生活也必然被政治包围,如同蜂巢中的蜜蜂,雅典人每日都在品尝权力的花粉。
在战场上,士兵苏格拉底的英勇与坚毅人所共知。在《会饮篇》中,亚西比德回忆起掩护部队掩退时的苏格拉底,他“两眼瞟着左右,不动声色地扫视朋友和敌人,让人个个老远就明白,谁要是碰一下这男人,他会极为坚定地捍卫自己。所以,他以及他的友伴都安然撤离”,但苏格拉底却有意地疏远了世俗意义上的政治。这样的态度最终让苏格拉底成为了殉道者。
公元前399年的那次致命的毁谤,其本质是一场政治迫害。在此之前,雅典瘟疫夺走了伯里克利的生命。伯里克利一派的政治生命也成了陪葬品,雅典人将瘟疫视作对伯里克利派系的神罚,他们因此遭到放逐。瘟疫、战争失利与政治动荡耗尽了雅典帝国的战争潜力。
公元前404年春,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向斯巴达投降告终。随后,斯巴达扶持“三十僭主”统治雅典,为首的正是苏格拉底的两位学生,克里蒂亚与查米迪斯。这些人的残暴超出斯巴达人预料。他们建政期间非法处决的雅典公民达1500人,随后的内战导致雅典损失了5%的人口。最终,斯巴达只得默认雅典民主派的复辟,而血腥与不安之门一旦打开,这重新建立起来的民主便成了弗兰肯斯坦般的怪物。恐惧并不能带来自由。
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应该为“三十僭主”的恐怖统治负责?这位刻意非政治化的先知,难道应当被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保罗·约翰逊认为,苏格拉底并不一定会赞同柏拉图等级分明的理想国。
他与鞋匠、石匠、面包师一同生活,与他们讨论哲学就像谈论天气,他的思想场域并非封闭在一个精英化的学院内,而是实实在在地楔入雅典的城邦生活之中。
透过思考,透过不断越过无知的边界,他书写着这座城市的灵魂:平等、开放与可能性。仿佛水一样可塑,一样弥散于某一特定的时空之中,为这时空所塑形,也同样可以刺破它,通向无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谈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