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科偏好和文科思维,来自父亲的影响,一种不言之身教,甚至可能还有遗传,那就是父亲对读小说的热爱。
如果父亲不爱读小说,我的文科思维或许就会轻一些?
小说,今天按照度娘的解释,是一种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不过,庄子所谓的“小说”,是指琐碎的言论,与今天的“小说”概念完全不同。鲁迅先生曾在他的名作《中国小说史略》里,借文献诠释了“小说”一词的概念流变和影响:
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所谓“残丛小语”,就是末技、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则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活动至晚在唐代演为“说话”的艺术,至宋代而极盛,产生了各种“说话”的底本即“话本”,后来又产生了白话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
对于我的父亲而言,他对小说的认识,与度娘的定义无关。在他看来,小说无非就是讲故事的书,跟传统说书人说书差不多,无非就是印成了书的形式,里边一样有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好看。
父亲看了一辈子小说,如今80岁的他,早上钓完鱼,午休之后闲来无事,依然会在我江南书房的阳台上,翻看我的书,以小说为主,兼看其他人物传记——在他看来,也与小说差别不大。
父亲翻看的这堆书里,并没有什么我认为的好小说及传记,但不妨碍他每天都会在我书房聚精会神读一会书。
2023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友前媒体人何三畏来我故乡见我,在父亲平常读书的桌上,摊开放着一本旧的《收获》杂志,那一页正好是范小青的《名字游戏》。
一
父亲爱读小说的习惯怎么培养的,他老人家也说不清楚。他说,读了书认得字了,就是喜欢看看报纸啊杂志啊小说啊,这些里最好看的,不就是讲故事的小说嘛,谁不喜欢看故事呢?
1943年出生的父亲,是长房独子,小时候是家里的宠儿。1958年他从朱家桥小学高小毕业后,又在该校读了三年农中,相当于农业职业中学毕业。朱家桥小学是鼎革后由推翻神像的东岳庙改建,结合了新学传入中国后毁庙兴学的传统。我小学也是在朱家桥小学读的,和我父亲是校友。
父亲年轻时的中国,文盲居多,农中毕业可以安排工作。父亲被安排到前黄一家公社办的电磁厂工作,岗位是给电线杆上的蝴蝶形磁头绕线圈。没多久,电磁场破产关门,父亲被暂借到前黄公社公安特派员办公室做记录,他那时算是乡村少有的读书人。
“那个时候,批捕人的文件都是我起草的。”父亲说,虽然是暂借,总是想要做好,于是他先看别人怎么弄,毕竟农中毕业,一看就会,后来批捕文件都是他起草,后来又看审讯记录,就像看故事一样,学到了许多东西。
父亲后来还是回家务农了。在农村,他打得一手算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是农民里的小秀才,胜过大多数同龄人,甚至许多民办公办老师。尤其是,像他那样爱读小说的,不敢说绝无仅有,也屈指可数。
那时候,农村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是如此。除了偶尔的露天电影,还有不多见的评书讲故事。父亲喜欢看听故事,最初可能来自故乡的滩簧戏,那是锡剧的前身。我祖父母曾经在滩簧戏团跑龙套,家里还有滩簧戏团的道具——鼓、钹、幕布。滩簧戏都是乡村故事,通常都是因果报应、道德教化,父亲自然也受影响。
但读小说,父亲是在农中毕业后,这也是读书识字的重要结果,毕竟读小说需要门槛。他读的小说,几乎都是从朋友那儿借回来的,包括被借调到公安帮忙时。我们村虽然号称晦庵嫡裔,耕读传家,当教员的比例不小,但我知道的也只有我的族伯朱文凯喜欢读小说。
文凯伯最初是民办教师,后来转了公办,是父亲最亲密的书友。他经常从学校带回小说,父亲都去借回来读。直到1980年代,父亲才会自己花一点小钱去租小说,更多还是从文凯伯那儿蹭读。我今天喜欢蹭书的“恶习”,大约也是父亲的遗传或身教。当然,作为回馈,父亲打鱼钓到的黄鳝,也经常便宜一点卖给文凯伯。
当年文凯伯和父亲两个老人之间,常分享他们读书的收获,有共同话题。或许,这种乡下难得一遇的知音,是他们愿意共享图书的原因。
文凯伯在小漕小学有位同事,后来当了前黄镇上文化馆图书室管理员,父亲和我托文凯伯的福,在她那儿借过不少书。1980年代我已上大学,我在这个图书室借到的最有名的书,应该是米切尔的《飘》和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至今仍然没有明白,1980年代中后期,前黄街上的图书室,怎么会有这两本书。
二
我开始认字后,也跟父亲一样喜欢读故事。上中学之前,除了在朱家桥小学读到的《木偶匹诺曹》《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类的书,其他的都是父亲借回来的书,父亲读什么,我就读什么。
通常父亲会把他借来读的这些书,放在他的枕头底下,或者母亲梳妆台的抽屉里。而我在认字之后,总能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找到这些书,无论字认不认识,遇到不认识的字便跳过,囫囵吞枣,估个大意,快速浏览。
快速是怕父亲发现,责怪自己不好好读书——读书和读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后来反省,今天自己阅读时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毛病,大概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后来我们父子聊天,父亲说道,他当然知道我偷偷看他拿回家的书,只是没点破。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个规矩的好孩子,学习干活都不用家里人操心。我后来写过一篇《那些年和父亲一起读过的书》,回忆了我们父子共同读过的小说:
我最初跟父亲阅读的那批书,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反映上海知青在东北的故事。知青小说之外,还有反映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与农村地富反坏右斗争的小说,后来有朋友提醒我说这书叫《虹桥战斗史》。另一类小说,是反映江南地区新四军游击队抗日的故事。至今回忆起来,似有些纪实性质。
那个时候还有手抄本,父亲藏得严实,我没能看全,当年若是流传出去,可是麻烦事。有一些我当时也没看懂,只是觉得奇怪,大人们怎么看这书神神秘秘的。
到我上中学,跟父亲一起读的书就多了。印象深的也有两类,一类是现代小说,比如《刑警队长》,我至今尤为书中女主角和刑警队长错过感到遗憾;还有一部叫《魂兮归来》,讲的是五四运动前后大学生的故事,其中还记得那个辅导员叫叶啸。那个年代流行的小说,父亲看过的,我也大致都草草翻过。
另一类是传统的话本小说,《三侠五义》《续小五义》等,都是托父亲的福,以至于跟同龄人谈南侠北侠五鼠闹东京时,常有自得。当然还有《水浒传》,我上小学时就被要求背关于水浒的点评,但小说却是上了初中才读到。
文革之后,人民公社解体,家境渐好,社会上的刊物也越来越多,父亲也借阅了一些江苏出版的刊物,我也跟着翻看了不少。这个时期,父亲和我已经开始互换各自阅读的书籍,父亲不仅从文凯伯那里借书,还从镇上的文化馆借书,我则从学校借书借杂志。
互换图书阅读,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我们父子俩共享的图书,最多的是各种武侠小说,从梁羽生金庸古龙,到还珠楼主等。另一类互换的书,则是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比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以及那个年代流行的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及各种杂志。
不过,从上高中开始,我与父亲的阅读出现明显分野,我有了自己的阅读兴趣,比如《永远的尹雪艳》《克莱默夫妇》《敦厚的诈骗犯》之类,父亲一概不关心,应该也没听说过,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兴趣:武侠小说、战争小说、回忆录。他到北京暂居的时候,我给他找的也是这些书。
三
在农村,读小说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尤其是一个农民,天天为生计奔忙,哪有时间读小说,务农的父亲爱读小说,颇有点不务正业的另类。
我上高中的时候,寒暑假跟农闲重叠时,父亲和我常常各拿一本书,各据一角,各自翻看,祖母总是忍不住嗔怪父亲:“这么用功,难道要像大儿子一样考大学吗?”祖母不知道的是,我常常读的也是小说。
但父亲并没有因为读小说耽误家庭生计,农田里的活他是一把好手,打算盘算账也是一把好手;我记得当年生产队过年前分红,并非队干部的父亲,总是在记账;此外他还自学了打鱼杀猪钓黄鳝摸甲鱼……尤其打鱼,是闻名四邻八村的大师傅。
后来经济管制放松后,父亲不仅卖自家种的水芹菜,夏天还卖冰棍,还去大菜市场批发豆子茭白到前黄镇上卖,甚至还捉蛇拾荒货(即捡垃圾)。这是那个年代一个无所凭恃的农民,所能够闯出的路子。
如果父亲年轻时有更多机会走出去,他所拥有的世界,应该远不止于此吧。可惜生不逢时。
四
父亲自电磁厂破产被借调到前黄公安特派办公室后,一直与武进公安系统的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们成长阶段最缺粮食的时候,也是当年前黄的人武部长张先生帮父亲渡过了难关。
父亲回家务农后,当了大队的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后来因为跟大队书记站一线,成了“保皇派”,又被“靠边站”。
1980年代早期,按照当时的政策,父亲被重新安排到公社一个部门,上班第一天,因为看不惯领导的做派,不肯给领导送烟,摔门就回了家,好多朋友相劝都不回头。这个脾气,我和弟弟都遗传了。
我后来想,父亲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风骨,除了本性,应该也与他对小说的热爱有关。他读过的最有名的小说,无非《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以及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这些小说里,多的是为人和侠义之道,父亲深受影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论《水浒传》的话,也可以用来点评父亲喜欢读的小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废弛,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田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
那些小说,多为弱者的救济梦,正义终究会取得胜利。如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父亲的不畏强权,急公好义,温厚忠良,一如其名“忠善”,除了天性家教,也有侠义小说的耳濡目染。他没有跟我谈过读小说的影响,只是说看着玩玩。但是,就我读小说的经历来观照父亲之读小说,我相信影响是有相似的一面。
父亲成长的时代,物质精神生活都极其匮乏。那个年代的小说,即使写得很不堪——包括价值观,今天的我完全无法接受,无论是武侠小说、战争小说,抑或知青题材,都向我们打开了通向不同世界的窗口,让我们知道不一样的生活的存在。虽然今天看来,许多小说文字粗糙甚至不堪,宣教意味浓郁,但相比同时代的报纸,可谓温和有趣得多了。
我觉得,小说其实是我们父子走出当下世界的一条路,那些书中的故事场景,让我们父子比同地方同阶层的人见识了更多的世面,即使只是纸上江湖,也让我们长了见识。父亲喜欢读小说的习惯,虽然没能改变他的农民身份,但他比其他农民生活得更丰盈,更幸福。
五
2023年10月17日晚,在成都有杏书店,我谈到了自己的自我构建,一如我在“假设的人生”之《假如我上了南京大学》一文中的设问和回答,如果我回到了故乡,我现在大概率会是一个从并不重要的地方岗位上退休、不用为物质生活操心的含饴弄孙的幸福胖老头,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心里仍然有股勃勃不平之气,但我不可能想象我今天的生活,今天我的灵魂的模样,一如我曾自许的,在我前黄中学同届校友中,在精神世界,我可能走得最远。
所以我从不后悔失去幸福平静的晚年。我相信,喜欢读小说的父亲,也有类似的自傲。
父亲喜欢读小说的习惯,更是影响了我。一如我前面提到的,也许是遗传,也许是耳濡目染,他养成了我对阅读的偏爱,后来更是对文科和文科思维的偏爱。
我赶上了时代之变,有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因为随了父亲对阅读小说的喜好,我自上初中开始,就有效地利用起了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从连环画报到各种文学杂志和小说,再到当时报纸上连载的各种小说。
我的中学订有羊城晚报,当年连载了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非常吸引我;同样通过报纸连载,我读到了亨利克·显克维奇的小说《火与剑》;我还和父亲要钱订了武术报,读了上面连载的《火烧红莲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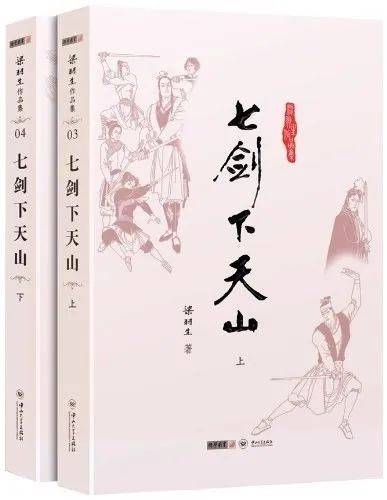
《七剑下天山》
梁羽生 | 著,朗声图书 |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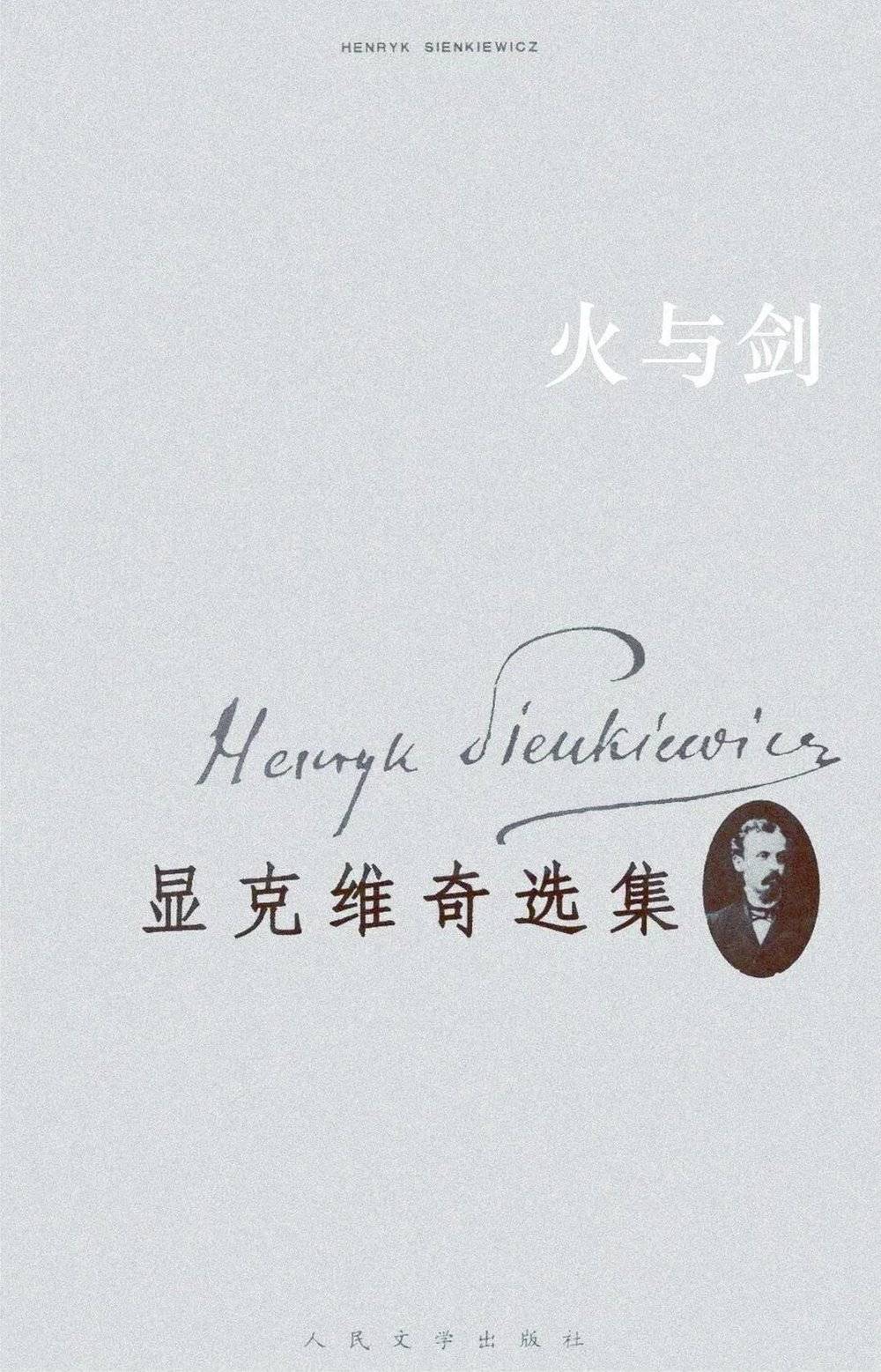
《火与剑》
[波兰] 亨利克·显克维奇 | 著,林洪亮 | 译
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
而我读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在一份连环画报上,至今还喜欢模仿这小说的开头,“尹雪艳总也不老。”我在杂志上读到了《克莱默夫妇》,尽管无法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婚姻观;在杂志上读了日本小说《敦厚的诈骗犯》……
可以说,父亲爱读小说,不只是耳濡目染让我也喜欢读小说,而小说里那些陌生的遥远的故事,激励了我对远方的想象。
回望我的人生,小说于我,不只是一种文学作品,也是不同的新生活新世界的图景,更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一种社会生活史,一种个体心理史和社会心理史,也是政治史。
在那些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中,我也能够观照到自己可能的命运,同时借鉴他们对抗命运的努力,寻找自己抗拒命运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无法成为小说评论家和小说作家的根本原因。
父亲对小说的热爱,也是我走向远方的起点,小说首先让我从低首专注于眼前这块土地,到逐渐抬起身子,能够用眼睛借着书里主人公们的生活,打量那些纸上的遥远的陌生世界,并把它们当作一种真实的生活去追求。
尤其是1984年程乃珊《蓝屋》对我的影响,让我从此相信个人奋斗,自我奋斗,形塑了我的一生。
在几乎无书可读的时代,我的那些今天看来大多不堪的小说阅读,其实是我最早主动踮起脚,看见窗外的垫脚石;也是我在农田里,直起腰,看见蓝色的帆影的开始……
这真是一种命运的拣选,天注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朱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