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独揽大权,历来评价不一,本书主张从张居正施政的具体内容出发,各自分析其利弊得失,追溯其源流因果,从全局角度进行综合评价,从全书的论述来看,作者对张居正“柄政”时期的作为是基本肯定的。此外,本书对张居正与宦官冯保之间的关系、个人是否贪腐等品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坚持不隐恶、不溢美的原则。
一、我所了解的韦庆远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的作者韦庆远先生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系原系1952年成立的档案专业,当时韦先生从中国历史教研室调入此处,现为档案学院)的教授,当时档案系里除了韦先生之外,还有刘文源、吴奇衍等好几位老师,都是研究明清史的,可见那时档案系中还有比较强的历史研究传统,也可见人大清史研究阵容的强大。
大约在1970年代初,已被解散的人大教师陆续从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回京,韦先生一家五口就搬到简称“铁一号”的张自忠路3号(因原来的门牌号是铁狮子胡同1号)人大宿舍,开始时住在大门口西侧最靠南的一间平房里。
那段时间正是我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一,他的长子比我高一年级,次子与我同级,我们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晚年韦先生写的《师凿书室记事》里说,这个书房的名字与他在江西干校时打石头的经历和感悟有关,我也曾在他说的那个大石坑“水晶宫”里做过短暂的小工,那时年纪小,如今回想起来,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感触。
从那时起直到大学本科毕业,除了在各家和院子里遇到,叫声“叔叔阿姨”之外,完全与历史无关,到了我硕士阶段攻读明清史,以及此后一直在明清史这个领域里耕耘,才开始读到他们的论文和著作,于是除了“叔叔”的称呼之外,又增加了“老师”这个称呼。
从此以后,我与这些父辈的来往反而比他们的子女多了,因为那些老同学几乎全都学理科,只有我一人是学历史,所以在这个院子范围内的晚辈中,能和他们偶尔探讨学问的反而是我,这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1985年,我征得顾诚师同意,确定以明代吏员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前人中除了日本学者有个别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之外,只有台湾缪全吉先生有《明代胥吏》一书。
偶然机会聊起此事,韦先生说他正好有此书,我大喜过望,因为当时想看到台湾和海外的书很不容易,图书馆里往往也没有,于是就去他家中借来复印。那时他家已搬至与我家同楼,在不同的单元二层,借还书的时候也趁机讨教。
韦先生对这个选题大加鼓励,提醒我这方面的材料过于分散,除了《大诰》三编这类官书外,不易查找。哪里想到30多年过去,大量州县档案被整理出版,学者们也搜集了很多与收税和土地确权有关的地方民间文献,竟让我不敢答应一些出版社希望再版我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一书的请求,因为现在可供利用的材料真是太多了!
1987年我硕士毕业后,随即参加了当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国际明史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为《明代吏典制度简说》,即硕士论文中的一部分。我所在的小组权威学者云集,最引人注目的是《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由于该书讨论的是“后张居正时代”,《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并未有针对性地与其直接对话,但其时韦先生已开始为写作本书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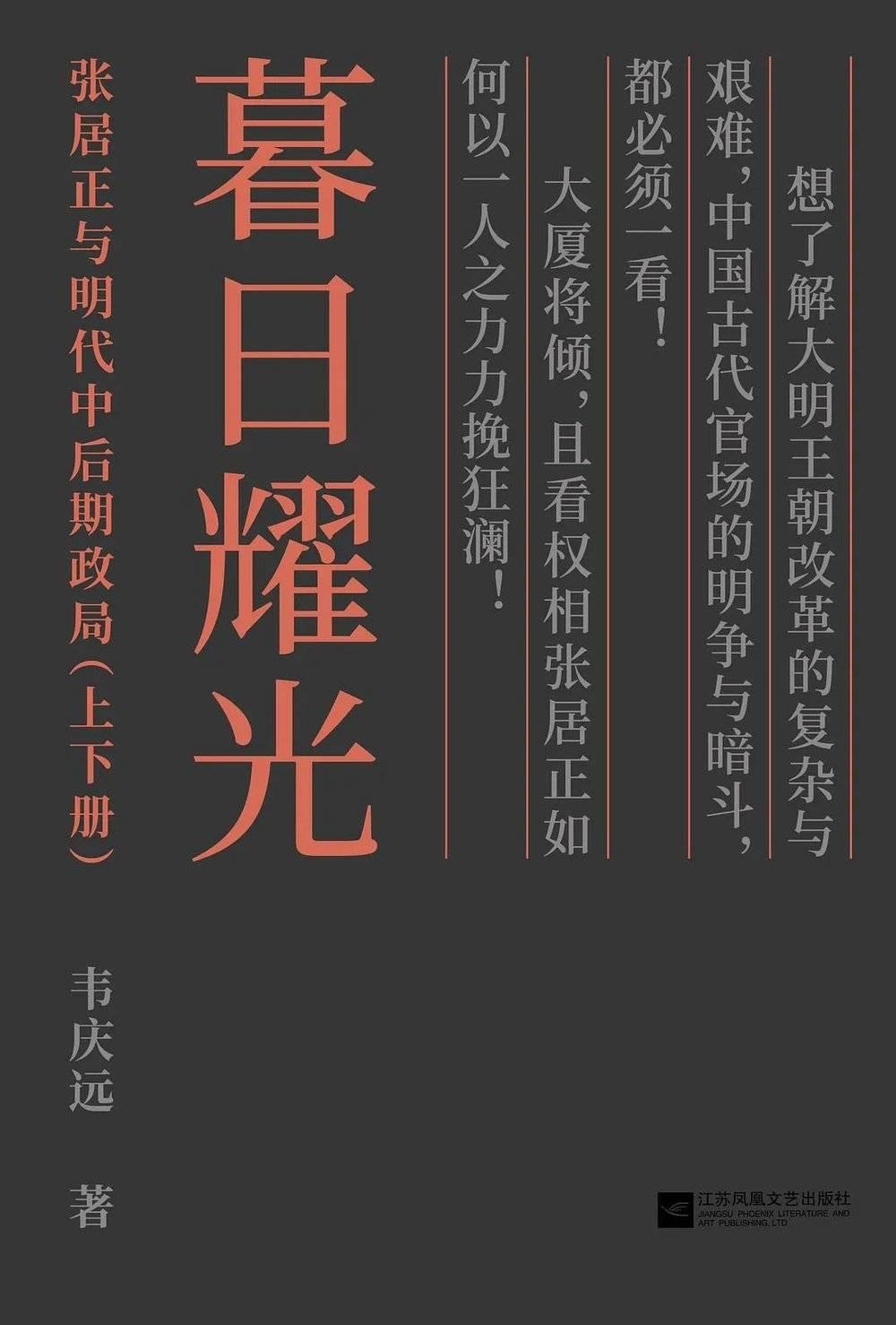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韦庆远|著 汉唐阳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我记得小组会上李龙潜先生发言,浓重的广东口音使多数与会者难以分辨其意,韦庆远先生作为广东同乡,则替他逐句翻译。韦先生还略长李先生数岁,但仍主动而自然地承担起这项“服务”工作,其平易谦和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韦先生是个风趣而随和的人,开怀大笑时其声远至。他对晚辈也平等待之,并多有提携。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向他讨教期间,他即赠我1984年出版的《档房论史文编》,题签为:“世瑜同志;庆远赠,八六年十一月于人大。”该书收录了他关于明清档案以及利用档案研究皇商和清代矿业的文章,我认为他是改革开放前后最早利用内务府档案、朱批奏折、六科题本和史书等材料的学者之一。
我自1990年搬到北师大居住后,每周回家探望父母时偶遇他,他会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或让我去他家一趟,要送我新出版的书,其《明清史辨析》上的题签是:“世瑜同志存正。庆远赠,1990.2。”
他回到广州之后,我只见过他一两次,《明清史续析》就是那时送我的,上面的题签是:“世瑜同志雅正。韦庆远持赠,丁亥元宵前夕。”这一年已是2007年,我也已年近半百。韦先生的口吻也越来越客气,大概是不再把我当小孩子了吧。
以上所述,可见韦先生执着、严谨、认真而又平易、开朗、幽默性格之一斑,或可视为其研究领域、作品风格之多样的一个注脚。
二、关于作者的明清史研究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是一部典型的明代政治史著作,与早年韦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亦有关联。
最早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是韦先生于1961年出版的《明代黄册制度》。黄册是明代的一种以户籍为基础的赋役册,早在1930、1940年代,梁方仲先生便已开始对包括黄册制度在内的明代赋役制度进行梳理,至此则始有专书出版,随后《历史研究》分别有王思治和岩见宏撰写的书评。
根据梁方仲先生1967年5月为人民大学所写的关于韦庆远先生的外调材料,韦先生此书出版前虽必定拜读过梁先生的相关文章,但却是在书写成后才去拜见梁先生并与之相识的。
二人相识之后,梁先生以韦先生为明史学者,故介绍他认识吴晗。事实上,韦先生此后的许多研究集中于清史,直至其学术生涯后期才复归明史。但是,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明代黄册制度》中,他还涉及军户、匠户制度、里甲制度、鱼鳞图册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上的问题,正是张居正改革想解决的;不能正确认识明初的这些制度,就没法正确理解张居正及其政局。
由于梁方仲先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一条鞭法》及《释一条鞭法》,韦先生一定理解梁先生的想法,所以便可以在青年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与本书之间找到一条逻辑线索。
与此类似的是,韦先生本对社会经济史用力甚勤,至1990年代后则较多转向政治史。《明清史辨析》中收有关于清代“皇当”和“生息银两”的两组文章,是韦先生利用档案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前者,也是对清代内务府事务的开创性研究。他认为,康、雍、乾三朝对皇家当铺的管理和经营都非常重视,虽然从中获取利银有限,但设置皇当的目的更在于及时获取金融波动信息,以便适时调节银钱比价和流通,控制金融秩序(类似“央行”的作用),此外,还有利于直接安排宫廷财政,也有助于体现皇帝的恩威。这也可以被看成是“赐本求利”的“生息银两”制度的一种方式,其关键在于背后有最权威的皇家“作保”的本金作为支撑。
这揭示了清代皇当不仅为了营利,而且是具有政治功能的机构,同时也揭示了皇当所属的内务府不仅是皇家的私人部门,同时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国家事务机构。
“生息银两”问题与典当业或前述皇当问题直接相关,应该是韦先生阅读档案时同时注意到的问题,当然“生息银两”不仅用于投资开当。这部分用于钱生钱的银两均来自内帑,由官府负责营利生息,这是最重要的特征。
由内帑拨付给不同官府人员,投资当铺等生意,赚取的利润在康熙时主要用于鼓励承运铜斤和食盐专卖,雍正时主要用作出差补贴,或用作婚丧或子弟教育等用费,但不得动用本金,相当于为不同的公职人员建立了一个福利基金。
这样一种福利基金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网络,而且具备监管机制。到乾隆时延续前朝政策,但在运作中弊端日益严重。韦先生还专门利用盛京内务府档案对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生息银两”的推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可以看到这里的运作更具组织性,但运作方式和兴衰过程与他地大致无异。
韦先生研究的“皇当”和“生息银两”问题的官僚资本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他也指出这种做法与明清时期的商业化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学者们已经发现,在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中,各种结社集资生息的组织普遍产生,如清明会捐资或集资生息用于祭祀祖先或济困,宾兴会捐资或集资生息用于赞助举子应试,还有宗族、神明会等等都用这种作为慈善、公益以及商业运作的投资形式。
但是,由皇帝亲自安排、各级官员领本经营的国家资本运作,在明朝并未出现,而是清朝——特别是满洲人的创举。已有一些经济史学者注意到清朝的皇帝比明朝的皇帝更富有商业性,原因是什么,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究,但我相信这必然引向对社会的探索,因为皇帝的算计必定是从社会上学来的,那些为皇帝办差的官员、将领、皇商都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档房论史文编》中曾收入韦先生的《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一文,其发表年代在1981年,早于他关于“皇当”和“生息银两”的系列论文,且未收于同一书中,但我认为这两个话题恰有逻辑联系。
本文简略提到山西介休范氏在明初就已在蒙古地区贸易,后来也长期来往于蒙古和辽东,七世之后便与关外的满洲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成为内务府皇商,顺治时被抬入内务府旗籍,从康熙到乾隆,凭借铜和盐的经营,其势力达到鼎盛。
虽然本文的论述重点在清代商业资本的局限性,但也显示了皇商在清朝的影响力。以明朝与清朝相比,虽然自明中叶以降社会上便有明显的商业化趋势,也体现在地方和中央的一系列财政政策改革上,但明朝皇帝并没有体现出某些清朝皇帝那样的商人特性,身边也没有那么多皇商和官商,清朝皇帝的这种特点也许从他们在关外参与马市贸易时就已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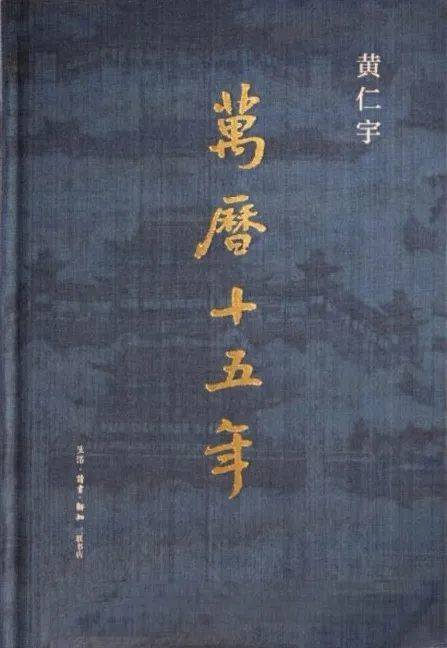
《万历十五年》 [美]黄仁宇|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1月
三、在张居正的时代认识张居正
正如作者在本书绪论中着重指出的那样,本书与此前相关论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将隆庆、万历时期的诸多改革举措视为一个整体,统称为“隆万大改革”。
本书将隆庆朝的六年视为大改革的始创期和奠基期,万历初的十年则为大改革的延续和发展期。对于隆庆朝的内阁纷争,韦先生并不认为那仅仅是相互争权逐利的“混斗”,而是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的立场冲突。
而对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独揽大权,历来评价不一,本书则主张从张居正施政的具体内容出发,各自分析其利弊得失,追溯其源流因果,从全局角度进行综合评价,从全书的论述来看,作者对张居正“柄政”时期的作为是基本肯定的。
此外,本书对张居正与宦官冯保之间的关系、个人是否贪腐等品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坚持不隐恶、不溢美的原则。可以说,从以上诸方面来看,本书是对此前张居正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的系统回应。
在绪论中,韦先生写道:“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都无法一生游离于所处的人际关系连锁之外。愈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其身心上反映出来的时代气息必愈浓重,其对时代的正负面作用必愈巨大和深远。”
在今天来看,历史人物无论大小,身上的时代气息都是同样的,不同的只是史料中关于大人物的记录更多而已。不过,一个人与其周围的人际关系网的纠缠,大小人物之间却有天壤之别。
张居正自入朝到拜相,就与皇帝脱不了干系,这是升斗小民可望不可即的。在本书中,作者对张居正经历的几位皇帝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将嘉靖帝称为“一个擅权执拗的皇帝”,把隆庆帝称为“一个心理变态、庸碌猥琐的皇帝”,而对张居正死时还是青少年的万历皇帝,用了“小时了了”这样的评语,暗含着“大未必佳”这样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三位皇帝统治了中国100年,略短于清朝康、雍、乾三朝的134年,祖孙三代连续统治时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很长的了,在帝制晚期中国,也是国力最强盛的两个时期,这样的不协调不是很值得思考吗?
我在年轻时也写过一本关于明朝皇帝的小书,对明朝的大多数皇帝同样评价不高,到后来研究社会史,就几乎不再关注皇帝,好像时代发生的变化都与皇帝无关,甚至可以将上述问题的答案归结为皇帝的无能,反而有可能为能臣发挥作用提供空间。
但是,如果嘉靖皇帝只是“擅权执拗”,能臣的空间就不可能大了。一方面,张居正就是在这个时期走上政治舞台的,没有早早地泯然众人;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以“倭乱”所显示的全球性贸易的影响并没有在中国沿海中断,这都说明存在着某种内在机制,只要不被突发事件打断,就能够发挥作用。中国皇帝的在位期对这种延续性是很重要的,当然也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少学者都对明代的阁权做过研究,多认为嘉、隆、万三朝是阁权最盛的时期;也有不少社会史研究指出,这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若说这二者间无关、甚至是冲突的,似乎不太好理解。
本书提到嘉靖帝执着于“议礼”和“崇道”,就前者而言,明史学者较关注嘉靖皇帝对反对派臣僚的打击,而社会史学者则注意到他提拔的拥趸多是起自寒微的东南沿海人士,比如温州人张璁、广东人桂萼、霍韬、方献夫,后起的徐阶虽曾反对议礼,但他是松江人,生于浙南处州的宣平,均受白沙、阳明之学的影响,因此观念比较务实,对社会基层的变革比较敏感。
就后者而论,学者们也注意到嘉靖皇帝特别注重改变礼制(如天地分祀等),但社会史研究同时注意到此时在基层社会(包括卫所)重申里社的重建,并配合乡约的建设,以因应明初里甲祖制的衰颓。这并不只是可有可无的礼仪问题,而是上下贯通的社会秩序问题。
到嘉靖后期,虽然阁臣中多有以青词受宠者,但夏言、高拱等也属于务实派,导致了整个嘉靖朝基本上处于因应时代变动的政策调整过程中。若非如此,我们就很难理解自隆庆改元伊始,就立刻出现“隆庆和议”和“隆庆开海”这样的重大转折,否则,我们要么就承认“庸碌猥琐”的隆庆皇帝非常重要,要么就会渲染高拱、张居正这样的英雄创造历史,而忽略了朝野之中已经普遍存在的对时代变革的共识。
韦先生在书中引用了一段材料,颇能说明张居正的“人际关系连锁”,也能间接说明某种时代共识:“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司、关司、屯马司、按察司还朝,即携一酒一榼,强投外教,密询利害扼塞。”“翰编”即翰林院编修,盐运使司、税课司、屯田、马政机构多在边地,这些机构的官员对实际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张居正初入朝为官时,便主动与交朋友,偷偷打听相关动态。他主政的时期,首先就重用一批了解实务的中央和地方官员,本书在论及张居正整饬吏治等各方面改革时也提到了诸多人事调整,比如户部的王国光、兵部的谭纶等。
需要注意的是,王国光是山西晋城人,祖籍长子,家族有泽潞商人的传统,后来他又曾任苏州吴江知县,对江南商业经济也有了解,主户部时编《万历会计录》,是隆万时期国家财政转型的设计师。
谭纶是抗倭名将,先在浙东、福建转战,对私人海上贸易的情况非常了解,后又调任西南、陕西,并总督蓟辽,所以熟悉边务。
对“隆庆和议”的达成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崇古是晋南蒲州人,家族也是晋商,经营两淮盐业,由于晋商与长城内外的走私贸易关系密切,所以王崇古应该最清楚两边的汉人与蒙古人需要什么,故而成为力主达成和议的重要角色。后来被张居正引入内阁的张四维也是蒲州人,其父张允龄是长芦盐商,夫人即王崇古的二姐。
另一位受到张居正重用的两广总督殷正茂,在隆万之际处理两广地区的沿海和山区的社会动荡。殷正茂是徽州歙县人,即徽商的乡人,先后在沿海抗倭和在长城沿线整饬边防的汪道昆和戚继光,前者也是歙县人,后者祖籍安徽凤阳,与著名的“倭寇”首领王直都是同乡。
虽然不能说他们都与徽商有多直接的关系,但肯定不会对当时的商业化大潮与边陲地区的开发和动荡的关系完全无感,可以说都是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的产儿。这些人或早或晚都曾在张居正主政时期处理边事,由于相似的背景,会具有较多的共识,故而成为改革时期的重要实践者。
本书在叙述了张居正用人的得失之后,也重点讨论了学术界始终重视的土地清丈和赋役改革。韦先生提到了前面所说的支持嘉靖帝“议礼”的桂萼的主张,也论及后为张居正重用治水的潘季驯在广东实施的条编之法。
我曾在另文中提及福建漳州龙溪人陈烨任大别山区的河南光州知州时,为在这个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自封投柜,称自己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后裔(传陈元光是唐代光州固始人),在当地建立了祭祀陈元光的广济王庙,以拉近与当地士绅豪强的关系,从此陈元光才普遍为其故里之人所知。
这个例子说明,在当时对一条鞭改革褒贬不一的声音中,也有不少基层官员还是支持张居正的。陈烨来自福建沿海地区,著名的“隆庆开海”造就了漳州月港的繁荣,因此那里也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地区,故更理解赋役改革对这类地区的意义。
在讨论到张居正与同僚、下属沟通治国方略的时候,韦先生也多次引用了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由于本书以张居正为主角,而收入张居正文集中的书信基本上是张居正所写的,只是间接透露出对方来信的一些信息,因此更多地突出了张居正在各项决策中的重要性和主导性。
但这恰恰使我想到,身居庙堂之上的张居正是如何了解全国各地复杂多样的情况,并适时地采取相应的对策呢?我相信,这些与他有较多共识的同僚和下属的来信,应该是他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甚至有些对策就是那些地方官员提出来的。
赋役改革的具体做法,本来就是明代中叶不同地方官员在基层实践的结果,最终被张居正采纳并推行于全国的,其他许多举措也完全有可能如此,我们对“江陵柄政”的时代性及其“人际关系连锁”,更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加以认识。
让我以两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张居正及其时代,作为这篇导读的结尾。
第一个例子是在“隆庆和议”之后,俺答汗西行,与西藏的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使蒙古信奉藏传佛教。张居正对此非常敏感,通过甘肃巡抚向达赖喇嘛转交他的信件,其中说:“渠西行劳苦,既得见佛,宜遵守其训,学好戒杀,竭忠尽力,为朝廷谨守疆场。……所言番人追贡事,此种僧人久失朝贡,本当绝之,兹因渠之请乞,特为允许,但只可照西番例,从陕西入贡。”(《张太岳集》卷30)
一方面请达赖喇嘛劝说俺答汗尽快回到原来的游牧地,另一方面也适当地恢复了与西藏地区的茶马贸易。并希望“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万世矣”(《张太岳集》卷31),体现了张居正营造中原王朝与蒙古、青藏高原各族和谐一体的努力,正像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评价的那样,清朝也因此受惠。
第二个例子是在万历二年十二月,神宗小皇帝连续数日御文华殿讲读。张居正为了“天下幅员广阔,山川地理形胜,皇上一举目可以坐照”,从而用人得当,故以成祖、仁宗故事,“造为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其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上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明神宗实录》卷32)
这段材料在本书中也有提及,但主要是说明张居正的用人,没有指出张居正希望皇帝从小就应该通过地图了解天下形势。实际上从嘉靖朝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制图时代”,前面多次提到的桂萼就曾一次给皇帝呈上17幅地图,而且都有说明。
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九边图》《筹海图编》等边防图,还有《蒙古山水地图》《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略图》等西北人文地图,这应该是16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开启在中国的反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赵世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