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基金小镇”,你能想到什么?我觉得你可能什么都想不到,因为基金小镇的面孔可能从来没有清晰过。
我是从今年开始意识到“基金小镇”存在的复杂性。8月31日,投中信息在天府新区的天府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首届天府创新资本论坛,其中一个分会场“天府(四川)母基金发展大会”由天府国际基金小镇承办,共邀请了接近30位来自四川省、市、区级政府母基金代表参会。
会议开始前,天府国际基金小镇总经理谭啸带着我和同事们在会场转悠,对应着座位桌牌介绍参会嘉宾的基本情况,密集输出到了大家都明显感觉到饿,而他明显还有很多话想说,因为就在我们准备领午餐券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句长叹:“很多人以为,我们只是个地产项目。”
包括上半年温州设立的大罗山基金村,“过去投资人都扎堆在大城市,现在要让他们搬到村里来”——前几年的投资人们如果听到这句话,多半会语气笃定地告诉身边的朋友,“面子工程而已,你别当真”。
但今年11月,温州大罗山基金村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却表示,基金村成立半年内已经有100多家投资机构完成入驻,总募资规模和投资规模超过了150亿元,其中还包括温州首只规模为5亿美元的QFLP基金,还有一只规模为21亿美元的QFLP基金正在推进当中。
恒择资本执行总裁刘少龙认为这是一项创举:“大罗山基金村,名字很特别……与国内其他城市往往以‘基金小镇’命名不同,它引入了中国人的村落概念。”维度资本董事长厉汉华补充说:“‘村’体现了各种金融要素的汇聚,‘村长’带来了业内权威流量,‘村民’带来了基金产品或管理人。”维度资本是作为温州本土创投代表,已经有三只基金落户到了基金村。大罗山也借此喊出口号,他们要举“全村之力”打造“浙江创投第三极”。
成都万华投资集团董事、天府国际基金小镇董事长姜涛在投中那场闭门会上,也详细介绍了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的发展成就:目前,小镇已经入驻基金机构533家,管理社会资金的总规模超过5180亿元。
一边是面貌模糊到业内人也认为基金小镇只是个“地产项目”,一边是多个维度的数字似乎都在宣告基金小镇存在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用大几千字的篇幅来回答这么几个问题:基金小镇此前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后还准备做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投资市场的参与者们能从基金小镇获得什么?

(过街天桥上的基金小镇标识,由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题写)
模糊的小镇
其实用“地产项目”来定义基金小镇,很难称得上是一种误解。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由成都本土知名地产商万华集团开发,核心区域超过200亩,被同样由万华开发的高端社区“麓山国际”收纳其中。一份发布于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园区简介指出,开发者们希望建设标准能够比肩“格林威治”。
格林威治是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紧靠纽约州的一个小镇,19世纪末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物质文明膨胀,小镇作为纽约富裕阶层的假日后花园被大量开发,绵延32英里的长岛海峡海岸线上散布着私人海滩、临海庄园和游艇港口。等到192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和米尔班克斯家族的豪宅开工的时候,格林威治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具代表性的富裕社区,带动其所在的康涅狄格州成为全美富人最集中的地区,收入水平排在全州前1%的家庭是排名后99%家庭的近74倍。
1990年代,金融从业者们开始挖掘格林威治的潜力。他们起初置业于此的目的也是度假,但随着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带动资本繁荣,他们忽然意识到格林威治的独特优势:这里距离曼哈顿区只有45分钟的车程,阡陌交通、富贵相闻,却享受着康州极低的税收政策——格林威治的金融业自此开始指数级增长,到千禧年的时候落地基金数量已经接近4000只,康州的基金管理规模在全美仅次于纽约和加州。
GAMCO Investors总裁Marc Gabelli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格林威治现有拥有的集群优势,是其他地方很难竞争的……人们可以交流思想,形成市场上真正稀缺的竞争力,它的存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知名对冲基金AQR的联合创始人David Kabiller赞叹格林威治“是个伟大的社区”,因为这里“经济充满活力,能够为专业人士提供良好的服务,也能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一流的学校”。
对于渴望经济发展但受困于地缘条件的后发地区,这种特质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成立的2016年,全国建成运行的基金小镇不超过30个,其中超过70%分布在浙江、广东、江苏这三个省份。到了2022年小镇数量暴涨超过了120个,沿海三省的占比则被压缩到了50%以下,而其中绝大部分小镇的形态都是“格林威治”的功能性魔改:
一座大大的园区,通过绑定足够多的优惠政策或倾斜资源,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投资机构设点,形成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金融资源聚居地,方便当地企业和资本完成更高效、高频的对接。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基金小镇”真的能提供足够的配套设施“激活资本市场潜力”,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2016年7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通过联合发文的形式,在提出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培育1000个左右以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为重点产业的特色小镇目标外,还为“到底什么样的体量可以被称为小镇”划定了数条硬性指标,即包括基金小镇在内的特色小镇,建设用地面积一般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聚集人口1万至3万人。
于是伴随着后发地区力争上游的壮志,大量地产商成为了基金小镇建设浪潮中的绝对主演。他们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成为主要的投资方与建设方。仅在天府国际基金小镇正式投入运营一年后,也就是2017年,有机构统计了各大地产商投入到基金小镇的“外宣投资规模”,发现累计起来已经超过了千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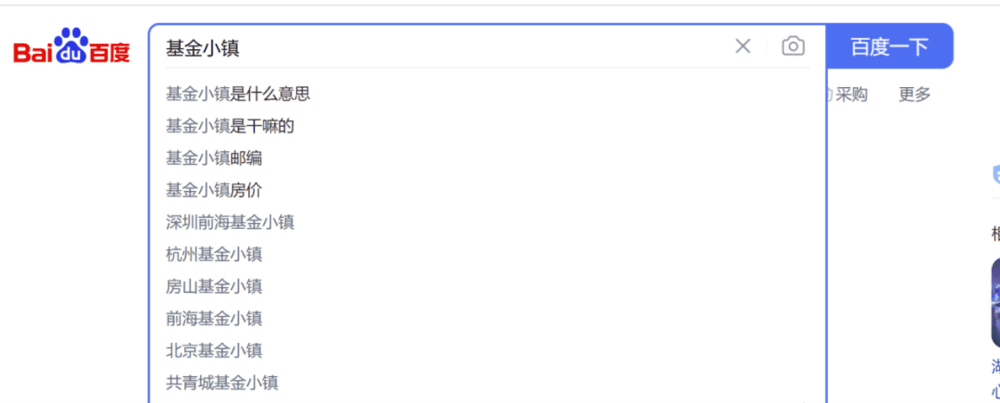
(在百度搜索“基金小镇”,排名最高前的联想词条是“什么意思”“干嘛的”)
当然,万华集团或多或少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一方面,万华集团对一级市场的参与兴趣在众多川企中几乎是独一档的存在——投中网此前在文章《成都LP的隐秘江湖》中考证,万华集团旗下的万创华汇是目前成都市场区域内仅有的活跃地产系机构,据今年一季度披露的信息显示,目前旗下拥有三只母基金和一只直投基金,管理规模达10亿元——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想办法妥善处理“麓镇”的运营问题。
麓山地块是天府新区成立之后最具代表性的高端地产项目,首批楼盘以欧式别墅为主,是成都市民们口头禅里“南富西贵”里的“新贵”,而麓镇则是为麓山地块精心设计的商业配套,规划面积达14万平方米。
但一直到2016年,在麓山国际社区入住率堪堪达到30%的情况下,麓镇的商业载体使用率始终没有突破过50%,成为了一个标准的“负资产”。一度发展到有传闻称,就连股东团队内部也对“麓镇”的前景不看好,如果不是以罗立平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与股东方争辩到脸红脖子粗,甚至可能都无法上马。
罗立平在后来的很多采访里,毫不避讳地谈到了当时的窘迫。他认为麓镇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引进小学”,无法“关联很多家庭”,再加上项目早期引入了很多不成熟的商家,导致整个商业体吸引力打了折扣。于是他决定将社区商业调整为基金小镇,认为这次改变既符合万华集团的“战略长远考虑”,又能妥善解决入驻率的问题。

(麓镇现在的样子,GP们的办公室藏在这些咖啡店后面)
模糊的居民
但即使有这些“特殊情况”,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仍然是个“基金小镇”。这个外壳在带来战略上远期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现实的困境:小镇是地产圈的新鲜产物,也是资本市场的新鲜产物。这就意味着没人想明白过基金小镇在完成“基金公司注册落地”之后还能干什么,甚至没人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来运营基金小镇。
在Boss直聘上通过“基金小镇”能直接搜索到的职位只有3个,2个来自福建财经新媒体团队“观澜财经”——根据职位简介,观澜财经受到当地政府委托运营管理厦门第一个市级基金小镇“古地石基金小镇”,运营目标是打造“两岸金融中心核心片区的基金会客厅”,因此分别要求求职者具备园区招商、企业服务、活动执行、媒体宣传四项技能,并且职位tag里要求“金融相关学历”——另1个职位来自连锁健身品牌“威思达健身”,他们正在寻找“深圳南山基金小镇门店”的健身房销售岗。
上海鹏欣房地产在前程无忧上发布了南通基金小镇“高级招商经理/招商经理”的职位,要求应聘者熟悉金融机构产业招商、孵化器(含众创空间)等产业功能布局、招商服务及发展模式,有不低于1项基金园区整体招商成功案例,因为这份工作需要参与到“项目可行性研究”当中,以帮助小镇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
有位匿名的知乎网友在2019年5月陷入了一场职业焦虑,她想知道“进入基金小镇,做投资类、基金运营类工作有前途吗”,迄今为止共收集到了4个答案。“幻想咸鱼”认为,如果职位没有更多的说明,那么基金小镇的工作本身更多应该是产业地产性质,并且带有孵化的特点。
一位个性签名栏里写着“清华博士资深投资总监-职场投资节节高”的网友对题主的想法不以为然:“基金小镇只是把基金公司集中到一个园区里而已,与基金形式无关,没什么特殊。是否(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帮助,还是看你进的公司和你个人能力得到的提升。”
在拉勾上,直接与“基金小镇”相关的工作岗位干脆没有,系统怀疑我输入了错别字提示我是否寻找的是江苏省徐州市的桌游吧“夜色小镇”。
金融和地产、策划与销售,这些职业技能混搭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基金小镇们被寄予厚望又无迹可寻的缩影。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月刊杂志《决策》,曾经在2017年3月刊通过一篇题为《浙江基金小镇崛起之道》的文章关注过这种两难困境。
作者在开头旗帜鲜明地指出“基金小镇”存在的必要性在于“零敲碎打的扶持不如一次性把扶持政策给到位,最大程度发挥政策效应”,也同时强调“基金小镇”的建设并不能直接照搬“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后者面向成本敏感型项目,前者则更偏向资源敏感型——文章所调研的浙江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距离上海火车一小时,建设规划由985高校浙江大学来完成。

(万创控股的办公室外景,这里在周末会变成创意市集)
而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似乎在不遗余力地放大“成都”在主流舆论中,稍显刻板但也最有辨识度的标签——“悠闲生活”。
舜雨婷是一名兼职集市摊主,经营后备箱咖啡。一个月之前她在小红书在刷到了基金小镇木莲街市集的种草,决定把摊位搬到过来试试。几周经营下来,她深刻感受到了运营方对于市集的重视:“这里的审核很严,他们希望你最好能长期经营在这里。”运营方向她介绍,如果能长期经营并且品类合适,摊主们将获得“廉价租赁小镇实体店铺”的机会,目前小镇中有一家网红汉堡店就转化于此项政策。
此外运营方还会充分采纳业主/住户们的意见,对市集的业态进行强制干预,以至于有些“摊主”看上去已经成为了整个街区的全职员工。有位经营“攀枝花有机农产品”的摊主就是上述经营思路的当事方之一,她曾经消失过一个月,引发了住户们集体表达的抗议。
运营方们设置的摊位费门槛是100元,要求每位摊主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经营到晚上9点,并且会根据商品品类提前设置好位置——“攀枝花有机农产品”现在出现在整个市集的中间位置,货物一字排开摆满了四张桌子,创造过“最强单日收入传说”,摊主们传闻她在5月的某日单日营收超过4万元。
舜雨婷由此判断“这里的人真的很有钱”,还有一个旁证是顾客们的消费选择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很少有人点“美式”,没有人点过“加浓美式”,看上去“劲儿不够大”又有“热量负担”的黄油啤酒、黄油咖啡成为了营收担当。
游艺对此也有同感。她的摊位售卖自己设计的童装,来到基金小镇木莲街市集之前,分别在东郊记忆、玉林路芳草街等更靠近市中心的市集出摊,无一例外生意惨淡。
“其他地方(的市集)都是为了让年轻人玩得更开心,而这里是一家老小周末生活的一部分,很符合我的用户画像。”游艺尝试分析自己定点的原因,“刚才有位大叔就来看了很久,他说他的孩子正在旁边上课……这里除了远,一切都很好。”

(曾经被麓镇视为痛点的“小学缺失”,现在似乎由教培机构补全)
不过这个策略的效果待考,因为摊主们几乎对“基金小镇”毫无体会。他们在自己的微信群里管这里叫“麓镇”,工作日的时候基本不会出现在这里。之所以周末愿意到这里凑热闹,很大部分原因来自“麓客社创太有名了”。
“麓客社创”是由罗立平在2014年发起的社区服务机构,与“麓镇”被改造为“基金小镇”的思路相同,“麓客社创”的成立旨在通过孵化兴趣社群、策划社区活动,维持住麓山国际片区的活跃度。
2022年,麓湖公园社区被评选为成都市国际化社区建设示范点位,天府新区践行新发展理念、建设公园城市先行区的首个典范社区,兴趣社群总数超过了100个。一篇拿到了罗立平采访授权的新闻报道曾经借用“麓客社创获奖”的契机剖析了麓山国际的居民成分:
在1.5万常住人口里,有70%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企业主、企业高管78%,律师、文化艺人等自由职业者占10%,其中博士学历占10%。没有提及金融业或投资人的存在。
舜雨婷在我的提醒下想到了大马路上那块鲜明的招牌,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记得在摆摊过程中遇到过“充满商务气息的人”。
最有“创投色彩”的记忆是她曾经遇到过一位自称在麓山国际开工作室的网约车司机,“小伙子说他想通过开车认识一些麓山国际的业主”,把生意“发展到有钱人的社交圈子里”。
游艺更是对“投资”的事情一无所知,她印象里最常出现的称谓是“婆婆”“姥姥”“爷爷”“家公”。我花了几分钟把我知道的数据告诉了她,她瞪大了双眼:“你说的这些真有点吓到我了。”
模糊的未来
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曾经对格林威治发起过强有力的挑战。有媒体统计,在棕榈滩大力展现对于风投行业友好姿态的2015年到2017年,注册在康涅狄格州的新设基金数量从73只锐减到了29只。
时尚杂志《Dujour》在当年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棕榈滩对于基金经纪人们的吸引力,就像粗玉米粉(一种佛罗里达州的特色小吃)那样简单直接——这里税收更低,而且还有美国东北部无法比拟的气候。”
但棕榈滩的成功也更多局限在数学意义上,格林威治的地位仍然安全。一家专门垂直于金融业的猎头公司坦诚地表示,“虽然他们的客户都有搬到迈阿密或者棕榈泉的想法,可很少人有选择立即执行这个计划”,因为“那里找不到运营一只基金所需要的人才,没有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太多的好学校可以选择。”
格林威治也很快拿出了应对措施。2016年,康涅狄格州为行政区内规模最大的两只基金公司AQR以及桥水分别给予了高达3500万美元和2200万美元的税收补贴。
更有证据表明,政策红利并不是“格林威治”的内核。例如2016年通用电气就宣布将把总部从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迁至波士顿。波士顿所在的马塞诸塞州,在美国创业者圈子里诨号“Taxachussetts”,通过把“Tax”这个单词融入到名称里用来形容该州税务沉重。
通用电气对此的说明是,“我司在研发方面支出巨大”,而波士顿拥有55所优秀的高等院校,能够提供“多元化且技术精湛的人才储备”。
小镇开发者们显然无法等来这样的大江大河,他们需要再造一个“小镇”。

(建设中的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二期,地产媒体称这里的建设是为了“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提供功能配套”)
从最新的新闻动态来看,“小镇再造”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实质性阶段:
2023年5月18日,中建八局官宣了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二期)2号楼主体结构正式封顶的消息。中国建筑集团在通稿中介绍,中建八局承建的二期工程包含3栋超高层塔楼以及相应的商业裙楼,最高建筑高度约179.6米,项目建成后将主要承担办公及会议中心功能,同时也将为整个基金小镇“基金+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与平台,打造集基金产业聚集、项目孵化加速、高端会议配套、人才商务服务于一体的一流新金融产业园区。
类似“基金产业聚集、项目孵化加速、高端会议配套、人才商务服务”的表述在2023年7月的另一篇报道里再次出现,每日经济新闻介绍了“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小镇运营方将这组关键词组合成了一个“技能包”,用类似于插件的形式与需求方共同建立“分镇”——根据公开报道,目前这个模式在成都市温江区和宜宾市三江新区已经完成了落地,前者为“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大健康基金产业分镇”,后者被命名为“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川南创投中心”。
在具体工作成果上,通过小镇平台,天士力干细胞项目、罗欣与阿宾制药合资项目等4个大型产业落户温江,8个产业项目正以“基金+项目”方式通过小镇平台洽谈落户温江。
最终在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需要更多技术操作”的时代,小镇似乎通过“不再拘泥于物理载体”“把自己抽象化”的方式进入了好日子。
成都万华投资集团董事、天府国际基金小镇董事长姜涛在今年8月的那场闭门会上,详细介绍了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的发展成就:目前,小镇已经入驻基金机构533家,管理社会资金的总规模超过5180亿元。
谈到对于未来的规划,姜涛的目标很明确:“未来将通过基金小镇‘产业引导基金+行业头部PE投资机构+社会资本+金融风险防控+基金生态圈’多层次服务体系,以资本牵引行业优质项目与产业区域联动、撬动社会资本助推产业发展”。
但如果真要做到这一切,麓镇与基金小镇似乎又要重新思考“相处模式”。
舜雨婷也谈到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感受。她的一位朋友几个月前相中了麓山社区的消费能力,决定在小镇租下一栋200余平的商铺经营美式烤肉,但朋友与运营方的沟通并不愉快。
“免租期就一直谈不拢,最开始说半年,最后运营方一直压缩到了一个月,根本无法操作。”舜雨婷并不明确运营方的决策逻辑,“我觉得他们这里的商业氛围其实还要培养,但我听说他们想要进行业态调整。”
我坐在舜雨婷的咖啡机前,希望能遇到两个“熟客”,好问问“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到这里来逛街”“是否在这里工作”,但从早上11点到下午4点一无所获。

在那个忽然降温的成都初冬午后,整个街区唯一活跃起来的消费场景是热气腾腾的关东煮,“家公”和“姥姥”们背着小书包,希望摊主们能够多打一些可以暖手的汤。猿辅导孵化咖啡品牌Grid在这一天推出了“雪花冰箱贴”的打卡活动,无数妆容精致的年轻人带着三角支架,在万创控股的办公室外围出了一个临时摄影棚。
游艺建议我等到晚饭之后,因为“那会儿会有更多约会的人”,而我无法判断这个经验的复现概率,因为我已经遇到了好几对在此取景拍婚纱照的新婚夫妇,摄影师熟练地催促着进度:“来,这个景我们再拍两组,然后再到那后面拍一组不同风格的”,而他的助手们面无表情地看管着新娘的羽绒服和平底鞋,准备好随时换场。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准备定格在神圣时刻里的小镇,正在经历何种变化。
(本文除谭啸、罗立平外,其余人物皆使用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蒲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