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即将驶入终点站,时间的刻度似乎带来了别样的体悟。
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重整旗鼓的一年。当外部世界依旧处于风暴的漩涡边缘,弥合撕裂与失序的一切仍是人类所求索的共同目标,旧的困顿与新的曙光为我们指引出前路的方向。站在小径分岔的路口,重新拾回内心的力量,显得尤为迫切。
阅读,即是汲取内在勇气的一种方式,是抵御迷茫与失序的良方。书籍,是一位冷静可靠的挚友,是一把凿开内心冰湖的斧子,也是一段想象与记忆的延长线。
与往年一样,经观书评在年底推出“年终阅读特辑”,邀请来自各个领域、拥有相异阅读旨趣的读书人,回顾自己2023年的阅读历程,与读者分享印象深刻的书籍,以文字和智识为桨,在浪潮中激荡起时代的通感与共鸣。
“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困境,解药或许一直都在,但在什么层面上、由哪些人如何服用,服用之后的效应如何扩散或传播,则是个学科工程性质的结构性难题。”
01
多年来,身为出版人,我的阅读其实都处于一种相对匆促的状态,2023年并不例外。我的阅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说起来都是功利性或者实用性的阅读。
一类是作为编辑实务的阅读。这类阅读不单纯关注内容,也关注体例、规范甚至版式等其他非内容的方面,总体上说并非基于个人阅读计划,而是受约束于身为出版人的出版规划;同时,编校过程中的阅读虽然也会有所收获,但关注焦点不可避免地会更偏重于字、词、句,无暇对相应论题或问题做更深入地思考与笔记摘要。
一类是接近于非实用性的阅读,比如今年案头放的中华书局精装横排版《春秋左传注》(上、下),同一版本系列里的《杜诗详注》(全三册),以及“里仁金”(里仁版《金瓶梅词话》)。我的专业并非中国古典文学,对于许多国学基本经典,很长时间里都停留在大致有点了解、大致读了一点的程度,但也一直都希望能把某些正典文本通读一、两遍,有时间了再集中于某一文本及对该文本的重要研究和相关背景下一点更深的功夫,就此能有个对自己所下的功夫有所交待的成果。
当然,这并非说我自己的写作水准达到了某些优秀写作者所谓的“下过功夫的,不敢不写”的程度。这类阅读看似全然由阅读欲望所推动,全凭了自己的兴趣;深想一层,还是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哪怕这只是一种无用之用的功利。但现实的问题是,能分配到这类阅读上的时间,总是被一再挤压,而一旦争分夺秒地挤出时间阅读,就又变成了为读而读的功利行为。
还有一种阅读,纯粹是为了当下要完成某篇“专业”文章的任务。当然,在自己的领域内,写什么文章,读哪些书,可以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这类阅读的优点是读得细致,思考也较为充分,而且留下了思考的文字结果。
事实上,为了写文章而作的阅读,即便抛开写的成果不说,对阅读者个人而言,也是一种更具效率、更有助益的阅读。可以这么说,写是为了更好地读;读,如果不抱着写的目的,往往难免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在心里留存不下太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我向大家推荐今年细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英国文学理论名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的革命者》;另一本是美国学者、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约瑟夫·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事实上,这两本书有着很明显的相关性。
02
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出版于2017年,中文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在本书中,诺思把20世纪的文学批评分为三个时期或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年代I.A.理查兹的开创性工作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诺思看来,理查兹不仅为初期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审美唯物论的哲学根基,并且提出了后世影响深远的方法论工具“文本细读”和“实用批评”,“由此把批评工程擢升至学科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0到1970年代,其间,作为学科的批评工程由美国的新批评和英国的利维斯派及其同道所承继,但理查兹所创立的唯物主义美学根基被置换成了唯心主义,而“文本细读”和“实用批评”的方法论重心,也从“培养读者的审美能力转移至培养读者的审美判断”,所谓的审美判断,就是为特定文本的审美价值进行等级排序。
在诺思看来,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叶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诺思所谓的文学批评,“确切地说,应被理解为一种体系性的活动,它致力于运用文学作品来培养审美感受力,以期实现更为广泛的文化与政治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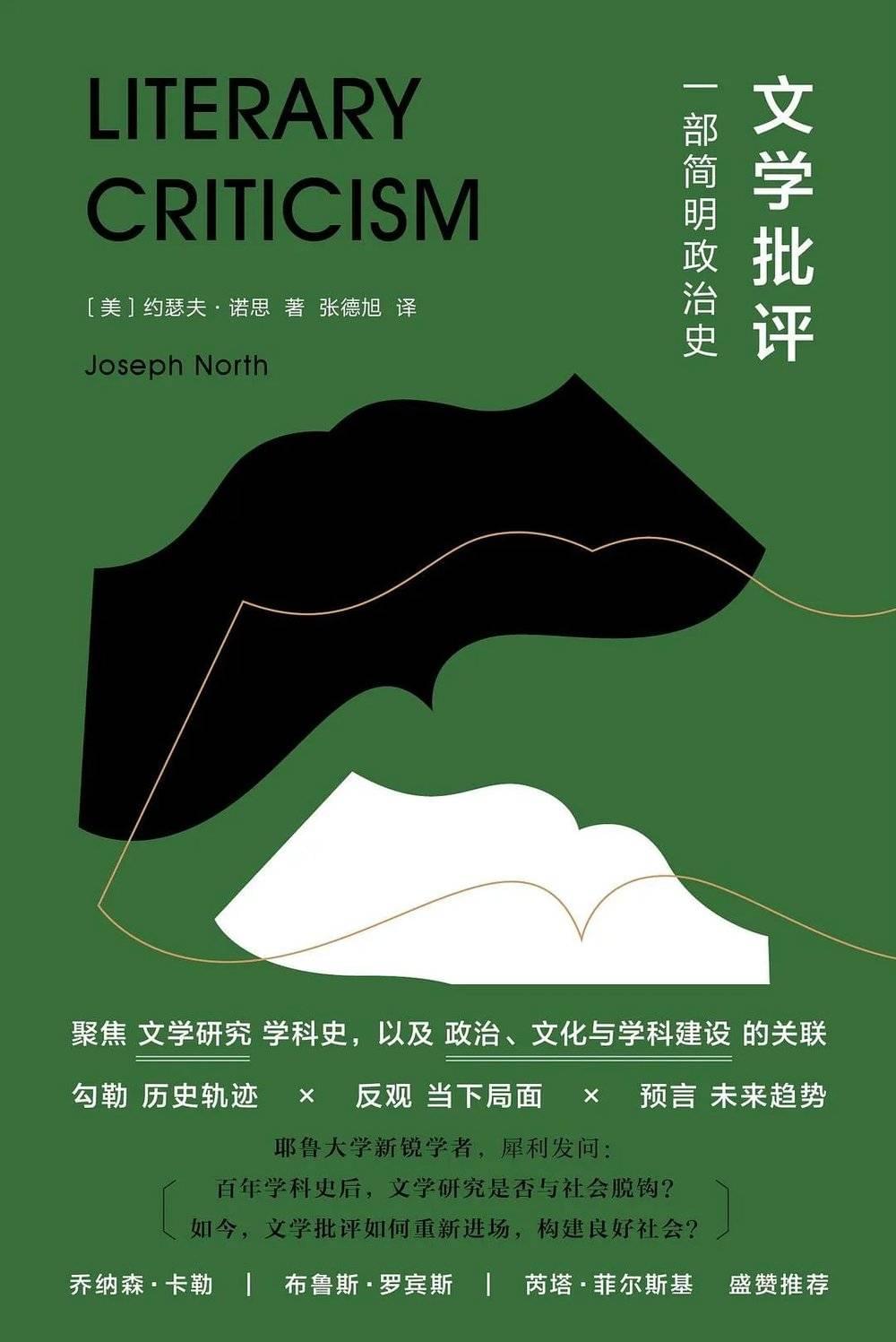
《文学批评 : 一部简明政治史》
[美] 约瑟夫·诺思|著
张德旭|译
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
第三个阶段则是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诺思写作本书的“今天”。诺思认为,在前两个阶段相争相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学术”,共同塑造着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而到了第三阶段,在这门学科内部,则成了一家主导的局面。作为学术的文学研究“日益成为学科整体工作的本质特征”,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成了主导性的文学研究范式。诺思认为,这一学术转向的结果就是,“视文学文本为分析历史文化的契机的研究取向,取代了视文学文本为培养读者审美感受力的手段的研究取向”。
简单地说,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成了生产历史文化知识,而不再是回应个人或群体该如何构建良好生活的需要。可以顺带一提的是,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1990年代提出的发生在中国知识人群体中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一断语,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种转向发生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比在英美晚了10年(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而实际上,在转向前,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并没有产出什么像样的批评成果,真正有了一点像样的成果,是在最近20年。
通过检视文学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诺思认为,在今天,文学研究继续沿用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已经行不通了。他通过本书提出的发问是,在当今时代,“文学学术研究需要如何重构自身,才能在当今时代有所作为”。他在本书中所做的就是,重审理查兹的开创性工作,精心评估其理论和方法论中被后世忽视和歪曲了的更具价值的线索与资源,来谨慎地为当前的范式建议可能的出路,或替代性的新范式选项。
诺思把文学批评史看成一部政治史,他的立意或源由首先在于,文学研究史的三个阶段与20世纪历史的广义分期大致重叠。“学科史除了与社会秩序的深层变迁大致保持同步前进,还有别的可能吗?”而在如何看待文学的问题上,左右翼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也确实导致了不同的诉求。
其次,在诺思看来,“当下的抗争正在感受力的层面展开……感受力当然不是唯一的抗争地带……但是抗争从来不会全然脱离于感受力。如果我们放弃感受力这块阵地,我们就无法取胜”,而“文学文本和其他审美文本正是培养各种能力和感受力的豪华的训练场”。之于宏观的政治问题,“文学研究相当于一个虽小但无比重要的测试用例,供我们思考那个更宏大、更核心的普遍性问题,即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如何培养我们过深沉本真的生活,并且它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03
文学研究的政治性,是个完全不新鲜的话题。特里·伊格尔顿1983年的名作《文学理论导引》(中文版书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结语一章的标题即为“政治批评”。虽然伊格尔顿用“政治的”一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种种权力关系”,这一点与诺思所谓“政治”的立意还是明显有别,但他在该书中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层意思与诺思则是相合的。
《文学批评的革命者》(原书名并无“文学”一词)一书出版于2022年(“新行思”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23年联合推出了中文版),伊格尔顿已近80高龄,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算是他对诺思所提问题的一种间接回应。
事实上,在《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正是被诺思当成了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这一普遍趋势的第一个样例。他认为,在伊格尔顿那里,较之理查兹而言更重视利维斯的作用,是他犯这个情有可原的错误的原因。但诺思也指出,在伊格尔顿1990年出版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还是对审美价值作出了积极的唯物主义式的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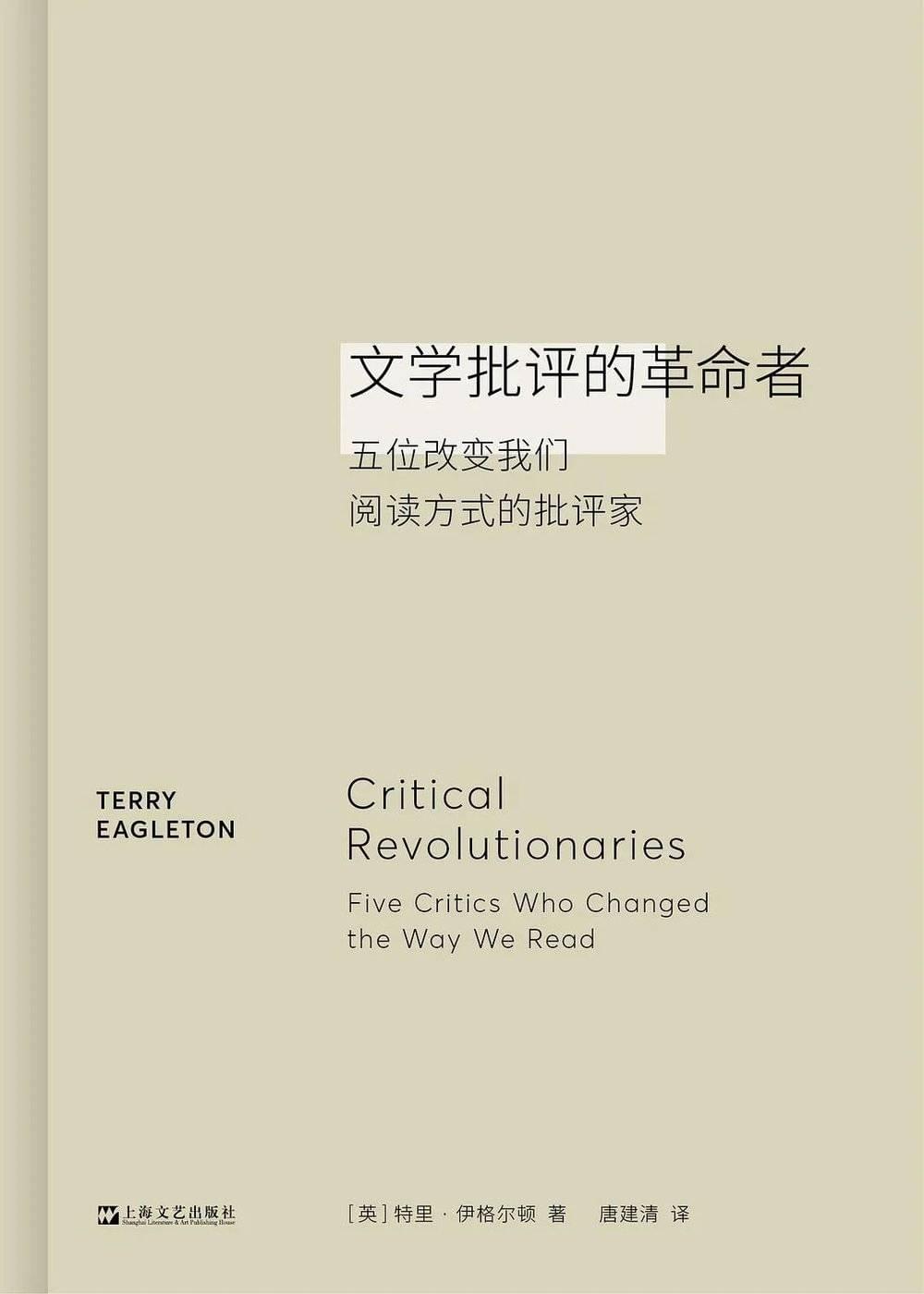
《文学批评的革命者》
[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
唐建清|译
新行思 艺文志eons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与诺思撰述《文学批评》一书的驱动力大致相同,伊格尔顿写作《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一书,“是因为我坚信,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正面临被忽视的危险”。在伊格尔顿那里,这个重要传统就是关注并关心语言与感受力的连接,这一传统的核心是相信,“对文学文本的细读是一种深刻的道德活动……定义和评价语言的质量就是定义和评价整个生活方式的质量”。
在我看来,诺思在自己的书中,把伊格尔顿完全归为一位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样例,明显是偏颇的。即便是在40年前40岁的伊格尔顿撰写《文学理论导引》的1980年代初,他也并没有把文学研究当成一种完全是为了生产历史文化知识的学术与思想活动。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利用文学来培养人们对语言潜能的感受性;从审美的层面上讲,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堕入康德以降的唯心主义传统,从一开始他就不仅仅把文学研究当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的生产,明白地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个“介入派”:“任何方法或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即通过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产生‘更好的人’,就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40年前《文学理论导引》一书的第一章《英国文学的兴起》中,伊格尔顿就对他在《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中为之画像的前四位批评家(对于他的老师,他书中的第五位文学批评的革命者雷蒙德·威廉斯,他只是顺带提了一下),做过精彩、到位且立场鲜明的总体性阐述。
当然,在那本书中,他的目标还在于梳理清楚,作为一门学科的英国文学,是如何因应当时正在上演的欧洲现代主义运动而确立起来的。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确实需要构建一整套理论体系和方便应用的方法论工具,这也确实造成了文学批评作为一项知识生产活动的面向。在诺思所说的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这一面向占据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而其《文学批评》一书的要点,即在于对这一主导范式所造成的局面与危险的警惕与反思。
显然是受了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引》第一章的影响,诺思在他的工作中也是回到了作为出发点的理查兹与利维斯等人,检视曾经在源头出现过、后来被逐渐忽视或歪曲了的唯物主义审美的火种。
而伊格尔顿在40年后重访他学术生涯早年曾经受过他们重大影响并接续其传统的这五位文学批评的革命者,或许也说明,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困境,解药或许一直都在,但在什么层面上、由哪些人如何服用,服用之后的效应如何扩散或传播,则是个学科工程性质的结构性难题。这一难题所造成的局势要有所改观,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以项目为主导的学术价值体系下,恐怕会更加地渺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杨全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