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3年的阅读是从一本“大部头”专著、法国学者塞尔日·格鲁金斯基的《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的历史》开始的。以往人们纠结于反“欧洲中心论”的时候,其实心目中多少都有着一个“亚洲中心论”,内心深处的潜台词是我们不是被动于世界大势,倘若不是内部的专制腐朽和外部的侵凌导致的延宕,我们曾经阔绰的祖上应该也能持续引领大航海的潮流和全球化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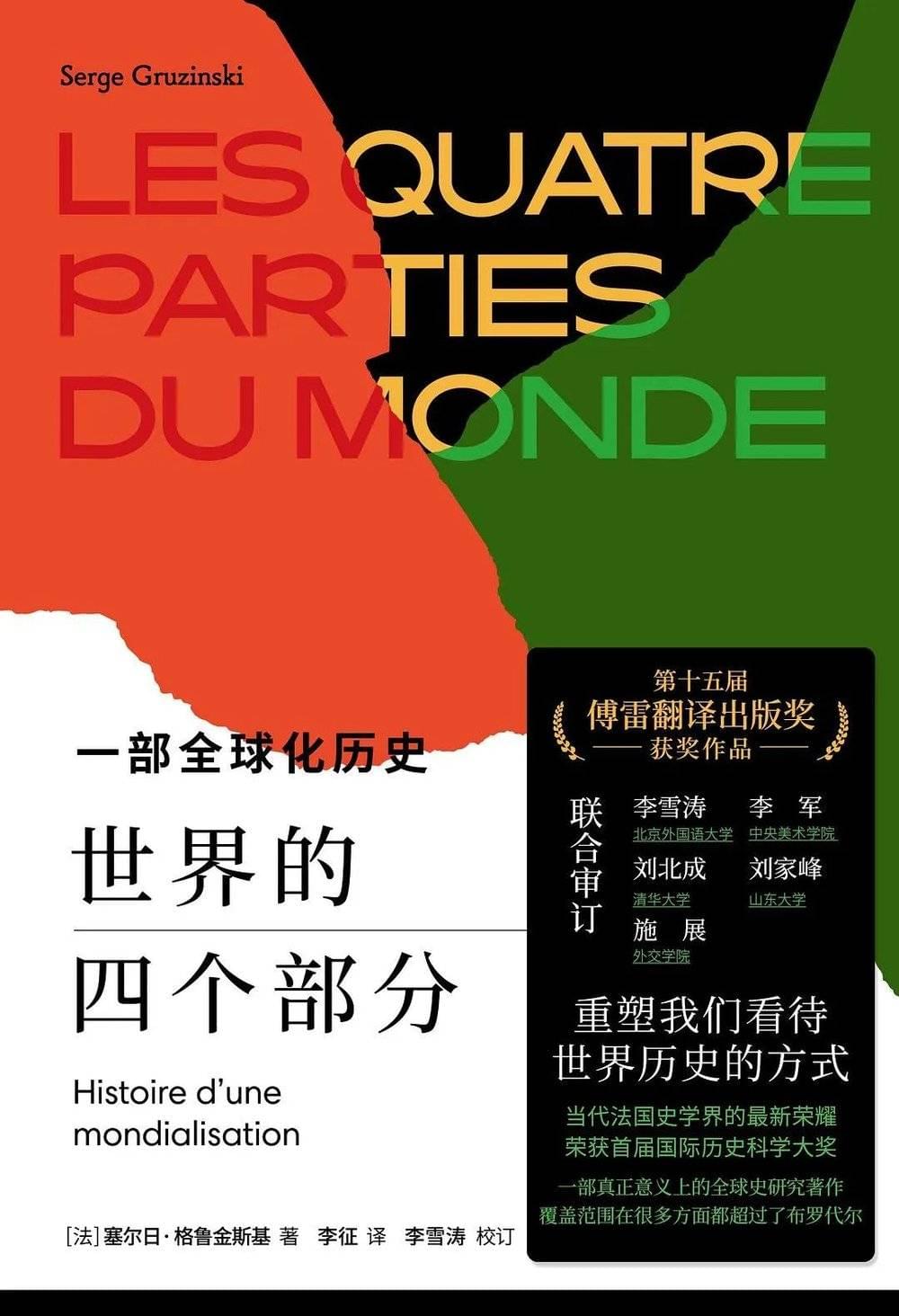
《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的历史》
[法]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著,李征 李雪涛|译
东方出版社,2022年11月
这种和“深渊”的相互凝视,妨碍了我们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全球化,因此,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从“美洲中心论”出发看“伊比利亚时代的全球化”,就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当人们读到德川时代的日本僧侣出现在墨西哥城街头的段落时,其“怪异”之感不亚于读阿米塔夫·高希从印度视角看中英鸦片战争给人带来的震撼。还是那句话,过度执着于“赶英超美”,或许反而矮化和窄化了人们的万丈雄心。
啃完《世界的四个部分》后,想深入探究“伊比利亚全球化”并系统研究之后全球化进程的雄心被点燃了。一如既往,这种系统性阅读的愿望和计划被别的琳琅满目的读物给打断了。在啃了几本剑桥近代史后,继续攻读的愿力无可避免地在艺术史大家西蒙·沙玛《富庶的窘境》一书前溃散了。看多了“大分流”之类奠基于精致的“唯物”史观之上的分析后,《富庶的窘境》之用力于观念变革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且我也想借此稍解早年阅读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所引发的困惑:西方是如何“善待”财富,进而跨越现代化的门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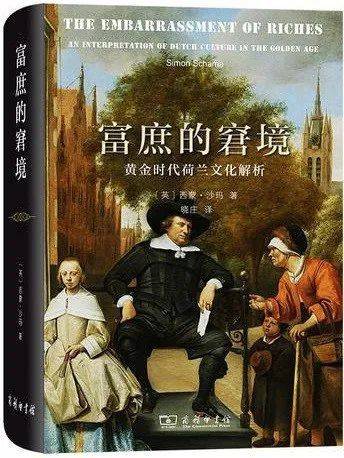
《富庶的窘境 : 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
[英] 西蒙·沙玛|著,晓庄|译
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
在艺术史大家西蒙·沙玛的笔下,意气风发的黄金时代荷兰人常给人以纠结之感。甫一挣得自由身,又陷入道德与享乐、宗教与世俗间的种种张力与纠结;既标榜道德,又不愿意放弃奢华;在享受奢华生活时,又怕逾越本分,遭致天谴。种种犹疑,不一而足。
这种状态被西蒙·沙玛归结为“富庶的窘境”,其实质是一个刚刚踏入现代富裕之境的社会如何安放自己的初心,个人又如何在一个复杂的、充满种种冲突与张力的富裕社会安身立命。与荷兰人富庶的困窘相仿佛,当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大明王朝也迎来自己“纵乐的困惑”。其与之后明清鼎革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至今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跃动着历史的余痛。
面对神权的光环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与张力,荷兰人守住了政教分离的底线,在尊重宗教权威的同时,坚持以世俗政权来规范社会,并以各种变通和妥协之道来应对“富庶的窘境”。当然,荷兰人并没有绝对摒斥宗教对俗常生活的干预。他们冀望充分发挥宗教矫正时弊、抚慰人心、提供救济的功能,对宗教让富者知所敬畏并行侠仗义、让弱者有所寄托倚盼,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定海神针之效,也有着深刻的体认。
问题的关键是摆正信仰和世俗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理顺了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关系,才算真正跨进了现代社会。荷兰人的种种纠结和为克服这种种纠结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算不上完美但可以接受的成果,给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初始范本。
回头看去,荷兰人的成功源于制度层面上的政教分离。这种分离不仅仅是指避免有形的神权政治,而是要将宗教信仰归入个人领域,不得以宗教和道德之名强力干预社会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连美国也都没有完全理顺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张力:动辄道德感爆棚,以宗教为推手,以宪法为名,发动一次次法律战争,要全社会都感恩清教徒的礼物等等。
回望那段全球史,荷兰的成功令大明的挫败更为彰显和令人气结。在黄仁宇看来,大明不敌八旗,是因为简单的前现代社会组织,动员力往往更胜于刚踏进现代门槛的白银经济。而在当时(甚至现在),有不少儒生将大明的挫败归因于放浪形骸的生活和道德的堕落。由此明清鼎革带来了双重创伤,既有对市场经济带来堕落的恐惧,又有富庶社会不敌简单横暴的前现代组织的宿命感。后来,历史的胜者也在有意无意间创造“简朴纯真有信仰”胜过“奢华现代太颓丧”的神话并甘之如饴。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一个刚踏进现代化门槛的社会,既无前现代如臂使指的简单动员力,又不能靠优越的技术克服不惜消耗人力的战术,自然会常常败下阵来。但真正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从技术水平到资源汲取能力都远胜前现代社会,历史和现实都更多地证明了这一点。
十七世纪欧亚大陆两端富裕社会的遭遇及其遗绪,令人感慨唏嘘。富庶的复杂社会,必然比简单小农社会难以驾驭,应对得法,则可迈入长治久安之局。如果一次次努力总是换来西西弗式挫败,总是停留在前现代半成品社会阶段,则人们的心理容易陷入宿命观,认为一切努力最终都敌不过命运的拨弄: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当然不利于一个有恒产且有恒心的社会的建成。
如果更因此陷入到前现代简陋社会效率更高、道德也更为高洁的迷思,且永远沉浸于革命建国教的情怀,遇到挫折便想回归到火热的年代,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而言显非吉兆。不忘革命建国遗产,将其作为民族精神建构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危难之际加以调用,是全世界通用之道;但若念念不忘,时时启用,则有害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总是回望革命建国年代,总想回归苍白素净的起点,回归甘地的纺车时代,也是一种准神权政治。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神权政治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社会的张力,只能在将社会强行拉回简陋粗鄙状态的过程中,对先进生产力和社会生机造成戕害。至于打着均贫富的旗帜而自肥,因其目标的高蹈与现实的无能间的差距,更是助长伪善之风盛行。
二
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只有将道德和准宗教情怀放到合适的位置,驾驭富裕社会带来的冲突和张力,才能驶过历史的三峡。当然,即使驶过历史的三峡,也不意味着一马平川和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确立,在很多情形下只是现代化的开端和序曲,围绕现代化红利和弊端的纵横捭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阶层间政治阵营的分化重组,是层出不穷的剧目,其中尤以市民阶层的兴衰最为人瞩目。
那么到底何为市民阶层呢?人们发现很难为其画一个精准画像,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它不是什么来加以定义,比如市民阶层不是工农大众、不是贵族、不是大资产阶级等等。市民阶层是上个世纪的中产阶层,职业多为高级白领或小企业主、小店主,以市民阶层为社会中坚力量的英国就被谑称为“小店主的国度”。其精神代言人为马克斯·韦伯、本雅明等,生活方式呈现者是托马斯·曼、茨威格、普鲁斯特等。
这些市民阶层的子弟多半包容善良,对下层民众充满同情,又自恋、自怨自艾,讽刺起自身所属种群的伪善与虚荣来毫不留情,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大风大浪显然缺乏各种精神准备和应对手段。他们本来大多都是经济上行期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的阶层,所倚恃的多半是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对政经大势的走向和愿景缺乏认知,遑论主动加以擘画。
除了自身成分的斑驳多元外,由于身处不同国度、不同的政治传统和不同的成长周期,由市民阶层而生发的市民社会,也呈现出复杂的调性。
马洛伊·山多尔在其《一个市民的自白》三部曲的第二部《欧洲苍穹下》,对法国和英国的市民社会做出了种种对比性刻画,读来颇有启发性。比如法国市民阶层,不如其德国同类那么保守谨饬,而更爱鲜衣美食,虽然个人生活散乱无序,但面临大是大非时头脑极其清晰,不像德国市民阶级,表面极其尊重等级秩序,对道德和文明的秩序感却鲜有把握。至于英国市民阶层表面上的冷漠和分寸感,其实代表着对他人权利空间的包容与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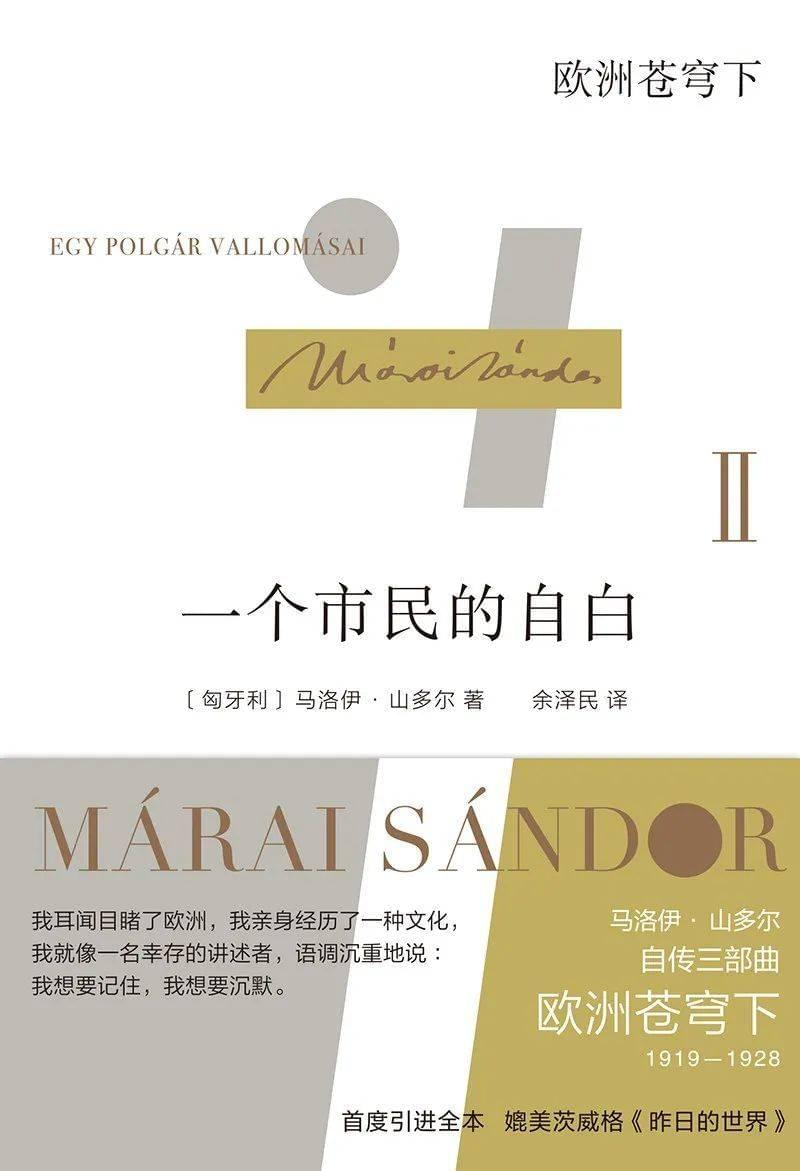
《一个市民的自白 Ⅱ : 欧洲苍穹下》
[匈] 马洛伊·山多尔|著,余泽民|译
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
将马洛伊·山多尔对英美市民社会的观察与茨威格、康托诺维茨、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人的观察并置而观,不难发现这些流亡者经历了大体相同的文化“震撼”,至少承认此前他们所认为的相对于英法浅薄的物质文化而言,中东欧的文化更为幽深丰富、更富有精神性和超越性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相比之下,其时的中东欧市民阶层更为孱弱。一方面是因为中东欧社会政治进程的滞后,姗姗而来的“少数人的民主”更多是自上而下的产物,面对依然手握大权——尤其是军权——的权贵阶层,其市民阶层的强悍程度当然不能与动辄街垒的法国同行、以及经历过漫长的宪政历练且刚刚经受宪章运动试炼的英国同行相比。
而另一方面,那些本该被他们引领的大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却经常选择与王朝统治集团结盟,这一点在被称为“革命之年”的1848年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腹背受敌、上下夹击之感,贯穿中东欧市民社会的生发与衰亡史,只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的回光返照期,上下夹击渐被左右夹击所代替。
更为吊诡的是,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来说意味着贵族阶层的再消亡和大众社会的再壮大,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战”的创伤则主要由市民社会承担。正如马克斯·韦伯的传记作者所言,“一战”后惊魂甫定的马克斯·韦伯突然发现其所代言的市民阶层已经趋于崩解了。
其实早在“一战”之前,中东欧市民阶层的没落就已是不争的事实。被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大群众萌发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热望,却难以被充分满足,哪怕是在经济上行期。而社会化大生产令市民阶层自身也难保无虞,从而无法继续成为大众进阶的楷模。而他们之前以自由和进步的名义所释放的力量,都成为对付他们自身的武器,他们不敌民族主义、不敌大众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市民阶层的没落和市民社会的解体正是“一战”得以爆发的推手之一。
当然,并非所有的市民阶层成员都坐以待毙,比如身为市民阶层“逆子”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们,在谙熟了大众政治的奥秘后,便裹挟市民阶层的年轻人对统治集团发起了绝地反击。当然市民阶层的孩子们也不都是铤而走险之徒,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美国大萧条中从中产地位滑落的年轻群体,他们凭借自身对政治运作的熟稔,成为美国新政的强有力推手和生力军。所以,说到底还是社会结构和政治架构问题。
这种市民社会的复调一直是历史的常态,而同一阶段的市民社会因为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传承的不同,也有着不同的样貌。当茨威格等人唱起欧洲市民社会的挽歌时,在那些拥抱迟到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社会,却迎来了市民社会的“小阳春”,比如日本的“大正之春”、民国的“黄金十年”等等。一如改革开放后,当新兴经济体开始践行对欧美中产生活方式的向往,大规模打造自身的中产社会时,欧美却开始了又一轮中产社会的解体——美国学者乔治·帕克描述此一历程的《下沉年代》,其英文书名本意即为“解体年代”。
事实上,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不难发现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历程鲜有一蹴而就的,其历程曲折或顺遂程度,端视其历史上市民社会传统之强韧程度。参透在逆境中保留市民社会元气之道,等社会重启现代化进程时,能够全方面激活市民社会的文化和观念资源,便可一窥历史演进的堂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