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好友刘文玲教授翻译的马塞尔·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新译本出版,甚感欣慰。近年来,对这本著作的翻译和葛兰言研究的势头重兴。时光复始,中西对鉴,不乏汉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翻译学等领域的中法学人对葛兰言的研究重新审视,这一重视必将衍生新的研究议题。
站在局外者的角度,本文拟初步梳理葛氏研究的来源特点和纷繁争议,从而提出重释葛兰言的必要性;也想要重回到葛兰言所处的时代,围绕这本著作,回应后世对于其模糊性的种种争论,重现对于葛氏研究的价值肯定。
一
回顾葛兰言的研究生涯,其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他对于古代中国的文本研究和阐释,包括《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1920)《中国古代的舞蹈和传说》》(1926)等,有别于传统汉学家的语文学阐释,他通过对上古文本的分析,拟提取古代中国的社会事实,将古代文本中呈现出歌谣和仪轨,放入一个通约式的人类社会结构版图中。这一从神话或文本表象出发,深入到社会科学关系的研究,从主题上说,既影响了法国如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也影响了近代我国民族学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类著作包括三部综合性著作,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思维》这类综合性的研究中,葛兰言想要探索中国文明的整体特性,比如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葛兰言在看似远超汉学传统的广泛领域中纵横捭阖,将算术、天文、语言、文字等题材,归于一个“关联性思维”的研究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葛兰言的学术版图清晰若揭,从中国文明的具体主题出发,归于对中国特点的统一性探索,这一目的,也切合了年鉴学派的所探索的整体性特征。
可是,对葛兰言研究模糊性的争议也正来自于此。第一个模糊性体现为:在专业化的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当中,葛兰言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的学科叙事,如托马斯·赫希(Thomas Hirsch)所言:“二十世纪法国历史学史中葛兰言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就像他在汉学史或者社会学史中的地位一样。法国历史学由于过于学科化,所以忽略了在历史学家看来更像是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
然而,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充分理解葛氏所面对该争议的缘由。需知,葛兰言是受过正统训练的历史学家,他深受莫诺的实证主义史学和古朗日的制度历史学的影响。古朗日重视对原始材料回到当时历史现场的阐释,从“过去历史中坚决把因为方法错误而混入其中的现代思想剔除”。
而葛氏的另外一个重要学缘来自于涂尔干学派。对于葛兰言,涂尔干学派有着研究范式和研究主题的双重影响。首先体现在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承袭上。1903年,涂尔干和塔尔德经历了一场著名的大辩论,最终涂尔干占领上风,确定了社会学发展的主流走向基于两个准则。
第一是界定了社会学的范畴领域:为个体构成到集体表象的机理关系。个体意识通过融合,孕育出新的实在——也就是社会的意识。涂尔干想要以类型化的特征,探索一个集体特有的思考和感知方式和其集体性表征,比如宗教教义、神话等。第二:准则也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外部性。这一外部性具体充实了孔德的实证主义,进而也为“制度——一切集体所确定的行为和信仰方式”的阐释提供了空间。
第二是研究主题的影响:涂尔干学派在承认社会事实外部性的基础上,将制度作为重要理解工具,开始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探索。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充分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传统史学的革新之中。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抛弃了古典历史学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在不同文明中发现了多元时间的并存。
此后,他们从社会整体层面考察历史,对集体现象的关注、比较分析的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视都验证了布洛赫的话:“涂尔干学派使我们历史学得益匪浅”。
而空间维度的探索,如渠敬东教授所说,涂尔干学派开始了比较文明研究的征途,“涂尔干正率领他的弟子们将《社会学年鉴》所奠定的研究范型扩展到整个世界的诸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以涂尔干《乱伦禁忌及起源》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起点,无论是莫斯(Marcel Mauss)《礼物》从太平洋岛屿的文明构型扩展到世界性文明区域的比较研究,杜蒙(Louis Dumont)《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对印度文明中的阶序关系的研究,还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态学和发生学的考察等,都是涂尔干关于文明之社会研究的拓展和升华。
葛兰言的研究路径,正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结合,无疑体现在了其对于《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的书写当中,他在引言当中开宗明义:要以实证话语“langage positif”来转述这些观念时,需要考证作者的整个概念体系和叙述体系,他也批评那些象征主义之癖的注疏家们也会自觉荒唐,这可能是出于他们职业道德所致。所以,在全本中,葛兰言所强调的解释方法,既有剥离后世道德引导性注解的古朗日制度史痕迹,也属于涂尔干年鉴学派时空维度的社会事实探索的知识版图。
第二个模糊性,具体体现在对其研究的方法的争议,这也造成了他在汉学领域的诸多争论。葛兰言试图追溯中国社会制度的起源,从他当时认为的雏形实际上是他的《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的乡村社会——一直追溯到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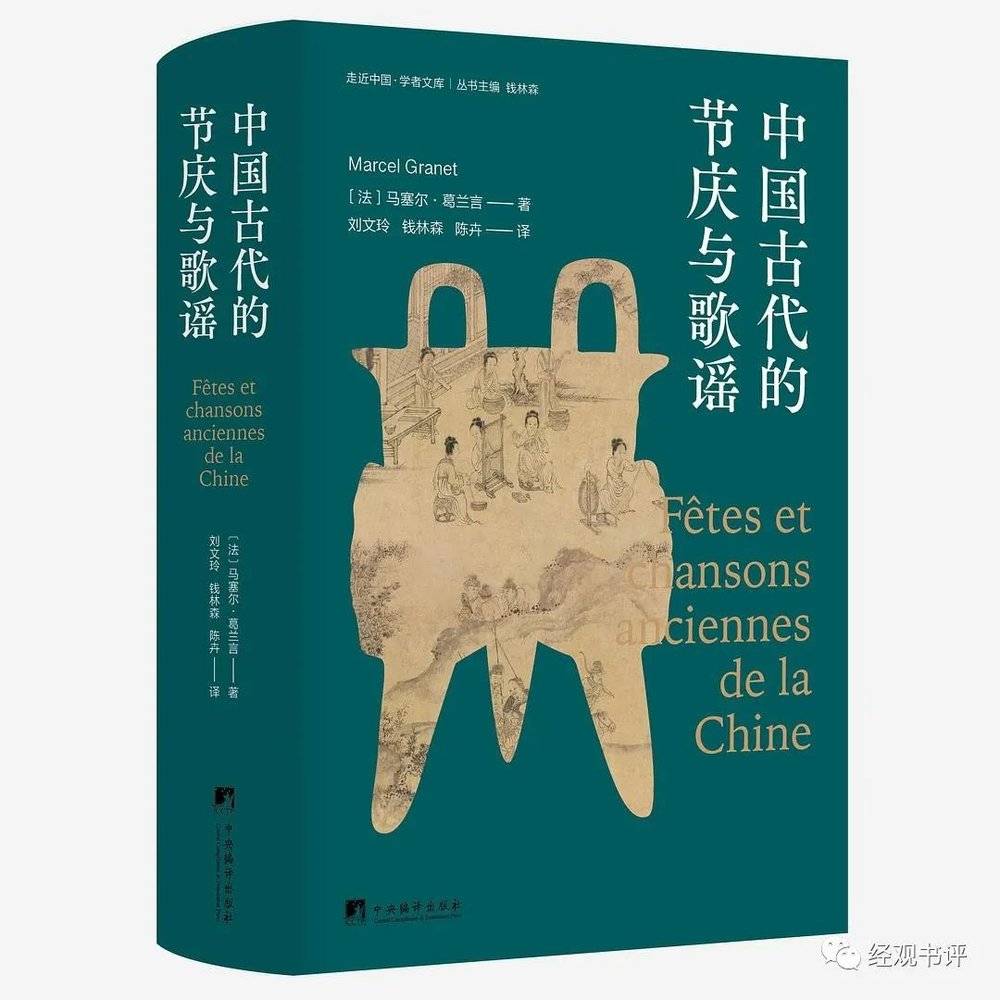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
[法]马塞尔·葛兰言(Marcel Granet)/著
刘文玲、钱林森、陈卉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9月
其中一个主要的争议就是关于葛兰言并不采用当时的考古证据,因为他认为其斑驳复杂,但后者被证明拥有着丰富性和无法比拟的精准性,这就导致考古发现拼接的历史和葛兰言试图提供的历史相异。
但如谢和耐所说,虽然其作品受到某种程度的批评,但葛兰言对于古代中国具体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如“痛苦的语言(Le Langage de la douleur)”“左与右(La Gauche et la Droite)”等都是分析和严谨的典范,可以说葛兰言成功地全面还原了古代仪式的精神意义。此外,不同于沙畹等人的语文学方法,批评者认为葛氏对大量袭用传统的传、笺、序、疏,译释十篇进行了误用。
以上争议我们可以权且理解为葛氏做出了追寻社会事实而非历史事实的解释,但另外一方面,需要注意到葛兰言和当时所在学术团体成员的关系。他的著作深受当时理论之争的形塑,关于其著作的争论也备受法国社会学学派中的导师和同行们的重视。
在葛氏论述华夏文明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其同僚和追随者关于希腊、罗马、印欧等文明的“人类学”研究所塑造的欧亚文明形象的影子。尤其与Louis Gernet联系密切,热尔奈在《希腊之宗教本原》(Le génie grec dans la religion)中对希腊社会结构特征、历法节律等方面的考察与葛兰言在《节庆与歌谣》中的研究系统顺序别无二致。”
对于此方法的批评,也见诸于民国时代的各种声音,而至后来葛兰言的追随者甚少。王铭铭教授将其缘由概括为第一是当时中国学界对英美社会学的范式选择,第二是在于如何看待治史方法与文献的关系。丁文江和杨堃二人的争论焦点在于方法与文献的关系,即以发现事实为目的的葛氏新法,是否有助于正确地从文献中发现事实。
前者指责葛兰言对文献误引错解,所称事实并非历史真相,因而怀疑其方法的适用性;后者则由介绍方法而阐明其发现事实的不同路径以及事实的不同类型。桑兵教授指出:两相比较,丁文江确有误会方法之处,但所指出的事实真伪问题,并未得到正面解答。”
二
基于对《诗经》原本的阐释,赵丙祥教授认为,葛兰言的治史方法,站在本土经学的层面,亦符合当时宋到民国“眼光向下的革命”趋势。赵教授将这一因缘归于葛兰言的中国际遇和受到清以来的学风影响。
本文拟跳脱对于材料方法的具体争论,回到“社会事实”的层面去展示理解这一问题。第一,如前叙所言,回到西学传统,对葛兰言材料方法的理解,必须跳出历史学科本来的叙事范畴,在西方社会学的集体层面研究中,找到其合理性依据。
第二,中国本土经学的演变也和社会结构相关。宋以来,确切说是唐后期以来,随着土地和财税制度变化、农民起义等战乱的打击、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兴起等,士族衰败,中小地主和工商阶层等“下层”崛起,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思想文化也随之跟以前不同,朱熹等人解经,不可避免地带有新的“下层”思维。
因此,对于《诗经》中以各地的“民歌”为代表的《国风》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愈发认可和推崇,这也是“下层”崛起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种反映。当然在“革命”思潮盛行的民国时期,这种思想越发突出。这不独指民国经学的民间化,更不仅指顾颉刚倡导的“民俗化”,这一东西之间或相映或暗合的演变,是理解葛兰言所从事的中国研究的关键性背景。
我们无法断言,葛氏的研究方法受其中国际遇的影响;但仅从本书的文本阐释角度也可见一二。首先,葛兰言对于《诗经》情歌的部分阐释,很明显体现出对于经典注解的亲疏关系。例如,关于《周南·桃夭》的解读,葛兰言不赞成《毛传》和《郑笺》将“宜其室家”解释为“是王室的美德才导致婚姻的规范化”以证明王室泽被黎民的效果甚于纯粹的婚姻规则,赋予该诗极深邃的象征意义的职责。
葛氏认为这样过于强调道德,反而无法回答“究竟何为这些诗句所喻指的婚姻规则”,而清代编撰者《皇清经解续篇》将其解读为“妇女有能力正确安排她们的家及其家人”,葛兰言认为后者虽仍有说教意味,但“近代注释家们要走得更远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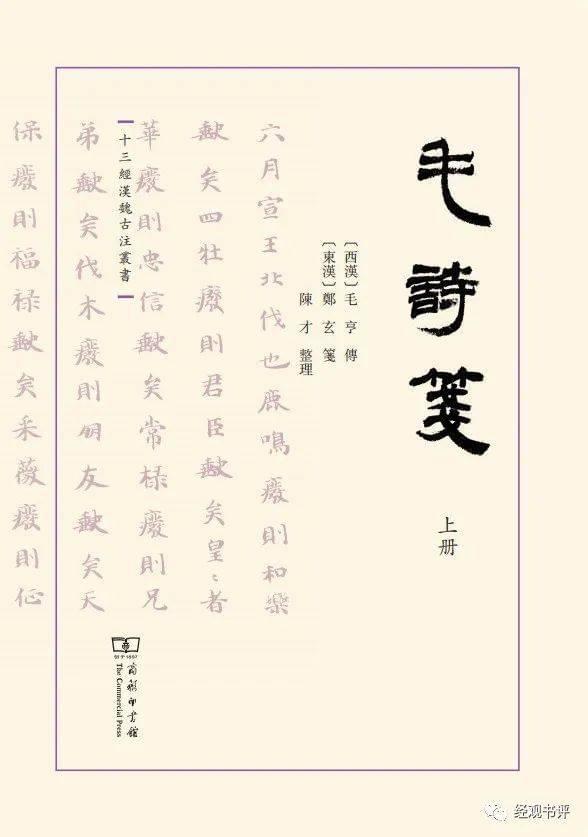
《毛诗笺》
[西汉]毛亨 /传,[东汉]郑玄 /笺,陈才/整理
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
其次,在本书中,在《诗经》翻译的语言学特征上,葛兰言也拟用历史学方法,纠偏语文学派的弊端。葛兰言对于《诗经》的翻译,采用了对仗的西译方法,也尽量采用法诗韵律上的工整,对仗复沓或者排比修辞。葛兰言这一翻译方法,灌注了明显的类型学特征,他提取了《诗经》原本中la loi de genre(体裁规律),拟以法语中的类型进行对应。
葛兰言曾明示:“我将一行含有3、4、5个汉字的诗,翻译成6或8个音节的法语诗句。中文的紧凑性给这项工作带来了困难,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借鉴了法国古老诗歌的简洁句法,这样翻译并不会违背原作。”对于此,钱林森教授从《诗经》学史角度,认为其是“确立西译《诗经》方法的第一人”;而从涂尔干学派角度,可明显勘见其在“比较文明版图的类型学研究”中所作的努力,在《节庆与歌谣》的民族学注释中的日本诗歌部分,也可看到这一努力痕迹。
这一特点可能也受到索绪尔、梅耶等历史语言学家的影响,虽尚无研究上更详细的考证,但可以看出:在翻译上,葛兰言试图剥离义理和训诂之间的内容,进行不同的翻译策略。他遵从传统经注对于字义的考辩,充分地注入其翻译当中,也尽量遵从其对仗形式。如《召南·鹊巢》,葛兰言将“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译为“ C’est la pie qui a fait son nid:ce sont ramiers qui logent là ! ”,两句都遵循“c’est...qui...”句式(是喜鹊筑好了窠巢,却是斑鸠住了进来),两句都遵循“c’est...qui...”(正是……)的句式, 这种翻译方式保持了原文的对仗形式和节奏感,同时传达了相同的意义,增强了诗歌的美感。
而对于义理的阐释,葛兰言在翻译中十分谨慎,尽量避免为其所用。如 《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诗序》认为这首诗讽刺了周幽王,并且“思贤人在野”,顾赛芬在《诗经译注》中把“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译为“A la vue d'un sage, quelle n'est pas ma joie!”,十分贴合《序》的注释。而葛兰言则是直接译成“Mon seigneur”,并没有按照《序》的注释来强调“王侯渴望贤人”的主题。他认为,依据学术宗教思想或虔诚的训诂学家构建的礼仪规则来翻译这些诗歌是十分危险的。
针对顾赛芬的译本,他做出了细致的考异。比如:对于《桧风·隰有苌楚》第4句“乐子之无知”的翻译,顾赛芬译为“je te félicite d'être dépourvu de sentiment”(我庆幸你没有感情)葛兰言译为:quelle joie que tu n’aies pas de connaissance(我多么羡慕你无知己),两者在“知”字的翻译上有不同的见解。
在《诗经译注》中,顾赛芬借助《诗序》的注释,将“知”翻译为“sentiment”,并把这首诗理解为在君王暴政下,百姓对毫无感知的苌楚的羡慕。葛兰言在《节庆与歌谣》第一章《隰有苌楚》的注解之后,提出了一个剥离该解释的假设。《隰有苌楚》与《桃夭》的构成具有许多相似处,《桃夭》中的“华”与“家”对韵,“实”与“室”对韵,如果把《桃夭》的对韵规律用在《隰有苌楚》上,“知”字就有可能是以模糊的方式指代家室,或者以中性方式指代配偶或知己。
在翻译工作中,刘文玲教授无疑重现了这一“回到历史现场”的特征,她以白话文的方式,贴合语义本身,回译了葛兰言对于《诗经》的法语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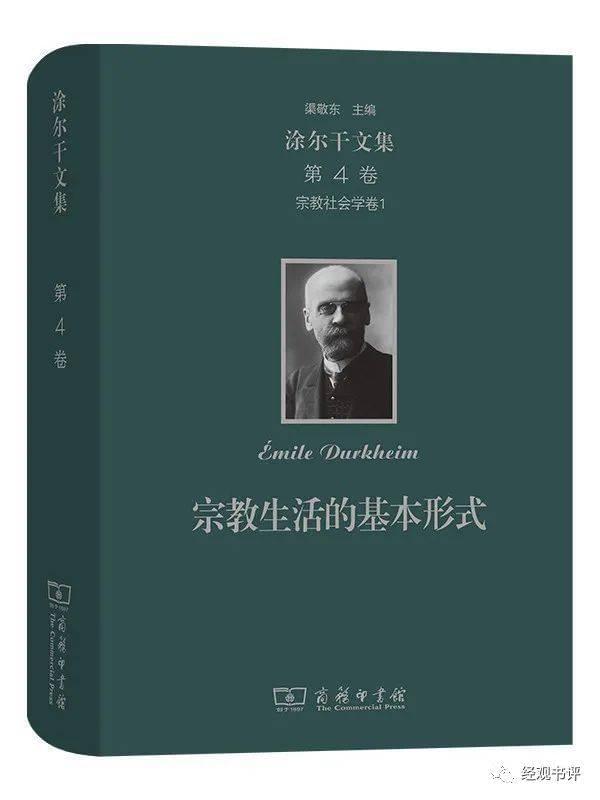
《涂尔干文集》
[法]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敬东 /译
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
而在概念阐释性的文段当中,刘文玲教授大胆加诸了作为人类学家对于文本的深入理解,在中文译文中丰富了语义概念,理清了法语词汇直译可能带来的模糊关系,从而展现葛兰言研究的脉络和学缘。如“un langage positif”,刘文玲教授在此考虑到葛兰言的实证主义学缘,将“un langage positif”译为“实证话语”。
在引言部分的翻译,“la Féodalité”,刘文玲教授将其译为“分封制”,也在译文的逻辑中,不动声色地强调了秦朝统一中央帝国成立前后的制度承续关系。如“le caractère accidentel des représentations ”。刘文玲教授将其译为“再现的偶然性”,作者谈论的是上古节庆的重构(reconstituées),并强调了区分真正信仰和个人主观之间的重要性,“再现的偶然性”准确诠释了这一意涵区别,也体现出涂尔干学派对个人主观意识和集体表征的区分阐释痕迹。
这一项工作的特征,可以说,是对重回葛兰言的最好诠释。而正是有了赵丙祥、刘文玲等学者的翻译工作,有了汲喆、钱林森教授选材的书系,我们才从多样之中,得以窥见葛兰言研究的全貌和其背后的丰富背景。而葛氏研究的珍贵价值,正蕴含于他的模糊性中,才得以被后来者不断诠释。这其中,既有基于各学科视角丰富的文本再探索,离不开对学者群像和学科史的重新审视,也指向中西范式下历史学科边界、翻译生成性等理论问题。
诚如谢和耐所言:“葛兰言诞生在一个还未曾准备好迎接他的时代”,但是,他也在后世的不断争论、理解和再理解中,一边揭开他所处历史时代的面纱,渐现其光芒;一边供后来者汲取其养分,为在各学科背景下获得新的研究土壤给予了可能性,亦为中西文明的互鉴与互解,提供了广阔深邃的空间。而各学科视角下重释葛兰言的诸多问题,只有跳脱学科藩篱,重回葛兰言的研究全局本身,才能找到完整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唐佳路(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石雨竹(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