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经济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人们相信经济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关于市场与竞争的理论指引着现实政策的制定,对经济学的信仰促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而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和其他学科的学者相比,也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和话语权。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贫富差距分化的恶果如阴影般笼罩全球,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界陷入争议之中。人们开始质疑,如果经济学理论对巨大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经济学家不仅没能预见危机,还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后果,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的失败?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的新书中回应了这一尖锐问题。作为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迪顿的成长经历横跨欧洲和美国,他被美国的繁荣所震撼,也为社会中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感到惊讶。因此,他的研究始终具备深深的现实关怀,并且因为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继《逃离不平等》(2013)、《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2020)之后(均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2023年,他在新作 Economics in America 中,从顶尖学者的内部视角,以幽默的笔调、生动的叙述和故事,反思和审视了主流经济学的局限,以及经济学家对现实政策的真实影响。
一、“内部人”身份
安格斯·迪顿成长于英国,在1983年移居至美国,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一位有移民背景、深深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者,他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了美国经济学界围绕不平等话题的各种论争、学术论争背后不同利益群体的对垒,以及种种矛盾之下,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正在衰落的现实。为此,作者不禁想要追问,面对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基础是什么?经济学家又应如何认识并发挥学术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呢?
Economics in America 一书展现了迪顿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它来源于作者过去25年对美国经济学界与公共政策制定积累的观察。作为顶尖的经济学家,迪顿的“内部人”身份为我们展现了解经济学与政策制定关系的一手资料。迪顿从未在政府机构任职,但他的经济学家同事和好友则穿梭其中,因而积累了大量学术界与政策界的生动故事与冒险经历——经济学也许是艰涩的,但关于经济学家的故事却非常精彩。
欧洲移民身份和文化背景,还让迪顿能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去观察美国社会问题和观念的特别之处,这往往是被浸淫其中的美国人所忽视的。在他看来,欧洲与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与欧洲人对平等价值与社会保障的重视及对政府的友好态度不同,美国社会更加强调个人对于机会的把握,认为社会保障只会抑制人们把握机会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迪顿在对这种积极性所创造的财富和成就表示赞赏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平等的担忧,因为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会因各种因素而无法得到机会或从中受益。
此外,美国人对政府表现出了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以至于迪顿因其同事公开宣称“政府治理就是偷窃(government is theft)”感到惊愕。迪顿试图去理解这种言论,逐渐察觉到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富裕阶层剥削普通人的工具。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经济学界似乎又有意忽视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因此,他希望从自身观察与经历出发,不仅能向读者展示经济学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观念与研究会对政策界产生多大影响,还能同时揭露美国经济学界如何因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过度热情而忽略了社会平等的研究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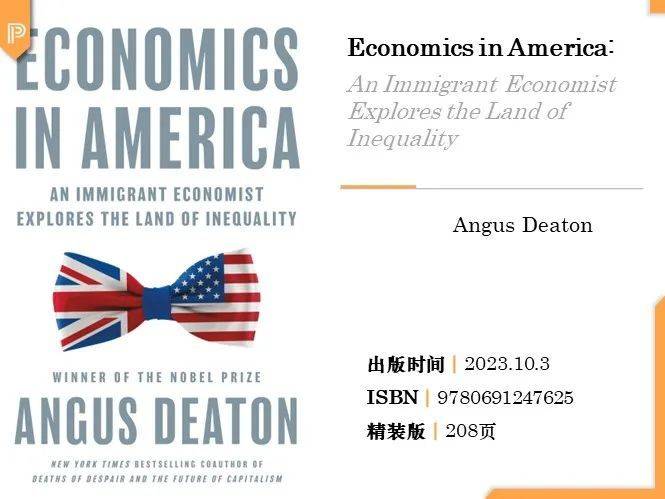
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
二、移民学者眼中的美国经济
作者基于移民学者的亲身经历,对不平等问题及围绕该问题的学界纷争进行了生动阐释。
在第五章中,作者记录下了自己在学术交流中所观察到的、大西洋两岸学术界对不平等问题的迥异态度。
早年在剑桥大学任教时,他发现那边的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会一起讨论不平等、正义与福祉问题。无论是肯尼思·阿罗与阿玛蒂亚·森的社会选择理论,还是詹姆斯·莫里斯的最优税收理论,抑或是约翰·阿特金森的动机理论,它们无不关注平等与正义、激励以及贫穷之间的关系。
然而,当作者前往美国后,他接触到的芝加哥经济学派采取了一条截然相反的研究取向。以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即便对不平等表示担忧,人们最好还是接受这一现状并保持沉默。在假定政治家自利的前提下,政府的市场管制、税收与政治行动均无济于事,因为管理者会被一些公司所“俘获”,并且会优先为提供资金的团体而非选民的利益服务。
例如,在医保体系改革的问题上,政治家名义上必须代表选民利益,但由于对竞选资金的需求,公众利益往往会屈服于医保提供者的利益。因此,相比平等,经济效率更为重要,而以正义为名义的再分配政策会造成效率的“无谓损失”,因此反而是不公正的。
这种学界论争也能在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养老金制度等具体政策议题上得到体现。
对外援助政策方面,新世纪以来包括 IMF、WB 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美国政府都致力于拓展对外援助。主流经济学界对此也表示支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著名全球问题发展专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他的专著《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中,他描述了外界的系统性干预如何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为此发起了“千禧村项目” (MillenniumVillages Project)。
然而,尽管上述机构与学者的宏大愿景振奋人心,仍有一些保守学者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比如,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搜集了一系列发展援助项目的失败案例,讽刺部分经济学家用艰涩的科学话语建立权威,以证明自身方案如何在因果上成立;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则指出了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对受援国带来的危险,并质疑 IMF 代表了华尔街的利益;记者妮娜·蒙克(Nina Munk)通过对“千禧村项目”的多年跟踪,记录下了萨克斯的援助项目如何导致了灾难、破坏与意想不到的后果。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声音逐渐得到了重视,促进了随后 IMF 及发展援助观念的改革。
此外,学界与政界在养老金制度上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养老金保障更多应该由个人还是社会决定?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右派倾向于个人决定,让个人去选择是否加入养老金方案,而左派倾向于社会决定,强调养老金的公共供给,因此个人有义务加入养老保险。
可见,以上种种分歧正体现了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学术界与政策界在这些问题上是互相论争,也相互影响着的。
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正在式微?
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华盛顿工作或担任过政策顾问(如作者的同事 Alan Blinder 就曾担任过多种职务),但总体而言他们对政策界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实际上,官员们很少采纳来自学界的政策建议。在这些官员的指示之下,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实际是为早已决定的政策背书,而不是对政策进行可行性分析;甚至对于著名学者并非出于逢迎的学术观点,官员们都可以进行选择性利用或直接忽视。
例如,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身为当代健康经济学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成员,竟然完全没有参与上世纪60年代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的设计过程。
此外,学术界影响力的式微也有自己的原因:在经年累月的学术争论后,经济学家对很多重要的政策问题仍无法达成一致,导致学术界难以合力影响政策界。作者回忆了其在普林斯顿的两位年轻同事 David Card 与 Alan Krueger 对最低工资的研究。当二人发现最低工资的提升与失业并不存在显著关系时,他们的研究成果遭到了右翼经济学家与相关行业团体的攻击。尽管之后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证实,这类观点依旧没有在政策制定者中促成共识。
与学界对政策界的有限影响力相比,政策界对经济学研究的干预反而更为突出。在第四章中,作者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下文简称 CPI)为例,向读者生动地展现了政治因素如何介入经济指标的测量之中。
CPI 既反映了社会通货膨胀水平,又是美国政府划定贫困线的参考,其政治与社会意义可见一斑。因此,当政客发现统计数据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时(尤其是数据呈现出高通胀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质疑统计人员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甚至会威胁后者辞职。即使统计过程无误,其背后所用的测量方法往往也暗含政治立场。
比如,价格指数既可以以简单的价格均值为计算标准,也可以将其视为反映生活成本的指数来计算。不同指数算法的背后反映的是政治极化的现象,尤其体现在两党对通胀与贫困程度的不同测量方式之上。通过对衡量通胀或贫困的指标与测度进行挑选,各政党可以重塑人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理解。可以说,经济学中所谓的“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存在的。
尽管经济学家在社会地位上不仅权力有限还反遭干涉,他们在智识上的洞见却具有跨越世代的影响力。作者援引了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评价作为论据。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家在思想观点上对政策界会产生比预想中更明显的影响,因为理论范式与观点可以通过经济学教材塑造政治家对世界如何运转的宏观看法以及解释具体政策时运用的话语。而弗里德曼更为深谋远虑,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发展与现有政策不同的理论并坚持维系它们,直至未来某一危机时刻真正来临时,这些曾在政界无人问津的理论终会焕发。
四、反思主流经济学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震动了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 IMF、OECD 等国际经济组织都没有预测到此次危机的发生,不仅如此,尽管经济学家并非金融危机的元凶,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些学者需要为危机承担主要责任——许多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过度推崇,尤其是对精细金融工程的青睐,为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在捍卫全球化、市场化与科技进步的过程中,没有关注到市场经济之下日益严峻的不平等问题。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背后,是收入与财富由劳工向精英转移的再分配过程,其伴随着的是数以百万计工作岗位被摧毁、大量社区的空心化及其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很多经济学家对于人们“绝望至死”(deaths of despair,指因自杀、酗酒、滥用药物滥用致死的情形)的现状无动于衷,更有甚者将后者的生活困境视为其自身问题。
对此,作者不无担忧地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追求人类福祉的初心。
作者援引阿马蒂亚·森批评了莱昂内尔·罗宾斯对经济学的著名定义,即经济学研究如何“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配置稀缺资源”(the 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among competing ends)。这一定义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与亚当·斯密等早期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经济学家的职责是“对社会福祉进行理性和人道的评估”(reasoned and humane evaluation of thesocial wellbeing)。凯恩斯沿袭斯密传统,也将经济学总结为旨在平衡经济效率、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的人类政治问题,亦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以自由与公正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率的做法。
在作者看来,尽管美国国内进步派与保守派经济学家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上有所歧见,二者之间实则具备更多共识,比如都重视经济效率,且都赞成市场在提升效率、搜集信息以及促进繁荣方面的有效性。因此,作者批评两派学者都仅仅从金钱的角度看待人类福祉而并没有把人视作为“人”,忽视了工作、家庭、后代及社区之于人们的实际意义,尤其忽视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群体对有尊严生活的追求。
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其政府对再分配政策(如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优化,不如把焦点聚焦在预先分配(predistribution)之上。预先分配指的是那些能够直接决定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政策,包括工会的组织、针对欠发达地区的“地区导向政策”(place-basedpolicy)、移民控制、关税、工作保障(job-preservation)措施与工业政策等。此外,作者呼吁经济学界能够与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以此重新发掘经济学背后的哲学根基。唯有通过学科思维的转变,我们才可能有机会缓解现实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作者:PUP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