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领我去向无路之地,
穿过黑暗像一颗陨星。
你是苦难和错误的信仰,
但却不是安慰……绝不。”
——阿赫玛托娃,致诗歌
一
2023年9月15日,早起看到一条用英文朗诵诗歌的视频,朗诵的诗中译我很熟悉,个人也非常喜欢,即卡瓦菲斯的名作,《伊萨卡岛》。
看完这条视频,和这首诗相关的往事突然涌上心头。我也顺便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些年没有坚持抄诗,我的人生又会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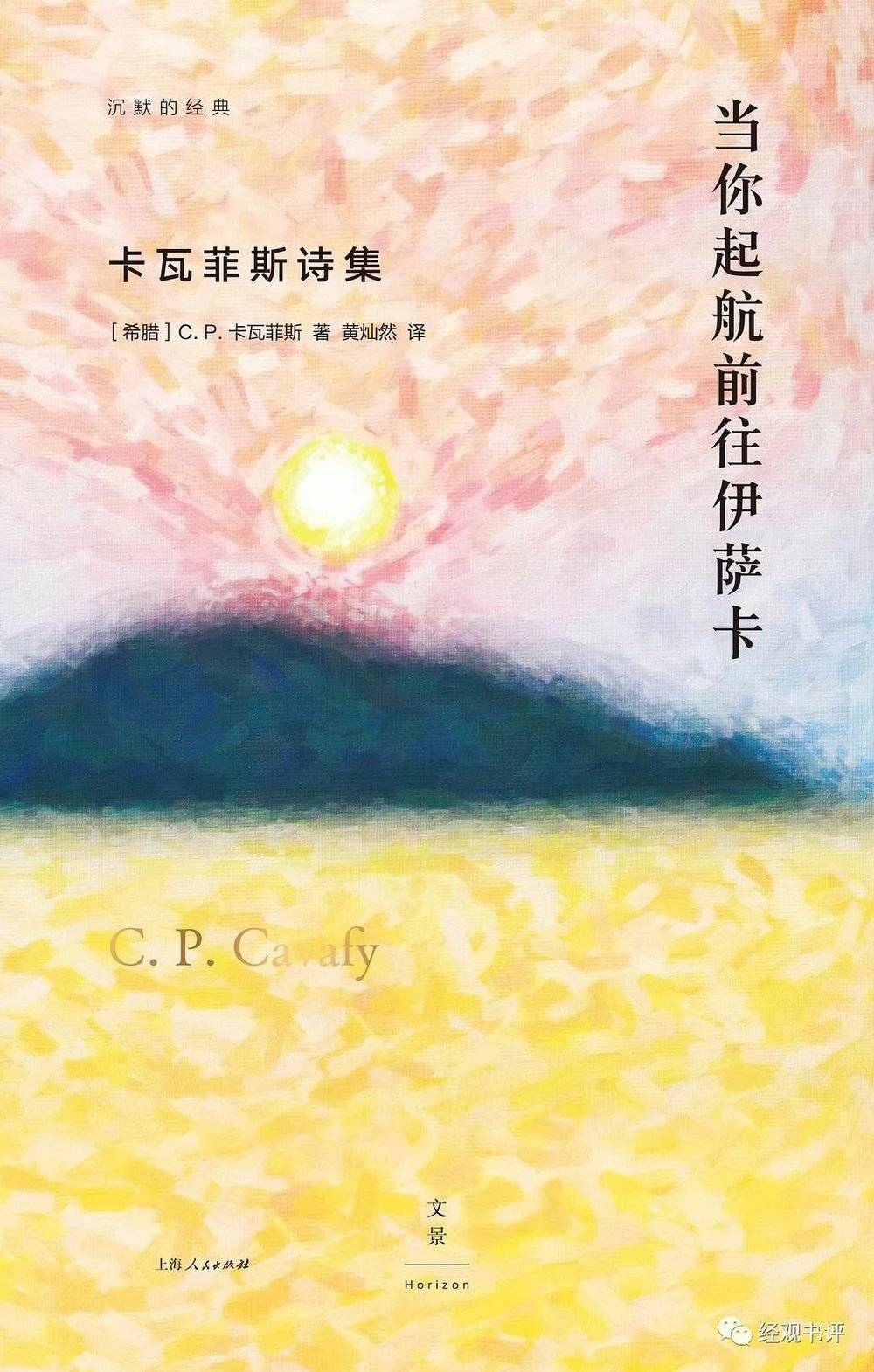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C.P.卡瓦菲斯 /著
黄灿然 /译
楚尘文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我最早接触卡瓦菲斯这首诗,是1980年代后期,上大学时偶尔在一部中篇小说中读到,很喜欢,当时并不知道卡瓦菲斯是谁。那篇小说名字和作者我都记不得了,内容大概关涉恋爱和分别,分别的理由是其中一位觉得自己已经殚精竭虑,却再也不能给相爱的人提供智识上的支持了,他引了一首名为《伊丝卡》的诗,送给自己曾经相爱的人。至今我仍记得其中这三句:
是伊丝卡赐予你如此神奇的旅行﹐
没有它你可不会启程前来。
现在她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
多年后,我读到今译的多个版本的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才恍然自己曾读到的《伊丝卡》就是《伊萨卡岛》。
伊萨卡岛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故乡。奥德修斯献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在回故乡的路上,因得罪海神波塞冬,历尽艰辛波折,突破各种生死考验,同伴死伤殆尽,最后回到故乡。他的传说,后来被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千古传唱,卡瓦菲斯这首《伊萨卡岛》,既有对远行的向往,更有对故土的思念。我年轻时读《伊丝卡》时,还只是一点朦胧的认识。
2013年,当时的我正艰难地主导着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做出了一定影响,却困顿于经营。那年8月,杂志的资方、也是我的老大哥马哥跟我说,到这年结束,他不想再投入了。我特别理解他,能够坚持5年,着实太不容易了。
那段时间,我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有着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沉重和压抑,但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
2013年9月初的一天,我找了套中华书局的《诗经注析》,开始抄读《诗经》,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磨砺自己,自我宽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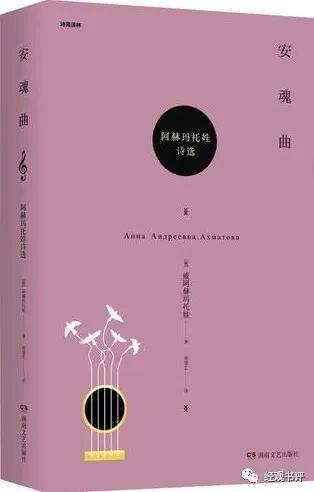
《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诗选》
[俄]阿赫玛托娃 /著
曾思艺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9月9日上午,在家偶然翻读到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是黄灿然翻译的,我一人躲在书房,朗读了一遍,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用签字笔抄录了其中一段:
你要把伊萨卡永远记在心上。
到那里去,是你的命中所定。
但是,请不要匆匆地到达,
最好要走很多年,
这样,当你登上那个岛屿,你已经老去,
满载着一生积累的财富,
而不要指望伊萨卡让你富有。
伊萨卡给了你神奇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不会去远行。
而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给你,
如果你发现她清贫,她就并没有骗你。
那时,你早已满是智慧和历练,
你一定会明白,伊萨卡对你意味着什么。
这一段,我当时感悟到的,与奥德修斯的原意不同,却有着我大学时代读到内有《伊丝卡》的小说的意思有些相同。这几句话,于我而言,那本杂志以及它所代表的媒体梦想,或许就是我心中的伊萨卡;同时,我内心也有某种自许,即我对媒体的理解,对于我的那些年轻的同事来说,是他们媒体生涯的一种伊萨卡岛;对于马哥来说,付出了巨大代价,看到了我们的努力,以及有某种金钱、地位未必能够带来的体面,与有荣焉。
那一天,我抄完诗时,简单扒拉几口饭,背着包出门步行了5公里。眼前的风景,是如此清亮,再无灰蒙蒙的压抑感。
二
也就是从2013年9月9日这一天起,抄诗正式列入了我的日课,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和晚上睡前(没喝多的时候)最后一件事,就是抄诗。要是哪天不抄诗,我会觉得生活中缺了什么。没想到,这一坚持已经10年了。
我上大学时,钢笔字在同龄人中其实不是太差,当过兼职誊写员。曾经为老师抄写过论文,一块钱一千字,最多一天能抄1万7千字。右手中指上的茧,很多年才脱掉。
兼职誊写员相当于勤工助学,活儿并非经常有,但我大学时代也喜欢读诗、抄诗,这纯粹是爱好,尽管自己一首打油诗也不会写。本来,我的大学时代,写诗抄诗送女同学是恋爱的开始,但我没有,或许不敢吧。
及后个人电脑普及,用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一手写得还不错的硬笔字也就废了。在微博时代,我抄的诗会放在微博上晾晒。晾晒并非得瑟自己一手好字,而是希望一种外在监督。
这种监督,在我有两种考量:一是让熟悉的陌生的朋友们监督我的坚持、我的韧性,毕竟人皆有惰性,做一件事,放弃比坚持更容易;二是重新拿起硬笔后,曾经被键盘掌握了的手指,几乎拿不住笔了,写出来的字歪七扭八,与当年完全无法相比,连自己都觉得丢人。但是,字如其人,我是个要面子的人,写得不好被人指点批评,其实就是一种督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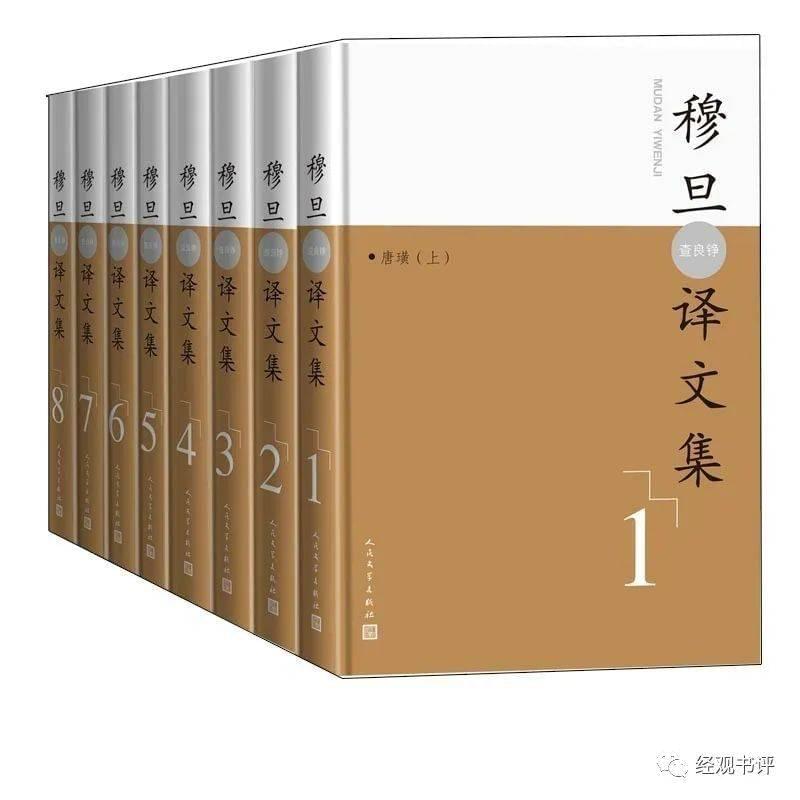
《穆旦译文集(全8卷)》
穆旦(查良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2015年6月27日晚上,乡邑友人、女作家赵波的《像候鸟一样飞》在北京的分享会后,餐桌上一位先生突然跟我说:“你就是朱学东啊,我在微博上关注了你,看你抄诗,我一开始心想,这么丑的字,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没想到,你坚持下来了,还在抄诗,字竟然变化这么大。嗯,坚持确实有效果。”
当然,变化的不仅是自己的硬笔字。我后来改用小楷抄诗,同样从磕磕绊绊歪七扭八起步,到如今,一手小楷抄的诗,虽然野狐禅没有章法,却也自有可观处。
加拿大作家格拉德威尔曾在他的《异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一万小时定律”:“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我知道这个定律很晚,这辈子也许除了睡觉之外,所有再自律的单项努力,也达不到一万小时了,抄读诗词也是。但成为一个专家并非我的追求,我享受这一过程本身。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以后实在混不下去了,可以在路边摆摊替人代写情书家书谋生了。旧时代这也是一种落魄秀才的营生,尽管如今人们多已不在乎家书情书了。
这是10年抄诗的直接收获。写好一手硬笔字或小楷,并不会带来商业上的成功,带来荣耀,但是,却有一种自我满足的自得。
中国人好讲字如其人,扬雄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虽然从统计学上说,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但于我个人而言,却真的在乎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我一直喜欢第二国际伯恩斯坦那句名言,曾把它作为座右铭:“终极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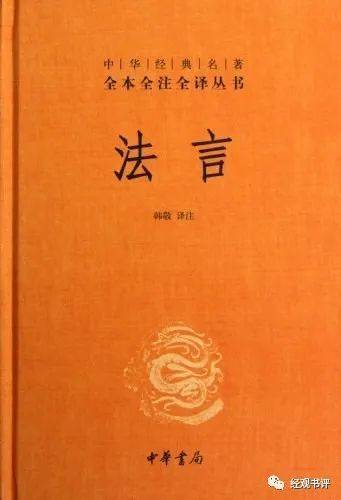
《法言》
扬雄 /著
韩敬 /译
中华书局
2022年3月
旧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虽不会吟诗,但常聆清音,俗耳针砭,诗肠鼓荡,读到的是言为心声,还是言不由衷、花言巧语抑或强作解语,我还是能读出来。
虽然不会写诗,但我在写文章时,常常能恰到好处地引用一些诗人的诗句或名句,或知者甚少之句,一旦引用,却能让我的文章增色不少。这来自于自己对诗歌的大量阅读,这是抄诗的又一个直接后果。
三
2023年9月5日,我抄写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的时候,这首诗忽然击中了我心中的痛苦,让我的郁结豁然解开,有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的《礼物》(西川译)的感觉: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2014年,当我离开那本杂志后,选了叶芝的《十九世纪及其后》,为自己的新生活歌唱,愿这样慢慢老去:
虽然壮歌不再重唱,
我们有的也乐趣深幽;
岸边的卵石咯咯地叫,
在海潮退落以后。
在我遇到压力的时候,我想起的是德语诗人威廉·格纳齐诺的一首小诗:
我想跟这片灌木丛一样,
每天在这里抵抗着
既不消失,也不抱怨,
更不说话。
它什么都不需要,
也不被征服。
这首诗颇有关汉卿铜豌豆的味道,当然审美愉悦要胜过铜豌豆。而在决定离开媒体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叶芝的《茵纳斯弗利岛》(袁可嘉译):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其实在叶芝的诗歌中,尤其是关于老之将至的诗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茵纳斯弗利岛》。
当我离开职场熔断职业生涯之后,我最喜欢的是乡邑前辈唐荆川的诗句:“世网幸疏如野马,微名犹在愧山樗。”当然还有龚定庵的“侥幸故人仍满眼,猖狂乞食过江淮”。也会篡改辛稼轩的词自我宽慰:“人间路不窄,杯底有大道。”
我觉得我的情绪喜好,合了中国的诗教传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说的“诗”,即《诗经》。《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虽然旧说诗教的传统都是以《诗经》论教,其实扩展到其他能够反映人类情感的诗歌,也多有教化的意义。
而我抄诗,教化就在抄读过程的潜移默化中,在春风化雨中,在润物无声中。在与纸张交互的沙沙摩擦中,在他人或美妙或悲伤或欢愉或愤怒的有韵律的文字世界里,逐渐体悟到了别样的宁静和激动。跟我读过的许多书一样,即使没能记住具体的诗句,但诗歌所代表的精神,却已在我心。当然,这也是我在写文章时总能找到合适的诗句表达的原因所在。
这么些年抄读下来,我个人的性格和精神世界,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脾气虽然依旧暴躁,但远不如从前一触即发,不仅对人宽容了许多,争名逐利之心又退化了许多,内心平静淡然了许多。生活中充满了自得的乐趣,又何须在蜗牛角上跟人争雌雄。
旧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则自我总结,抄诗就是一种灵魂的自我秘戏。而内心平静淡然了,并不意味着我见到社会问题会真的不关心,我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关怀社会,当然,这也是为自己。
我非常喜欢阿赫玛托娃的诗。2014年国际诗歌日,我在央广中国之声做直播节目,便借用了这首诗来表达我对诗歌和阿赫玛托娃的热爱:
你领我去向无路之地,
穿过黑暗像一颗陨星。
你是苦难和错误的信仰,
但却不是安慰……绝不。
诗歌是苦难和错误的信仰,但却不是安慰,绝不。仅2014年,我就抄了阿赫玛托娃的那首不朽的长诗《安魂曲》3遍。
1957年4月1日——我出生前正好10年时,在《安魂曲》这首巨制的代序里,阿赫玛托娃记下当年在列宁格勒监狱等候儿子消息17个月时,与一位陌生的、同样等候亲人消息的犯人家亲属的对话:
“您能描写这个场面吗?”
我说:“能。”
当时,像是一丝微笑掠过曾经是她的那张脸庞。
这段隐含着历史残酷性的对话,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影响。它让我今天依然花费大量时间坚持写流水账。
王小波曾说到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拉斯的《情人》和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对他的写作影响最深: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诗不光是押韵的,还有韵律……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字,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
也因此,我开始抄诗后,非常认真抄了穆旦译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抄了穆旦译奥登的《中国组诗》(抗战时大诗人W·H.奥登和依修伍德来到中国,后来出版了《战地行纪》,内有“中国组诗”,当时穆旦是陪同的翻译),抄了穆旦译奥登的名作《悼叶芝》——当然也有穆旦自己的诗。

《叶芝诗选》
[爱尔兰] 叶芝 /著
袁可嘉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0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说,奥登的《阿克琉斯之盾》的第六节,“应该镌刻在所有现存国家的大门上,镌刻在我们整个世界的大门上”:
一个衣着褴褛的顽童,
在那空地漫无目的地独自闲逛;
一只乌儿从真实的石头上溜之大吉;
两个姑娘遭到强奸,两个少年残杀第三,
这就是他看到的公理,他从未听见,
任何世界会信守诺言,
或任何人因别人痛哭而呜咽。
如今我也已近暮年,没有曹操烈士暮年的不已壮心,却有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羽扇豆》的感觉,它是如此地击中我,也许,正是我这个年龄,最容易被如此平静地描摹一棵羽扇豆一生的诗击中:
它们站着。只站着。便具备某种意味。
即使它们变得发白了,也绝不会退缩。
10年来抄读的诗歌,成了一种精神的自我涵养自我完善,是一种个人的向内在的流亡,一种个人的形而上的奋斗。那些诗歌会时时提醒我自己,不堕落,不同流合污,哪怕被时代抛弃,自己的信念也要自己持守,保持自己的审美趣味。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自我存在的意义。诗歌和书籍,就这样影响了我的精神世界,一起参与并形塑我的余生。
借用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里,将奥登、斯彭德和爱尔兰诗人麦克尼斯视为“精神家庭中的亲戚”的说法,我抄读的许多诗人,也是我“精神家庭中的亲戚”。
四
奥斯卡获奖电影《死亡诗社》中,基廷老师这样告诉他的学生为什么要读诗写诗:“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充满激情,诗歌美妙的文字里呈现的那些美好的情感,悲伤的命运,欢愉的生活……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正是因为对世俗生活的爱,在一个粗鄙的时代,抄读诗词也就成为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规训。
我抄读的诗,多分享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和朱学东一起抄诗吧”的活动。当时和我一起抄读诗词的朋友,从学生到年长者,各行各业都有,俨然成了一个小运动。
一位我尊敬的大姐曾经跟我说:你抄我读,你选的诗很好。一位大学学妹通过朋友转达她的谢意:每天晚上休息前,读我抄的诗已经成为习惯。“朱老师,我特别佩服您,每天坚持抄诗写小楷。坚持,则有万水千山!”
如今我早已退出了微博,很意外的是,依然有人坚持抄着诗,且还冠之以“和朱学东一起抄诗吧”的话题,截至2023年9月21日晚上9点,话题阅读量1.2亿,话题贡献最大的是一位网名叫“莫草阁”的女网友,当年她开始抄诗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如今仍然每天坚持抄诗,把时间“浪费”在了抄读诗词这样美好的事情上。
吾道不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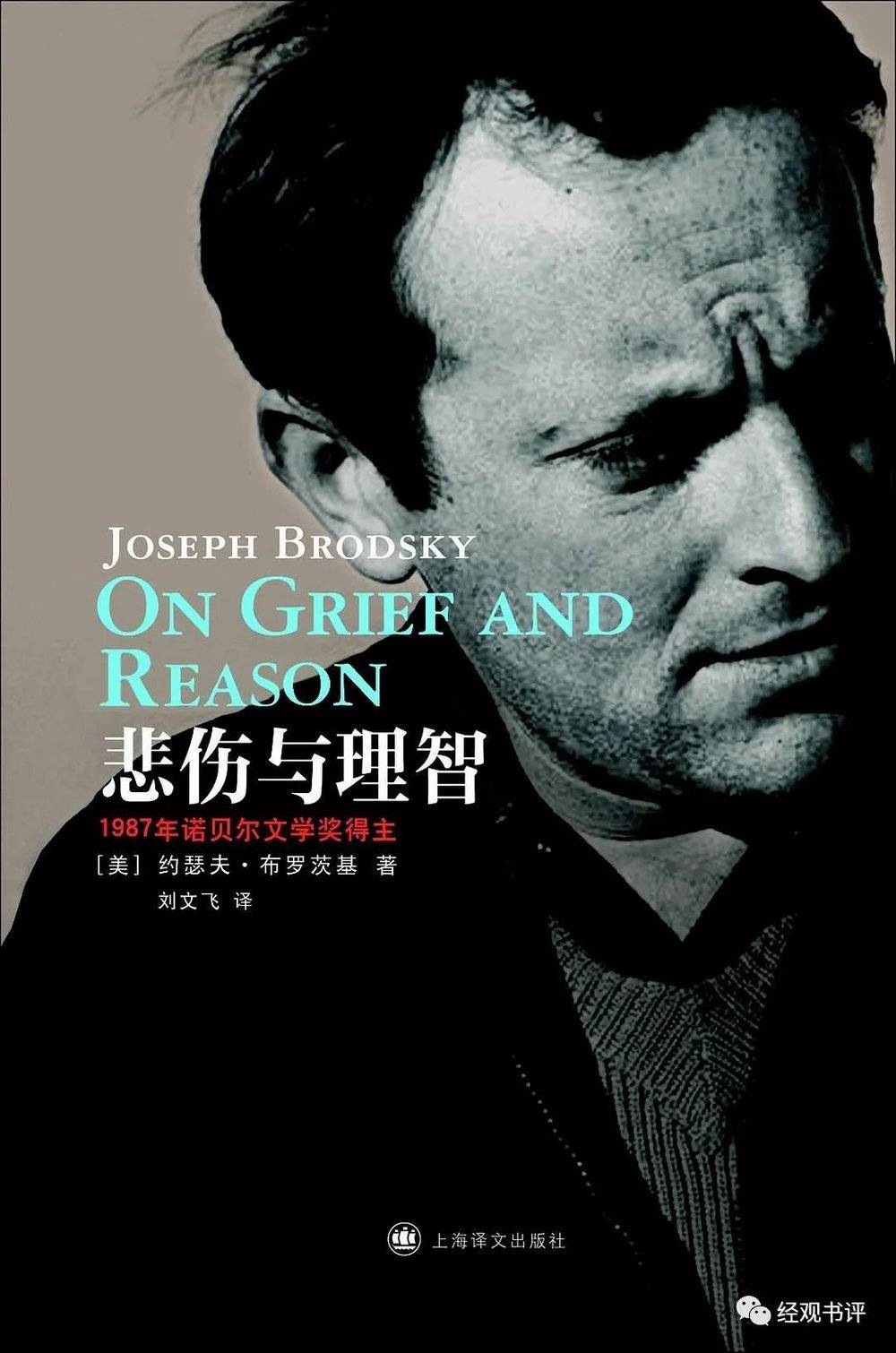
《悲伤与理智》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刘文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4月
这也更让我相信,蝴蝶的翅膀的力量,这就是粗鄙时代里一种哈维尔说的“力所能及的政治”。
假如2013年9月我没有开始抄诗,也许我也能度过自己的精神困境。但是,我这10年间的时间会浪费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一定知道,我的字不会像今天这般。我可能会汲汲利益,或许我的物质生活会比今天好,但我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一定不会如今天这般丰盈……
没有经历过那些巨人海神的人,怎么会理解伊萨卡岛的真正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朱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