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三教九流汇集于此,留下诸多故事传说。一座城的兴衰沉浮,有定乾坤的商业大亨和冒险家,也有推波助澜的底层小人物。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钥匙,租界又是揭秘近代上海的钥匙,究竟是租界里的哪些人,成就了民国魔都的繁华?
史学家叶文心的《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超越既有研究框架,跳脱宏大视角,从民国报章杂志里追本溯源,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为普通人立传上,将市民文化的蛛丝马迹投射到沪上变迁,作者在编织史料的同时不乏解读的趣味性,由此展开一幅沪上社会文化史的鲜活画卷。

《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
[美] 叶文心 /著,王琴 /译
守望者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过往学界往往将上海社会史研究聚焦于名流阶层、左派运动史,而叶文心更看重中产阶级小市民在推动经济上起到的作用,“上海繁华是平常人的城市史。这部城市史改写了近代中国无数平常人的命运”。这些普通人在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身处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沪上打工人在失业危机中风雨飘摇,以微薄之力深耕金融、出版、百货等行业,默默无闻改变着城市的面貌。
一、第一批城市中产阶层
叶文心开篇以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提出的“经济主义”阐释了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以来中国人对金钱的态度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从春秋战国时代以降,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宰着历代封建王朝,直到明代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才有了转机,商人子弟通过科举入仕。中国古代社会层级向来按照“士农工商”划分,士在最上,商在最下,可见其地位之卑微。
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文人、农夫、工匠、商人各司其职服务于民,并无贵贱之分。从那时起,士大夫为了生计游走江湖从商变得习以为常。不惑之年才中状元的张謇弃官从商,言商仍向儒,秉承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开拓者。
自开埠以来的上海则是另一番局面,新式商业崛起,令其一跃成为东亚第一大都会。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帮派军阀、乡绅政客、资本家买办……各色人等鱼龙混杂,淘金为乐者大有人在。从过去无商不奸到商儒相济,近代商人不再受困于道德约束。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还只是贵族的特权,随着上海白领精英群体的壮大,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商学院为职场人提供了学习进修、培训实习的机会,报章杂志和出版机构也为他们指明了生财之道。
“教育的目的不是把学校变成企业,也不是颁发学位来装饰门面,而在于弥合学校课程和企业实务之间的鸿沟,让学生在坚实的学识基础上投身职场”,教育家黄炎培对于职业教育的主张如今看来对于职业能力的提升仍有启示意义。可以说,这批赚得第一桶金的城市中产阶层在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利益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推动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做出的贡献显而易见,与此同时,也在社会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拜金观念。
西学东渐改变着商业运作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人情世故。工厂从师承学徒过渡到了老板雇员关系,上级对下属的规训在德能勤绩上趋于量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投机者遭到了重创,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在团队纪律和效率上提出了更高要求。财富的高度集约化甚至扭曲了道德标准和理性准则,商人在大众的印象中已没有了士人低调、勤俭的美德,纸醉金迷的生活暴露出了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的本性。
上班族用时间买下的生活,到头来却没时间去好好生活。这不是当代人的难题,而是每个时代平庸者的宿命:不甘于现状却又无力改变,日复一日穿梭于家庭与工作之间。
叶文心以中国银行小职员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日常生活为样本,洞察着中产阶级多元化的消费路径以及一言难尽的精神困境。20世纪初的中国银行业以蓬勃朝气示人,能在银行谋上一职的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着他们的是步步高升的大好年华。然而这些看似光鲜的银行职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体面。
上海地标式建筑——海关大楼上的亚洲第一大钟为社会规范和进度的实施定下了有序的基调,为了确保上海这座精密的现代机器正常运转,作为齿轮的上班族在公司制定的日程里“合槽”,消解个性默默付出。“民国时期上海时钟在新型企业中使用,强化了这些企业的经济纪律……单位曾是企业自发、自我规划而产生的一个时间与空间单元,自从单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践的制度之后,就变成了依靠时间纪律来总括集体活动的一个空间隐喻。”
面对严苛的业绩考核,钟表对于员工的管理意义远大于上级。长此以往一板一眼例行公事,服从于一言堂家长制的高层,乏味枯燥已然成为常态。因此为了生存,银行小职员不得不遵从着儒商文化,谦逊修德,遵从上司,私下不免滋生负面情绪甚至深度抑郁。
二、小市民夹缝求生
如果说“民国时期资本主义企业对20世纪中国意义最深长的一个贡献,就是透过以时钟制约的管理哲学,把个人修养德行的经济意义制度化,把个人知识的充实与伦理的实践变成添增加值的经济行为”,那么银行小职员的经济收益可以看作是通过自我实践、修行与研习达成了应得的个人目标。
然而,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学徒练习生、职业青年、个体小商贩、歌女舞女、司机保镖等底层做工人仍占大多数,流动的雇主、朝不保夕的工作,在动荡的环境下安全感极低。这些出身地位略低于中产阶层的“小市民”,经济状况更加不堪,对于高档娱乐场所望而却步,只得和同僚喝酒小赌当作消遣,在寻欢作乐中分散焦虑不安,这更是魔都上海的日常景象。
20世纪初,沪上已然是自由开放、多元化的城市,它是茅盾《子夜》笔下的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赵伯韬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是王安忆《长恨歌》里弄堂女人王琦瑶百转千回的传奇人生。从开埠到开放,上海的“蝶变”有目共睹,上海人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篇章,对于生活的书写也比以往掺杂了更多复杂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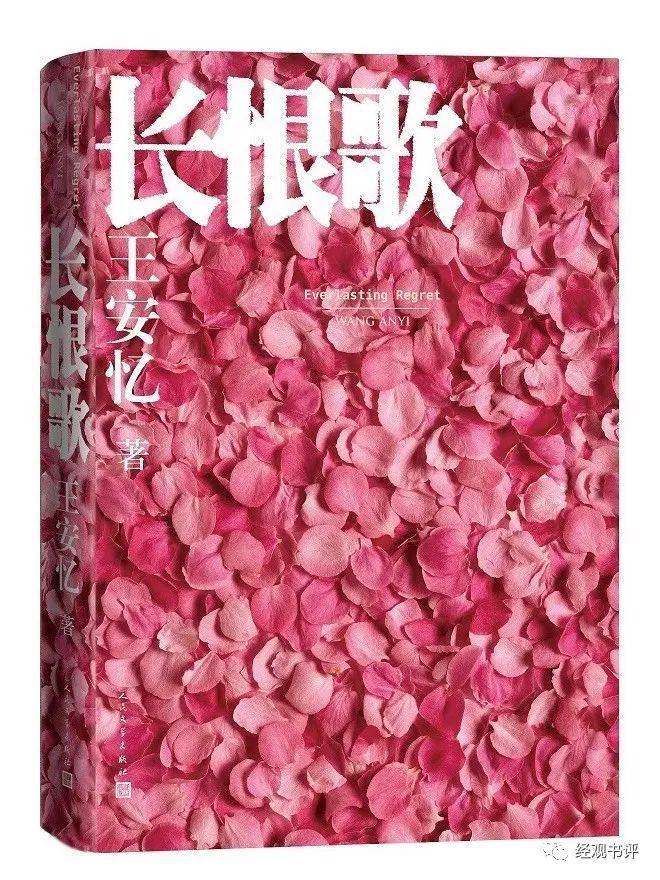
《长恨歌》
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8月
人力车夫、女佣遭拳打脚踢,学徒受虐待被毒打等等这样为了一口饭受皮肉之苦的故事渐行渐远,诗人刘半农有首诗《学徒苦》,生动表现了学徒生涯的艰辛:
学徒苦!学徒进店,为学行贾;主翁不授书算,但曰“孺子当习勤苦!”
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众对于“苦难”这样老生常谈的话题有了全新的阐释:“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能取得成功,无论是物质经济上的发达还是社会地位的晋升,人们总是会看他能不能‘吃苦’。”这样来看,大众对苦难的认知延伸到了不可说的精神世界,身体挨得过物质匮乏,情感却禁不住无声指责。苦难一旦和成功学挂钩,如同个人背负起家族荣耀甚至民族使命,在极端承受下走多远,成多大事就看造化了。在曹禺《日出》的尾声,陈白露一句“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道出了多少命运无法翻盘的底层人的辛酸。
当时两种杂志风靡上海滩,如果说《良友》主打中产阶级青睐的莺歌燕舞、岁月静好,那么《读书生活》则是底层民不聊生、家门不幸的缩影。《读书生活》里所刊登的百姓故事揭露了弱势群体的“苦难”真相:勤俭节约、老实本分的人不一定被命运眷顾,理想的实现步履艰难,吃得苦中苦,也成不了人上人。在男尊女卑的时代,父辈是全家的经济依靠,没有身家背景的女性在社会上往往没有立足之地。“所谓的痛苦,正是因为达不成中产阶级理想化的小家庭。”
《读书生活》的受众,大多是相似处境的底层,因此这些故事读起来颇有共鸣。杂志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资产阶级美梦注定会成为泡影。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民众饱受灾荒贫穷的煎熬。只有团结起来参加救亡运动,实现民族解放,个人的命运才能会有转机。这份左翼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市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助推了爱国运动。抗战时期,师傅、商人、小老板为了活下去赚昧心钱,道德滤镜粉碎,从而改变了他们与员工、学徒之间的商业伦理关系。
三、民国全球购
本雅明在其“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中,从巴黎街道、咖啡店、市场、购物中心、沙龙剧院等城市商业建筑以及游手好闲者、妓女、乞讨者等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体验中,洞悉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化进程。当这一意象挪用在了上海繁华街市,大都市流光溢彩的景观同样能带给观者新奇、震惊的视觉体验。
在魔都这座公众窥豹一斑的奇幻世界,海上名媛从私人社交场走向公众媒介,海报、月份牌挂历、香烟广告牌以及《良友》杂志上的女性形象作为城市流动的景观被观看,刺激底层消费欲望,为大众的审美取向打了版。

《良友忆旧: 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
马国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
与高档洋气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暴露在市场摊位上鲜血淋漓的生牛肉,可以高大上,也可以如此接地气,从精致惬意的小资味到世俗鲜活的烟火气,上海无疑是将摩登与怀旧融合得最天衣无缝的城市,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名不虚传。
做生意讲究的是聚人气,在电力供应受限时期,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租界成为当时年轻人夜晚返工之后消费娱乐的好去处,乘电车参加读书俱乐部、看电影,上海人的业余生活相比内陆城市的人们来说更加多姿多彩。所以说到了大上海,去百货大楼逛逛才算不虚此行,初代网红商场“永安”,如今依旧延续着往日的风光,作为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唯一保留下来一家,“永安”见证了中国现代百货业的辉煌兴衰。早在百年前,郭氏六兄弟就以前瞻性的商业布局在沪上租界黄金地段率先开启了全球购时代。
那时的“永安”,在运作和管理模式上效仿巴黎乐蓬马歇、纽约梅西百货,创下了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商业神话,其倡导的“新、全、奇”一时间成为业界争相效仿的对象。“新”即是将购物理念提升到娱乐和享受,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交易,闪耀的霓虹灯俨然一道靓丽风景线,新式商场橱窗安置嫦娥奔月、圣诞老人等应景的装饰,吸引着路人驻足围观,店里的布局陈列吸睛引流,和街市铺子的随机摆设形成了鲜明反差。
正是这些文化附加值,为买家带来购物以外的惊喜,推动着租界的繁荣,“南京路不仅出售商品,它所生产并让人们消费的是城市投射出来的景象。这景象不是所有店铺和商场的简单拼贴,而是整个视觉产业运作的结果。”
这里不得不提“四小姐”郭婉莹,这位留过洋的“富二代”曾坐镇商场,在选品上自然眼光不俗。在“永安”买得到像西门子电器、派克钢笔、菲利普收音机这样的大洋彼岸尖儿货,作为世界的窗口,洋人也能在此满足东方想象,购得苏州刺绣、江西瓷器、金华火腿等本地特产。而“永安”之所以成为业界标杆,还在于学历颜值并重的售货员,可谓业界一大“奇”观,这些差异化经营点,足以激发公众到此一游的兴趣。
“永安”的兴盛,甚至让上海的老字号也迎来了转机,比如绸布行里的“三大祥”——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以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推出高端定制、西式裁剪等服务,款式多样、价格亲民,同样也是上海滩不可抹去的记忆。
于是,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魔都上海,汇聚了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好物,老字号和大型百货商场的竞争盘活了“她经济”,将中产阶级对国货难以割舍的依恋以及对洋货的热切追捧和猎奇拿捏得张弛有度,这场贯穿于普通人生活中的“土洋博弈”,在周期性的“国货运动”中也难分伯仲,形塑了上海文化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正如叶文心所指出的,“近代上海史的核心,是一个外来事物在地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近代中国城市精英如何协同国家的力量,把外来事物在地化、把曾经令人骇异的现象融合进本土日常生活的过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刘晗、曹望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