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鸳鸯蝴蝶派”作家及其作品,往往如同滞在滤网上的残渣,无法经过纯艺术的检验。尽管它们一度风靡,如今也只能作为衬托那些经典的背景杂音而存在。归根到底,“鸳鸯蝴蝶派”的写作是一种文化工业,以利润为导向。
因此,若以文化史角度切入它们,便可发现在清季民初社会变动之际,一个新的现代知识人的形象被发明了出来,区别于其他古典典范:诸如历朝历代的名士与清流,这些现代知识人更多地服膺于经济秩序而非政治秩序。他们是追求商业利益的职业作家,那个逐渐成型的近代经济体制在他们身上显影,透过他们人生的三棱镜,我们或可窥见这一经济体制的光谱。
美国历史学家林郁沁的《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中国民间工业史》(以下简称《美妆帝国蝴蝶牌》)即以“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仙的生平为线索,透过其写作与民间工业实践,描画出民国时期中国颇具草根色彩的本土“小工艺”的兴衰。“小工艺”这一术语是《美妆帝国蝴蝶牌》一书的核心,陈蝶仙曾长期为各类报刊撰写有关染料、化妆品等轻工业制品的专栏,当时的评论家将这些文字涉及的诸多内容称为“小工艺”。后来,创办了家庭工业社的陈蝶仙,更是成功将他源自“小工艺”的作坊制品变为国际品牌。到1934年,家庭工业社已是中国第二大化妆品与日用品制造商,仅次于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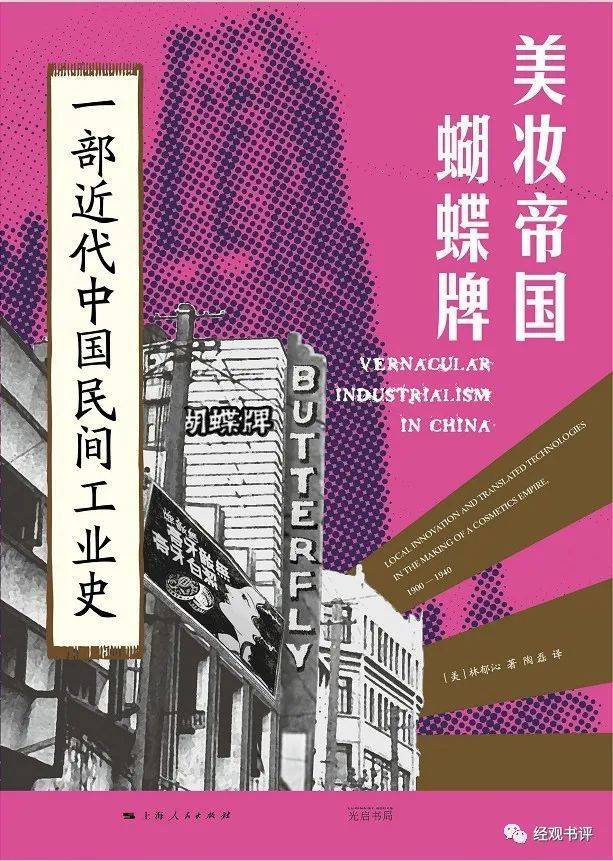
《美妆帝国蝴蝶牌: 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
[美]林郁沁 /著,陶磊 /译
光启书局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在常见的西方中心论历史叙事里,工业的传播路径是一条由西到东的单行道,正是工业,负载文明的火炬照彻了一整片蒙昧昏暗的大陆。由是,通商口岸的开辟往往被此种叙事认定为民国工业的关键节点。尽管我们必须承认通商口岸在引入新技术方面的重要性,但民国的工业,并没有因口岸的存在而沦为殖民主义的内部景观,它们不是锁在八音盒里的音符,仅供给极少数人使用。
若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重述民国的工业史,考察自下而上的微观构建,陈蝶仙倡导的“小工艺”就颇值得关注。它源自家庭作坊乃甚闺阁,比之前述的工业生产方式,“小工艺”有更多的手艺成份。而透过缠绕在“小工艺”之上的诸多话语,以及无数陈蝶仙们围绕着妇女杂志的知识生产,我们便能够管窥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济与性别关系的丕变。
“化妆品制造库”
陈蝶仙事业的起点,在1914年的上海。是年12月,身为职业小说家的陈蝶仙,用“天虚我生”之别号于沪创办《女子世界》杂志。作为民国初年众多妇女杂志中的一员,《女子世界》存续时间并不算长,一年后便告停刊。但林郁沁提醒我们注意,编辑杂志之余,陈蝶仙自撰的“化妆品制造库”(以下简称“制造库”)专栏,可被视为一种“针对性别与特定阶层开展的国货制造”。该专栏服务的读者,是新兴城市中产阶层的女性。开设“制造库”的目的,是要向这些女性介绍在闺阁里制作化妆品的知识。
为何创办后来成为药业巨头的家庭工业社的陈蝶仙,在清末民初之际会提倡自制化妆品,而非购买市场上流通的制成品?事实上,自制化妆品的行为处在传统与现代的铆合点。在礼制社会中,诸如胭脂之类的化妆品往往是诱惑的象征:它将女性牵引到充满未知的外部世界之中。但家庭手工业,一如“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分工所暗示的,是独属于女性的一种家政学。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前期,自制化妆品这一行为从来都充满矛盾,它既显出女性持家的德行,又促使女性涉足科学知识的畛域。由此,“女性”被发明了出来,不单单是作为他者,而是作为改革话语的一部分。改革传统女性与改革传统中国,是一体两面的事业。改革话语尤其关注身体,它将诸如缠足、蓄发之类的身体特质视为国家衰弱的症候。自制化妆品,同样被纳入改革话语之中。这一行为,在节俭之外,也是塑造现代性身体的尝试。
不过,我们仍应该看到,自晚明以来,上层女性便开始从事家庭制造业,譬如在《红楼梦》里,就有对自制胭脂的描写,胭脂同样也是这部小说中的重要意象,暗示着主人公们阴柔多情的气质。改革话语天然地要利用传统话语的外壳,将之切削为合适的器皿。如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洞见,惨烈的革命仍需与旧制度结盟才能得以保全。制度与文化的惯性,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外部的冲击。将中国的近代化视为膝跳反应般地冲击与回应,无疑过分机械,并且忽视了历史的细节。
我们尤其要关注“制造库”的文体特质。1897年,一位名叫裘廷梁的举人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写道:“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近代文学的语言意识由此而来,并非仅仅如马拉美所说,是为了“纯洁部落的方言”,白话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其具有改革国民性的功效。
“制造库”的文体,却并非白话,而是1920年代以前风行的浅近文言:一种减省了典故,含有大量白话成分的文言。故而,我们也能想象到“制造库”文体日后所要面临的责难。拥护白话文的语言改革者们,对陈蝶仙之流的创作不屑一顾,认定他们滥用陈旧的浪漫主义符号,并磨蚀了文字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但吊诡的是,白话文很早就蜕变成一种精英的文学语言,更适应巿场的,仍是“制造库”的浅近文言。
攸关本土的消费
从作家转型为工业家,对于陈蝶仙而言,意味着他必须更积极地涉入利益计算之中。金钱,也正是他自传性的早期小说《黄金祟》的主题。汉学家周成荫在《身为名人的作家》一文中写道,晚清作家喜好戏仿古典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这“得益于新的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包括更为廉价地大量印刷技术,比如平版印刷术和金属活字的运用。这些都使得19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版《红楼梦》的巨大市场,以及一个热衷私人操作的、续写《红楼梦》的产业。”
《黄金祟》同样受益于《红楼梦》。陈蝶仙曾为这部小说的单行本题诗,诗云:“一半凭虚一半真,五年前事总伤神。旁人道似红楼梦,我本红楼梦里人。”小说主人公珊,彷徨于浪漫幻想与现实的家计之间,不得不勉力应对一个日渐塌缩的世界,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滑入命定的崩溃之中。
而从朦胧的文字世界中出来,在五四之后的“国货运动”推动下,陈蝶仙很快学会用民族主义话语吸引本土消费者,家庭工业社的无敌牌牙粉开始与日货争夺市场并最终在国内崛起。当然,中国本土的消费者并非被外部力量推入一个消费社会之中,消费社会的产生,是自明清时期以来市民阶层兴起的必然结果。
正如日本美学家阿部次郎在《町人美学:德川时代的艺术与社会》一书中所考察的由中古转向近世的日本,它与儒教中国类似的地方,在于原本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制的社会,因町人(即商人)的崛起而崩解。尽管德川幕府1649年发布的《告城镇居民》中,仍对町人的日常用度有一系列繁琐的规定,包括町人的用人不可穿丝绸衣裳;家中不可置备描金家具;盖房不可使用金箔银箔雕梁画栋……阿部次郎认为,“町人阶级是德川时代的胜利者”,他们所创造的暧昧、矛盾的平民文化,最终汇入明治大正时期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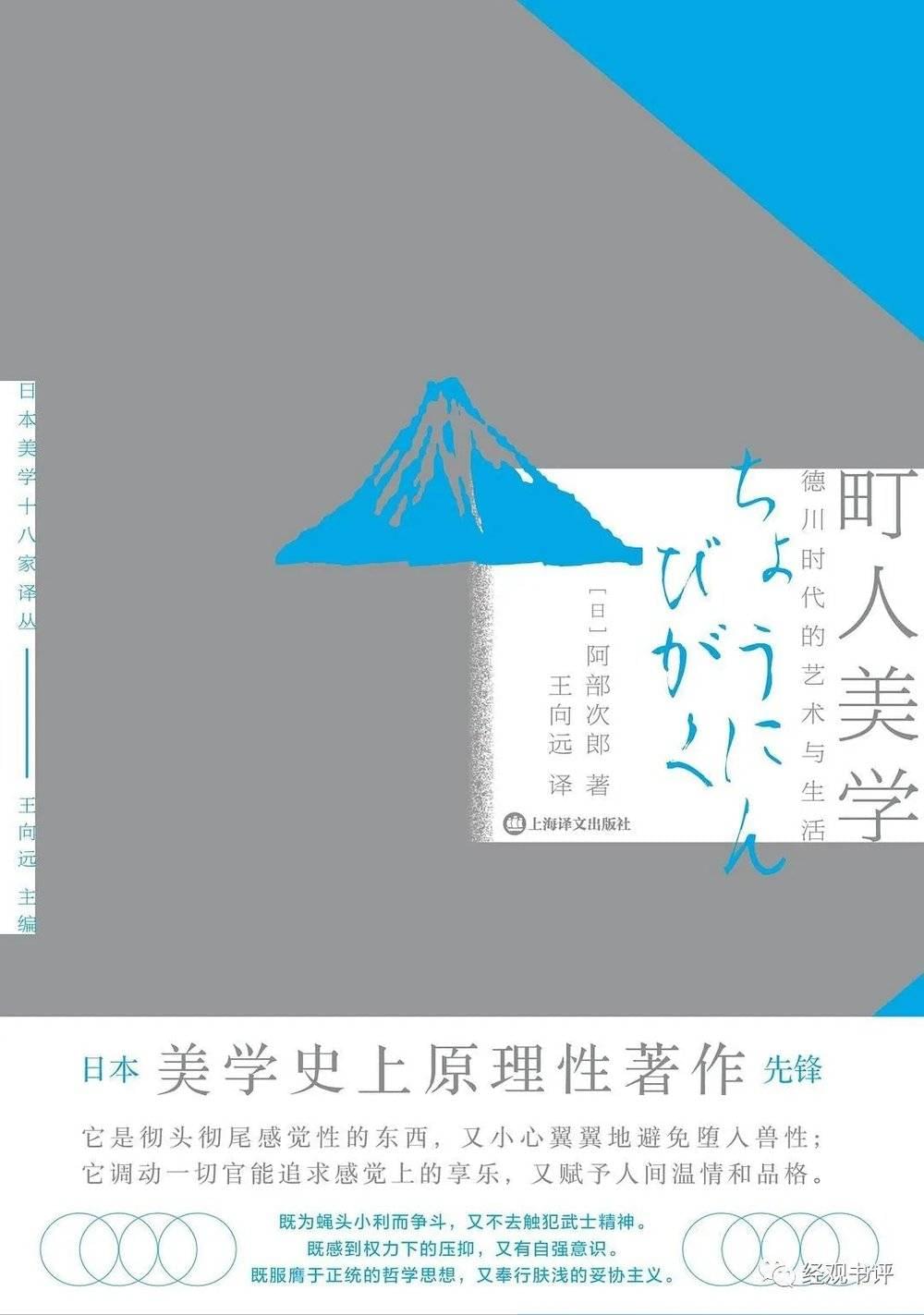
《町人美学: 德川时代的艺术与社会》
[日] 阿部次郎 /著,王向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2月
而在中国,明清时期的禁奢令亦不少见,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大诰》即规定“两京堂上文职四品以下及五府管事,并在京在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俱不许乘轿,违者参问。”清代亦有《大清通礼》颁行于世,但这部文书却从未得到认真执行,清人葛士浚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写道,《大清通礼》“在外不过行之督抚,督抚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县,止有告示一张,挂于署门,遵依一纸,报于上司,州县奉行之事毕矣,原非家喻户晓也”。
如同他的连载小说及“小工艺”专栏,陈蝶仙操持其化妆品工业时,运用的也是所谓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在其专栏中翻译并绍介自制化妆品相关的技术知识之际,他往往会遭遇语言的多重窒碍:拉丁文、德文、英文陷在他的中文里,如同经过一番咀嚼后嵌在假牙里的肉渣,它们是一种昭示着权威性的修辞,却常常拼错,显然,这些文字的作者并没有精习如此多的西方语文,他是一个业余工业家。
而陈蝶仙并未受制于他的业余性,他反过来利用了此种业余性,将之塑造为家庭工业社,乃甚“国货”本身的核心特质之一。即使到二战后,“客厅即工厂”的家庭作业模式,亦是香港、台湾等地区经济腾飞的基础。对此,林郁沁认为,“普通民众被动员起来参与本土主义工业”,是一种后殖民趋势的表现。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或可视为此类路径在20世纪初的预演。
反刍过去,思索当下
《美妆帝国蝴蝶牌》所运用的主要素材,是陈蝶仙之子陈定山的回忆录。但在爬梳个中细节后,林郁沁仔细剃去了陈定山回忆录中为尊者讳的部分,尽量还原一个真实、复杂的陈蝶仙,并以其生平为引,串联起近代中国民间工业的历史。透过对少量档案的逆向阅读,重构出一个已然消逝的社会。
此种微观史学的典范,都以描摹一个相对静态的、日常性的历史主体见长,它们所刻画的此在,仿佛凝在一块琥珀里。此类叙事呼应着六七十年代史学界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运动,在其理论的延长线上,依照葛兰西“消极革命”观构建起来的,则是所谓“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简称SS)。
印度历史学家本杰明·卡扎利亚在《后殖民理论与历史》一文中认为:“贱民这一术语,宽泛地意指着‘非精英’,并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他者或与历史学家所称的自我相异的人”。在SS的研究视域中,历史学家是那些捡拾被遗忘的回声的人。而在其演进中,贱民逐渐被抽象成一个普适的文化符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陈蝶仙们视为非典型的贱民,他们早期的技术尝试常常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是一种“山寨”。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民间工业的当代形态,看到深圳那绵延一片如同雨后的蜗牛壳般紧挨在一起的仿制品市场,我们便能嗅到其身上隐含的贱民气质。
林郁沁有意寻找民国时期民间工业与当代中国“山寨”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她看来,对“山寨”的描述,往往滑入两种极端,一种将之斥为损害原创性的元凶,另一种描述则类似海盗党的观点,将“山寨”设想为一场又一场去中心化的革命,创客们籍此撬动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坚固结构。
而《美妆帝国蝴蝶牌》作为一部微观史学著作的价值,正在于其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视点,能够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立场,重新审视当今社会关于所有权、创新以及工业文明本质的常识,使读者不再被世俗定见与激进的浪漫想象所局限,而能够更清晰地反刍过去,思索当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谈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