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我们会认识到,美国和中国的世纪贸易之争,其影响远远大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之争,作用方向上也许都是相反的。在与日本的贸易之争中,美国更贴近“自由贸易市场”的方式解决了那场被认为是“雌雄之争”的摩擦,毫无疑问它大大增强了美国政界、学界对“自由市场”的信心和雄心,上世纪90年代末,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基本代表了这种盲目的顶峰,以至于在面对中国这样的“沉睡的雄狮”时也壮志踌躇。
但是,中国入世20年后,当我们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并且对政府与市场、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时,美国变得局促不安,尽管这种不安最先以经济利益冲突表现出来,那是因为经济实力是所有短期对抗的基础,长期讲又要看各个国家的科技实力,这种实力,也许更基础的决定变量是适合科技创新的制度供给。
一、非正式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中美之争未来难断,但是这一场世纪之争,对世界影响之深远可能当前无法充分估计。在中美之争之前,就有很多研究“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著述,中美贸易之争开始之后,人们更是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但是否至此就是“大类历史的大分野”,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ford Delong)在他的《慵懒地走向乌托邦》中写道:“一个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经济,每一代都不得不对社会和政治进行革命性变革,而政府要应对这种不断重复的变革,就一直处于一面管理民众,另一方面考虑他们的利益的压力风暴之中。”这种叙事实际上赋予了政治的主动性,似乎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看到政治的积极调整,但事实可能未必如此。
Bradford Delong从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攫取了1870年~2010年的140年,在此之前人类一直活在泥沼之中,在此之后人类快速发展,之前的模式似乎一去不返。2010年不仅仅是经济的分水岭,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政治与文化不满,形成系统性的不稳定浪潮。看上去,人类历史璀璨的20世纪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相应的满足感与获得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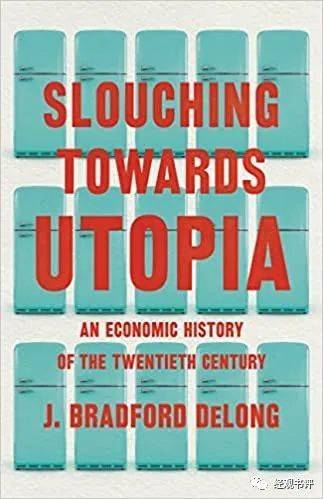
《Slouching Towards Utopia: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J. Bradford DeLong Basic Books,2022年9月
怎么划分人类历史阶段,实际上决定了怎么看待历史的起承转合,也就对推动历史进程的要素做了归因。假如把制度作为人类大发展的前提,那么经济发展后产生的很多问题仍然应该通过政治的途径解决。
近代经济的突飞猛进如果是一场人类社会的偶然,“市场”经济出现后(计划恐怕一直是人类社会大多数政治形态下的选择),出现的很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通过政治制度对“市场”经济进行修正。但是,倘若只有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民主”体制才是可以不断修正它的制度,那么也许意味着“市场”经济才可以供给“民主”制度,且是促进它不断调整的基础,这种互为前提的共生关系可能是造成“历史没有终结”如今又跨进新的世纪的原因。
制度曲折反复的典型土耳其就很值得探究。《失衡的世纪》这本书恰恰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禀赋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经济学家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提升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这些直接原因,开始转向那些影响并带动这些投资,同时又决定了它们生产效率高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深层次原因。”
而制度的影响,又是本书着力的重点,制度并不仅仅是文本上的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通过直接影响各主体的行为以及各主体间的关系来塑造社会结构,进而间接地影响经济结果,但是“一些制度是在价值观、信念、社会规范、群体利益以及权力分配的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能够迅速变化,有时甚至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价值观、信念、社会规范以及相关制度的改变相对缓慢。”
非正式制度可能在很大程度、很长时间内对社会结构、权益分配甚至是正式制度实际发挥的作用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许多非正式制度根植于具有明确界限的社交关系网络中,这些界限既限制了制度涵盖的地域、社会和政治范围,通常又主要为特定群体的私人利益服务,这些利益会增强利益团体阻碍采纳新正式制度的能力。
通览本书行文的组织,作者不失时机地把土耳其的不同历史阶段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口发展、制度变革、产业政策的阶段性以及特殊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等角度进行全面的剖析,造成一种历史纵深感的同时又会有复杂的交错效果。
作者谢夫凯特·帕慕克是一位土耳其的经济史学家,尽管他想要做到全方位刻画土耳其经济的发展轨迹,但是他对土耳其历史、宗教的理解恐怕和普通读者还是很大差距。而和作者不同,我们对土耳其的兴趣恰恰在于它根深蒂固又与众不同的宗教文化发展脉络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土耳其独特又变化剧烈的历史做一个简单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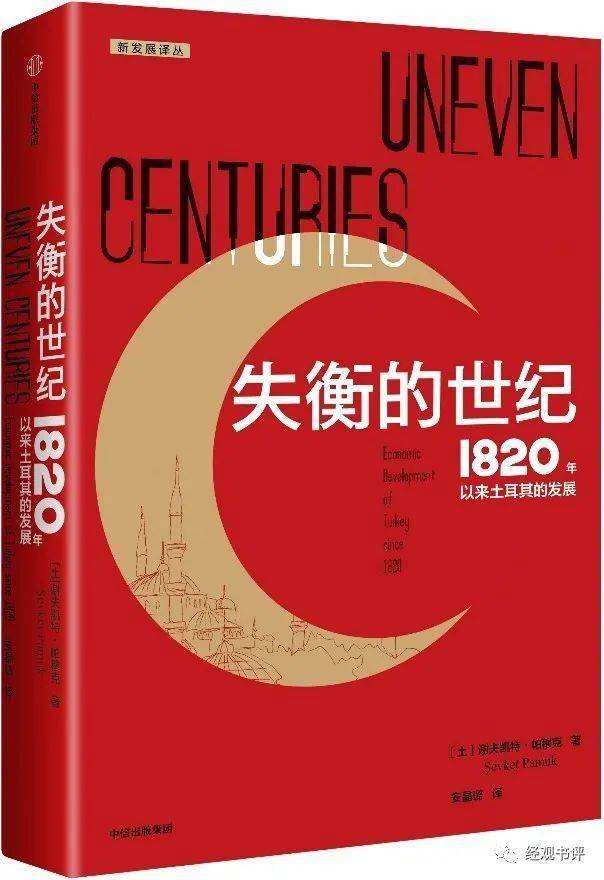
《失衡的世纪: 1820年以来土耳其的发展》[土]谢夫凯特·帕穆克 /著,安晶璐 /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4月
二、土耳其政治与文化的演化
奥斯曼帝国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伊斯兰国家,从溯源上讲其主体民族出身是土耳其人,诞生在一个族群高度混杂的区域,那里居住着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语言上讲着土耳其语和希腊语。这样一个多语言、多宗教的帝国横跨三大洲,足以证明他的建国得益于他对变幻莫测的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和灵活性。
16世纪初,帝国控制者哈里发建立了以多语言、多信仰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官僚体系,导致盘踞在安纳托利亚的苏菲主义和什叶派少数被边缘化为对立势力,与此同时,三股逊尼派伊斯兰势力崛起:当权的正统乌莱玛,神秘与极端派系,传统的市井与公会伊斯兰。
这个时候苏丹律法已经有一些世俗化的基因,到18世纪世俗化官僚开始掌权,19世纪,受到来自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扩张,奥斯曼改革派决心推行国家现代化,转向西方的开明专制。
1820年前后,土耳其开启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虽然这个时候西方在帝国眼里仍然是蛮荒与异端的。这其中包括:废除了禁卫军后随即革除了罚没与充公办公室,让私营经济有了一定安全感;废除了蒂玛尔——即军役封土制度,这是这个善战帝国成立之初即设立的独特的封建制度,它一方面弱化了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同时也走向了更加注重国内经济发展的道路。
同时,苏丹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效仿欧洲政府体例成立对等的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旨在向欧洲观察家们展现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决心。在加强对外交流方面,允许西方在帝国发行报纸(最早1796~1798法国大使馆在康斯坦丁堡发行第一份小报,1820年代陆续出现新的报纸);青年党人(the Young Turks)前往欧洲学习语言,并在欧洲大陆四处旅行,这也意味着,隔离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墙被拆除,自此再无法控制随即流通起来的思想和不断开阔的见识,在强烈的对比之下,这些青年党人产生帝国衰败的失落之情,从而积极坚定地投身改革。
虽然坦齐玛特(Tanzimat)改革时期,军事、教育、行政和司法都开始实施更加激进的世俗化转型,但仍然期望通过伊斯兰意识形态来组织动员民众,拒绝接受西方思想,只对西方的技术张开怀抱。
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ülhamid II,1876~1909)时期的世俗化,是通过在宗教之外设立并行的行政机构以隔离政教,然而政府职能世俗化却导致伊斯兰教愈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宗教事实上主导和占据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凯末尔革命之前,土耳其青年党进一步为之提供了准备,基于涂尔干的实证主义建立了宪政,并展开了关于物质与精神的碰撞的大讨论。
1923年,共和党革命重新定义了土耳其的伊斯兰,世俗化成为凯末尔·阿塔图克建立的新国家的重要原则,所有宗教表达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理,废除了哈里发的地位,判处苏菲派教义违法,阻止一些伊斯兰的神秘仪式,实现把土耳其伊斯兰标准化、限定化和局部化,通过上面的改革,以期让共和的理论和制度统领人们的日常生活。
奥斯曼帝国高度集中的权力和经济体制造成社会原子化,社会关系个人化。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传统的诸如手工业行会、伊斯兰兄弟会、地方宗教和地主阶层的崩坏,社会失去了联结不同精英团体(军队、官僚和法律教育体系)的社会组织、统一宗旨或价值体系。凯末尔可能减小了伊斯兰宗教的影响,但也切断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联系,打破了统一价值体系和文化支柱甚至是身份认同,而这些才是能够保持一个政体合法性的关键。
1950年新当选的中间偏右民主党政府,主要受安纳托利亚农民和小市民支持,他们的宗教生活鲜少受城市居民影响,他们感受到的宗教压制大大减轻,于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宗教情绪不断高涨,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大量恢复,神秘宗教团队的社团活动越来越频繁。到1980年代,宗教复兴变得更为明显,不仅政府态度出现显著转向,宗教媒体和文学也蓬勃涌现。
当然,这个时间不乏对土耳其的“莱依主义”(Laism,政权还俗)与普遍意义上的“世俗化”的争论。造成这个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教育精英和中产对复兴的伊斯兰熟视无睹,直到1980年代,共和党学界和知识分子还认为,只需要通过对农民阶层加强教育,改变他们的文化落后的现状。
近代土耳其政治更迭频繁,1937年正式宣布世俗化,1946开启多党政治,1950年首次公开选举,1980年又恢复军人干政,至此“强化民族文化,摒弃西方影响”为包括凯末尔在内的共和主义人士所拥护,新的一批青年军官反对严格的世俗化,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拨款加强对教育体系的支持,土耳其国内宗教事务理事会预算大幅提高,出于宗教原因的刺杀开始显著增加。
此时也有一些文化是否可以和技术相割裂的讨论,事实证明,世俗化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现代化,仅停留在减少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但允许其成为反对党和保守主义阵营的信仰支撑和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庇护所,使改革路径最终以失败告终。
奥斯曼时期,虽然帝国是多种族、多宗教的构成,但是实行了严格的针对非穆斯林的歧视政策,比如米勒特(Millet)制度和耶尼切里(Jannissary)制度。土耳其在世俗化的同时似乎又有试图减少非伊斯兰影响的倾向。
1913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大批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在奥斯曼政府的施压下, 一些希腊人被迫离开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西部。1919年,希土战争爆发后,起初希腊取得割地,但在凯末尔当权后,希腊占领军溃败,大批希腊人于1922 年及此后离开了土耳其。
1923年洛桑和平谈判期间, 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决定用土耳其的东正教希腊裔人口交换希腊的穆斯林。前后导致百、十万人的迁移。非穆斯林在政府治理中没有发挥和他们经济地位相对等的作用可能也是世俗化从根本上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的另一个佐证。
土耳其的简单历史可以看出,政教分离需要在世俗政治与宗教两个层面各自形成精神的统领,世俗政权并不能仅仅是政府治理的程序与机构,世俗政权需要有独立的目标成为世俗层面人们可以借助这个政权实现追求的途径和达成共识的安排。提高对不同宗教群体的代表性,也是现代化政府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两种方式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看到。
凯末尔革命并没有完成土耳其走向民族国家的目标。相反,改革从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对非土耳其穆斯林裔的歧视与财产剥夺上讲,打击了原本就相对世俗化的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是倒退。
二战结束后,军事政权慢慢走到台前,国内政治动荡,尽管跟随国际经济趋势改革不断,但是正式制度已经深陷军事和宗教的非正式制度泥潭,经济不停地陷于危机之中。1948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北约援助及多边贷款推动了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改革(苏联战后还提出对土耳其海峡领土要求),农业经济迅速恢复,但在经历了集约化发展,农地面积提高等措施后,农业经济贡献于1960年达到顶点,经济再次下行反过来让执政党强化了军事统治,经济上也重返“进口替代工业化”(1963~1977)。长期政局动荡和石油危机导致土耳其70年代末遭受了国际收支危机。
1980年,为了顺应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化浪潮,土耳其也不断的推出新的政策,但是新的政策和制度与既有制度、不断变化的权力分配及国内政治形势间相互作用,并没有实质上改变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间周而复始的关系。
1989年,全面放宽资本账户的决策加剧宏观经济不稳定持续十多年。2001年受益欧盟候选国资格,政治经济制度有所改善,但是2008年,埃尔多安开始建立专制政体,政治经济形式又不断恶化。
土耳其的未来远没有划上句号,近现代过程中的世俗化尝试,没有摆脱宗教在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决定作用。正式制度的改革没能改善非正式制度的环境,非正式制度取而代之左右了正式制度的走向。这可能是“历史没有终结”的原因,那些隐于底层的非正式力量才是决定人类或民族历史走向的根本力量,浮于表面的改革可能引人一时兴奋,但最终可能证明不过是走马观花的纸面乾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秦勇(作者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