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据环球网援引法国媒体消息报道,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本文首发于2014年11月22日,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ID:jingguanshuping),作者:瓦当,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米兰·昆德拉的故事——米兰·昆德拉当年去申请移民,却不知道该去哪个国家,移民局的工作人员指给他一个地球仪让他自己选。他反问道:“还有别的地球仪吗?”这是一则流亡者的寓言,幽默、荒诞,暗含着命运的反讽。
从2003年《无知》出版到2013年《庆祝无意义》问世,米兰·昆德拉整整沉默了十年。这十年也是昆德拉热渐渐落潮的十年。对于一位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作家,“时过境迁”这个词显得过于残忍。但事实无可奈何地表明,昆德拉已日益成为一个老去的文化符号。当他每年都被媒体热炒为诺贝尔文学奖夺奖热门人物时(虽然结果总是令人心酸)——总有读者惊问:“他还活着?!”随着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日远,人们对与之相应的“史前”题材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也在不断降温。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世界处在新的剧烈的政治、文化变迁中,人们似已无暇回忆。同时,知识与现实事务的复杂化,使得人们开始习惯直接使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专业语言说话,而不再倚重于文学,公共知识分子彻底取代了文学家在大众文化中的明星地位。这十年也是昆德拉发现的Kitsch一词由“媚俗”转向“刻奇”的十年,这两个中文译法的含义最大不同在于:虽然两者都指向过度的抒情,但前者意在取悦大众,后者侧重取悦自己。前者尽管红极一时,但后者更切近本源。从Kitsch在汉语翻译中的变化中,也折射出中国读书界对昆德拉长期的误读正回归真实,这为重新解读昆德拉提供了契机。
昆德拉未尝不曾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正如他在《庆祝无意义》借阿兰的眼睛感慨新千年审美的变迁:女孩们全都穿着露脐装,肚脐成为新的性感焦点。伴随着对流行和感伤的模仿,“我们将在重复单一的肚脐的标志下生活。”好在,昆德拉向来视幽默为“天神之光”,他自觉继承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遗产,将喜剧精神发扬光大。
在这部简洁明快的小说里,我们竟也可以看到站在小便池边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加里宁的前列腺炎。历史大场景消解在笑声里,唯有笑声能够瓦解一切坚硬的事物。不可否认昆德拉的小说依然是迷人的,但美学上的程式化也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愉快的结构自由;轻佻的故事与哲学的思考常相为伍,非认真的嘲讽的滑稽的特点”。
二十年前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概括的上述原则至今依然成立,甚至在结构上,《庆祝无意义》也与他之前除《为了告别的聚会》之外的所有单行本小说一样,保留着整饬的七章的复调结构。而《身份》《慢》等作品中的虚拟梦境手法,也不出意料地漂移进这部新小说里。
风格既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形式的凝结,意味着主题的重复。昆德拉曾在《巴黎评论》的访谈里提及:“我的每部小说都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或《好笑的爱》来命名,这些标题之间可以互换,反映出那些为数不多的主题。它们吸引着我,定义着我,也不幸地限制着我,除了这些主题,我没有什么可说或可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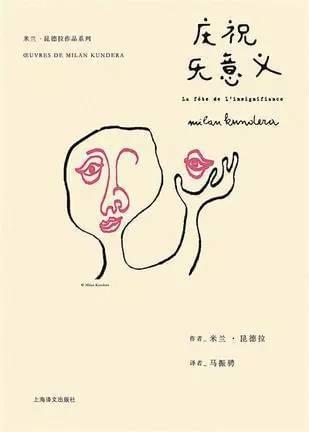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著 马振聘/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7月
昆德拉一如既往地喜欢谈论,他的小说几乎是为谈论而生。《庆祝无意义》既是一部篇幅短小的中篇小说,也可以看做是一本关于无意义的主题故事集。书中寓教于乐地穿插着许多小故事,如斯大林与二十四只鹧鸪的故事、加里宁与加里宁格勒的故事、阿兰母亲的故事……以及夏尔的木偶剧和夏加尔的画展、卢森堡公园的雕像群和鸡尾酒会,构成一座洛可可式的市集,轻盈、细腻、繁复,散发着罗曼蒂克的气息,也充满众声喧哗。
“写作而不制造悬念,不搭起一个故事,不模仿真实;写作而不描述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放弃这一切而只与基本的相接触。(《被背叛的遗嘱》)”
昆德拉永远是他自己最好的阐释者,或者说他的写作是自己写作理论的注解。这既是他小说中最为独特之处,也是最值得商榷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昆德拉几乎把小说变成了哲学读物,这恰恰可能限制了其文学上抵达的深度。多数情况下,生动和深刻二者毕竟不可得兼,而文学应以生动求深刻,不易反其道而行之。
与大多数专注于叙事艺术的小说家不同,米兰·昆德拉本质上是一位戏剧诗人,善于精心营造戏剧化场景,并把戏剧的假定性带入小说中。最经典的例证莫过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和萨宾娜在镜中做爱的情景,《庆祝无意义》中最美妙的桥段则属于凯列班和一位萍水相逢的葡萄牙女仆。
凯列班“坚持不做法国人,而且要充当一个外国人,只会说一种周围人谁也不懂的语言。”由于自己浅褐色的皮肤,便假装巴基斯坦人。凯列班跟达德洛家的葡萄牙女仆说巴基斯坦语,“她也趁这个少有的机会不讲她不喜欢的法语,也只用母语来说话。他们用两种不懂的语言进行交流,使他们互相接近。”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的亲吻有着不可妥协的纯洁。”这种腼腆使他们产生怀旧心理,怀念昔日的纯洁。“尽管我有花心丈夫的恶名,对纯洁却有一种不能消除的怀旧心理”——凯列班深情地说。
沉浸于被自己感动,为想象中的自己感动,这都是刻奇的表现。“不仅是对凯列班——他对自己故弄玄虚不再觉得有趣,对我所有这些人物来说,这场晚会都笼罩着愁云惨雾:夏尔向阿兰袒露他担心母亲的病情;阿兰自己从来不曾有过这份孝心,对此很动情;动情还因为想到一位乡下老妇人,她属于一个他所陌生的世界,然而他对那个世界同样有强烈的缅怀之情。”
自我感动在现实中对应的往往不是善良,相反很可能是生活里的漠然,无谓的撒谎,甚至无谓的残忍。达德洛关于自己行将不久人世的谎言,阿兰的母亲投水自杀后将拯救者溺死,这些行为他们自己也无从解释,却都通向人性的幽暗之处,通向虚无主义的深渊。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古拉格、文革都可以视为“刻奇”泛滥造成的灾难。
按照书中拉蒙的天文馆理论:“天文馆建立在历史的不同点上,人们从那些天文馆说话就不可能彼此相懂”。“即使是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如果生日相差太远,他们的对话也只是两段独白的交叉,总有一大部分不能为对方明白。比如说(阿兰)——他从不知道玛德兰念错从前的名人的名字,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还是她有意滑稽模仿,好让大家明白她对于发生在她本人生命以前的事丝毫不感兴趣。”昆德拉写出了人类深切的孤独,绝望无药可医。
昆德拉的高明在于太善于从肤浅的生活中提炼出深刻,又能将深刻肤浅化,使肤浅的读者觉着深刻,而深刻的读者最终厌弃这种肤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昆德拉的写作本质是媚俗的,绝非刻奇。他以媚俗嘲讽刻奇,他毕生反对的正是伪崇高的自我感动式的刻奇。这再次构成他写作上的悖论。
没有谁能怀疑昆德拉敏锐的命名能力,从“生活在别处”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些书名早已是脍炙人口的格言。现在轮到“庆祝无意义”——既是指的无意义的庆祝,更侧重庆祝“无意义”。当嘲讽与抵抗的对象消失后,嘲讽或抵抗也就失去了意义。达德洛“癌症没有生成”的残生,亦可被理解为隐喻历史已经终结后无意义的余绪。
昆德拉悲哀地看到“我们的玩笑已经失去能力”,世界现已进入“玩笑的黎明,后笑话时代。”“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借助阿兰的梦境,“我梦见的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不是未来的一笔勾销,不,不,我期盼的是人的完全消失,带着他们的未来与过去,带着他们的起始与结束,带着他们存在的全过程,带着他们所有的记忆。”
哀莫大于心死。最后,我忍不住也要刻奇一番——《庆祝无意义》实在是一首虚无的挽歌!虚无又有什么意义?且听昆德拉漂亮的回答:“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挡:不必认真对待。”至此,昆德拉早年从安德烈·布勒东那里领悟到的“对生命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也已瓦解。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庆祝无意义,我们别无什么可以庆祝。
(本文作者系作家,著有《多情犯》《到世界上去》《慈悲旅人:李叔同传》等)
(本文刊登于2014年9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ID:jingguanshuping),作者:瓦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