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作者: [美]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译者: 谢美裕、尤陈俊,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头图来自:《武林外传》剧照
一、没有资财的寡妇
1. 贫困与官方所宣扬道德的局限性
很多寡妇实际上并不具备捍卫清廷所极力颂扬的那种贞节的经济能力。从案件记录来看,寡妇为了替亡夫还债或办理丧事而在他死后很快就改嫁的情形,绝非罕见。实际上,她将自己卖给新的丈夫,在与后者成亲之前用所得聘礼来偿还亡夫生前欠下的那些债务。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份来自清代巴县的契约中看出此种端倪:
立主婚出嫁文约
孙门余氏今因夫身故,遗子孙文榜幼小,家贫无靠,难以苦守。有在城商民汪钊请媒证说成孙,余二姓,余氏自行主许与汪钊为配,遗子文榜,女二姑随母带至汪姓教育,交书聘定,甫养成人之后,孙姓归宗,不得阻滞。当日请亲友街邻众议,出备财礼钱二十六千文整,账目除灵棺木追资费用。当日交足,开销各项明白,认从汪姓择期完聚。日后倘有本族孙姓伯叔人等不得别生异言。此系二家情愿,中间无强逼情由。今恐无凭,立此婚约一纸为据。
永远为照
媒证:亲叔孙芳庳(代笔).孙国甫(主婚)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立婚约人
孙门余氏立
上述文字强调此份契约乃是寡妇主动自愿地订立,并特别言明她是“立”约之人。就此而言,这份契约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婚约文书,因为后者从不以新娘的名义来撰写。该契约的上述特点,意味着人们明白寡妇拥有那种受习俗和法律保障的拒绝再嫁的权利。
由于其亡夫家的姻亲们太过贫穷而无力养活她及其子女,那些没有财产的寡妇于是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再嫁他人(如同上述那份契约中所约定的那样),这种情况看起来颇为常见。我在清代档案中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寡妇让自己后来再嫁的男子保证其亡夫之子不致被迫改从继父之姓。
上述这份契约的目的之一是记下双方商定的各种条件,以便在将来万一闹至官府时可借后者之力加以执行。另一个目的则可能是将寡妇的再嫁之举予以正当化。上述这份契约将寡妇描述为迫于贫困和抚养幼子之需,才不得不放弃守节。这份契约还努力刻画这名寡妇对已故丈夫的忠诚,亦即她是用再嫁所得的聘礼来偿付亡夫的丧葬费用,而她本人虽离开了亡夫的家族,但会确保其子留在亡夫家族的血脉世系之内,故而保全了其宗嗣。换言之,在既有的物质条件下,她已竭尽全力做了一名节妇所应做的事情。
我们无由得知这份契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那名寡妇自身真实的想法;这种契约充其量只是可能记录了她那已被层层(例如常见的书写风格、契约的格式、为她代笔的男性等)过滤的“声音”。即便如此,这份契约仍提示我们,当时的人们时常因为无法在自己生活中实践正统的价值观而心怀愧疚。
雍正十一年(1733)来自贵州遵义县的一起案件,显示了官方所宣扬的那种道德是如何不切实际。郑氏之夫袁瑜(农民)于雍正十年(1732)去世后,她和四名幼子只好向娘家舅妈借钱度日。她的姻亲们虽希望能帮到她,但实在因同样家贫而自顾不暇。这名寡妇在允诺用将来再嫁时所得的聘礼来偿付借款后,才为其亡夫赊到一口棺材。
然而,当她表示勉强接受再嫁后,郑氏发现自己成了香饽饽,因为她生出儿子的能力有目共睹。由于这一原因,并且替她说媒的姻亲也颇为其利益着想,郑氏得以开出较好的再嫁条件。其中一名求婚者是她的表兄弟雷栋(35岁) ,因其妻“没有生得儿女,见郑氏儿子生得多,想娶他[她]做妾”。雷栋通过媒人表示愿意出二两银子作为聘金。但郑氏不愿为妾,同时也担心这样嫁过去的话会对她的那些孩子不利。另一名更具吸引力的求婚者是邹登朝(37岁),其妻已去世且未留下子嗣,故而郑氏若嫁给他的话,则可享有妻子这种完整的身份。邹登朝愿意出五两银子作为聘礼,而这个数额足以清偿郑氏之前欠下的那些债务。邹登朝还表示愿意抚养郑氏的那些儿子,且会让他们保留其生父之姓。郑氏对此表示接受,于是在她的第一任丈夫过世约六个月后,她再嫁给邹登朝为妻。
后来邹登朝被控杀人(被郑氏拒婚的雷栋打了邹登朝,邹登朝在自卫时将雷栋杀死),知县因此留意到郑氏再嫁的时间。我们知道,清代的律典禁止寡妇在夫丧后三年内再婚。当知县就再嫁的时间这一事实问题讯问郑氏时,她试图为自己辩解:
小妇人丈夫留下四个儿子,年纪都小,饿不过,日夜啼哭。小妇人还饿得起,就是饿死了,也说不得可怜,四个儿子若饿死了,把丈夫的后代都绝了。小妇人没奈何,只得嫁了人,好保全这四个儿子的。
郑氏上述所言,看起来是在影射宋明理学用来反对寡妇再嫁的那句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像前述那名声称自己“假顺”的寡妇何刘氏那样,郑氏声称自己是为了其广夫更长远的利益着想才未自尽相随于九泉之下。
针对这名寡妇后一段违法的婚姻,知县也讯问了那位同样也应受到惩处的媒人。媒人的供述十分直白,丝毫不做道德上的掩饰:
郑氏的男人死了,连棺材都没得,后来说郑氏嫁了人就还银子,才赊了一口棺材。他[她]家有四个儿子,因没有饭吃,饿不过,日夜叫唤,那[哪]里等得丧服满?这些人都好饿死了………替他[她]做媒只算做了一件好事。
知县最后决定从宽处理,做出判决称“郑氏虽贫无所依,犹当终丧……第保婴以继夫后,情尚可原……应请原情,免其拟罪离异”。
在本案中,无论是寡妇,还是知县,均不得不以她对其第一任丈夫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忠诚为由,为她在第一任丈夫死之后迅速再嫁的行为做辩解。但是,这仍不免让人觉得,这名知县或许只是迫于那种造成缺乏财产的寡妇在其夫死后再嫁的情况相当普遍的经济现实,才做出了如此让步。事实上,在档案当中,我并未发现有任何一起案件真正执行了那条关于寡妇在为亡夫服丧三年期满之前不得再嫁的法令。
在19世纪,清廷允许对这类案件进行某种程度的从宽处理。嘉庆二十一年(1816),刑部颁布法律规定称,在为亡夫所服三年丧期内再婚的寡妇,在接受惩罚之后,可继续保有与她那位新丈夫的婚姻,除非再婚之前双方之间有通奸行为。
光绪四年(1878)版本的《大清律例》在注释中规定,为了支付亡夫丧葬费用而提前再嫁的寡妇,应在按照“不应为”律处置的基础上减轻处刑(从杖一百减至杖八十) ,并可保有与她那位新丈夫的婚姻关系。至19世纪早期,对于那些因贫穷而卖妻的丈夫,官府已开始采取与上述相同的方式加以处置。这种宽大处理的政策,源于官方逐渐意识到强迫穷苦妇人守节的做法徒劳无功。
2. 性契约之取消
并不是每一位贫穷的寡妇都能有在商议将她再嫁的过程中为其利益着想的姻亲。故而,有些寡妇在得知姻亲将她再嫁他人时订立的契约中所写的那些条件后大感震惊,但为时已晚。特别令寡妇们感到绝望的情形是那位新丈夫很穷。寡妇再嫁的首要目的便是想借此摆脱贫困,她一旦发现再嫁后仍将陷入困顿,则难免会感到惊惧。有些寡妇因此拒绝成亲,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摆脱此类婚姻。
在乾隆四年(1739)来自湖北来风县的一起案件中,寡妇张氏(45岁)拒绝与她的新丈夫蒋昌义(43岁)圆房,结果被蒋昌义杀死。张氏是苗人,而其他主要涉案者皆为汉人。据蒋昌义供称:
小的是个穷人,苦积二十多两血汗银子,费十四两财礼,连盘缠酒水都用完了。娶了张氏进门,原想他[她]同心协力帮小的做人家,不料他[她]看见小的穷苦,又见小的说没有田地,他[她]就不喜欢。头一晚和衣睡到天明,第二夜吃酒后,送亲的客都睡了,小的叫他[她]睡,他[她]只在灶边坐了不理。小的扯他[她]进房,他[她]说他[她]这样年纪改嫁原只图个饱暖,“如今到了你家,你这样穷苦,我嫁你做甚么,你还来缠我”。小的拿灶上的刀吓他[她],他[她]把布衫爬开,挺起肚子说“你要杀就杀,宁死也不从的”。
之后蒋昌义将张氏刺死。
在对这起命案的判决当中,我们再次看到,对张氏守节与否这一要点的斟酌,对于如何评判蒋昌义求欢.这名寡妇继而进行反抗和蒋昌义随后将她杀死之举均极为重要。如果这名寡妇之前同意成婚,那么新丈夫要求与她圆房的行为,以及他在被拒后表现出来的那种愤怒和所做出的某种程度上的暴虐行为,皆可被视为合理。若张氏之前未同意再嫁,则蒋昌义可能会被判定为强奸犯而她将被认为是节烈女子。
如下这段关于该案案情的摘要,详述了张氏与蒋昌义之间婚姻的合法性:
缘昌义于乾隆四年三月内凭媒冉文美娶……张氏为妻,氏翁梁五主婚,得受礼银一十四两。四月初一日原媒及氏堂兄张相荣,前夫堂兄梁文臣、胞弟梁二,梁么子,梁师保,婿张人天德一同送氏至蒋家完配。
张氏与蒋昌义缔结婚姻的各个环节,均举行了恰当的仪式,包括延请媒人,支付聘礼,女方由其亲戚组成的送亲队伍护送至男方家中。且张氏这边有一位合适且具有权威之人(为她主婚的公公梁五)认可此桩婚事。因张氏的父母已过世且她没有兄弟姐妹,于是便由她的堂兄出面代表娘家。此外还有一份有效的婚契被提交给衙门作为证据。
而且,所有的证人均证明张氏自己同意改嫁。蒋昌义的邻居189证实“张氏是好好来的,并没听得有逼嫁的事”。张氏的第一任丈夫的兄弟作证说:“嫂子情愿改嫁,还哥子生前所欠账目,省得日后累他儿子。这再文美替蒋家做媒,讲了十四两财礼,是小的们接收,交与父亲替哥子清还债务。”她的堂兄张相荣也证实了上述说辞: “他[她]先嫁与梁均正,生有儿女,乾隆元年均正身故。张氏有个女儿把与小的做儿媳,张氏就随女儿在小的家住。因他[她]前夫欠人债务,张氏情愿改嫁清还前夫账目,兼且本身衣食有靠。”
由于张氏是自愿再嫁,她那反抗与新丈夫圆房之举显然并不适当,被认为乃是出于憎恶新丈夫家的贫穷,以及(按照知县的说法)她那暴戾的“苗气”蒋昌义被判处绞监候,但由于该案中其新妻子张氏有不顺从丈夫的行为,他在秋审时应可获得减刑。事实上,在该案的刑科题本中,特意提及这名寡妇的再嫁之举并不违背法律,以及她触怒其新丈夫的那种程度。
就贫穷寡妇的生存策略而言,此案当中同样含有丰富的信息。张氏的姻亲答应将照顾她的儿子。但张氏为了安置其女儿,不得不把她许配给堂兄的儿子;作为此项交易的条件之一,张氏在其堂兄处觅得了暂时的栖身之所。但她并无长远的谋生之道,且还需偿还亡夫留下的债务。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她除了改嫁,别无其他选择。她用改嫁得来的聘礼还清了债务,但看起来对蒋昌义家的具体经济状态事先毫不知情,直到过门后,才发觉自己是从先前那种缺乏经济保障的生活进入又一种同样缺乏经济保障的生活当中。
张氏拒绝与蒋昌义圆房,这表明她大体上将这桩婚事视为一种性契约。在这种性契约中,她通过拿自己的性劳动力及其他由她的性别所决定的劳动力,来与一名之前素未谋面的男子进行交易,来换取经济方面的保障。
甫至蒋家,张氏就认定自己被骗了。她心想若无法从这名男子那里获得经济保障,则就拒绝与后者圆房。张氏可能希望蒋昌义会把她退回去,然后再要回聘礼。碰到新娘拒绝圆房的情况时,的确偶尔会有人采取这种做法。此外,张氏并非唯一从契约中所写的那些赤裸裸的条件之角度看待这桩婚姻之人。当张氏拒绝与他圆房时,蒋昌义悲叹自己为了娶上媳妇,辛苦劳作了许多年才挣到娶亲所需的钱;很显然,他也觉得自己被骗了。
张氏的上述情况并非特例。咸丰十一年(1861)来自直隶宝坻县的一起案件,涉及一名“因夫故家贫不愿守孀”的寡妇张郑氏。其亡夫之兄弟张熊将她再嫁给冯中礼,冯中礼为此付了两百吊钱的“身价”。待她到达冯家后,“张郑氏见冯家穷苦,不愿合(和)冯中礼成亲,哭闹寻死,冯家不敢强留”。翌日早晨,冯中礼和其兄弟将这名寡妇送回张家,并想要回聘礼。张熊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在随后双方发生的打斗过程中杀死了一名冯家人。
对这些寡妇而言,经济保障是其接受第二任丈夫的最低限度条件。无论是她们还是她们的新丈夫,均认为顺从丈夫的求欢与其圆房是对妻子最基本的要求。就像其他不幸的新娘那样,这些寡妇拒绝与新丈夫圆房的举动,表明当时在社会大众当中存在着某种广为人知的共识,办即倘若女性想取消她自己不感接受的婚姻,则拒绝圆房是最好(可能也是唯一)的策略。
这种拒绝圆房的策略,透露出寡妇在决定将自己再嫁的掌控力方面颇受限制。一旦她原则上同意再嫁,司法官员便不会插手此事。显然,即使媒人并未顾及寡妇本人的意愿,她也无权反悔。她一旦过门,就成为那名男子的妻子,而妻子这种法律上的身份,界定了女方的义务和男方的权力。摆脱这桩交易的唯一途径,便是迫使她的那位新丈夫将其退回去。
二、拥有财产的寡妇及其姻亲
1. 维持门户与通奸
守节生涯需要有财产作为经济上的依靠。在那些资财富裕的宗族中,比较贫穷的寡妇有可能获得族中义庄的接济,因此不会感到有被迫再嫁的压力。一些宗族用这种方式来购买象征资本( symbolic capital ) ,以增强吸引其他精英宗族的女儿们嫁入其族的能力。
本节所讨论的并非富家大族中的那些寡妇,而是那些尚能勉强糊口度日而不必再嫁的年轻寡妇。这类女子守节与否,取决于她们能否精打细算。正如某位守节寡妇的兄弟所解释的:“妹夫在日置有一石多田,三条(头)牛,(所以)妹子情愿守节。”在我阅读过的大多数案件材料中,寡妇的亡夫生前便已与其兄弟分家,自立门户,一旦他去世,其遗孀便成为这个独立家庭的当家人。
霍姆格伦(Jennifer Holmgren)认为,“若其丈夫在去世前便已分家,那么‘忠贞’的寡妇与其子能在亡夫家族中获得相当程度的经济独立、尊重和权力”。但是,正如那些强迫寡妇再嫁的案件所显示的,若其姻亲心存贪念,则寡妇赖以独立生活的那些财产便容易遭到觊觎,即使寡妇有儿子,也无法幸免。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用曼素恩(Susan Mann)的话来说。“在中国的家庭中,那些性欲依然旺盛的年轻寡妇成了暧昧和焦虑的直接根源……她们在家庭中的存在,难免会制造性诱惑和紧张关系”。
对于那些没有资财的寡妇来说,关于贞节的法律话语儿乎可谓不切实际,但对那些仰赖其亡夫留下的财产度日维生的寡妇而言,守节是其维持生活自主和生计的关键性前提。只要寡妇守节,那么其他人便不能合法地对她的自主权和财产进行剥夺。但她的姻亲们也很清楚,若能劝诱她再嫁,则他们控制寡妇那些财产的障碍就会得以清除。另一个有着同样效果的办法,是将寡妇污蔑为奸妇。我们可以在一名强迫寡妇再嫁的姻亲的供词中看到这种想法:
是小的该死,想得他[她]的家产,起意想嫁卖他[她]……小的到谢氏家劝他[ 她]改嫁,果然谢氏不肯依,与小的吵过一回。小的总想要嫁他[她],小的起意抢嫁……小的逼嫁谢氏,虽因图占家产,原想等他[ 她]到王家去,与王化章成了婚,才敢得他[她]家业。
当双方的争执闹到官府时,无论是对寡妇还是其姻亲的判决,皆取决于该寡妇是否守节;法律只支持有能力证明自己是在捍卫那名已故丈夫之利益的那一方。
这些寡妇多半只有20多岁或30岁出头,并养有幼子。由于需要有人帮忙耕种田地,她们会雇用工人,而她们雇用的对象多半是其亡夫的远房穷亲戚。该受雇男子搬来与寡妇及其孩子同住的情形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农忙时节。受雇的男子以自己的劳力换取最简单的报酬(食宿、衣物或者地里收成中的一部分)。寡妇会替他洗补衣物,而这名男子则与她同桌共食,和她的孩子嬉戏,甚至可能成为她的知心人,尤其是当这名寡妇与她那些亲等相对更近的姻亲不和之时。通过此种方式而形成的组合,毫无疑问属于非正统的家庭形式,但核心家庭所拥有的那些基本要素,在这种情形当中基本上也都具备。
有些寡妇会与她雇佣的工人有染。我们无法知晓这种情形是否会时常发生,但我所描述的上述组合模式,确实反复出现在诉讼案件之中(就像在前面那些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在很多案件的描述中,寡妇主动勾引其雇工并与他发生性关系,雇工则可能是由于太穷,不敢冒着得罪女东家而失去工作的风险。虽然也有例外,但这种对一般公认的家庭权力关系的逆转,亦即“家中的男人”服从女子并依赖她维生,意味着这类女性对她与其性伴侣之间的关系拥有一种或许无与伦比的控制力。
在这种方式中,那种为了能保有自主性、财产和子女的守节要求,与其他的需求产生了冲突。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即便是不实的指控,也足以危及寡妇的地位。
司法档案显示,牵涉寡妇贞节的诉讼,大多并非发生在官方那种超然绝俗的贞节崇拜层面,而是发生在寻常生活的层面。具体而言,略有薄产的寡妇为了维护自家门户的独立,奋力抵抗其姻亲的觊觎,她的姻亲则出于义愤、无耻贪婪或其他更复杂的动机,决意将这名寡妇逐出夫家。双方均摆出一种捍卫父权价值观的姿态,根据法律当中那种关于寡妇之“性”( sexuality )的典范相互争辩。以下将讨论这种争执,以及当事人所相应采用的策略。
2. 利益算计与务实妥协
当然,并非所有的寡妇都始终与其姻亲不和。有的寡妇会与其姻亲达成务实的和解。这种和解未必完全合乎官方的理念,但能使她自身的需求和其夫家的需求得到平衡。
乾隆二十七年(1762)来自山西赵城县的一起案件显示,姻亲在某些情形中可能会容忍寡妇与人通奸。张氏(33岁)的丈夫严思齐于八年前过世,并未留下子嗣。乾隆二十三年(1758)时,这位寡妇的侄子严腊根(其亡夫兄长之次子)过继到她亡夫名下,成为嗣于。
但是,如她后来所供述的,“因腊根年小照看不着家务,原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里雇族侄严国富做庄稼的。他不要小妇人工钱,小妇人替他做衣服鞋袜”。严国富(37岁)供称:“小的见张氏是年轻寡妇,原时常调戏他[她]。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小的与张氏成了奸,后来乘便奸好。”
根据该案刑科题本中记述的案情摘要,这名寡妇的风流韵事,“经氏夫堂侄严秘娃看破,因系家丑,未肯声扬”。张氏与严国富之间的奸情,因此毫无阻碍地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张氏想将一块地卖掉用于还债,但在采取行动前就被其姻亲察觉。张氏亡夫之嗣子严腊根的哥哥严年娃找她的情夫严国富对质。据严国富回忆称,“[严年娃]一见小的就脱下衣服,赤着身子,口里混骂说小的奸他婶母,又卖他家的场地,扑来要打”。在双方之间随后发生的打斗中,严年娃受伤而死。
在上述严年娃的那番混骂之语中,严国富对那名寡妇的性侵占,被认为类似在经济上侵占田地,均被严年娃视为对其家族资产的侵犯。只要这名寡妇的风流韵事不至于威胁到其亡夫家的财产,那么她的那些姻亲便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毕竟将来终会有某位其夫家家族成员去继承这份财产。当寡妇打算卖地的消息传开后,那名雇工严国富便立刻受到怀疑。他被认为肯定是想利用与寡妇之间那种非法的关系,来趁机将寡妇夫家的财产捞到手。倘若这名寡妇因此怀孕,则恐怕也会造成类似的危机。
某些寡妇采取的策略是招赘,亦即拥有薄产的寡妇与一名贫穷男子结婚,招他上门来同住。由于寡妇无须改用这名入赘男子的姓,她勉强可被视为仍属其亡夫家族中的成员。但这种选择,只有在寡妇的姻亲不反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有不少寡妇并没有会对其生活加以干涉的姻亲。
曼素恩指出,中国农民当中常见的是那种三代同堂的小家庭(1929年至1931年间,当时全中国的家庭平均人数为5.2人),因此应该有相当高比例的寡妇没有大伯或小叔。曼素恩认为,那些其亡夫生前乃是家中独子的寡妇享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权利,因为其公婆和幼子皆须仰赖她生活。享有这种自主性的寡妇,无论其操行如何,可能都不会面临被逼再嫁的威胁,因此最有可能采取招赘的策略。
光绪二年(1876)来自江西彭泽县的一起案件显示,那些没有姻亲对其加以监督的寡妇,相对而言更有可能与人通奸、招赘而不会受到惩罚。寡妇吴骆氏与其子吴蕾夏一同生活。同治十一年( 1872),她雇了一名其自家无地的外来移民张春兴帮她干农活。数个月后,该寡妇开始与这名雇工私通,两人在寡妇的卧房内同宿。吴蕾夏(当时已20多岁)试图加以干涉,结果却被寡妇吴骆氏赶出家门。
除了来自其母亲的这种对待,吴蕾夏还惧怕张春兴,且不愿面对其母亲与人通奸的丑事一旦暴露后将遭遇的那些后果,故而尽管遭受恶遇,却不愿采取行动。但随着流言四起,张春兴开始担心自己会被村长赶出村子,因此向寡妇提议招他入赘。寡妇此时并不乐意,可是张春兴以公开两人之间的奸情相要挟,她只好屈服。而寡妇的儿子吴蕾夏(其亡夫家中唯一能代表家族进行抗议的成员),再度放弃干涉此事。
此事数年后才引起官府的注意。因张春兴企图廉价卖掉吴家的田地,寡妇的儿子吴蕾夏这次终于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对亡父遗产的继承权,伙同几名友人将张春兴杀死。吴蕾夏得以减刑,他对其亡父遗产的继承权也得到了实现。此案中,同样是由于威胁到吴家的家产,才引发了吴蕾夏后来的干涉之举。
寡妇吴骆氏和雇工张春兴这对野鸳鸯此前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的自由空间,是因为寡妇亡夫的家族中无人愿意出头或能够干涉此事。清代的律典明文规定只有女子的丈夫或近亲才有权“捉奸”,把奸夫奸妇送交官府治罪。在我阅读过的所有控告寡妇与人通奸的案件中,兴讼者都是她夫家中的近亲、继子或嗣子。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提起诉讼,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通过揭发寡妇的不贞而从中获益。
乾隆二十七年(1762)来自河南遂平县的一起案件,展示了姻亲拥有否决寡妇招赘之想法的权力,以及寡妇若对此加以反抗所可能招致的后果。农夫萧松死于乾隆二十四年( 1759),留下遗孀萧陈氏和三名幼子。次年春节刚过,萧松的哥哥萧逢春、弟弟萧四便和萧陈氏分家,这名寡妇得到萧氏兄弟之父留下的全部财产中的三分之一,即她丈夫应分得的那个份额。萧逢春还安排了雇工王虎替这名寡妇干农活。在王虎的协助下,萧陈氏得以维持独立的家庭,尽管她全家仍住在业已过世的公公的房子中(分家后她得到了堂屋,而她的大伯、小叔则分别得到前屋和后屋)。据该案的案情摘要中所写:
王虎与陈氏素不避忌,二月十五日陈氏曾面告王虎,欲行招伊为夫。王虎允诺,嘱令陈氏向萧逢春商议。萧逢春不允,陈氏即于是夜潜至王虎牛屋成奸,以后时常奸宿……讵陈氏因奸怀孕,于十一月十三日私产一女,当即殇亡。王虎畏萧逢春知觉,意欲逃逸,陈氏出言阻止。迫至傍晚,萧逢春回家闻知,随同萧四向陈氏查问,陈氏直认与王虎奸生,复欲招王虎为夫。萧逢春听闻忿(愤)怒,即行斥辱,欲唤氏父陈志祥一同送官究治。因值天晚,未及往唤,至十四日,萧逢春……遣萧四两次往唤陈志祥,未赴。十六日晌午,萧逢春因陈志祥尚未到家,辄行气忿(愤),当将伊侄萧腊斥詈,并令转告陈氏次日一同进城禀官。萧腊告知伊母陈氏。
当晚,陈氏在将她三个儿子都溺死后自己投河自尽。官府的最终判决把这几条人命皆算在寡妇的那位情夫头上,判他斩监候,理由是他对寡妇的“奸淫”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萧逢春则因未能及时赶走这名工人避免通奸的发生,而受到杖责。
就在萧逢春不同意陈氏招赘王虎的当晚,陈氏主动与王虎发生了性关系。这种挑衅行为可能是陈氏刻意采用的策略,以迫使其姻亲认可她的意愿。因此,当人们发现此事后,她索性公开承认与王虎之间的那种关系,并再次提出要招赘王虎。当面对此种局面时,很多姻亲或许都会不得不接受这种既成事实。
按照当时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平,萧氏兄弟的行为算得上是相当得体。他们在其兄弟身故之后妥善地安置了其遗孀,并尽力帮助她维系自己的家庭。萧逢春看起来对其弟妹与人的奸情是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而并非觊觎她的财产。甚至就算将陈氏赶出萧家后,他也可能仍会替她的儿子保留财产。将陈氏逐出萧家被认为势在必行,从萧家兄弟首先想到的是要找她的父亲过来,便能够看出此点(按照萧家兄弟的想法,陈氏的父亲可协助他们将她送交官府处置,然后再领回娘家)。而在这名寡妇看来,与其失去自己的那些孩子,还不如带他们共赴黄泉。
清代司法档案中呈现的那些节妇的情况,迥异于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所做的描述。武雅士关于中国人婚俗的代表性研究,是基于日本侵略者于20世纪初在中国台湾收集的资料。他指出,通奸和招赘当时在中国台湾北部的农村寡妇当中颇为常见,这意味着寡妇可自由做出这类行为而不会受到惩处。他甚至在一篇论文中断言,对“前现代中国”的普罗大众而言,“寡妇应当守节这种观念没有任何影响力”。
司法案件或许夸大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毕竟它们属于官方制作的文书记录。但我们不应认为武雅士的上述概括涵盖了所有寡妇的情况,或者中国其他地区与历史阶段的情况。武雅士所观察到的高比例的寡妇不贞行为,也许只反映了那种没有姻亲干涉其行动的寡妇的情况。若果真如此,则武雅士的研究告诉我们的是许多女子在能避开惩罚的情况下将会采取哪些行动,但他并未探讨其他女子若采取同样的行动时,实际上需要面临哪些风险。
另一个可能性是武雅士分析的那种“前现代中国”的寡妇之形象,浸染了台湾地区当时独特的政治色彩。在他所引用的资料当中,完全没有关于清代司法官员推行正统观念的记载(毕竟,这部分内容已随着光绪二十一年[ 18951日本侵略者霸占中国台湾而消失不见)。治权更替及许多传统精英选择留在清廷实际统治的地区而离开了台湾,对那些道德标准和财产权利的推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我引用的所有清代案件中,当事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法律的力量对于纠纷两造而言皆是一把双刃剑。在大多数案件中,只有在纠纷的某一方选择告到官府时,州县官才会介入处理。故而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的不贞寡妇都会被官府治罪或者被其夫家的人逐出家门。如果寡妇的公婆仰赖她生活,或者她在夫家根本就没有姻亲,那么她完全可以没有风险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关于贞节和财产的话语,既能被那些有办法证明自身守节的寡妇援为己用,也能被那些有办法证明她们不贞的夫家人所利用。通奸和招赘有时会被容忍,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人们显然非常清楚法律会支持那些对此类行为表示反对的夫家姻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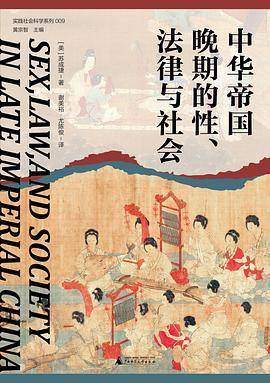
作者: [美]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大学问
原作名: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译者: 谢美裕 / 尤陈俊
出版年: 2023-5
本文摘编自:《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作者: [美]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译者: 谢美裕、尤陈俊,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