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马向阳,题图来源:《黑天鹅》
知名财经媒体人叶檀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原来她生病了,得的是乳腺癌。倘若不是她主动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病情,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今天,不管是病人的主治医生还是陌生路人,为病人保密相关信息(包括相关的疾病名称),据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显著标志,但文明进步并没有消除隐私保护权之下人们对于疾病的诸多偏见和傲慢。根据《济南时报》视频号报道,镜头中的叶檀稍显憔悴,坦陈自己刚刚“进入了一条黑暗隧道”,一头浅浅的黑发似乎刚刚冒出来。叶檀笑言,“癌症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难言之耻”,尤其乳腺癌又和激素相关,更是“隐私中的隐私”。她由衷地希望,“疾病就是疾病,就是不幸,它不应该带来羞耻和自责,恰恰相反,它应该带来爱。”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叶檀主动披露自己的病情和状态,无疑是在向疾病和成见开战。在视频的结尾,叶檀稍显羞涩,摘下头套,露出一头黝黑的浅发,并提及两位曾经和她同样不幸遭受乳腺癌折磨的公众人物:一位是美国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另一位则是美国知名女性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尤其是桑塔格,作为一名毕生都在和荒谬和偏见作斗争的“女战士”,她在1976年患癌症后,曾经历了种种因为此类疾病的恶劣名声所引发的痛苦,医生的不祥预测带来的恐惧和绝望,以及深陷化疗困境时伴随的自我厌恶、自我贬损和自我羞耻感。
痛定思痛,桑塔格于1978年写就了赫赫檄文《作为疾病的隐喻》,向社会偏见和习俗投以匕首,10年后,她觉得意犹未尽,于1988年再度创作《艾滋病及其隐喻》,以批判围绕在当今疾病和大众认知之上的种种社会迷思和“神话性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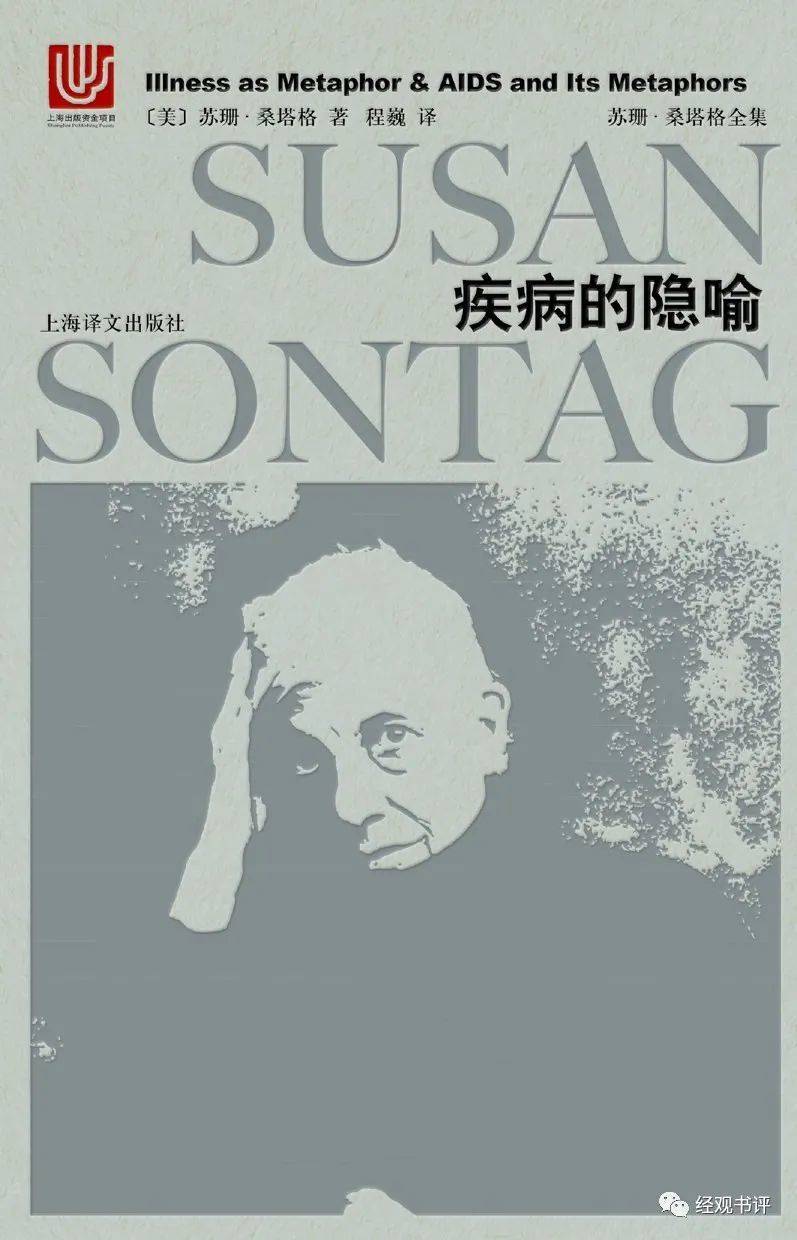
《疾病的隐喻》[美]苏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用福柯的权力话语来形容,过去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围绕身体和疾病而展开的种种救治、隔离、放逐和规训,充分揭示了身体或疾病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权利和道德、世俗力量等不断参与和争斗的经典场域,这一场围绕身体而展开的激烈抢夺,实际上掩藏了太多的关于正确与荒谬、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的神话隐喻和精心修饰的各种权力修辞学。
无处不在的凝视:从愚人船到结核病
按照福柯的知识谱系学,人类自远古以来,对于身体的各种规训,便催生最早的一系列“装置”发明。
愚人船就是标志人类早期“文明”的“装置”系统。1050年~1350年是麻风病在欧洲大陆最肆虐的三百年,这种大规模流行的疾病虽然传染性并不强,且不会立刻致命,但却被视为“上帝之怒”。
在欧洲主流社会看来,患病者不只标识了一种受难,更是一种天谴式的惩罚。由麻风杆菌引发的丑陋的脸部肿瘤,被引申为一种道德判断,患者身体出现的持续不断的病变和溃烂,被看作是一种因为“魔鬼附体”而引发的道德污秽、肮脏和不洁。
根据历史学者帕里斯的统计,从中世纪最盛期到十字军东征结束,当时的麻风病人遍及欧洲,麻风病院成倍增加,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麻风病院多达19000家,仅法国官方登记的就超过了9000家。为了应对麻风病引发的社会恐慌,当时的人们发明了一种叫做“愚人船”的大型船只,将成批的麻风病人装上船,放逐到远离欧洲大陆的荒凉小岛上,任其漂流在茫茫黑暗的大海中,自生自灭。
14世纪之后,麻风病逐渐减少,但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依然没有消失,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贫困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接替了麻风病在人们心中的疯癫和恐惧角色,成为了“愚人船”里的新主人,这些社会边缘者被持续放逐,有些病人摇身一变成了海洋大盗。
从中世纪开始到20世纪末,类似“愚人船”这样的装置被陆陆续续发明出来,从现代医院到敞视式监狱再到集中营,按照福柯的说法,作为一种有效地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标识并隔绝开来的手段,这些装置都充当了代表了文明之规训、惩罚、监禁的权力系统之一部分。
福柯在研究现代临床医院的诞生时发现,在医院这样的现代化装置系统中,医生以一种专业主义为代表的权威眼光凝视每一位病人的身体,通过凝视不仅建立了权威,就连病人也发现自己“暂时不再是一个公民了……他沦为某种疾病的历史”——成为医疗档案里所拥有的图表报告和影像资料。
无论是医生缺少表情的询问,或者是沉默无语的凝视观察,还是冰冷的手术刀以及机械的治疗方案,都揭示了病人身份的一种惊人的转换:病人偕其身体是一种临床医学的实验对象,医生通过分类与对标管理,将病人的身体与病症进行程式化、标准化、机械化的治疗,此刻的病人只有将自己变成小白鼠,成为医疗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才有机会在医院里存活。
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在19世纪普遍流行的结核病上,关于病人连带其身体的处置方式,更显示了世俗道德力量的强烈影响。
在由此构成的关于结核病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疗方案的相关神话性思维中,我们可以列出诸多著名患者的名字:卡夫卡、梭罗、济慈、史蒂文森、雪莱、肖邦、D·H·劳伦斯、爱伦·坡、契诃夫、艾米莉·勃朗特……在经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想象之后,许多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都保存了经典叙述文本:从《茶花女》到托马斯·曼的《魔山》,从司汤达的《阿尔芒斯》到马克·吐温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在许多艺术家、医生、观察者看来,结核病无疑是一种“浪漫之病”——病人通常都被认为是“被太多的热情消耗掉了的人”,甚至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就像《魔山》中借小说人物之口所解释的那样:“疾病(此处指结核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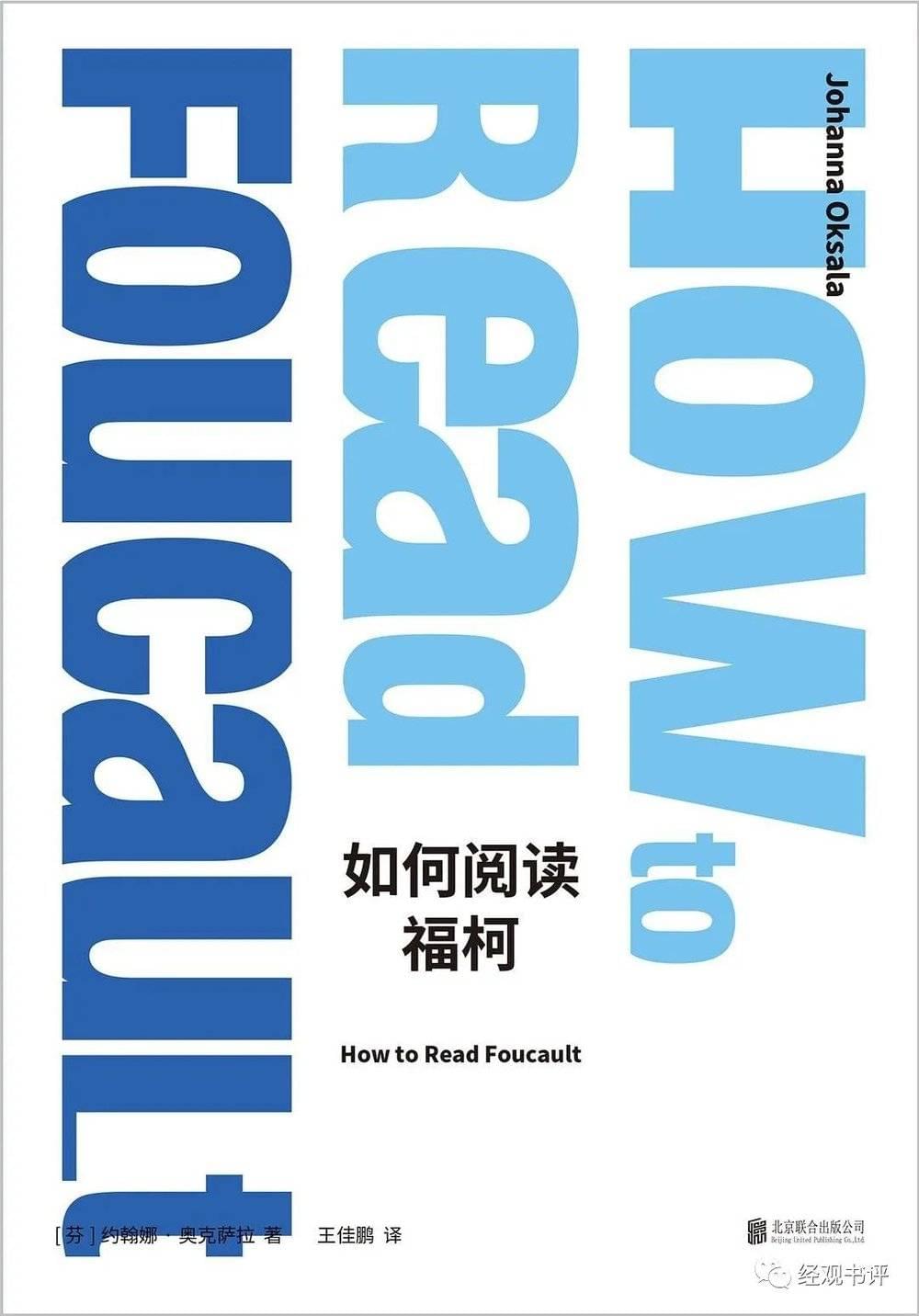
《如何阅读福柯》[芬]约翰娜· 奥克萨拉 /著 王佳鹏 /译 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援引了大量的文本来描述19世纪结核病的神话性思维,这其中突出表现为当时的浪漫主义文艺对于死亡的美化态度,尤其是关于结核病只能诞生于资本主义贵族身体内的经典描述,使得结核病一度被看作是一种优越品性或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结核病患者不会马上死去,而是在加速生命的过程中彻底照亮了自己,使生命变得超凡脱俗。换言之,肉体沉沦,精神却在上升。
想象一下《茶花女》的主人公——结核病人玛格丽特·戈蒂埃吧。她生活奢华,内心却无家可归。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发现,19世纪以降,随着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结核病和交际花经常缠绕在一起,结核病不仅使戈蒂埃显得更加娇弱而性感,更预示了一种高贵的死亡方式,最终使得主人公的情感实现完美升华。
就像作家史蒂文森所描绘的那样,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它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它更新了一种人生信条:人们将在意识上变得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而与结核病人相比较,健康反倒显得平庸而粗俗。这就像把林黛玉和一个酒肉胖子的比较,前者无疑有肺痨之嫌,却有着轻盈的灵魂和高贵的澡雪精神,而后者体魄健康,却只不过是一个沉重的肉身附带无趣的灵魂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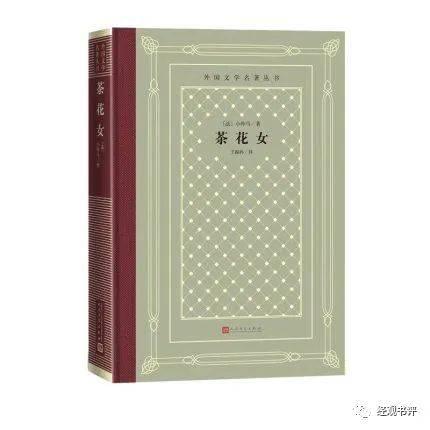
《茶花女》[法]小仲马 /著 王振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些神话叙事,曾令无数才子佳人竞折腰。那些柔弱的、气息很浅的年轻女子与苍白的、佝偻着身躯的年轻男子唯恐自己没有机会能够染上这种在那时几乎无药可救的,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的、非常可怕的疾病。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结核病的死法简直太美了!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不止一次望着镜中的自己喃喃自语:“我宁愿死于痨病”。
“为什么这样说?”他的一位朋友1810年10月间去雅典拜访他时问道。拜伦回答说:
“因为女士们全都会说:‘看看可怜的拜伦吧,他弥留之际显得多么有趣啊。’”
写到此处,桑塔格也不由感慨,浪漫派给结核病带来最主要的礼物,并非是什么残酷美学或者说疾病之美,甚至也不是对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的追求,而是那种关于“如何生活才能显得有趣”的虚无而感伤的情感表达方式。
直到1882年,科学家罗伯特·柯赫发现了结核杆菌,并指出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首要病因,继而1944年链霉素被发现,关于结核病的神话才逐渐解体了。
普遍的对象化:从癌症到艾滋病
无论是世俗势力或者宗教力量对于疾病的道德评判和心理评判,还是专业权威医生凝视的目光中咄咄逼人的权力判断,若干世纪以来,关于身体的争夺都是一个主体性逐渐丧失、病人的身体被不断客体化、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以专业主义和科学之名对身体进行各种征服、统治和宰制、并让这种处置从私人领域逐渐向公共领域进行转变的过程。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的两篇论文中,桑塔格有意将19世纪流行的结核病、梅毒和20世纪的代表性疾病癌症、艾滋病并列,进行一系列影响深刻的比较分析。
如果说结核病源于激情或过剩的热情,那么20世纪的流行的癌症则被视作是源于“情感压抑”机制所导致的不治之症,癌症毫无疑问只会带给患者更多的羞耻感——癌症患者通常被视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一种不能正常表达欲望、感情、甚至性生活不能正常满足或者是激素紊乱的人。癌症病人同样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拿破仑、格兰特、塔夫特、汉弗莱、兰波等大人物,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弗洛依德和维特根斯坦也赫然在列。
梅毒、癌症和1983年才被正式命名的艾滋病,往往和道德堕落、缺少生命活力和性生活紊乱划上了等号。尤其是艾滋病,因为涉及到性传播这一途径,更被视为一种瘟疫,是一种对社会整体道德感的审判,更是一种特别降临于西方同性恋者头上的“天谴”。尽管艾滋病在最初流行时本来是异性间的性传播,这一事实早被许多道学家置之脑后。
癌症及其寄生于这一疾病之上的诸多隐喻,更多反映出当代社会文化中的诸多危机:我们对于死亡的阴郁态度,我们的情感焦虑、以及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感。晚近的艾滋病更标志了今天社会的“道德破产”,甚至是预示着一个“世界末日”正在来临。
几个世纪以来,被抢夺的身体,正在变成一系列可见的、可以清晰描述的数字、资料、病历和知识体系,病人的身体也不再被视为身体本身,它只是我们需要救治、惩罚、监控、放逐的管理对象。在全球化带来的更加猖獗的、无边界的瘟疫大流行面前,国家、政府以及专业医生,都非常喜欢用军事隐喻来表达对疾病的态度——为了赢得这一场“战争”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各种纷繁的检测装置和数据代码,逐渐取代临床医生的目光,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看不见的、无处不在的凝视。
在一个更加没有边界感的全景敞视空间中,我们应该警醒,不要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面部识别等等所有这些新发明的文明装置和系统,变成一张“一直在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结实的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马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