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刘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201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土耳其学者M.许克吕•哈尼奥卢的《凯末尔思想传记》;2017年,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译本,书名改为《凯末尔传》。此书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的历史生平叙述甚少,主要集中探讨凯末尔的思想来源,确实更像是一部“思想传记”。
《凯末尔传》首次对凯末尔的思想生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通过探讨凯末尔的思想来源、形成过程及其内容,展示了凯末尔从在萨洛尼卡——这个动荡的“马其顿民族大熔炉”——作为穆斯林男孩的青年时代,到他在非宗教和军事学校的教育,再到他拥抱土耳其民族主义、参与“青年土耳其党”到创建土耳其共和国——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世俗共和国——的精神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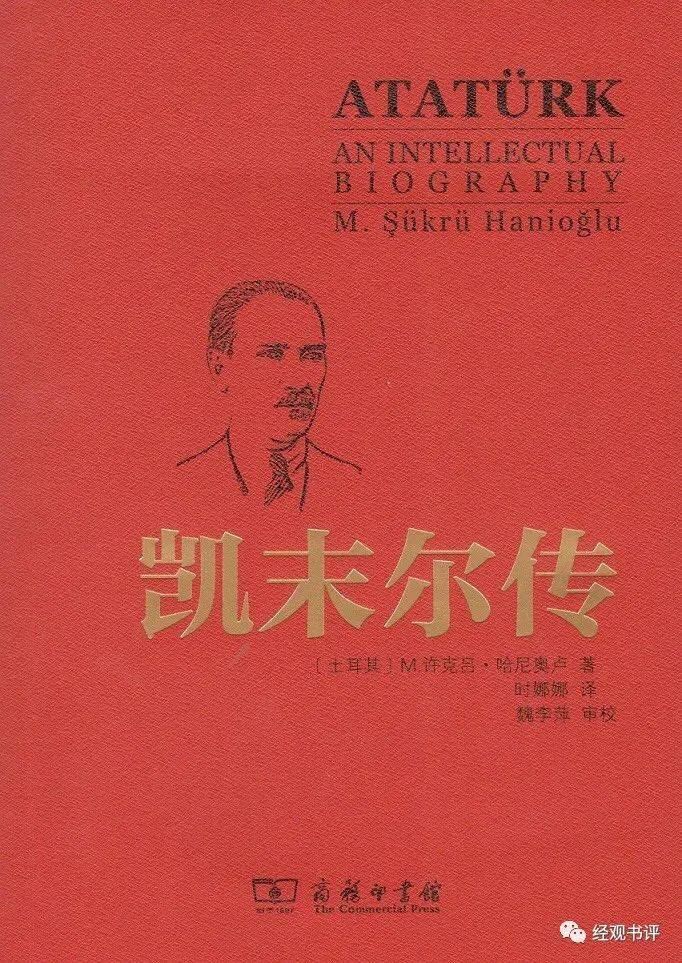
[土耳其]M.许克吕·哈尼奥卢/著 时娜娜/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7月
哈尼奥卢认为,凯末尔的思想——后来被冠以“凯末尔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神圣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凯末尔时代至高无上的新宗教。凯末尔利用当时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等——的奇特组合,构建了一个伟大而虚幻的乌托邦框架,并以其强硬的专制手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土耳其共和国。
哈尼奥卢此著,实现了他的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将凯末尔置于他的历史背景中,表明凯末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思潮及智识氛围的产物;而不是诸多“神话般的传记”所说,凯末尔通过思考“不可想象的事情或以不可想象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愿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许多土耳其史学家倾向于将凯末尔视为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他不受周围世界的影响,单枪匹马创造了“现代土耳其”这个奇迹。但是,哈尼奥卢强调,与主流土耳其史学的这种说法相反,凯末尔并非不受其社会环境和知识环境影响的孤独天才。他的思想和行动是由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氛围、社会和政治现实塑造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社会中只得到了有限的支持,但并不是凯末尔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
第二,哈尼奥卢详尽追溯了凯末尔思想、智识方面的发展,这是以往研究得比较少的方面。哈尼奥卢指出,凯末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思想的演变强烈地影响了其政策。哈尼奥卢详细研究了凯末尔的宗教思想,特别是他对于伊斯兰教的论述。宗教在人类社会和土耳其的作用是凯末尔的主要兴趣领域之一,毕竟,他主持缔造了穆斯林国家中的第一个世俗共和国。
第三,哈尼奥卢揭示了从奥斯曼帝国晚期秩序到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不稳定的历史过渡进程。他强调,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转型,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而不是史学描述的“突然断裂”。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将一直延续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当代历史进程中,直到今天,仍一再浮现,深刻影响着当代土耳其国家与人民的命运。
哈尼奥卢强调指出,在实施了大部分计划后,凯末尔于1938年11月10日去世,享年57岁。他的遗产在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流传了下来。他的智识贡献并没有形成一种连贯的意识形态,但在“凯末尔主义”的标签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尽管土耳其政府当局投入了大量精力将凯末尔主义发展为官方意识形态,特别是在1960年之后,但其实很难将“凯末尔主义”的国家学说与凯末尔真实的精神遗产联系起来。凯末尔曾经一心一意地努力实现他的乌托邦,为此不惜诉诸铁腕统治。凯末尔重塑了土耳其的国家和社会——在凯末尔之后,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二
2006年,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被授予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彰显他“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的象征”。
帕慕克2002年版的小说《雪》——帕慕克称这部作品是他“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政治小说”——可谓完美凸显了这一授奖词所宣称的“帕慕克特质”。《雪》是具备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小说,思想绵密,冲突激烈,形象地探讨了土耳其所面临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族与世界等诸多深刻而纠结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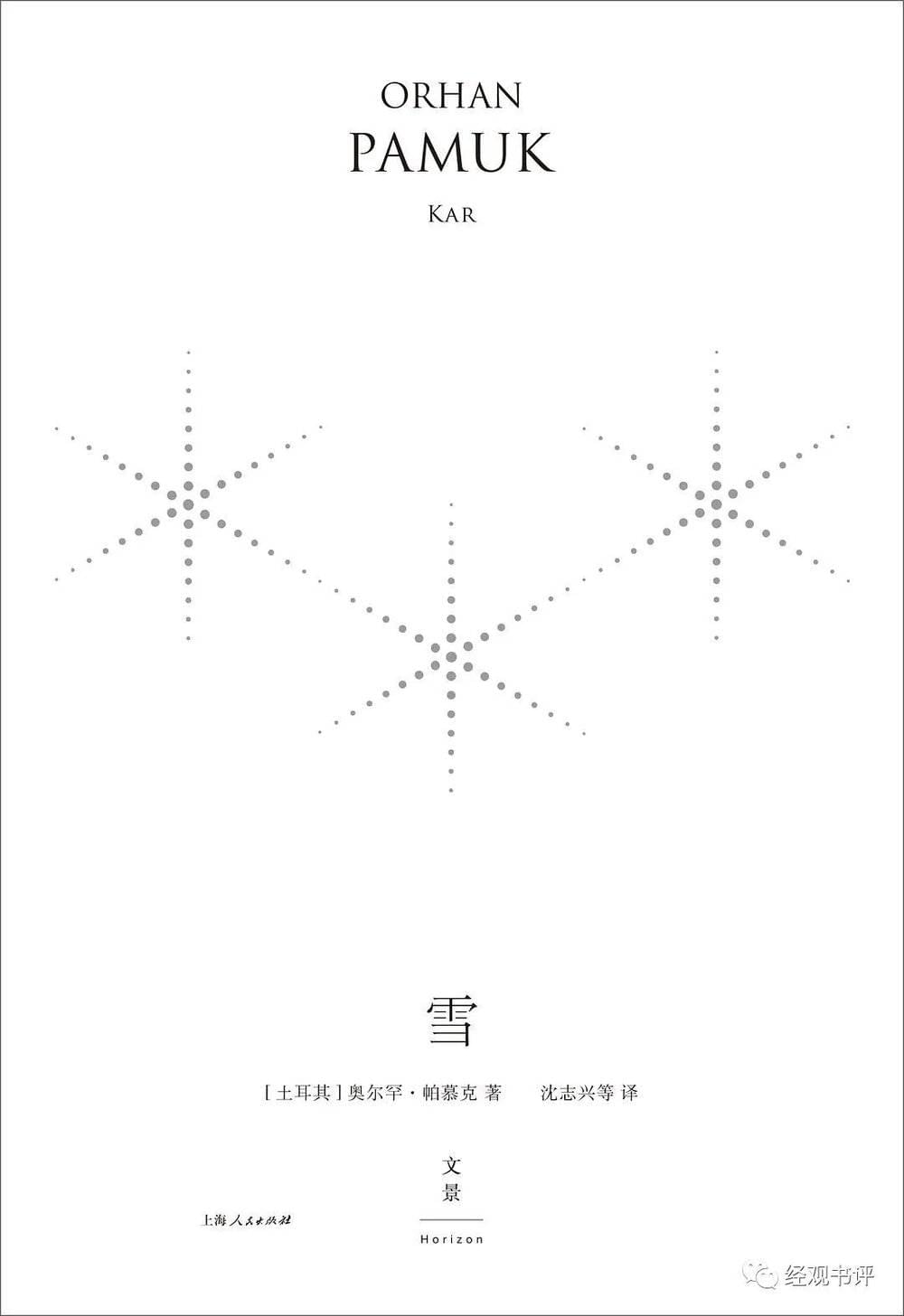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沈志兴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
《雪》的主要情节围绕20世纪 90年代初发生在土耳其东部边境小城卡尔斯的一场军事政变展开,主要冲突发生在政变的发动者、凯末尔世俗主义者、戏剧演员苏纳伊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神蓝”之间。主人公、土耳其流亡诗人卡(Ka),在流亡德国十二年后重返故国土耳其,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卡尔斯,调查那里的少女因戴头巾而掀起自杀浪潮的原因。他到达卡尔斯后,暴风雪便覆盖了这座城市,使这座边城沦为一座孤城。
当地的世俗政府为了推动西化,禁止戴头巾的女大学生进入课堂,而有女生竟采取了自杀方式来表示反抗。这引起了当地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报复行动,教育学院院长成了替罪羊而惨遭杀害,进而引发了以苏纳伊为代表的凯末尔世俗主义者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神蓝”为代表的宗教激进分子之间的激烈冲突。
在当地剧院中,一场名叫《祖国还是头巾》的戏剧节目正在上演,穿着黑袍的神秘女人因为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而将黑袍点燃,此举引起宗教学校学生们的强烈不满。正在大家乱成一团时,苏纳伊策动了军事政变,从幕布两边出现的士兵对准观众连续开枪,杀害了手无寸铁的观众。稍后,一辆坦克和两辆军车袭击了宗教学校的宿舍,并拘捕了所有的学生。卡尔斯的库尔德人也受到袭击、拘捕、杀害。卡亲身经历了这场政变,试图调和各方势力,但一无所成,最终孤独地离开卡尔斯;四年后卡被暗杀于法兰克福街头。
佩戴头巾是穆斯林妇女的标志,在《古兰经》第 24章里有关于女性着头巾及黑袍非常详细的叙述。凯末尔以“凯末尔主义”(六矢主义)为准则,对土耳其进行了西方化的改革,于1925年宣布女性的头巾、黑袍和男人们的费兹帽、缠头等一概废除;1926年宣布废除一夫多妻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土耳其社会中佩戴头巾的妇女数量增加。1980年,土耳其军人政变后,政府曾发布对公职人员的《服饰法》,禁止妇女戴头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禁止戴头巾的女大学生听课或考试;1984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声称佩戴头巾的女学生是“共和国的敌人”,应予开除;1988年,土耳其议会曾通过允许女大学生戴头巾的决议,但被总统及宪法委员会否决。此后土耳其社会中关于妇女佩戴头巾问题的争论一直不断,尤其是针对大学生佩戴头巾的问题。
《雪》的故事情节,就是在这一社会政治背景中展开。帕慕克所讲述的这个情节激荡、氛围凄美的故事,形象地体现了现代土耳其现实中纠结复杂的剧烈冲突。
凯末尔通过各种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重构,重新塑造土耳其民族的记忆和未来,将曾经多民族共存的奥斯曼帝国,转变为单一民族的土耳其共和国。共和人民党与军队成为了“凯末尔主义”的守护者。20世纪中后期,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多党制的确立,厄扎尔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冷战背景下倡导的土耳其一伊斯兰综合体,政治伊斯兰运动逐渐兴起。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利用选举和政治组织等民主制度来推动其议程,但遭到了土耳其政府和军队日益强烈的反对。
经历了多轮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沉浮勃兴之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选举中获胜,并在之后的选举中保持了统治地位。正发党一度试图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来吸引选民,推进伊斯兰主义议程,同时注重保持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和世俗主义,争取符合加入欧盟的“西方标准”。但是,埃尔多安的“威权统治”,在土耳其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关于威权\民主、传统\现代、东方\西方、世俗\宗教、土耳其模式\新奥斯曼主义等诸多方面的激烈辩论。可以预见,埃尔多安掌舵下的土耳其,面临的仍将是日渐分裂的国家和社会。
帕慕克在21世纪初期的一个新闻访谈中曾经谈到,他认为当时崭露头角的埃尔多安,还是会面向西方、面向欧盟。此时此刻,面对着有可能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埃尔多安,不知道帕慕克是否仍然会如此乐观?
三
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的话,伊斯坦布尔必定是它的首都。”英国历史作家贝塔妮•休斯在《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一书中,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融于一书,叙述了这个“三城集于一身”的“世界之都”,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跨越欧亚,汇通中西,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形成“四海一家”、独具一格的文化,最后却又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走向衰败,退居到历史和世界的边缘。

[英]贝塔尼·休斯/著 黄煜文/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
休斯在该书中简略地提及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的一个“心结”——亚美尼亚大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对于亚美尼亚族人的大屠杀(研究者估计60万-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无辜杀害),是首次使用了“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一新词加以描述的“国家组织的种族屠杀罪行”。值得一提的是,帕慕克曾经因为同情亚美尼亚族记者朋友、揭露土耳其当局在该问题上的谎言,而成为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全民公敌”,一度面临“死亡威胁”。
一战时,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协约国作战。1915年,俄国进攻奥斯曼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多年来一直在争取从奥斯曼帝国自治,很多亚美尼亚人支持俄国军队。1915年4月25日,土耳其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等人策划、组织了对于亚美尼亚人的有组织的屠杀。
当时,美国驻奥斯曼大使摩根索出于国际道义的立场,对塔拉特表示抗议。塔拉特则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应付摩根索。当时两人有对话如下:
塔:“你干嘛对亚美尼亚人那么关心?你是犹太人,而他们是基督徒。你抱怨什么呢?你干嘛不让我们随意处理这些人呢?”
摩:“你似乎不明白我的身份是美国大使,而不是一个犹太人。我以人道的名义对你提出的要求,而不是以某个种族或者宗教的名义。”
塔:“我们对这里的美国人也很好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抱怨。”
1921年3月14日,塔拉特在德国柏林被亚美尼亚刺客索戈蒙•特里利安刺杀身亡。刺杀塔拉特,是亚美尼亚人惩罚大屠杀组织者的 “复仇行动”(Operation Nemesis)之一。(埃里克•鲍格森:《复仇行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复仇计划》)国际法学者拉斐尔•莱姆金自青年时期就关注德国法庭对特里利安的审判。他询问教授:为什么亚美尼亚人只能使用暗杀手段,而不能诉诸法律手段来惩罚塔拉特?教授回答说,塔拉特代表奥斯曼土耳其国家行使主权,没有法律可以审判他的罪行。但莱姆金认为,“主权无权杀害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
由亚美尼亚人所遭受的屠杀和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莱姆金创造“种族屠杀”(genocide)一词。1933年,已经成为律师的莱姆金在马德里的国际法会议上提出,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制止 “种族灭绝”罪恶重演,为此必须制定处分这类罪行的国际法,使得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最终被绳之以法。莱姆金为1948年联合国《反种族屠杀公约》的通过付出了极大的个人努力。(彭小瑜:《从奥斯曼帝国到科索沃》)
2017年,历史学家冈特、阿托、巴尔托马在其著作《让他们不要回来——萨伊弗:奥斯曼帝国对亚述人、叙利亚人和迦勒底人的种族灭绝》一书中披露,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前后对于亚述人、叙利亚人和迦勒底人施加过大量的种族灭绝暴行,亚美尼亚大屠杀,只是奥斯曼帝国对少数民族广泛实施暴力灭绝罪行的突出典型。
巴尔干半岛一度被称作“欧洲火药桶”,中近东地区曾经是“民族熔炉”“民族走廊”,进而言之,以往尊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老欧洲”,曾经是“民族大坩埚”“民族绞肉机”,其近现代史中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征服、战争和屠杀。当下的俄乌冲突,可以说是“老欧洲”的“民族主义疾病”的又一次发作。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昏乱喧嚣和铁血政策遮蔽着世界的时刻,回顾奥斯曼帝国至土耳其共和国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对我们应该是有所警醒、不无裨益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