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刘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将近六万人。如此惨祸,举世瞩目。震后,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面临着民众与反对党对政府救灾不力及建筑领域腐败的强烈批评。2023年5月,土耳其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土耳其未来政局的可能变动,引发国际观察家的密切关注。我们结合土耳其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部分著作,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行一个概览。
一
202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报告:土耳其卷》。该著全面介绍了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人口发展、资源禀赋、政治局势、民族与宗教等概况,并对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发展趋势等进行了专题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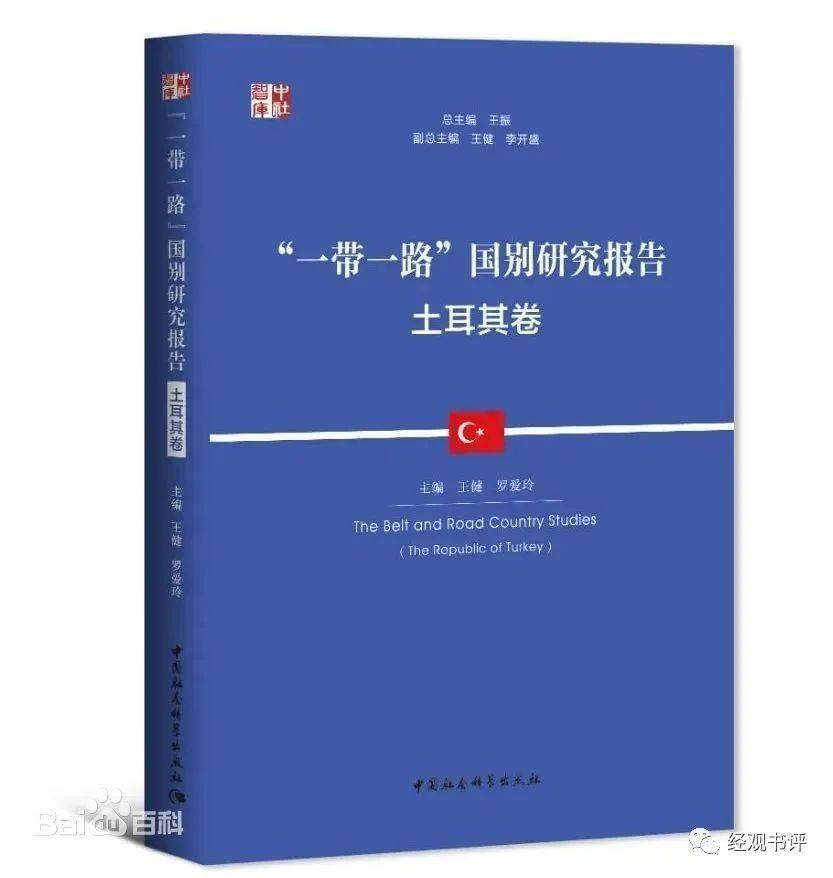
王健 罗爱玲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二十年来,土耳其最大的政治变局是正发党的崛起,以及埃尔多安通过控制正发党而对土耳其政治制度的全面改变。该著认为,21世纪的土耳其研究,不可避免地与正发党捆绑在一起。
自2002年以来,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不断赢得土耳其中央及地方选举,连续执政至今,完成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变革,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凯末尔连续执政15年的共和人民党的影响。2018年,埃尔多安领导正发党进入了第五个任期。在2023年5月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埃尔多安及正发党能否如愿获胜进入第六个任期,是众多观察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随着正发党不断赢得选举,埃尔多安逐渐显示出个人专制的苗头,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秩序开始有所违背,招致批评和不满。这部分抵消了正发党以往的成绩,使得国家宪法秩序遭到侵害,在很多观察家眼里,土耳其也从曾经的“民主模范”转变为“威权国家”,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正在变为“一人统治”的国家。
在土耳其多党民主制的政党政治光谱中,政党的身份认同一直存在问题。共和民主党号称“中左式”的“社会民主”党,但在选举中,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够,在针对国家民主化和腐败等问题时,主要目的仍然是削弱正发党的执政基础,为反对而反对,这是共和民主党无法一党执政的原因之一。
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受制于族裔民族主义,将对方看作死敌。幸福党以伊斯兰主义为纲领,反西方,亲中东,亲伊斯兰;爱国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纲领,反对北约,主张联俄联中——爱国党和幸福党可谓分别处于左右两个极端。
该著指出,土耳其建国后的政治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共和民主党模式,即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秩序。世俗主义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是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秉持世俗主义的国家精英、军队、司法机构和以大城市为基础的商人等阶层,都会捍卫世俗主义秩序。
但这种模式忽视了广大基层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宗教情感和经济需求,并经常以保护国家和世俗秩序的名义压制这些群体。共和民主党自1946年实行多党制以来再未能获得一党执政地位,即是明证。
第二,正发党模式,即世俗与宗教脆弱平衡的秩序。正发党改变了伊斯兰主义者的传统立场,走向亲西方的立场,适应民主自由的话语方式,同时强制推行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对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和宗教教育施行了强大的压力,容易招致世俗力量的激烈反抗,是一种脆弱平衡,很容易被打破。正发党模式也很容易倒退到土耳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专权、等级和暴力中去。
第三,“民族观念运动”模式,即伊斯兰主义的秩序。民族观念运动的“衣钵传人”幸福党在21世纪以来的历次选举中只能得到2%~3%的选票,可见传统伊斯兰主义者的道路行不通。从土耳其世俗化的进程来看,民众对于政治力量被宗教力量的操纵也很反感,他们更希望建立一个“没有沙里亚法,没有政变”的社会。
该著指出,长远来看,如果土耳其希望平稳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民主,并达致各党权力的平衡,就必须依赖共和人民党的改变。共和人民党作为世俗主义的坚定执行者,仍然受制于土耳其建国以来的威权遗产和族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
该党必须进行自我变革、自我解放,发展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才能制衡正发党等中右政党,同时,以民生和民意为突破口,实现单独执政。共和人民党和正发党等中右政党轮流执政、相互制衡,才能解决土耳其“多元而分裂”的政治局面。
该著强调,凯末尔主义者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观念运动”是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反西方主义者,是寻求替代凯末尔主义道路的挑战者。
而正发党则是作为分裂于“民族观念运动”的中右温和派,寻求的是共和人民党与“民族观念运动”二者的调和,一方面推行伊斯兰的社会政策,赢得广大保守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政策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赢得部分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众的支持。
一方面通过寻求加入欧盟而施压的社会改革进程,扩大社会边缘力量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欧盟施压的民主化进程,削弱世俗主义国家精英的权力,因而获得不同的社会、族裔和宗教群体的支持,填补土耳其中右政党的权力真空,得以连续执政至今。
正发党在渡过执政难关后,也有放松改革、加固权力、走向威权的倾向,在其第三、第四任期的执政措施中有所体现,比如埃尔多安多次压制新闻媒体,对于反对派领袖进行司法迫害,强力镇压“伽奇公园示威”等。这种破坏民主秩序的威权倾向,不仅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谴责,也激起了反对党的反弹。
2023年3月10日,土耳其大选正式启动,反对党已经宣布组成反对埃尔多安的联盟,选出了联盟的挑战者,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集中力量挑战正发党。这次大选的结果如何,引人瞩目,国际社会将拭目以待。
二
土耳其地跨欧亚要冲,长期以来是沟通东西的桥梁。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建设共和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土耳其面临着“向西”还是“向东”的重大战略抉择。研究土耳其现代史的学者昝涛在《重新发现土耳其》中的一系列文章,比较透彻地阐述了土耳其从“面向西方”“全盘西化”到“平衡东西”的根本立场的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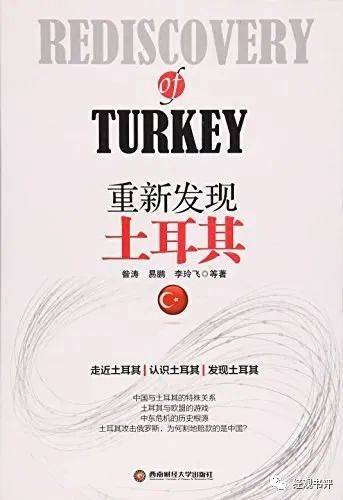
昝涛 易鹏 等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土耳其建国以后,长期追随欧美。凯末尔主义者是坚定的西化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一种高级文明,即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全盘西化,采纳欧洲文明,建成一个世俗国家,同时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精神与制度上的联系。凯末尔不惜以强权高压的手段,全面推进土耳其国家世俗化、去伊斯兰化的进程。
冷战之前的土耳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凯末尔提出了著名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原则。至今,土耳其也未违背凯末尔的这一遗训。二战中,土耳其一直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快结束时才加入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中,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前哨,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加入了北约阵营,执行的是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冷战期间,土耳其外交的主导力量是外交部和军队,都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控制。他们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是与西方结盟。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这一国家战略定位才有所改变。厄扎尔时代赶上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土耳其内政外交的调整提供了机遇。内政方面,厄扎尔是土耳其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总统,他的上台代表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土耳其在国内社会阶层力量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导的土耳其进入了平民崛起的时代,新生的中产阶级借助已经比较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将厄扎尔推上了领导地位。
厄扎尔所寻求的是土耳其能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向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并密切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从欧洲的“边疆国家”,转变为欧亚大陆的“桥梁国家”。厄扎尔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标,而是将加入欧盟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利益和机遇。
进入21世纪以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的诸多政策,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厄扎尔时代的遗产,正发党可谓是忠实地执行了厄扎尔设计的国家战略,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加入欧盟,并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下,结合土耳其自身国力的变化,致力于成为一个逐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枢国家”。
总的来看,加入欧盟仍然是土耳其的长期国策。对于土耳其内政来说,欧盟是一项强势的外部规定性,土耳其必须按照欧盟的各项标准和要求行事,接受欧盟的监督与评估。欧盟的外部规定形成了新兴保守主义力量遏制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的有效手段:土耳其选举精英善用欧盟标准,对军队、国家官僚进行控制和调整。
尽管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刁难、偏见和歧视,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成为土耳其逐渐决心加强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寻求“平衡东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英国著名的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在2009年的著作《新的旧世界》中的“土耳其”一章,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土耳其近现代历史,着重分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议题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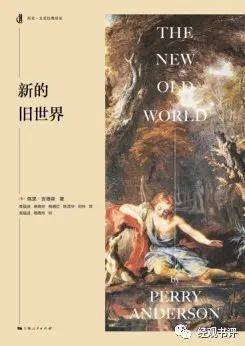
[英]佩里·安德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安德森指出,西方国家推动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主要原因:
第一,在于中东社会独裁统治盛行蔓延,其触角已经延伸到西欧内部的移民社区。如果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在欧洲内部笼络住一个坚定的穆斯林民主国家,可以有效地预防西欧内部的移民威胁。
第二,土耳其可以成为中东地区“自由秩序的灯塔”,起到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作用。
第三,欧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认为给世界提供了最高水准的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将经济繁荣、政治自由和社会稳定“以无与伦比的方式结合”——即使存在着一些瑕疵。
但是,欧洲自诩的开放、多元文化中,却存在着“文化封闭”的危险,如果能够吸纳土耳其“入盟”,就能避免过于自我封闭的“欧洲中心主义”。对于土耳其来说,其民主制度在欧盟内部也将得到庇护和巩固。
总之,欧盟内部促成此事的传统理由很多:军事上,土耳其是反恐堡垒;经济上,土耳其有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和廉价的劳动力;政治上,土耳其是欧盟在亚洲周边邻国的典范;外交上,它是沟通欧亚文明的桥梁;意识形态上,土耳其将使欧洲出现真正的多元文化状态。
但是,土耳其如何才能达到欧盟的标准、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呢?安德森指出,欧盟可能在坚持自身的意识形态原则的基础上,设置一些土耳其必须达到的前提:土耳其必须撤离塞浦路斯,并为其占领进行补偿;同意给库尔德人权利,就像欧洲的威尔士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获得的权利一样;承认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但是,以当时(2008年)——乃至现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而言,要实现这其中的任何一项,看起来都很渺茫,因此,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时间表,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
安德森在该章末尾强调说,期待未来在欧洲有更加美好生活的土耳其人的梦想应该得到尊重,但是,要这一梦想破茧而出,不能仅仅依靠国外。换言之,土耳其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还有待于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提升和改善。
曾经的奥斯曼帝国被称为“西亚病夫”,与“东亚病夫”大清帝国遥相呼应,同病相怜。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从一个世纪以来的建国、西化、世俗化到逐渐自主化、伊斯兰复兴的 “东西探索”的艰难历程,对于我们——尽管有着传统历史文化及国家体量上的巨大差异——或许会有着别样的启示、激励与警惕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