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姜振宇、姜佑怡,原文标题:《姜振宇、姜佑怡|人类文明传承的尽头是“黑暗森林”还是“星辰大海”? ——〈流浪地球2〉拾零|影评》,题图来自:《流浪地球2》
面对《流浪地球》,用几条微博或者一两篇影评来对它进行评判和定位,是远远不够的:优秀的作品永远会比评论活得更加长久。但作为与作品的诞生处于同一时代的观众,尽量调动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抵达、发掘和呈现作品的(有时是创作者不自觉的)幽微而伟大之处,既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责任。
作为小说,《流浪地球》的“美学核心是科学推动世界在宇宙中流浪这样一个意象”(刘慈欣《寻找家园之旅》)。在两部电影的改编中,宇宙当中孤独的地球形象,有赖于来自人类天文学科技知识的审美震撼力。
在电影中点明这一点的是一个短暂的镜头——周喆直在手机上展示的1990年由“旅行者1号”探测器拍摄的照片《暗淡蓝点》。这张照片是包括刘慈欣在内的“科幻圈”向大众传播科幻审美时,最常用的经典道具之一,其中人类乃至地球的渺小和脆弱第一次被(人类的科技进步)直观地展现出来。
问题在于,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审美内核之后,巨大的困难便自然浮现:我们如何能够相信,人类有能力规划、描绘和执行这样一个长达2500年,跨越时空、步入星海的计划?

一
科幻作品当中的科学毕竟是相对容易的,一方面它总是有模糊和犯错的空间,科幻迷和一般读者多数时候会表达大度的原谅;另一方面科幻作品可以将类似“重元素聚变”之类已然接近科学风格式奇幻的内容,作为不假讨论的前提设定放置在背景当中,合格的科幻迷甚至会为这种非科学的创作权力加以辩护。
比较困难的是另一件事情:如何论证作品中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正当性及合理性?缺乏本土历史的美国科幻作家往往会直接挪用其它大洲文明古国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经验,极富宗教意味的历代记(Chronicles)式叙事方法也极为常见。
但在整个科幻史中,孱弱的科幻作家们鲜少有魄力去刻画那些需要百代以上人类来传承和解决的长久困境,刘慈欣在原著小说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加以描绘,《流浪地球》第一部在无意识中提供了一些方案,第二部则尝试直面这个困境。
就像《带上她的眼睛》结尾“透明的地球”的宏大尺寸超出了我们这些人属智人种有限的想象力一样,两千五百年的时间跨度也超出了我们的日常想象。好在现今仍旧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时间坐标:从当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21世纪初,向前数2500年,乃是孔子尚且活跃的东周时期。
“流浪地球”计划倘若能够成功,就仿佛是地球上数十亿人繁育百代之后,不但依然传承且信仰着孔子们的主张和判断,而且严格地推进先祖们的计划。需要指出的一个细节是,这一百代人当中,有九十九代不曾见过太阳,也无法想象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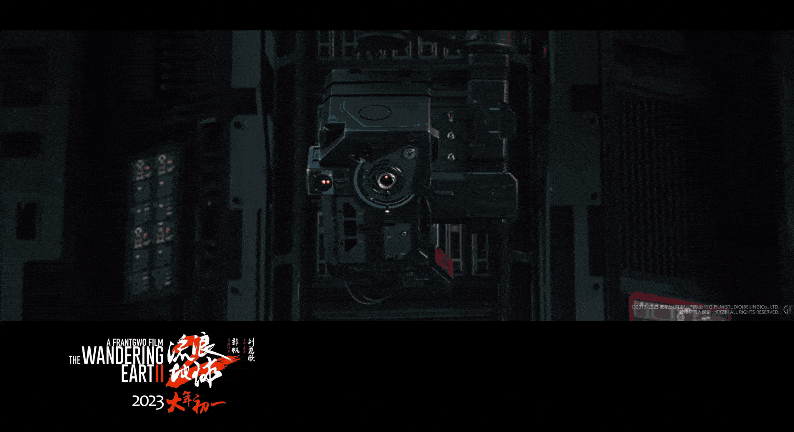
刘慈欣在小说中毕竟还是提出了一个颇为勉强但非常符合科幻气质的解决方案:依托死硬冰冷的科学推演,将灾难放在每个个体的生活周遭,于是计划的传承就由非人的外物来进行保证。在作品中,作者使用凡尔纳式干枯瘦硬的笔调,书写了灾难持续数十代之后,已然蜕变得面目全非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小至家庭婚姻、情感娱乐,大至灾难救援,事无巨细,无不笼罩在科学推演的流浪进程之下。
理论上讲,当宏大的灾难性变革变得如小说中这样无法“低头不看”,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之密切相关的时候,后辈传承延续先辈的计划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这样以整个人类社会为标本的思想推演由作者独自完成,因而必然是粗浅而幼稚的。毕竟如此宏大的灾难性变革只在想象当中发生,而我们身旁最聪明的,那些以人类整体思想和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们,总是无暇将思辨的智力与目光投向现实之外。
因此在这方面,科幻作家们并没有足够多的社会理论作为支撑。除非我们大胆地,将过去四百年间人类对现代性的普遍追求——如其所是的——视作如同太阳危机一般的变革本身。更进一步,我们还需要同时将这个难以简单描绘的进程说带来的变化,引发的反思,以及在被它吞没之前微不足道的抗拒一同纳入视野。然后,再用它来映照那个想象当中更为宏伟可怖的两千五百年计划。
就像现实当中似乎具有先天正义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诸多困境和罪恶一样,刘慈欣对前述解决方案(特别是人类对科学假说/结论/规划的信心)的脆弱性有着明确的认知。现代生活当中的人类往往忽略每个人的“此时此刻”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刘慈欣小说中的工具人们也在面对无孔不入且无法忽视的、全面颠覆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之时,也往往显得如我们现代人们一样傲慢、有限和愚蠢。
不仅是在《流浪地球》原作中,而且也在《三体·黑暗森林》等诸多作品中,刘慈欣都乐于从否定的意义上,展示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怀疑和悖离。这种反讽乃是一切科幻作家的权力:冰冷的科学已经向人类提供了事实,宏大到构成崇高审美意味的解决方案也摆放在明处,但同时人类的逼仄的自由意志与陈旧的道德准则仍有选择高尚、质疑和自我毁灭的权力。当然,刘慈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总是会在最后机械降神般地给予人类以怜悯,告诉大家在规则和末日的彼端,仍然有希望存在。

二
电影就没那么自由。作为远比科幻小说更深层次嵌入人类现代文化和工业生产体系中的大众精神消费产品,《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必须从正面论证和回应这样的困境,并至少作出尝试解决的姿态:为什么这样一个持续一百代人的计划,能够成功呢?
第一部电影尽最大的可能回避了这个问题。剧情整体突出的只是一次性的、短暂的,尽管同样是决定性的灾难。在这个短暂的“木星危机”当中,电影给出的情节框架是好莱坞式的家庭回归、牺牲以及“最后一秒拯救”,带有浓烈的前现代意味。当然,在那个距离未远的“前疫情时代”,《流浪地球》能够发出中国科幻电影的清音初啼,与以导演郭帆为代表的整个团队,与西方影视文化工业体系的碰撞交流密不可分。
正是在这种碰撞中,郭帆团队意识到了某些文化思维基底处的差异,进而获得超越和建构的起点。具体呈现在作品中的,就是关于“带着家园去流浪”的中式情感和关于“饱和式救援”的诸多宏大叙事,我们在此无暇再次展开,只是需要指出一点:这些内容并不见于刘慈欣的原著当中。刘慈欣的态度会显得更启蒙、现代和复杂一些,在他的自我剖白当中,科幻是“寻找家园的路”,因为“并不知道家园在哪里,所以要去很远的地方寻找”。
当然,在两千五百年的时间跨度面前,无论是西方大众文化语境中常见的“家庭”,回归本土历史的“家园”,还是纯洁少女的呼唤,实际上都是无效的答案。它们就像发表之前被废弃的习作,是确立坚定之前必要的试错和标靶,是自我纠偏的必要对象。而对它们的否定,是迈向伟大的必要前提。《流浪地球2》基本上完成了这件工作,用一种极富中国式现代化风格的方法,给出了一种共同事业下薪火传承的方式,此时的气质终于和原作者相接近了。
张鹏“五十岁以上的出列”是整部电影最为高光的时刻之一,但它的复杂性和在地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讲述。如果只是将这个场景视作集体英雄主义和部分群体自主牺牲的投射,以之唤起上至治水移山,下到切尔诺贝利的人类历史事件及其中所内蕴的传承精神,那就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建构和战斗意味。“出列”一幕有其叙事的前后语境,在前是为了完成任务直面牺牲的志愿者,在后是周喆直“这公平吗”和“唯有责任”的断言。

当“师父”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决策,取代个体英雄主义的时候,镜头赋予他以极具人性化的温情:并无血缘关系的父辈拉住子辈的手,然后以父辈的牺牲,向子辈完成了事业的传递。科幻作家灰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极为特殊的人类关系形态。《流浪地球2》中的三条故事线,主人公们实际都是各自事业当中的一对“传帮带”关系。
这种关系直接来自以国营工厂等为代表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当中,其中“老同志要负责新同志工作生活的一切,让他慢慢成长”。在此过程中,“师徒”之间建立起的是一种“亦父亦友”的关系;它与前现代的“学徒”或“学艺”式的人身管辖关系最大的差异,在于二者实际上共同处于一个笼罩性的“事业”或“组织”当中。二者之间的先辈或“师父”是先行者而非简单的“掌权者”,他或她不但参与后辈的职业能力培养,也在相当程度上提供情绪和生活的支撑。
在这样的逻辑当中,“传承”就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张鹏并不只照拂刘培强一个宇航员,马兆管理的是整个数字生命研究所,周喆直在外交会议之外,显然也有诸多并未言明却可供推想的事务。《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给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此前科幻电影鲜少尝试的叙事逻辑:我们所看到的人物、情节和画面,既不特殊,也并非事件的全貌。呈现给我们的镜头只是两千五百年间的些许切片,但其中的勇气和壮丽,就已然惊心动魄。
三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终于抵达小说之外。就像电影在不断融合刘慈欣诸多创作中的灵光一样,刘慈欣其实也在多部小说中反复推进一系列相类似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论“什么是现代中国的代际关系”。
《流浪地球》式的传承,以及其中对基层自组织形态的描绘,是当且仅当人类共同面对一个巨大危机的时候,才能获得其正当性。它的有限之处,在于难以映照于现实当中的基本发展,除非重新复活一个统摄性的宏大叙事,以科学方式加以论证,并且如同电影和小说中的一系列危机一样,把它推到每一个个体的面前,成为每个人的宏大叙事。这些叙事当然早已存在,无论是叫“现代”“启蒙”“自由”,还是“革命”“解放”“发展”,它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人类历史并未终结”的一再确认。
刘慈欣乐于书写这样历史语境当中的中国现代家庭,特别是乐于从正面塑造其中的父亲/父辈形象,这哪怕放置在鲁迅以降的中国文学当中都极为罕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如《三体》中的章北海和他的将军父亲——似乎是刘慈欣唯一一次用了千余字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全频带阻塞干扰》中用“敬畏”物理学家儿子的将军父亲;《圆圆的肥皂泡》中的以兴趣玩乐最终实现父亲夙愿的圆圆,《西洋》中的外交官父亲和他的叛逆儿子,其它还有《地火》《地球大炮》《微纪元》等。
其中刘慈欣最早期的习作《中国2185》中,共和国初代领导人和2185年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的三十出头的哲学博士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后续所有代际关系的理念原型:“生着就是变化着,永生就永远变化;一百年里可以万变不离其宗,但'永远'下去,总要离其宗的”。
这个判断更进一步的阐释,就是在“生存”的大方向下,子辈的“继承”并不只是简单的重复父辈的工作,而是独立地应对自己所需要应对的问题;这种后续的应对,在必要的时候将会把父辈的工作视为助力、资源或者包袱、累赘。在《微纪元》中,当先辈的宇航员意识到自己成为新人类的威胁之时,他自觉地销毁了原本用以复兴前代文明的“种子”;在《三体》中,脱离了地球的星舰人类清晰地意识到“走向宇宙”所需要的代价,乃是舍弃地球人类所珍视一切伦理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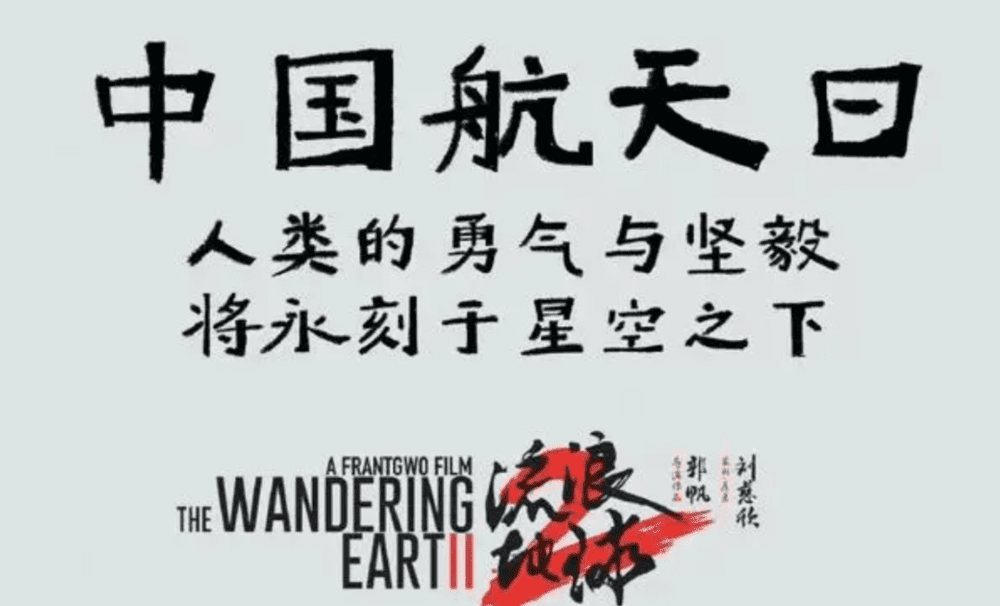
但在刘慈欣式的立场之下,这些“背叛”倒不如说是“变化”,后辈仍旧是先辈的继承者,只是需要面对的,是剧烈变化之后的环境:在《流浪地球》中,这就是以MOSS和图丫丫、图恒宇为代表的数字生命派——他们从未也不会背叛人类,只是传承文明的方式与先辈的设想略有不同。
四
小说毕竟源自虚构。就像科幻作品的读者并不总是能够想象人类个体与超越性的自然规律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在细小但真实的日常缝隙中暂且忽略人类宇宙中前所未见的现代化状况,当然也有它的正当性乃至必要性。
但我们的时代毕竟仍旧拥有它自己的未来,尽管看上去并不遵循数百年来绝大多数科幻作家的幼稚幻想。只要物理学仍然存在,人类——至少是某些地域族群和理念——的进步和发展就必然会拥有它们自己的空间,我们总会在日常的表象之下,时不时地接触到,那些尚未完成的宏大命题,一如《流浪地球》中所规划的两千五百年时间跨度,4.2光年空间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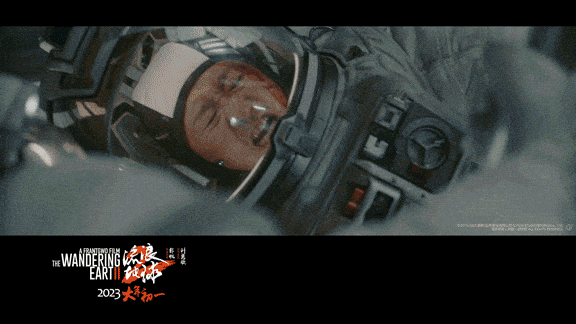
这是牛顿以降原始人类为适应技术爆炸面前,相对落后的现代文化状况的微末努力。重点不在于它能够抵达何处,而是一旦开始积攒勇气,一旦尝试运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理性认知能力,一旦开始实践和运动,从启蒙之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代虚妄中,就有了召唤出希望的可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姜振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专职博士后)、姜佑怡(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