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鲁迅在追溯自我精神史的形成时,早年经历中的两个“耻辱”事件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一是“父亲的病”,与此相关的是“家道中落”问题,其二是“幻灯片事件”。这两个在鲁迅精神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事件,学术界的讨论却显出一冷一热的不同。
关于“幻灯片事件”,中日学者有过大量讨论,丰富甚至改写了鲁迅的论述,而有关“父亲的病”的讨论,基本还在鲁迅的自我论述范围内。受鲁迅自述的影响,几乎所有鲁迅传记对此都以浓重的笔墨予以追认。
特别是《〈呐喊〉自序》被纳入中学教材,《朝花夕拾》被定为初中一年级“整本书阅读”书目,“父亲的病”作为鲁迅文学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可谓妇孺皆知。“父亲的病”已成为鲁迅文学轨迹的因果论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父亲的病”阴面形象的中医批判,特别是作为“庸医”典型的绍兴中医“陈莲河”(何廉臣),也成为鲁迅笔下代表中医的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如此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学生命和一个医疗事件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联系。
本论尝试在近代中西医论争的背景下,重审鲁迅的何廉臣批判,并通过这一案例考察汇通派中医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境遇。
二、“父亲的病”的凸显
父亲周伯宜的病与死在鲁迅创作中出现得很早,但“父亲的病”与何廉臣批判结合到一起,则是到了《父亲的病》(1926年)一文中,才最终实现的,这将是本文的一个起点。
“父亲的病”在鲁迅文本中的主题演化有一个清晰的过程。鲁迅最早采用自叙传的方式书写“父亲”,是在1919年8月8日创作的《我的父亲》一文中,该文作为总题“自言自语”中的一篇,署名“神飞”,发表在9月9日《国民公报》“新文艺”栏上。“自言自语”是一组并不成熟的文章,它内部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面是《野草》式的深入内心的文字,一面是《朝花夕拾》式的重返记忆的篇章。
关于“自言自语”和鲁迅这两部作品的关系,不少研究者做过专门论述,钱理群就认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言自语》是《野草》的草稿:不仅在写作思路与写法上有前后一贯性,而且有些篇章是可以对读”。这一点同样适合讨论“自言自语”和《朝花夕拾》的关系,且尤其体现在《我的父亲》与《父亲的病》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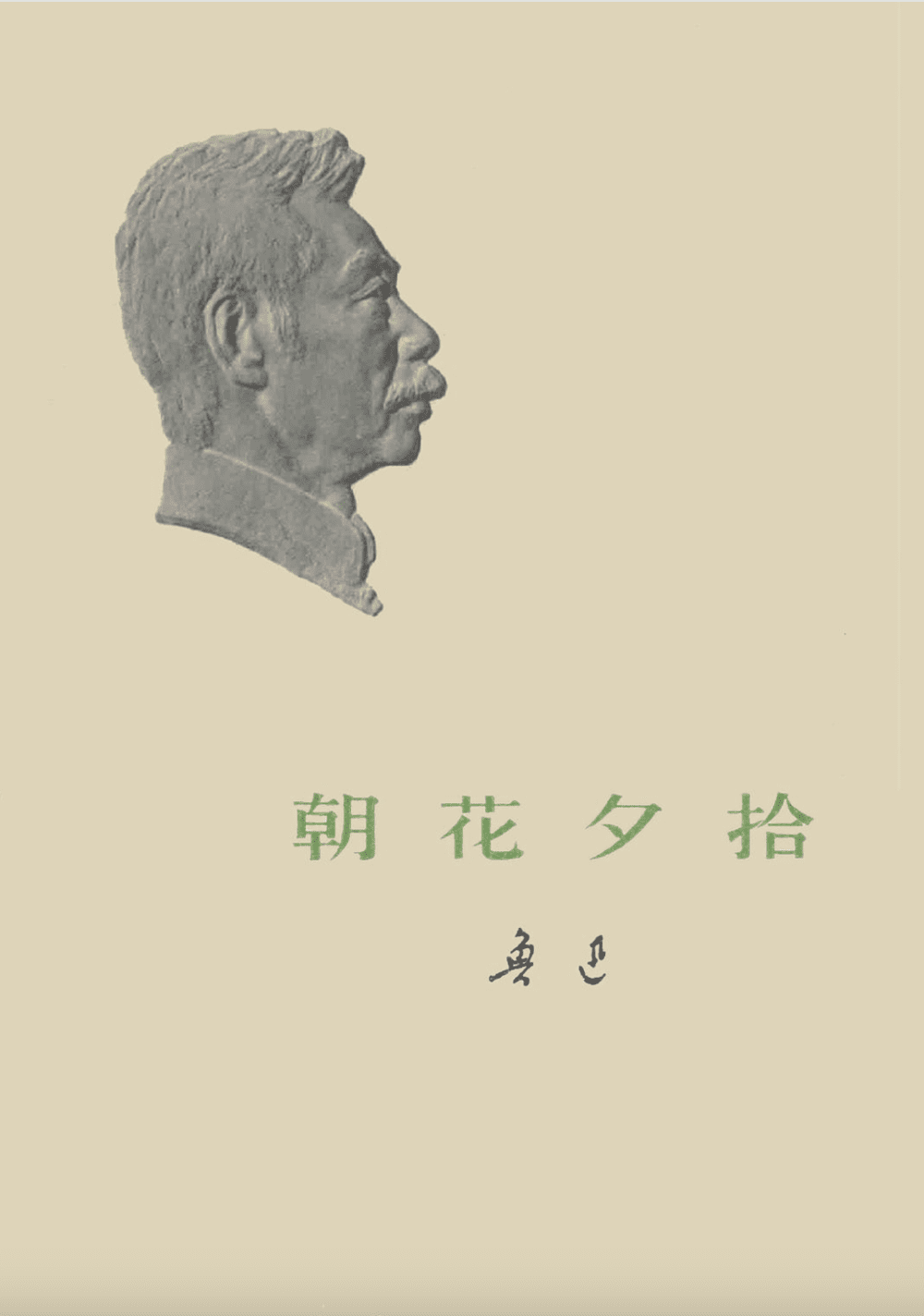
《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我的父亲》这篇300字的短章,是“父亲”临终前的一段记录:父亲躺在床上即将死去,老乳母却让“我”大声叫他,这引起“我”成年后对临终前不令病者自然入死的行为的厌恶,并将之视为对“父亲”犯下的大过错。
这一段情节,同《父亲的病》结尾处高度相似,只是在《父亲的病》中,“老乳母”成了“衍太太”,同时“父亲”为叫嚷所引起的临终前的不安也得到了强化。这是鲁迅第一次写“父亲的病”,显而易见的是,鲁迅从记忆中提取文学资源时,并没有在疾病和治病上留下笔墨,主要是关于父亲的死,这和鲁迅同期创作更重视对传统伦理的批判是一致的。
第二次写“父亲的病”,是1922年12月3日的《〈呐喊〉自序》,文中鲁迅第一次将“父亲的病”作为影响到自己生命轨迹的重要事件凸显出来了。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这里第一次正面处理了“父亲的病”,谈到自己作为长子,为父亲奔走取药时的遭遇,并过早地体验到世态炎凉的屈辱。文中,鲁迅对父亲患病的诊疗细节有很具体的描绘,并对“开方的医生”作了批判,包括后文谈到留日学医,源头便是“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父亲的病”成为鲁迅追溯自己文学史的重要一环,到此已算是实现了,但这里的中医批判,显然还是指向一般意义的“中医”,而没有特别的针对具体的个人,直到此时,“父亲的病”还未明确地与何廉臣联系起来。这种变化,是到1926年才确定下来的。
第三次写“父亲的病”,是在1926年10月7日《父亲的病》中。这篇文章对“父亲的病”作了非常具体的呈现。如果说《我的父亲》中“我”的忏悔意识是文章的主要情绪,《〈呐喊〉自序》中“父亲的病”部分,作者主要表现为父病奔走,认识到中医之不可信,那么,到了《父亲的病》一文,上述两方面就实现了融合,但这种“融合”在《父亲的病》中并不居于主体位置,因为《父亲的病》的中医批判是特别针对“陈莲河”(何廉臣)的,正如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所诧异的:
在《我的父亲》改作成《父亲的病》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里,除了上面提到的主题的深化之外,还有在描写临终情景之前,添加了一段让读者一读便感到极为荒唐无稽的故乡S市中医们诊病开方的情形。《父亲的病》约有三千四百字,比起《我的父亲》篇幅要多出六倍以上。而其增加部分大半是对中医的冷嘲热讽。
藤井省三看到了从《我的父亲》到《父亲的病》叙事重点的变化,联系到《〈呐喊〉自序》,“父亲的病”在三次“追溯”中都有不同,呈现为中医批判主题的上升和指向的具体化。因而,藤井省三在文中说道:“如果把《〈呐喊〉自序》中所谓的‘欺骗’与《父亲的病》中对中医的描写结合起来读,那么读者一定会更进一层地坚信,中医就是荒诞无稽了吧。”
“父亲的病”这一贯穿性的事件,从一次不成功的系列创作(指“自言自语”)中逐渐凸显出来,并且成为两篇经典作品的核心情节,这与中医批评因素的融入是密不可分的。进一步考察,会发现鲁迅的中医批判,最终越来越指向以“陈莲河”(何廉臣)为代表的中医。
从“父亲的病”的凸显角度来看,中医批判的主题日益明确,这就与研究者习惯把鲁迅的中医批判泛化为传统文化批判的看法存在龃龉,因为伴随着“父亲的病”的凸显,中医批判不是越来越泛化,而是越来越具体到何廉臣。
三、何廉臣批判的凸显
实际上,在鲁迅的中医批判中,“陈莲河”(何廉臣)的形象,和“父亲的病”一样,是逐渐凸显出来的,并且也是到了《父亲的病》,才实现了某种“融合”。“陈莲河”(何廉臣)从鲁迅文化图景的“幕后”走上“台前”也是有迹可循的。鲁迅最早将何廉臣作为中医代表来批评,是在私人书信中。1918年1月4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写道:
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先生耳。
谈到开药方时,鲁迅提到的何廉臣是绍兴人很熟悉的,因而随意出之,具有默会的讽刺效果。在给许寿裳去信后不久,钱玄同开始不断前往绍兴县馆动员他“做点文章”,并促使周树人向鲁迅转变,这便有了著名的《狂人日记》,距与许寿裳通信才两个多月,在这篇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中,就有一位“何先生”: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联系不久前鲁迅与朋友的通信,谈及给国人开方困难时要请教何廉臣的“药方”,而这里就让“何先生”出洋相,让他面对患者却无药可开,两处恰能形成呼应,这很能见出鲁迅的讽刺性。此时,从私人书信到公开的虚构文本,鲁迅都谈到了何廉臣,显示了他把何廉臣纳入自己的文化批判的意图,因而《狂人日记》中“何先生”诊病的情节绝非无意为之。
《狂人日记》之后,1919年六、七月间的小说《明天》中又出现了一位庸医“何小仙”:
单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声“阿呀!”心里计算:怎么好?只有去诊何小仙这一条路了……
“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纸角上的几个字说道:“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
与《狂人日记》中“何先生”无法开药相比,何小仙倒是开了药的,但结果是造成病人的死亡,这与《父亲的病》中的陈莲河(何廉臣)很相似。鲁迅在《父亲的病》中极力渲染“陈莲河”开药的荒唐,写到这位擅长以“败鼓皮丸”治疗水肿的医者运用“医者意也”的逻辑: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
这段情节与《明天》中“火克金”的思维逻辑是相同的,《明天》中的“保婴活命丸”需要到指定的“贾家济世老店”专门购买,而陈莲河的“败鼓皮丸”也有指定的药店,鲁迅写道:“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可见鲁迅在塑造何小仙时,是在记忆中的“何廉臣”这张形象草图上做的修改和发挥。
上文笔者分析了“父亲的病”的上升叙事以及“何廉臣”批判从幕后到台前这两条线索如何一步一步结合在一起,“父亲的病”何以一步一步由自我反思向暴露“陈莲河”(何廉臣)的荒唐转移。读者或许认为这是由于何廉臣治死了鲁迅的父亲,因为鲁迅本人也说过:“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里也还要提出一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来:为什么“中医”的形象要以何廉臣为代表?
考察周伯宜的诊疗过程,前后凡三位医生,无论从诊治时间的长短,还是用药的荒唐与否上看,何廉臣都算不得最典型的一个。《父亲的病》写了两位医生,第一位“名医”和鲁迅“周旋过两整年”,所开药引也极为奇特,陈莲河(何廉臣)来诊,前后只“单吃了一百多天‘败鼓皮丸’”,而与之相关的篇幅几乎构成了整篇文章的主体。
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则周伯宜生病期间,前后只有两年,并且有三位医生给父亲诊病,第一位“姓冯的医生”,总是醉醺醺的,很快便被打发走了,第二位是绍兴名医姚芝仙,第三位才是何廉臣。在周作人的回忆里,论荒唐且医术最坏的是头一个“姓冯的”的医生:
当初所请的医生,乃是一个姓冯的,穿了古铜色绸缎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那时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请他一起诊治,他头一回对我父亲说道:
“贵恙没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等他隔了两天第二次来的时候,却说的相反了,因此父亲觉得他不能信用,就不再请他。他又说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边,因为“舌乃心之灵苗”,这也是“医者意也”的流派……可是这一回却不曾上它的当,没有请教他的灵丹,就将他送走完事了。
结合周作人的回忆,“陈莲河”(何廉臣)在三个医生中,绝算不得荒唐。据藤井省三的考察,何廉臣的用药,如芦根、蟋蟀、平地木(紫金牛)以及破鼓皮,“乍一看这些药方虽然都是些离奇古怪的东西,而实际上是每一种都有治‘水肿’的好药效。是有利尿作用的药方”。
泉彪之助在《〈父亲的病〉考》一文中还写道:“用医生的眼光来读《父亲的病》,倒觉得他是位很亲切的医生……所使用的药也可以说是明代以来传统医学中的正统药方。”将周氏兄弟的回忆作一比较,会发现《父亲的病》不仅把三个医生简缩为两个,顶荒唐的一位的“舌乃心之灵苗”“医者意也”之类的昏话,也被摊到何廉臣头上。
另外,周家人的态度或许也可以作为何廉臣并非庸医的佐证。实际上,1896年周伯宜的死,丝毫没有动摇周家人对何廉臣的信任,如鲁迅祖父周介孚1904年病重时,家人就请来何廉臣为他诊治,到了1910年暮春时,鲁迅祖母蒋氏受风寒病危,蒋氏临终前,鲁瑞也差遣王鹤照去请了何廉臣来。
前一次诊断时,鲁迅已在日本留学,后一次鲁迅已回国在杭州教书,陪侍蒋氏的就有周建人,可见,作为长子且学过西医的鲁迅,他对中医与何廉臣的态度,和周家其他人似乎很有些两样。
鲁迅对何廉臣的评价,不仅与周家人不同,甚至将其他医者的荒唐言行挪到何廉臣身上,倘全归于“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恐怕难有十足的说服力。正如笔者在后文要指出的,鲁迅针对的“陈莲河”,不仅仅是“父亲的病”中的何廉臣,更是“新旧之争”中的何廉臣。
四、为什么是何廉臣
鲁迅特别针对何廉臣,原因不仅如其文中所说的误了父亲的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不过被鲁迅一笔带过了:
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这段话里压缩了极丰富的信息,揭示这些信息,将能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何廉臣批判。
鲁迅这里谈到的“中医什么学报”,《鲁迅全集》的注释为“指《绍兴医药学报》,1924年春创刊,何廉臣任副编辑,在第一期上发表《本报宗旨之宣言》,宣扬‘国粹’”。
《鲁迅全集》中的注释存在错误,《绍兴医药学报》并非1924年春创刊,而是早在清末(1908年6月)便由何廉臣、裘吉生等人创刊,刊物出到1923年第141期时停办一年,后又于1924年重办,改为《绍兴医药月报》,并到1928年10月——何廉臣去世前一年——才停办。
《绍兴医药学报》前后长达20年,是清末民国时期中医药类刊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刊物之一。注释将《绍兴医药学报》的创办时间定为1924年,这就将何廉臣办报的时间挪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注释中提示其宣扬“国粹”的一面,就很容易把它和鲁迅文中的描述形成互证关系,形成对鲁迅所塑造的何廉臣保守乃至反动的文化形象的追认,但鲁迅的批判意图是非常具体的,即对中医界试图科学化中医的行为的警惕。
《父亲的病》中有一段不大引起读者注意的话: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
这里谈到中医在遭遇西医之后的“让步”,涉及的正是民国中医界面临西医冲击时,一批具有变通思想的医者主张中西汇通的观点,鲁迅非常清楚何廉臣正是汇通派中医,不仅被推为绍派医学的“越州翘楚”,在国内中医界也享有盛誉。
鲁迅在《父亲的病》中,之所以不针对荒唐至极的冯姓医生,对耽误父亲的病更久的姚芝仙也以一个医病纠纷的传言带过,而特别留意用药更正,名望更重,同时还活跃在杏林的何廉臣,这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因而,《父亲的病》不可单作“旧事重提”看。《绍兴医药月报》第一期所刊何廉臣所拟《本报宗旨之宣言》中,何廉臣写道:
老朽不才,见异思迁,二十年前研究东西洋医药学书之译本,深羡彼邦于诊病用药实事求是……尝取著名伟效之西药以治对症之病,虽时著奇效而有时竟全不效且有发生流弊者……诚有如日本医士和田氏所云:“西医之理论说明虽若脉络贯通,而内科之治效尚少,中医之理论说明,虽间有支离灭裂,而内科治术之实效,远胜乎西医之上。”
何廉臣在《宣言》中表达的医学态度,正是鲁迅在《父亲的病》中所谈的中医作出“让步”后的那一套观点。民国时期,医学领域中,最为新文化知识分子所不能容忍的,并非顽固派中医,更不是新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如何小仙一类巫医,这两类“旧医”在新文化知识分子和西医面前,是毫无招架之力的。
这两类医生虽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笔下最常出现的中医形象,但在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中,构成实质性挑战的恰好是那些具有相当文化修养,不仅熟悉传统医籍,在医学界拥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并且具有相当的民众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多方涉猎西医知识,且能“与时俱进”的传统医者,他们接纳了进化、竞争以及各种科学话语,主张取长补短、中西汇通。
这些被视为骑墙者的汇通派,主动和时代话语结合起来,在新文化知识分子和西医看来,是推行医学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在《随感录三十三》中,鲁迅写道: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鲁迅讽刺的“大官”,是曾作为自己上级的前教育部秘书长蒋维乔。蒋氏将传统医学解剖学的概念与现代解剖学概念扯到一起,鲁迅对此深恶痛绝,而何廉臣作为汇通派中医,便被视为在科学里羼进鬼话的人。
具体到1926年《父亲的病》的写作背景,它与1925年中医界争取教育系统立案也有着微妙的联系。1925年8月17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医学教育组讨论并通过了两项与中医有关的提案,其一是《请教育部学校系统添列中医一门案》,二是《由本社请教育部规定中医学校课程并编入学校系统案》,这两项提案实际上是1913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后,中医界向教育部请愿失败后的再次尝试。
颇有意思的是,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一个宣传美式教育观念的社团,这次年会竟通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提案,这里也要作出说明。这次提案是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提出的,年会在山西召开,获得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一点,时为教育改进社代表的袁希涛在开会致辞中说得非常清楚。
山西当时是全国强制教育和地方自治的模范地区,阎锡山又是民国政界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实力派。和东部地区不同,山西政界不仅不赞同废除中医,还对中医予以大力扶持,阎锡山亲自发起组织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促进中西医汇通,何廉臣正是该会的名誉理事,山西也是民国时期中医研究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
中华教育改进社1925年的年会,获得了阎锡山的大力支持,会上还邀请阎锡山致辞,因而在医学教育分组讨论中,由中医提出的两件议案获得了“照原案通过”的决议。年会上通过的提案,显然也是中西医汇通派的观点,提案所列出的诸多科目与西医相关者就很不少,提案说明中也谈到:
古无显微镜,而今有显微镜;古无化学,而今有化学;古之手术,不及今之考究;古之消毒,不及今之完全;故解剖生理,外科法医,花柳创伤疗法,精神疗法等各门则兼采西说,以求周密。
山西的现实政治力量构成了这次议案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1920年代中期,中医药界已产生了数量不少的中医医院、学校、报刊杂志以及联合团体,这次提案由于大量中医药团体、医院、报刊杂志以及中医名流的参与,一时间造成了不小的声势。
不可避免的是,在山西的年会上通过的提案,旋即引发西医界和新文化界的强烈抵制,并掀起新一波的中西医论战。何廉臣所编的《绍兴医药学报》从1925年第2卷6号起就对此保持关注,此后又跟进报道中医团体组织的请愿活动,直到1926年还在不断发表捍卫决议的观点,即便到了1929年,何廉臣已处于老病之际,“废止旧医案”引起中医界震动时,何廉臣还让儿子何幼廉代替自己参加中医的抗议请愿活动。
1925年的提案和请愿活动,发生于鲁迅还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对此虽未作正面的讨论,但显然对绍兴中医界的活动有所察觉,这也就是鲁迅在《父亲的病》中所说的何廉臣“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
1925年由中华教育促进会的中医提案所引发的中西医论争,一直持续到1926年才逐渐平息。1920年代,何廉臣在中医界是颇有分量的人物,一面在绍兴行医,成为绍兴首屈一指的中医,另一方面,又通过《绍兴医药学报》提倡中西医汇通,与全国中医界保持沟通,在江浙乃至全国中医界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同时还积极参与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的救亡运动,与主张“医学革命”的废医派展开论战。
1926年,当鲁迅沉入“旧事重提”的阶段,重新回顾“父亲的病”时,这位与父亲的死有关的“旧医”,还在医学界发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父亲的病》便以一个被改造了的何廉臣形象,既回到记忆的过去又介入鲁迅所处的当时,这使得“父亲的病”从早期的内向忏悔转为外向批判,何廉臣的形象也从影射转为实指,这是很能显示鲁迅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精神和强烈的现实介入品格的。
五、何廉臣的医学改良
接下来,我试着寻觅并打开新旧之争中被遮蔽一方的声音。
现代时期的中医,是一种亦中亦西的医学类型,它与传统医学有着重大差别:如在与西医的对照中,确立自身的某些理论优势,诸如强调生命的整体性,标榜长于治本、工于内科等;又如吸收了西医的知识和治疗工具,包括接受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以及温度计、听诊器等医疗器械;再如有关医学传承、知识传播、施诊施治乃至防疫和医疗行政等机构层面的全面现代化,包括兴学校,办报刊,设中医院等。
上述种种新特点,无不令其与传统医学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何廉臣也是有相当的先觉意识和批判性的。以往有关何廉臣的研究,多是医学“内史”角度的专业讨论,笔者这里试着从“外史”角度考察其医学观点与时代的关系。
何廉臣生于1861年,少时习举子业,后随父习医,并从绍兴医家樊开周等人临症数年,1886年又往苏、沪诸地学习,开始接触西医,并积极参与医界活动,1891年回绍悬壶,逐渐成为越中名医。1903年后何廉臣到上海行医,同沪上名医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等人交往,并组织“中国医学会”,何廉臣被举为副会长。1906年何廉臣又回绍行医,并积极参与和推动医界社会团体活动,1908年任刚成立的“绍兴医药研究社”社长,并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主要研究中医药学、介绍西医学、阐发中医药学术。
何氏撰著作品四十多种,尤以《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重订伤寒广义》《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为代表,至今仍为医界所推崇。何廉臣早在1908年就曾有编撰《全体总论》的计划,其所列参考书以中译西方解剖学、生理学著作为主,书名显然是效仿合信的《全体新论》。何廉臣这本未能成书的生理学著作,体现了一个传统中医对西医生理学、解剖学的接纳,这篇目录比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所编的《人生象敩》还早一年。
比较何廉臣《全体新论》的大纲与鲁迅《人生象敩》的目录,很可以看出西医理论在杭绍地区不同的接受和转化情况,何廉臣和鲁迅可同视为在杭绍推广生理学教育的本土先行者。在何廉臣的多种著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所写的《新医宗必读》,这本书几乎不为研究者所关注,或许是因内史家对于这类通俗医书并不看重,但这部通俗的普及医学讲义,却很能体现何氏的医学观念与时代之关系。
《新医宗必读》虽刊于1909年,实际早在1907年之前便已写就,联系到何廉臣1908年创办《绍兴医药学报》,提前编写的《新医宗必读》可以视为预备工作,因而书中的一些章节后来也刊登在《绍兴医药学报》上,特别是其中有关医学汇通的观点,即便到了1920年代,还在中医界报刊上转载,可见何氏有关医学革新的主张,很早便已成熟。这本书在社会观念上,受梁启超等维新派影响很深,如其一再强调的“过渡时代论”。
何氏全书以《医与国家关系论》开篇,认为应该大兴医学教育和医学改良,要“仿照东西各国医学堂之课程”,使“新而优者起,旧而劣者仆”,如此方能“中西医术并精……内则为人命人种之栽培,外则为国体国权之竞争”。“绪言”谈到改革医学之根本方法是“多派留学生,分赴欧美日各国,学其最新之医学,学成而归以为改革之先导”。
何氏还谈到“世界医术,德国为上,英美次之,日本亦佳”,“欲医学思想之发达,而求医界学术之改良”,有赖于现代医学堂的建立,因此他肯定了派遣留学生的意义,认为“幸而近今政府已知医学一科之重要,遣太医院医生出洋留学矣”,又写道“德日维新,首重医学,英初变政,先讲卫生”,这与鲁迅留日学医时所持观念是相同的。
何氏在书中提出了汇通中西的改良主张,认为中医生理学、病理学、器械之用应主要学习西医,而诊断学、证治学以及方药学,则可中西互参。《新医宗必读》全书十三章,实是一部医学改良的总方案。就当时来看,何氏的改良主张不乏激进,因而他也常招致不满,被认为“扬西抑中太甚”。
《新医宗必读》序二是由蔡元培所写,他的评价也值得一引。蔡元培谈到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显示了独特的优长,但中医积累了“四千余年之经验”,“举彼此治疗之成绩而观之,遂亦互有得失”,主张摒弃中西之见,积极吸纳西方医学经验。基于这一立场,蔡元培评价了他视为朋友的何廉臣的医学实践:
其宗旨以西医之学说,国医之经验,或调和,或并行,参酌焉以汇通其理,惟其中《新医宗必读》,并不拘于教室讲义之体,其内容亦不涉学理之奥窔,大意在比较中西医界之同异,而各举其所长,以消彼此相嫉之意见。此诚过渡时代必不可少之著作也。
蔡元培这篇序言写于1906年,是其中年时期的观点,他在留德归来后对传统医学的看法也未有根本变化,这一点从其就任教育总长以后还曾为中医杜同甲登报打广告,为《卫生报》题词,都可以见出。尤其在1929年“废止旧医案”发生时,裘吉生(《绍兴医药学报》创办人)作为中医界的代表,也曾利用私交会晤了蔡元培等人,并获得了国民党内多位元老的支持。
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鲁迅曾看到过《新医宗必读》,但此书作为一部医学教科书,当时在上海发行,并由各大书坊分售,在清末民初江浙沪一带是颇有影响的。此书出版后不久,鲁迅便从日本回国(1908年),先后在杭州、绍兴的学校教书,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期间,鲁迅讲授生理学,并且也在编写生理学、解剖学讲义,他在搜求参考图书时,是不难注意到何氏著述的。
因而,笔者认为鲁迅极有可能在回国任教期间见到过该书。当然,不懂外语的何廉臣,仅靠阅读汉译医书获得的西医知识,是无法和鲁迅相比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细节或许能佐证笔者的判断,即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鲁迅将何廉臣写作“陈莲河”,一般认为这只是鲁迅将“何廉臣”原音倒序而造的名字,但这里或许还隐藏着另外的信息:
《新医宗必读》写成之后,何廉臣特意请了当时的沪上名医陈莲舫作序,陈莲舫作为十数代祖传医家,又曾被聘为御医,在上海医界名望极高,而“陈莲舫”与“陈莲河”,仅一字之差,且“河”与“舫”在意义上是相关的。
陈莲舫在序中谈到自己年事已高,无法参与到“借助于泰西医学”,为国医正误、为国家服务的事业中,但他将这希望寄托于何廉臣身上。鲁迅作品中影射现实人物的命名,常有精心的设计,将何廉臣写作“陈莲河”,同时影射陈莲舫,未必不是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惯例。
六、余论
鲁迅的何廉臣批判不能单纯地看作鲁迅个人的情绪化表达,鲁迅设置了自己文学起点的动力装置,这动力源于一次屈辱性的医疗遭遇,虽然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但凭借《朝花夕拾》作为国民读物的巨大影响,这个起点得以巩固,新文学家、新文化知识分子(医生)与传统及与大众(病人)间的某种医病关系也再一次得到确认。
由于鲁迅的巨大影响,何廉臣批判也成为中西医论争中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在此之后,奔走在中医正名之路上的人几乎都要面对鲁迅的发难,而陈莲河(何廉臣)尤其是中西医论争中很难忽略的形象。1958年版《鲁迅全集》在《父亲的病》这篇的注释中,就认为何廉臣等人“只是当时我国医学界(中医)的一部分情况,我们不能以一部分的不良作风来概括全体”。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性,将鲁迅父亲之死的涉事医生从“全体”中分割出去,不失为顾全大局之法。藤井省三与泉彪之助等学者则是从诊疗用药的角度为何廉臣辩护。何廉臣的后人则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认为“因鲁迅父亲的病绍兴名医都不能治……开方经霜芦苇,与原配蟋蟀一对,药不能说不对,实际上这两味药是办不到的,也就暗示病不能治”。
中医界也有论者将何廉臣习医分为不成熟到成熟两个阶段,把《父亲的病》涉及的这一段,归入早期医术未精时,这是《越医薪传》《越医汇讲》等书所持的观点。上述辩解未必立得住脚,也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鲁迅面对的具体问题。
表面上看,鲁迅的何廉臣批判似乎是一场单纯的追剿巫医的行动,但何廉臣并非巫医,而是最有可能对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制造威胁的汇通派中医,鲁迅对此是相当清醒的。不仅仅是针对何廉臣的批判,1929年鲁迅、余云岫等人对“皇汉医学”(可视为日本的中西医汇通派)的批判,以及西医界对中医使用现代医疗器械、兴办学校等现代化举措的警惕和抵制,都是直接针对中医之利用和转化现代医学知识下手的。
中西医汇通是自明清以来便自觉展开的医学实践,到了近代,受西医冲击,融合汇通渐成趋势,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东西融合开始受到批判,这与同时代的思想倾向大致相仿。就思想界的倾向而论,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经历了从“西学东源”到“中体西用”,再到20世纪初以制度上接纳现代民主政治为标志的“中西并用”阶段,融合可说是一个思想底色。
但新文化运动之后,全盘西化渐占上风,具有文化守成主义倾向的观念不被认可,这集中体现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对文化调和观念的抵制,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表现得再清晰不过。新文化知识分子更自觉地在新与旧的框架内讨论中西文化,陈独秀将“新旧调和论”视为当时社会上“狠流行而不祥的论调”。
鲁迅则将之命名为“二重思想”,认为这好比约燧人氏以前的古人合作开饭店,即便竭力调和,也只能半生不熟,认为社会要进步,“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鲁迅的“二重思想”论与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颇有可比之处,虽然他们在价值判断上不同。
金、刘二人将新旧之争中这种具有调和色彩的二元论理性视为1895年(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典型特征。如果说上述讨论还是思想领域具有形而上色彩的论争,医学领域的新旧之争尤其是针对汇通派中医的批判,则是在疾病与身体知识(形而下)的层面提供了理解这种分歧的场所。民国时期力主废除中医的余云岫就认为:
今日吾人之所谓医学者,科学也……旧医之学,以太古以来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之以谬误之解剖、空想之哲学,推演而成生理、病理者也。新旧医学,其本末颠倒如此,尚得谓有可通之路哉……无沟通之路可寻,而必欲勉强牵合,则有格格不入之势,虽同冶一炉,犹然冰炭水火,貌合神离……亦惟以欺俗世、盗虚声已耳!
余云岫谈到的问题正是鲁迅的何廉臣批判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力因素下被迫展开的,中医现代化亦如此,其间充满纷争,从中西医汇通到当代的中西医结合,从民国时期盛极一时的“艾罗补脑汁”“人造自来血”到当下形形色色的补脑液、补血剂,以及围绕中成药之研制,诸如青蒿素究竟归功于中医还是西医的争论,乃至刚刚过去的全球疫情下围绕连花清瘟功效之争论,等等,都属于鲁迅、何廉臣批判延长线上的问题。
鲁迅的何廉臣批判至今已近百年,一方面,中国医学图景并未按照新文化知识分子的预期展开,中医现代化持续走到当下,并成为现代中国医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这种进展似乎也未能取消鲁迅的何廉臣批判中的合理性。不仅如此,即便在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大大进步的当下,中医话题仍然是引爆社会撕裂的敏感话题之一,相关论争似也不见得比鲁迅所处时代更为温和,这凸显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复杂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邓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