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S (ID:neusmag),作者:张旭晖,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鼠类、猴类等非人类的动物常被用于实验室研究之中,这些动物实验一般用于环境和生物化学研究、产品和药物开发等。对于绝大多数实验用动物而言,其下场往往是死亡。据估计,每年用于实验的动物数量远超1亿只[1]。
然而,作为实验对象,我们对于人类与动物存在明显的双标:对人类不能实施任何对人本身有危害的研究,且只有在知情同意的状况下,才能被允许参与研究;而对于动物,它们一次次地成为了人类研究的“基石”,人们既没有问过它们是否知情同意,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禁止对动物开展有害实验。那么,动物实验真的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吗?如果答案是能,那我们是否应该在研究的同时,加入更多的伦理道德考虑?如果不能,又有什么方式可代替动物实验呢?
动物实验:历史悠久但效用存疑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动物实验已成为了科学的一大支柱。许多分子机制、生理过程和疾病状态,涉及复杂的组织和器官水平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多个器官系统之间的交互,在开展药物研究时,试管内难以构建复杂反应、疾病表型以及药物动力学行为,动物模型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且随着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可以对动物实施定向工程,以便针对特定药物或疾病展开研究。同时,出于伦理原因,许多实验条件(如高能辐射、致命毒物等)无法对人体实施,动物便成了理想的实验对象[2]。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法律法规中强调动物实验的必要性。例如,自1938年起,美国政府便要求新药与化妆品产品开发,需进行动物实验。该举措是为了规避此前一系列药物或化妆品导致用户伤亡的情况。到1962年,另一项修正案进一步要求,企业在开展任何涉及人类的试验前,必须证明药物的安全性以及能适用于动物[3]。然而,除了保护人类受试者及未来用户的安全,动物实验是否真的能为药物及化妆品开发背书呢?
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实际上,人类临床试验的成功率本就不高。据估计,多达90%的新药都会面临失败[4]。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预测药物对人的安全和效率时,动物实验的结果往往只能提供微弱的支持。
2007年,一项针对221个动物实验的元分析表明,动物实验结果能够预测人类临床试验的概率只有50%[5]。无独有偶,2015年,一项针对37种化学物质对小鼠和人类毒性的研究,也只得到了随机水平的预测效果[6]。即使是已经通过药监局批准的药物,动物实验也只能对其中19%的药物给出有效预测[7]。
看上去,动物实验就像是抛硬币,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临床伦理学家盖尔·范·诺曼(Gail Van Norman)也提及,“在动物身上安全的药物中,有50%不能继续投入市场,因为它们对人类有毒,而50%恰好是随机概率。”
动物实验继承者:器官芯片技术
细胞生物学家唐·因格贝尔(Don Ingber)指出,即使动物能够展现出人类疾病的全部症状,但其机体患病的通路可能完全是不同的。而新的药物以及精准医学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差异。近乎半数新药都是生物制剂,包含单克隆抗体、腺相关病毒基因载体和CRISPR RNA疗法,它们针对的是人类生物学,以至于甚至不会在非人灵长类体内与分子发生反应。
此外,动物实验无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根据盖洛普调查,从2001年到2017年,动物研究的人群接受度从65%降低至了51%,反对率则从25%上升至了44%[3]。由此来看,无论是科学和道德,似乎都在提醒我们寻找新的方式。
近十年的科技发展为推动解放动物实验提供了可能。2010年因格贝尔团队在《科学》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肺器官芯片(organ-on-a-chip),它是一种物理微尺度的特定人体模型,以硅为原材料,尺寸仅仅和橡皮擦相当,包含多个微流体通道和多孔柔性膜,在膜的两侧分别培养不同的细胞,可实现对人体肺泡中的呼吸伸缩生理过程进行模拟[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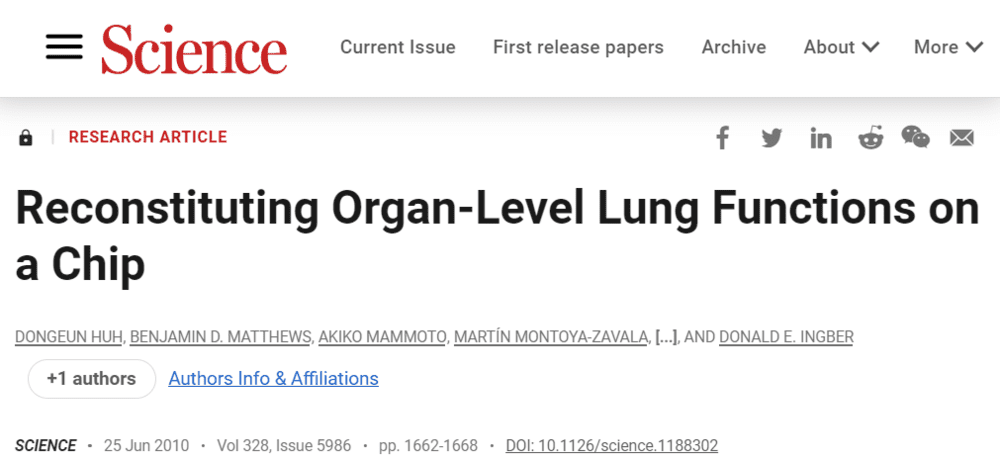
论文题目:Reconstituting Organ-Level Lung Functions on a Chip
在此之后,器官芯片迎来了革命性的发展。仅因格贝尔团队就开发出了超过15种器官芯片,包括肠、肾和淋巴结等。相比于过往的细胞研究,器官芯片能够模拟真实的生理过程,可以根据用药方案分析药物浓度随时间在人体内的变化方式,同时,它们与人体的相似性将使得研究结果更为有效,透明芯片也有利于研究者进行观察。“动物是某种黑盒”,因格贝尔评价道,而现在“你能够深入了解药物作用的机制、药物毒性的机制以及疾病的机制”。
器官芯片相较于动物实验的效率提升也将是显而易见的。以毒性测验为例,使用肺芯片可以测试二十多种药物,预测效果比动物研究好7~8倍[9]。在药物开发中也将有助于企业针对亚群体展开更有针对性的测验,能够节省数年时间和数百万美元的成本[3]。
新法案:更加多元的非临床研究
近期,美国的一项新法案(The FDA Modernization Act 2.0)修改了自1938年前对药物开发的规定,将原有的“动物”改为了“非临床试验或研究”。自此,在开展人类临床试验前,动物实验不再是药企的必要工作,基于细胞或计算机的试验都将被纳入。今年9月,此次法案修改在美国参议院获得了全票通过,极为少见地,共和党和民主党均对此表示支持。
法案的成功修改,当然离不开技术突破,包括器官芯片在内的多种技术都为降低动物实验需求做出了贡献。例如,利用个体细胞改造组织以及培养类器官被用来测试细胞对于药物的个性化反应,计算机模型也已足够发达可用于快速筛查许多化学物质的潜在用途与危害,有助于药企缩小新药的搜索范围或发现已有药物的新用途。
该法案得到了社会层面的许多好评。“FDA现代化法案2.0将加速创新,通过减少目前科学不支持的繁文缛节,为市场更快速地带来更加安全、更高效的药物。”议员兰德·保罗(Randal Paul)对该法案高度称赞,“这项两党法案的通过朝着结束动物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迈出了一步。”
但相对于政界人士,大多数药企似乎集体噤声了,目前还只有位于特拉维夫的Teva制药公开表示支持法案,辉瑞也在网站上宣称承诺减少或取代药物研究中的动物,或至少减轻它们的痛苦。诚然,新技术的发展为解放动物带来了许多利好,但问世时间尚短,加之动物实验早已成为药物开发的常规流程,新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动物实验的现状,未来仍然充满了未知。
参考文献
[1] https://www.animal-ethics.org/animal-experimentation-introduction/
[2] Ingber, D. E. (2020). Is it Time for Reviewer 3 to Request Human Organ Chip Experiments Instead of Animal Validation Studies? Advanced Science, 7(22), 2002030. https://doi.org/10.1002/advs.202002030
[3] https://neo.life/2022/10/what-if-we-didnt-have-to-test-new-drugs-on-animals/
[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90-of-drugs-fail-clinical-trials-heres-one-way-researchers-can-select-better-drug-candidates-174152#:~:text=Despite%20these%20significant%20investments%20in,advance%20to%20the%20approval%20stage.
[5] Perel, P., Roberts, I., Sena, E., Wheble, P., Briscoe, C., Sandercock, P., Macleod, M., Mignini, L. E., Jayaram, P., & Khan, K. S. (2007).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effects between animal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trials: Systematic review. BMJ, 334(7586), 197. https://doi.org/10.1136/bmj.39048.407928.BE
[6] Wang, B., & Gray, G. (2015). Concordance of Noncarcinogenic Endpoints in Rodent Chemical Bioassays. Risk Analysis: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35(6), 1154–1166. https://doi.org/10.1111/risa.12314
[7] van Meer, P. J. K., Kooijman, M., Gispen-de Wied, C. C., Moors, E. H. M., & Schellekens, H. (2012). The ability of animal studies to detect serious post marketing adverse events is limited. Regulatory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RTP, 64(3), 345–349. https://doi.org/10.1016/j.yrtph.2012.09.002
[8] Huh, D., Matthews, B. D., Mammoto, A., Montoya-Zavala, M., Hsin, H. Y., & Ingber, D. E. (2010). Reconstituting organ-level lung functions on a chip. Science (New York, N.Y.), 328(5986), 1662–166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88302
[9] Ewart, L., Apostolou, A., Briggs, S. A., Carman, C. V., Chaff, J. T., Heng, A. R., Jadalannagari, S., Janardhanan, J., Jang, K.-J., Joshipura, S. R., Kadam, M. M., Kanellias, M., Kujala, V. J., Kulkarni, G., Le, C. Y., Lucchesi, C., Manatakis, D. V., Maniar, K. K., Quinn, M. E., … Levner, D. (2022). Qualifying a human Liver-Chip for predictive toxicolog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p. 2021.12.14.472674). bioRxiv. doi: https://doi.org/10.1101/2021.12.14.47267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S (ID:neusmag),作者:张旭晖,编辑: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