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谢婵 编辑|马可
春节即将到来,人们陆续返乡。经过奥密克戎病毒的劫掠之后,位于湖南省中部的衡阳市衡东县城正在逐步恢复生机。但在县城最好的医院——衡东县人民医院里,医护人员和重症患者们仍然在与新冠搏命。
过去三年,疫情在这里留下很多痕迹:院门口还没来得及撤掉的巨大核酸棚,小轿车上放着“疫情防控监督员”的红袖章,还有随处张贴的告示牌,提醒人们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禁止探视。但现在,没有人在乎这些,人们略过告示,随意出入医院,有人甚至不戴口罩。
这家医院,各科室加起来有500多个床位,医务加行政、后勤人员共900余人,其中急诊科33人,呼吸科38人,两个ICU病房加起来共54人。过去三年,他们几乎没有过跟新冠病毒正面交锋的经验。疫情放开后,你能想到的所有困难都集合在这里了:医护感染,ICU床位不足,呼吸机不够,药品紧缺……医院想了许多办法应对,甚至冒险般地启用了一栋还未交付使用的大楼,那栋楼在通水、电、空调之前,要先为新冠病人们打通氧气输送渠道。

那是一罐半人高的氧气瓶,护士将它从走廊另一端搬出来的时候,连着磕到两张病床。她小心翼翼踢开病人的鞋子——病床太满了,尽管高峰期已经过去一周多,呼吸科走廊里仍然堆满了病床,一共28张,一直延续到电梯口和厕所旁。
护士们没有多余精力去计算每天要用多少罐氧气。每个涌进呼吸科的老人都需要吸氧,每个临时床位旁边都立着一罐氧气,每一天都能听到很多次氧气瓶滚动的声音,整层楼都会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 护士在给病人换氧气瓶。
最难熬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但疲惫、恐慌和无能为力依然在延续。1月11日,三个呼吸科医生一直到零点还没下班,他们在看老人们的肺部CT。对老人们来说,病毒如此猛烈。一位老人刚来时,CT片显示肺部有点点絮状,过了五天,CT显示她肺部几乎全白,医生们已无能为力。一位没有基础病的六十多岁老人被诊断为重症,要转运去衡阳市里的医院,但临上救护车时,血氧降到了四五十,实在没有办法,又拉回了ICU,没过几天,老人就去世了。
一整晚,护士们都在处理突发状况,病床呼救的铃声此起彼伏。晚班3个护士负责照料这一层的90多个病人,这是平时工作量的两倍。
靠近护士台的一张病床上,张勇在陪伴母亲。老人有糖尿病,躺在床上吸氧。张勇在莆田做生意,妈妈感染新冠,他不得不放下生意回来照顾。住上院的第三天,老人有些糊涂,总以为自己还在家里,一会儿说要去关门,一会儿要去拿被子,一会儿又让张勇去看看鸡怎么样了。到了晚上,老人吵着回家,张勇耐着性子陪着母亲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来来回回,刚把她哄上床,她就要吵着下来。他像骗小孩子那样骗她,有时候说“医生不让你回家”,有时候说“这里没有门”。她还是下了床,没走两步,就被输氧的管子绊住。
黄珏的父亲运气好一些,住在病房里,老人主要症状是“出气不赢”(方言,呼吸不畅)、全身酸痛。黄珏送他来医院那天是1月2号,没有人查健康码,也没有人阻拦,她还有点不习惯,“感觉打仗打完了,突然把所有的东西就丢在这了。”那天,急诊室里人挤满了人,压根没有地方下脚。呼吸科护士跟她讲,“我这里60多张床位现在住了90多个病人。”
到了晚上,走廊上不会关灯,争吵声、叹气声、呼叫护士的铃声、氧气瓶滚动的轰鸣声、睡不着觉的人们刷短视频的声音,全部混在一起。临近年关,县城的鞭炮声也在夜晚频繁响起。
很多老人呆不下去,天天吵着要出院。呼吸科护士谢文明完全理解,“要是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可能也睡不好”,但这就是医生和病人要共同面对的状况:“要说更好的解决方案,真的拿不出来了。”

■ 夜晚的住院处走廊。
有一天查房的时候,女医生一遍遍告诉其中一个病人,“你是新冠阳性,你不能出院,要是熬成肺炎你就白折腾了。”
住了十来天后,黄珏的父亲也天天吵着出院。下午不输液,他躺着无聊,就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溜出去闲逛。他逛去过急诊,看见了“病人多到要把医生吃掉”的场景,他还逛去了另一栋住院楼,在那栋楼的七层和八层,“全是我们这种病”。
谢文明回忆,刚放开时,几乎每天都送过来20多个病人,那时候呼吸科室里大部分病人还是阴性,她们把走廊中间的门关上,将阳性和阴性病人隔开,坚持了一周,病人越来越多,“所有的病人都变成了阳性”,没有人再提起防控的事情。
所有医护人员和整层楼的病人几乎都感染过了,最近突然来了一个阴性病人,他问谢文明,自己要在这感染了怎么办,谢文明没有答案。

放开第二周,县医院就开始应对感染高峰。
最高峰时,医院每天来看病的人有900多个,而平时接诊量只有400多人。呼吸科原本62张病床都是满的,几乎每天都有20多个人在等待排队入院。最忙的一天,原本夜里12点要下班的谢文明一直忙到了凌晨5点。那天她抢救了一个危重病人,抢救完写材料,还要给其他病人输液打针。
她一直在心里喊:“怎么这么多病人,怎么这么累。”但这是自己的工作,她得做。

■ 呼吸科护士谢文明深夜给患者拿药。
几乎就是靠着这种朴素的信念,医护人员撑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几乎所有医生护士都在发热,带病上班,有的呼吸科医生一边给自己输液一边去看病人。医生陈海军他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一直忙到凌晨1点,回去就高烧了,第二天还是得来上班,“病人太多了,不忍心,不去管好像心里过不去。”
护士们“打着寒颤”去做急救,县医院120急救中心主任崔建很心疼同事们:“这不是坐办公室,你熬不住可以歇一会儿,院前急救的护士是要去救人的啊。”
120急救中心是受到冲击最猛烈的科室之一。高峰期,出车量一下子激增到日均30多次。有个护士一天拉了10多趟病人,在急诊门口放下病人后崩溃大哭,哭完又继续出车。崔建说,“和网上的段子一模一样,发烧的司机载着发烧的护士去拉发烧的病人。”
医院一共有四台救护车,其中一台是负压救护车,过去三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四五次与新冠相关的出车记录,有时候是运阳性病人,有时候是去拉密接者。但现在,崔建说,以目前120急救中心的资源,根本不足以应对放开后的这一次冲击。
急诊床位一张都腾不出来的时候,病人只能睡在120急救车的担架上,这也导致救护车无法去接下一个病人。

■ 救护车驶出衡东县人民医院。
县医院处理不了的时候,他们就要想办法把病人转运到市里医院。一天晚上,一辆救护车转运一个危重病人去衡阳市里,“去的时候知道没床位,但还是想碰碰运气,万一赶到的时候正好有位子空出来呢。”那天晚上折腾了三个小时,跑了五个医院,最后“耍赖似的把病人扔给了市里医院”。
转运始终是个麻烦事。1月11日这天,ICU的一位医生站在门口给市里的三家医院连着打了三个电话,一遍遍讲述他手头一个病人的情况:“3号送来急诊的,4号突发心衰插了管,冠心病叠加病毒肺,后来就陷入了昏迷,一直到今天还没有醒过来。”家属肖自清和家里姊妹站在ICU的门口,听医生打完电话,然后告诉他们结果:都没有床位。他们问了医生好几遍,老人能治好的几率有多大。但医生没有答案,唯一能告诉他们的是“要看病人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县医院之前,肖自清的母亲在家里喊“全身都痛”,村里医生上家里来看了一下,开了一服中药,但吃完没多久就咳了血。
崔建提到,“对口帮扶我们的衡阳市南华医院帮了很多忙,但现实情况确实是一床难求”。由于乡镇医院条件有限,从乡村转运到县城的患者也很多。但很多时候,乡镇医院的医生都会让老人们自己打电话叫救护车。崔建观察到,老人们喜欢在早上7点打来电话,他猜想,老人们可能以为医生早上才上班,很多人都是熬到天亮才打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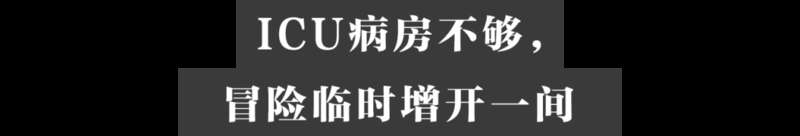
陈海军工作了30年,作为急诊科和ICU主任,危重病人平日里也见得多。但这一次,场面仍然让他感到艰难。往常急诊室里最紧急的时刻也不过是同时开展两台急救,但在感染高峰,这里常常有四台急救同时进行,再拉进来的病人只能放在地上,医生跪着做心肺复苏。“这个病人还没看完,又来一个。一个插管的,一个上呼吸机的,谁有生命危险就先管谁。”

■ ICU病房里。
许多决策都是在慌乱和冒险中做出的。为了尽可能多收治病人,医院领导瞄上了那栋刚建好、还未交付使用的大楼,将其中的三层拿出来,增设三个科室,包括一个ICU和两个综合医科。这栋楼里空空荡荡,电梯间里裸露着木板,没有通水、电和空调之前,却要先通氧气。刚住进去的几天,氧气盘总是发出嘀嘀嘀的警报声,要么压力过高无法使用,要么压力太低供氧不足。呼吸机也来不及喊工程师过来调试。
开设一个新的ICU,目前并不算是合适的时机,ICU病房的建设比普通病房要求更高。但病人实在太多了,“危重病人不收进来可能就丧失生存的机会了”。医院接收到卫健委最新的要求是“应收尽收”。有一天晚上,党委书记和分管业务的院长临时开会,“不开肯定是不行的”。陈海军记得,新ICU12月20号那天开科,起初只有8个床位,后来增加到16张,最多时收治了19个重症,“基本上以新冠重症为主”,但平时,对于一个县城医院来说,同时有三四个危重症已经是“了不得”的情况。
新增的综合科的医护人员,大多数是曾经负责核酸、引导扫码和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新增的三个科室提供了150多个床位。随着感染人数越来越多,床位还是不够,病人一直溢到外科,甚至是产科。过去,外科医生临时转为救治内科疾病的医生,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感染科主任邓昌鸿同时兼任综合一科的主任,常驻新楼的七楼,从内科和外科抽调来五位医生共同负责这个科室的54个病人。
为了填补人手的空缺,连后勤和行政办公室也抽调了20多人到临床一线。在呼吸科,甚至有一位50岁的、已经离开临床多年的曾经的护士也回来帮忙。“刚开始肯定有些不适应,但同事们回来帮忙还是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采购设备的手续也简化了,采购呼吸机不再需要招标,打个电话报备就行,院领导和县领导都支持了该做法,“只要能给病人快速用上就行。”但呼吸机的价格翻了倍,对于原本财政压力就大的县医院来讲,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20多天前,崔建订了一台新的负压救护车,绕开了原本繁琐的救护车报备手续,但也许是各地都在抢购救护车,这辆车还没有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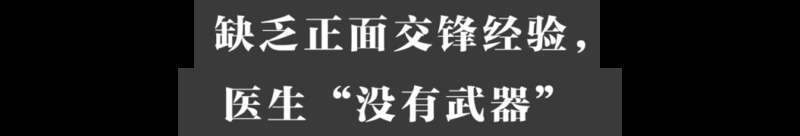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过去三年里,这里的大多数医生都没有直接跟新冠病毒打交道的经验。呼吸科一位副主任和感染科主任邓昌鸿是为数不多接诊过新冠患者的医生,但那也是2020年初的事情了。此后政策有了明确规定,县里的新冠病人会全部转运去市里定点医院,“做什么防护、走哪条线路都有明确的规定”。
“新十条”出台之前,也有一些轻症阳性患者被留在了院里的新楼集中隔离,“没什么治疗方案,基本上就是给中药,隔离在这里自愈”。
邓昌鸿是那种更在乎科学和常识的医生。2020年初期,他率先建议医院单独开设发热门诊。过去三年,他有过对现状失望而转身的时刻,最终还是回来牵头承担起新冠救治培训的重任。普通医护对这个病仍然有很多困惑之处。他的经验和讲课材料主要来自于南华系、湘雅系、深圳三院等医院的诊疗方案,其中南华医院是衡东县人民医院的对口帮扶医院,而深圳三院在此前曾经收治过很多新冠患者,“数据比较丰富”。卫健委的诊疗方案他也看,但“很多地方有些模糊”。
抽空学习显得非常奢侈,一位护士提到,医院前阵子下发了一些学习材料,但她那阵子刚感染,又没日没夜地照顾病人,实在没有力气学习。这阵子身体好了一些,但等输了那么多液,查完房交完班,补好当天的材料回到家,“连饭也不想吃了,别说是学习”。
急诊科和ICU主任陈海军也说,高峰期,“连病历都没有时间写,更不要谈新冠救治业务的讨论和复盘总结”。

■ 陈海军主任在ICU查房。
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这里也缺药。布洛芬时有时无,“这段时间有,用完了就没有了,过几天再等上面配送下来一批”。最长的时候,布洛芬断供了三四天,只能靠其他药物代替。
院内还算充足的是国产阿兹夫定,刚放开时,邓昌鸿去县委开会,提出要“发狠”地储备药物和设备,他不敢居功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建议,但县里提前备好了阿兹夫定。这款原本抗艾滋的药物如今被用于治疗新冠,“艾滋吃3片,新冠吃5片”。由于阿兹夫定的临床数据并不全面,此前曾有过不小的争议。但在这里,许多医生们都感觉阿兹夫定“吃了还是有效果”。
在呼吸科,患了新冠的老人们拿到的药主要是阿兹夫定、银黄清肺胶囊和肺力咳合剂,银黄清肺胶囊主要用于支气管炎和咳嗽,2019年曾在巴基斯坦临床试验成功,被誉为中成药正式走进巴基斯坦的标志。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早期收治的新冠肺炎普通型患者中,有研究者选取了45例应用肺力咳合剂联合常规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是应用肺力咳合剂配合常规治疗3天后,发热、乏力、咳嗽症状消失率分别达33.3%、33.3%、44.1%。
此前,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一次医护人员培训会中提到,“目前社区医院针对新冠病人一般就开四种药:退烧药+抗菌素+咳嗽药+中药。但这大概率是在消耗病人最宝贵的病后72小时,因为这些药物都不主攻新冠病毒。很多老人服药后症状没有减轻,住进上级医院后也只是打吊瓶、吸氧,最终无法缓解肺部发炎症状,导致死亡。”
邓昌鸿认为,这不能怪基层医生,因为他们“没有武器”。哪怕是在县医院,抗病毒性药物几乎都没有,陈海军提到,“(新冠诊疗)指南推荐的药物基本上都缺”,抗生素紧缺、免疫球蛋白也紧缺,呼吸科医生打开自己的电脑,搜索“MY”(注:免疫),显示两种免疫球蛋白都是“0瓶”。尽管这不是治疗新冠的药物,但在临床一线,医生会用免疫球蛋白治疗合并感染且免疫力低下的患者。辉瑞也向上争取过,医生们听说“有过几盒”,但大多数医生没有见到过这款药。在医院办公室工作的一位主任说,“哪怕是市里的医院,估计都没有这个药。”一位护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看看辉瑞那款叫Paxlovid的药是哪几个字母拼出来的。

和一线城市的医院相比,县医院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这里很少能遇见因为焦虑和慌乱而抢购新冠特效药的故事。这里也没有太多的规矩,老人去世,家属们就在病房里披麻戴孝点起了烛火,还在住院部楼下放了一挂鞭炮。这里不禁烟,呼吸科的窗台外密密麻麻全是烟头,家属抽,患者也抽。有一天晚上,一辆老年电动代步车,开上了六楼。
一位医生告诉《在人间》,对于新冠病人的救治,目前医保报销力度“比其他病还要高一点”。但对于很多危重症的家属来说,医疗费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ICU门口,肖自清听见医生说大概的治疗费用要好几万。他愣在原地,好半天没有再回医生的话。但昏迷中的母亲中间睁了一次眼。就是这一眼,让家人又燃起了希望。最终他们签了字,将人转运去市里。

■ 老人家属在医院门口商量转运事宜。

■ 急救人员将肖自清母亲转出ICU,准备转运至衡阳市里医院。
一个老人在家里熬了十几天,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医院。直到老伴说,“快过年了,咱们再不好都没人买年货。”他才愿意住院,现在,他睡在走廊上,老伴睡在病房里,两人都是排队排了一天多才被收治入院。
陈海军说:“很多病人,呼吸困难的时候不肯来,等到后面肺部病变很严重了,已经有一些其他器官的并发症了才肯来,这时候几乎都是重症了。”
最近几年,政策上不断倡导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县域内整体医疗水平。院里的新住院楼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修建起来的。新的住院楼会带来更多床位、更好的设备。每个科室都期盼过搬去新楼,对呼吸科来说,在每年的流感季,他们不用再加床让病人睡在走廊上,也不用再搬那个高大的氧气瓶。只不过,谁也没想到,新的大楼还未正式投入使用,疫情冲击就如此猝不及防地到来。
熬过这一次冲击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许多医护人员都在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崔建的父亲是在这一次感染高峰里去世的,去世前,家里只备了普通的感冒药。一位护士的外婆在县医院去世了,她要等下班才能赶去殡仪馆。院长的母亲也去世了。
距离放开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急诊科的医生们终于有空在下班后和同事们一起吃顿饭,在饭桌上,一位医生举起手机读出声来:有二十多个院士在这个冬天离世。
这天晚上,护士谢文明推着两车的药去给病人输液,等查完房,交完班,又坐回电脑前写最后一点材料。接近凌晨两点,她终于起身,这离她的正常下班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在洗手池前摘掉口罩的瞬间,她近乎发泄似的重重叹了一口气。
在她守在病房的这些时间里,医院门口的道路每一天都比前一天繁忙,汽车从早堵到晚,买完年货的人从马路上横穿而过。摩的师傅、卖玉米的、算命的摊都守在医院门口。街道上的香樟叶子郁郁葱葱,路边绿化带也换上了颜色鲜艳的塑料花迎接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