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受访者基兰·塞提亚国内没有什么介绍,他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分校哲学教授,前段时间的文章《不公正随处可见,你能做什么?》就出自他。乍看之下,塞提亚思考的问题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人生中的痛苦与悲伤?痛苦是没有意义的吗?悲伤是一种自怜和自私的体现吗?上述问题,有无数的哲学家都详细论述过,只不过,塞提亚仍旧对这个主题有自己的洞见。在他看来,悲伤/痛苦是一种复杂的压力反应,且并没有证据表明,“悲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恳求、沮丧、接受)是对所有人适用的模式。
对我而言,塞提亚就人生的“目的活动/非目的活动”的区分还是很有启发的,按照他的原话就是,“你不会碰到‘你当下的行动正在抹消或动摇你对这项活动的参与’这种问题,因为你对这项活动的参与中没有任何试图抹消它自身的固有性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Brian Gallagher,由译者苦山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校对:光明右使,原文标题:《悲伤,它并不总是一种自怜》,题图来自:《旺达幻视》
旺达·马克希莫夫(Wanda Maximoff)正因弟弟刚刚逝世悲痛不已。这位拥有心灵感应和能量投送超能力的超级英雄独自坐在床脚,在看家庭情景喜剧《左右做人难》(Malcolm in the Middle),这时她叫来了伴侣幻视(Vision)。
这位敏锐的、有着迷人英式口音的人形人工智能穿过她的卧室墙壁,在就该剧令人费解的打闹式幽默闲聊了几句之后(幻视不明白为什么凉棚倒塌在马尔科姆的父亲身上是个笑点),他很快从旺达的戒备和疏远中意识到,她的心情并不愉快。

接下来是漫威迷你剧《旺达幻视》(WandaVision)中最令人称道和感动的时刻之一。“旺达,我并不自以为知道你现在的感受”,幻视说,“但我想知道——如果你想告诉我,如果那能给你带来些许安慰。”旺达仍然十分戒备,她说:“你为什么觉得谈论这事能给我带来安慰?”幻视以为这是一个真诚的问题,而非一种回绝的态度,便开始解释他读到过的某些内容,但旺达打断了他:“唯一能给我带来安慰的是再次见到他。”
最近,在读基兰·塞提亚(Kieran Setiya)的新书《人生多艰:哲学如何帮助我们找到自身之道》(Life Is Hard: How Philosophy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时,我想起了这个场景。该书除了终章(“希望”)之外的每一章都讲述了我们必须面对的困难,包括病痛、失败——和悲伤。
塞提亚写道:“悲伤总如混乱的波澜一般袭来,不受理性所控。”旺达的状态也完全符合这种描述。在冷淡地回应了幻视伸出的援助之手后,她看到他脸上浮现出悲伤和沮丧,于是对他说:“对不起。”她几欲落泪地说下去:“我太累了。就像有一股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打来、把我击倒, 当我试图站起来的时候,它又一次向我袭来。我没办法……我迟早会被海浪淹没。”
“不”,幻视说,“不会的。”旺达笑了,转向他,问道, “你怎么知道?”
“唔,”幻视说,“因为人生不可能只有悲伤,对吗?”他似乎也明白,对于自己接下来要提出的情感和哲学观点,他本人并非传述它们的最佳人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失去,因为我不曾有过心爱的人可失去,”他说,“但,悲伤如果不是不渝的爱,又能是什么呢?”
“我很喜欢。”当我在我们的视频通话中描述这个场景时,塞提亚如是说。他家离他执教哲学的麻省理工学院不远,他坐在家中的办公室里,四周都是书架,书本堆满了各个平面,摇摇欲坠。他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张老棒球场的黑白海报(在塞提亚有关失败的讨论中,棒球经常出现)。
“看待悲伤的正确角度是,它是一种持久的爱的表现”,他说,“悲伤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其实是一种复杂的压力反应,各种感受——恐惧、焦虑,有时也有快乐的回忆——都被绑定在这种反应中。这种反应也就是,当对象不再如过往那样可及时——当对象离去时,爱却仍在继续。”

塞提亚解释说,幻视阐释悲伤的方式十分重要,因为这种看待悲伤的方式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这样一种倾向形成了对抗:它将悲伤视为“只要我们在引导下好好面对现实,就可以轻易消除的事物”。只要我们能够接受我们所爱的每个人终将逝去,只要我们接受了死亡是最终的结局,那么我们就能摆脱悲伤的痛苦。
这种倾向认为痛苦是徒劳的。对于塞提亚来说,这种看待悲伤的方式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可以消除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件需要细想如何好好面对的事。”
在我和塞提亚的谈话中,我试图将他整本书的内容都涵盖其中,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引人入胜、颇有见地。在悲伤之外,我们还讨论了许多内容,包括疾病(disease)和疾患(illness)的区别、好好生活为何不仅仅是快乐生活、孤独的坏处、对疼痛的哲学思考如何帮助他管理自己的慢性骨盆疼痛、对社会正义的理智思考为何不能取代真正的改革倡导、电影《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中的哲学——当然,还有生命的意义。
问:你认为在“应该如何处理悲伤”这个问题上,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答:人们谈论悲伤的五个阶段,但是事实证明,悲伤分为五阶段的理论并没有实证支持(译者注:此指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于1969年提出的模型,认为悲伤包括“否认、愤怒、恳求、沮丧、接受”这五个阶段)[1]。它是高度不可预测的。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模式。
还有很多证据表明[2],强迫人们处理悲伤会适得其反,如果你现在不想谈论它,也不想去细思它,这多半就是正确的反应。因为被迫直面悲伤往往会放大创伤反应、使创伤反应变得更加复杂。
从哲学上讲,关于悲伤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总是一种自怜。它并不自私。悲伤的某些方面完全是他向的,只与你所爱之人的失去有关。消除悲伤意味着无法正视、理解现实。它是一种失败,主要是因为它意味着你无法承认你失去了对方。
我认为,只要我们学会了像哲学家那样将两种悲伤区分开,就可以更清晰地关注上述这一点——哲学家将我所说的“关系性悲伤”(relational grief),也就是对于关系本身的悲伤,和仅针对失去他人、因他人逝去导致的丧亲之痛这种悲伤做了区分[3]。

问:我喜欢你提出的关于悲伤的难题。你说,假如悲伤的理由是我们失去了所爱之人,而这种失去的事实永远不会消失,那么我们似乎永远也没有理由停止悲伤。
答:没错。看起来,如果一时感到悲伤是件合理的事,那么,一世陷于悲伤也是合理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人要如何安排自己的悲伤呢?因为我们不想永远沉浸于悲伤之中。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引入“悲伤应该采取什么形式”这类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仅仅对悲伤做理性的推理(试图想清楚该对已然发生的事给出怎样的理性反应)是无法帮我们得出答案的。
不永远陷于悲伤当然是可以的,但仅仅是理性一者并不能给我们任何进一步的指导。因此,我们不得不落回非理性但可以从文化中找到的习俗。或者,如果没有这类习俗的话,我们必须发明我们自己的习俗或是我们自己的哀悼传统。
问:悲伤是否能将“快乐”(happiness)和“好好生活”(living well)鲜明地区别开来?
答:是的,因为悲伤是一种不快乐的形式,或是一种情感痛苦的形式,但这种不快乐与痛苦并非和好好生活彼此对立。以这种方式回应失去他人的现实是好好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快乐是一种信号,昭示着糟糕的事情。但这个信号并不是在提醒你应该改变这种不快乐,因为你无法改变它。它昭示着某件可怕的事情已然发生,而你正在正确地关注它、理解它,以作为对这件事的回应。
有一个哲学上的思维实验能够阐释快乐和好好生活之间的对立,那就是把某人置于一个模拟现实中:他们是唯一一个被置入这个模拟世界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并非现实。但模拟出的世界很棒,他们也并不知道它是虚假的。他们真心感到很快乐,但他们自以为在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虚假的,他们并没有真的在做这些事。他们并没有真正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在与他人或世界交往、接触。
在这个例子里,一个人经历了快乐,却并没有在好好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并把“好好生活”定义为以正确的方式与现实接触。
我认为这和这样一种愿望是一致的:当你好好生活的时候,快乐会是它的副作用。我们应该认真对待我们的不快乐,不是把它当作需要逃避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信号,表明我们正从周围的世界里发现了一些需要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处理的事物。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在传达我们的生活正如何进行。
问:你说快乐是主观的,但“好好生活”不也是主观的吗?
答:你很难去说如何才算好好生活。如果你遇到某类人,他们对于如何生活的看法完全是自私的——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其他任何人——我不觉得有哪个观点能够证明他们是错的。但事实上,我确实认为,这不是一种好好生活的方式。他们就是在“如何生活”这件事上犯了个错误,即使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在书中,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书记员巴特尔比》(Bartleby by the Scrivener)的例子,这是一本精妙绝伦的中篇小说,故事里的巴特尔比宁愿不再做自己的工作、宁愿不接受帮助、宁愿不吃饭,最终死去。如果你真的认为对于“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那你就不得不如此评价巴特尔比:“唔,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没什么错。”
我不知道如何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些极端的例子中(一头是巴特尔比,另一头是那些彻头彻尾的自私者)看到,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界限,当你的生活方式超出了这些界限时,哪怕你恰好觉得这是适合你的生活,你也真的没在好好生活。你犯了一个错误。
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疾病和残疾与好好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该作何解?
答:在对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中,令人惊讶的结果之一是,与非残疾人的期望相比,盲人、聋人或有某种身体残疾的人群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高得惊人[4]。事实上,残疾对一个人好好生活的能力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实际影响。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过上体面的生活。
的确,缺乏视力或者失聪会断绝你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但是大多数的身体残疾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美好事物,让我们能够好好生活,而且,不论身体残疾与否,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触的、能够从中获得满足的事物本就相当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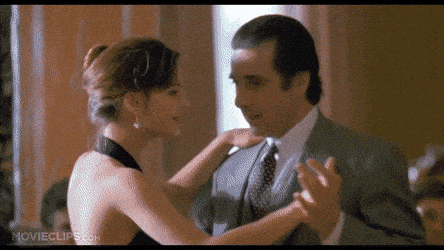
这表明,一旦你对人类的福祉有了多元化的看法,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局部身体残疾的人仍有可能过上相当好的生活,也能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得出这种结论的调查数据抱有猜疑。
问:你把健康的身体比作一种“透明界面”,在诸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还有身体。这对疼痛的本质有什么启示?
答: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疼痛是件坏事。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很愚蠢。通常而言,当哲学家们被要求举例说明生活中的坏事时,他们会提到疼痛,然后就不再多说了。但事实证明,疼痛在很多个层面上都是坏事。它之所以糟糕,理由之一在于它不仅仅是种糟糕的感受,还破坏了这种身体的透明性。
很多时候,当我们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时,我们只是专注于关注其他人,或是关注我们正在交流的对象,或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不会真正去思考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什么。
假如一个棒球运动员开始思考具体要如何移动双手去投球,这通常会成为引发易普症的原因之一(译者注:Yips,也称“投球失忆症”,是一种不自觉的腕关节痉挛)。这会干扰他们身体的正常运行。疼痛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它也往往会造成这一点。它使人过分关注自己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本透明的、对世界的体验。这就是经历慢性或急性疼痛的人们所面临的部分挑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在性”(inwardness)的一部分。
问:对于疼痛的这种理解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它吗?
答:对我来说,光是认识到这些描述就有助于我理解自己的慢性疼痛体验。慢性疼痛曾让我很迷茫,因为,在一天又一天里,我基本可以自如地生活,但考虑到实际的疼痛程度,它产生的影响又比我想象的要深刻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它不断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让我更加难以直接体验这个世界,而这种直接体验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到的。
这有助于解释我对哲学的工作狂态度。为了应对“疼痛阻碍了我与事物的关系”这个发现,我的主要策略就是让自己投入到一些足够引人入胜的活动中,让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以此来压倒我因疼痛产生的、对身体的注意力。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放松。如果我躺在沙滩上,没有什么外界事物能让我集中注意力的话,那么,我的注意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到我不希望去注意的地方。
问:多数人的轻微疼痛是否比少数人的深切疼痛更值得治愈呢?
答:尽管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我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承认这个事实会给我们对伦理学的看法带来很多困惑和难题。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唔,如果只有一个人处于深重的疼痛之中,如果我们给这一个人的痛苦程度打分,然后我们去观察一千个、一百万个或者十亿个正处于轻微疼痛中的人,再给他们的痛苦程度打分,那么当我们计算它们时,总会存在一个节点,在这个点上,多数人的痛苦超过了一个人的痛苦。”
事实并非如此。不论多少人的轻微疼痛都比不上单个人的真正剧烈的疼痛那么糟糕,也不比后者更值得缓解。

问:我喜欢你在书中将这个问题置于你自身的慢性疼痛这个背景下对其进行反思的方式。
答:像我这样认为许多人的轻微痛苦并不大于一个人的深重痛苦的哲学家通常会说,这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但是当你看向某个单独个体的生活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经常说长期疼痛的缓解可以弥补短期的锐痛,而且你能够意识到这种说法的吸引力:你可以这样想,也许存在一位患有慢性疼痛的人,此人可能愿意接受一场非常痛苦的手术,以短暂的剧烈疼痛来换取对长期的中度疼痛的摆脱。
但是这种说法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慢性或持续性的疼痛给未来和过去蒙上了阴影。它不只是一系列原子化的疼痛。它让你处于一种对未来充满焦虑的状态,让你难以回忆起不曾疼痛的过去。正是这些对预期和记忆的进一步伤害,使得慢性疼痛成为了一种可以用短暂剧痛来交换的东西。如果我所经历的只是一系列完全孤立的疼痛,那么这种交换就不会有意义。
问:社会隔离的痛苦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有什么启示呢?
答:对于社会隔离带来的痛苦,最好将它理解为社交需求的挫折——广义地说,也就是对友谊的需求。在公共政策中,人们对于孤独对健康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孤独如何激活了大脑中与身体疼痛有关的部分,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这是很正确的态度。但是,只有当我们从更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它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它剥夺了生命中最伟大的财富之一,也就是友谊。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隔离的痛苦是一个人作为人的基本价值没有得到承认、没有得到欣赏的痛苦,也是失去了欣赏他人这种价值机会的痛苦。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孤独是如此艰难(因为它否定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在实践的层面,它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孤独。
问:从伦理的角度思考孤独如何能帮助人们克服它呢?
答:如果我们缺少的是持续的道德尊重——如果缺少的仅仅是对我们存在的基本认可——那么我们甚至在建立亲密友谊之前就可以开始应对自身的社会隔离:只需要承认他人、也让他人承认我们即可。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的简单形式已足以满足我们在孤独或社会隔离时产生的需求。
有关孤独的社会科学理论所建议的也正是这一点:即便没有深厚的友谊或亲密的联系,你也可以仅仅通过鼓励人们与他人建立短暂的互动来消解他们的孤独感,并且效果惊人。基本的人际交往在满足我们的社会需求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问:新冠大流行会对我们处理孤独的方式产生长期影响吗?
答: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影响将是非常棘手的,因为我们已经转向了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如今,那些例行的小规模社会交往比过去更少见了。以前,在平凡的任何一天里,你都会和周围人进行一些小小的互动,因为你必须亲自去完成所有的事务。现在,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是远程进行的,我们失去的是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实际上却是我们社会现实感中的一个很深刻的部分。
问:你为什么在书中说孤独是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
答:这之所以对社会来说是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应对孤独所需要的策略是你很难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去实施的。也就是说,这里有个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当你变得与社会隔绝时,就会产生一种对社会交往的恐惧和焦虑,而这种情绪是难以克服的。
在新冠大流行的余波中,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弄清楚它对人们社会关系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规模之大是任何人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我们需要在社会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个人可以克服孤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人的帮助、他人伸出的援手、那些无法由个人单方面提供的社会支持,将会对解决孤独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认为,整整一代孩子的社会生活在各种敏感和成长的时刻被打乱了,他们很可能需要外界帮助他们从这种影响中恢复过来。
问:我们怎样才能在追求个人抱负的同时,不把我们的人生简化为一个能以成功或失败来评判的“项目”呢?
答:这个嘛,我认为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个是用单个总体式叙事来定义我们生活的倾向,我认为这是适得其反的,既因为这意味着存在一件可以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我们的事情,也因为它把我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一件“核心体验”的篮子里,从而让我们错过了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好事。但另一个方面在于,我们与这些活动的时间性的关联中存在一种转变。
我对目的活动(telic activities)和非目的活动(atelic activities)做了区分。这个术语来自语言学领域,但它要追溯到希腊词“telos”,意思是“终点”。目的活动是一种有最终结束状态的活动,这个最终状态是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比如在工作中获得晋升、结婚或找到一份工作。
我们把这类事情看作是“项目”,它们有着这样的结构:你想要的东西总在离你有一段距离的未来,或者说,在你实现它的那一刻,它就成为了过去、业已告终。而你现在所在做的就是努力完成它。你正在试图把这个意义的来源、这个项目、这个目的活动,从你的生活中抹去。这件事里有一种自我挫败、自我矛盾的特征。从最终来看,试图消除你生活中意义的来源并不是实现好好生活的一种自洽方式。
问:有哪些活动是不会像项目那样终止、值得我们投入其中的?
答:非目的活动是没有终止末点的活动。所以,走回家是目的活动,散步就是非目的活动。又或者,生孩子或是给孩子做晚餐是目的活动,而养育孩子是不断进行的非目的活动。
当你参与的是一项不以未来某个终点为目标的非目的活动时,你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满足感总是在未来,或是在目标实现的下一刻就被抛至过去。你不会碰到“你当下的行动正在抹消或动摇你对这项活动的参与”这种问题,因为你对这项活动的参与中没有任何试图抹消它自身的固有性质。
对于我们人生中的各项活动来说,一种非常有帮助的转变就是减少对目的活动或“项目型活动”的关注,转而去关注非目的活动的价值,也就是过程的价值。

问:这就是电影《土拨鼠之日》中比尔·默瑞(Bill Murray)的角色在无数次重温同一天之后所获得的洞察吗?
答:你可以这样想。这部电影之所以涵义丰富,部分原因在于它探索了许多不同的哲学思想。其中之一就是与目的和非目的活动有关的这个观点:主人公菲尔(Phil)被困在这个重复的循环中,无法完成任何事。他无法真正做成任何事情,无法给世界带来任何永久性的改变。因此,目的活动——至少是大部分的目的活动——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你可能会想,“啊,《土拨鼠之日》中的场景其实是在提出这个疑问:‘我们能否在非目的活动中找到足够的价值,使生活变得有意义?”
但事情并非全然如此,因为仍然有一些目的活动是菲尔能够做到的,也就是改变他自己,因为他每天都记得前一天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有很多非目的活动是他无法参与的。他只能参与那些发生在庞克瑟托尼(Punxsutawney)的活动。话虽如此,它仍然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不同活动间的区分;我认为,在我们尝试思考成功和失败时,就需要做出这种区分。
当你重视非目的活动,也就是参与某事的过程时,你与失败及成功的关系是极为不同的。假如这就是你生活的价值所在,那么你的人生就比我们的人生更少地被押宝在成功和失败的前景上。
我在书中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如果我是一名试图挽救某人生命的医生,那么我能否成功挽救他们的生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并不是说我应该对成功或失败漠不关心,而是说,不断尝试拯救生命的这个过程之中也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医生,我所从事的所有特定的项目——所有的外科手术或是我正着手进行的任何事——都是这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都系于这条非目的活动的线索之上,而这个过程就是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的过程,即使我在某个特定的活动中没有成功,我的生活仍然是有价值的。
问:为什么你认为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个人生活和研究成果是一个警世故事?
答:这个嘛,阿多诺是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批判理论家,是一个从事社会批判和对掩饰不公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我之所以认为他是一个警示故事的原因在于,由于目睹了德国革命的失败,他对渐进式的社会变革非常悲观,因此脱离了政治生活,成为了一名象牙塔知识分子。
他被卢卡奇·格奥尔格(György Lukács,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开创者。编者注)描述为住在深渊大饭店(Grand Hotel Abyss)里听贝多芬的音乐、并不真正接触社会。

他的经历反映了对社会正义的思考取代真正为正义而战的危险,也反映了因为斗争之曲折而退缩的危险:为正义的斗争是循序渐进的,并且常常是静止和令人沮丧的,但不应因此从中退缩,并说“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等着,直到某种革命发生”,而是应该继续施加这种渐进的压力,希望这种压力会缓慢、逐渐地将人类历史的弧线转向正义的方向。
在我看来,他的悲观态度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阿多诺抵制某种特定的乌托邦主义,还坚定地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并非理想的人类繁荣愿景(我们现在并不真正有能力去构想这一愿景),而应当首先关注、解决不公正和人类苦难——这些想法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只是认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放任自身的知识工作取代政治和社会参与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诱惑。
问:那么,你会对王尔德的“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丝毫不值得一顾”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吗?
答:我的直觉判断当然是对它表示怀疑。有一种复杂的对立观点认为,即使是不现实的乌托邦想法,在激励人们参与社会行动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有一些值得为之斗争的东西是很重要的,这其中蕴含着力量——尽管我并不认为非得是乌托邦愿景才能激励我们斗争。通常情况下,即便我们的地图上没有乌托邦,对具体的不公正的补救也足以激励我们采取行动。
问:当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两位哲学家终于在索邦大学(Sorbonne)的院子里相遇时,你从她们的谈话中发现了什么有趣之处?
答:唔,西蒙娜·韦伊对我来说也是个警世故事。她致力于为正义而战、为穷人而战,反对权力之暴力。她真的加入到了人群中,真的试图做出改变。在这次对话中,波伏娃说:“这些都很重要,但生活的意义同样重要。”韦伊回答道:“很明显,你从来没有挨过饿。”
她为这场论辩下了定论,但如果我们只关注对不公的纠正,那么波伏娃的话也有道理,我们确实需要心怀愿景,并非乌托邦式的愿景,而是对人类生活中积极有益之事的愿景(而不仅仅是对改善糟糕事物的愿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生活值得活下去。

我认为,即使我们认识到了弥补不公和减少人类痛苦的紧迫性——比如抗击气候变化、争取气候正义,这是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事业——关键在于要让生活变得积极有价值。在这样的生活中,有足够的艺术、文化、哲学和科学存活下来,使人类的生活变得丰富、有价值,不公和痛苦也更少。
问: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在生活艰难的时候拷问生活的意义?
答:人生的意义问题讨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命、宇宙和万事万物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生命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命?
我确实认为这个问题很紧迫;在观察人类的生活时,我们会认为它充满了痛苦和不公正,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对它报以悲观的态度。
我们想要的是以某种方式来描述和定位人类生活,这种方式要既准确又不自欺欺人,还能帮助我们与生活中的困难和不公正的历史达成情感上的和解,这种和解并不否认它们,而是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一个“故事”,让我们能够借此肯定和接受人类生活的方向。
正是那些生活看起来已经够艰难、人类生活的历史看起来已经够糟糕的时刻,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理性地接受宇宙的时刻,正是在这些时刻,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会变得无比紧迫:“我们能不能讲出一个足以对抗这个问题的故事?”
问:你为什么要写“我们可以希望生活有意义,希望它是在缓慢而不稳地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未来”?为什么不是说,在这个时刻,生命要么有意义,要么没有?为什么意义取决于某种未来的结果?
答:它与人类生活之整体的形态有关。如今,我们对人类生活的整体有了一点了解,但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包含了未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在这段历史被书写之前,我们不知道如何体会人类的生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展望可能的未来,希望人类历史所呈现的形态是我们能够肯定的,希望它会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朝着能够赢得我们肯定的人类繁荣的方向发展。但无论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等到答案。我认为它会取决于人类在未来几百、几千年里的经历和遭遇。
问:我喜欢这个答案。如果有人问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会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答:一点不错。
参考文献
[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75020/
[2]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91160/
[3]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481885.2019.1632655?journalCode=hpsd20
[4]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13-020-09570-2
原文/nautil.us/life-is-hard-and-thats-good-24992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Brian Gallagher,由译者苦山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校对:光明右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