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作者:艾莉森·阿列克西,译者:徐翔宁、彭馨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头图来自:《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剧照
离婚人类学
离婚可能让人释怀,人们在艰苦斗争之后终于得到了向往已久的自由。同样,离婚也可能带来难以招架的孤独,它时时刻刻体现着某种个人失败,想象中的美好未来提前破灭。事实上,离婚过程中人们在这两极中摇摆:时而觉得自己成功地幸存下来,时而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另外,离婚受法律束缚的同时,对个体、家庭、社区的含义都不甚相同,影响机制各异。离婚可能会彰显自私行为,促使性别关系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甚至是“瓦解”家庭纽带,摧毁整个国家。
即便如此,离婚也能成为赋权、独立、幸存、逃离的符号象征。本书将在上述层面上探讨离婚:人们是如何想象、执行离婚,并最终心理上跨过离婚这道坎的,特别是在离婚被过度解读成女性权力、破坏社会的纽带的这样一个时代。
文化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的关注一直漏掉了离婚这个议题。不论是这个领域早期对于继嗣结构的关注,或是施耐德影响下人类学者对于既往亲属研究的批判(the Schneiderian shift),还是新近对于选择的家庭、繁衍技术的探索,人类学的研究始终聚焦在亲属关系上。尽管亲属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可或缺,它依旧可以被视为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核心议题(McKinnon and Cannell,2013;Strathern,2005)。
然而,即使文化人类学对于亲属关系有这样广泛持续的关注,也很少有人类学家探索离婚这个领域(有几个例外,包括Hirsch,1998;Holden,2016;Hutchinson,1990;Simpson,1998)。家庭以及夫妻关系如何通过自主选择亦或是外力或法律而解体,似乎没有像其他形式的亲属关系那样吸引人类学家。美国和日本的学界中,大多数离婚研究都出自社会学家之手,我的研究借鉴了很多他们的洞见。
本书凸显了离婚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尚待挖掘的潜力。尽管离婚和其他亲属关系一样,在不同文化下以不同形式呈现,但离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从离婚入手,研究者可以探索个人、法律、社会以及经济结构等方向的交互。在离婚过程中,人们解体又重组的不只是亲属关系,还有经济上的收入支出、法律和社会意义的身份等方面。从上述变化中,我们可以探索文化规范、理念、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局限和潜能。
比如婚姻不再“理想”,人们选择离婚,而恰恰是离婚将“理想”家庭结构的讨论推到聚光灯下。更重要的是,离婚协商常常伴随巨大的压力,牵涉到诸多关于个人轨迹、家庭转变甚至是国家变革的话题。与常见观点相反,我不认为离婚只是代表失败或者结束,它也是极为重要的起点,虽有争议,但人们会有新的社交途径,新的社会关系。离婚中充盈着情感和争执,是一个研究个人、政治以及公众关系交汇点的重要手段。
日本亲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安藤麻里子被求婚的时候已经和她的男友在一起四年了。两人就读于同一所精英大学,本科时相识,毕业后都在东京的金融行业工作。尽管他们不在同一家公司,但这类职位的要求与作息却非常相似——高压高强度,工作时间长,傍晚和夜里还要参加与同事、客户的社交活动。当两人都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麻里子的男友觉得是时候结婚了。麻里子自己呢,确切地说,并不反对,但她认真花时间去思考了自己想要从婚姻中得到什么。她最终同意结婚,并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婚后住所要离她母亲近,以方便照顾年岁渐长的母亲;第二个是她想要一直工作。
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人们对女性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期望,即在结婚或者生第一个孩子时就离开全职岗位。虽然大多数女性在小孩开始上学时,会回归劳动力市场,但是回归的时候很可能只能做兼职或者工资很低的职位。麻里子喜欢她的工作,并且这份工作是她非常努力争取来的,她并不想放弃。她的男友答应了她的条件。他们在2000年结婚,那年两人都是25岁。
尽管麻里子一开始就明确地希望建立一段符合她的需求和规划的亲密关系,但没过多久他俩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虽然她的丈夫遵守了承诺,让麻里子继续做她的全职工作,但是他同时对这个新家的家务分工也抱着固有的期望:很明显他希望麻里子包揽从打扫房间到洗衣做饭的所有家务。当麻里子想要得到丈夫的协助时,最好的状况是他口头答应但是什么都没做,糟糕的情况是他直接拒绝并且让她感到愧疚,因为她没有做好在他看来是妻子份内的事。
由于麻里子的全职工作仍是一样的辛苦,而她整个周末还要全部投入到家务劳动中,令她崩溃又紧张。在打扫和洗衣服的间隙,她得做一整个星期的餐食,冻在冰箱里,这样才可能在工作日下班以后很累时吃上一口饭。她过了一年这种高强度连轴转的日子之后,突然明白了这样一件事:她的丈夫在保证她可以婚后全职工作时,并没有说谎。他确实同意麻里子全职,只是他同时也认定,她的全职工作并不能减免任何她在家务上的责任。
换句话说,当麻里子说要继续全职工作时,她丈夫理解的是,在理所当然属于麻里子的全套家务事以外,她想要再做一份有偿劳动。两人在结婚几年之后就分开了,麻里子说分开之后两人关系还算过得去。她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别和一个家庭主妇的儿子结婚。不论这个男人说什么,他总会期待他的妻子像一个家庭主妇那样做。
麻里子选择离婚不仅是因为她丈夫不想分担家务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以及一些未言明的对她的要求,清楚地指向了她一开始就想要极力避免的一种婚姻模式。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常态的(婚姻)模式似乎表明由负责赚钱的丈夫和全职的妻子组成的婚姻和家庭才是最牢固和最成功的。在人们印象中,男人从早到晚地辛苦工作,依赖妻子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在这个亲密关系的模型里,虽然夫妻双方紧密而相互依存,但是他们之间不太可能有共同兴趣或者情感联结,因此属于一种我称为“脱节依存”(disconnected dependence)的模式。
该理念下,夫妻双方仅仅通过生活中“实际”的方面产生联系,比如共同财产、家庭财政。除此之外,两人自觉地追求各自的兴趣爱好,朋友圈和情感生活都没有交集。但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历了数十年经济衰退,男性挣钱养家的主导地位在经济体以及亲密关系中受到双重挑战。公司的规模日益变小,更喜欢大量雇佣可以随时炒掉的合同工,而不是全职员工。同时,婚姻指导手册和互助团体敦促配偶们摆脱这种无联结依存的亲密模式。所有年龄段的人们开始设想(亲密关系中的)情感联结和共同活动。几十年前最理想的亲密模式现在成了离婚的前兆。
在我做研究的过程中,很多与我交谈过的人都对离婚、性别和劳动三者关系有一个清晰的、可能过度简化的认识:当一个女性拥有一份工资足够高的工作时,她就会离婚。很多男性以为我的研究只是问问那些女人挣多少钱。对于这些男性以及抱有类似看法的人而言,女性只要能够经济独立,她们就不想再受婚姻束缚,离婚就会发生。这一群人断言,经济状况和离婚直接挂钩。我同意两者之间有关系,但是并不是因为经济决定论说的那样——金钱在无意识地影响人们在亲密关系中的决定,或者经济需求是女性和异性婚姻之间唯一的黏合剂。
相反,我认为,两性对于婚姻问题的诊断以及离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回应一个由劳动模式塑造的亲密关系模型。我把这两者的交融称为日本亲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概念中,我将亲密关系何以可能与雇佣结构、税收系统、男女有别的招聘过程联系起来。在战后时期,该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准则,并且暗示这个涉及家庭、亲密关系、劳动等场域的准则,是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更自然、更健康,也更有益的。
现在,当人们在认真考虑离婚或者思索如何避免离婚时,更倾向于反驳和拒绝从前(战后时期的)这个常态化的准则。像之前的例子提到的那样,人们感知到实实在在的、由配偶的工作形态引发的风险,这风险是对婚姻和家庭的,也是对个体的。日本亲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在战后恢复阶段强有力地塑造了人们对于异性婚姻的期望值和婚姻中存在的可能性;在现阶段,它左右着人们如何决定离婚的过程。
女性花钱买离婚?
在很多文化中,人们在社交中尽力避免谈钱,即使金钱在亲密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已经注意到,不同场合中,人们希望极力减小经济、市场给有爱的关系带来的影响,就好像一谈钱,约会就变成卖淫似的。
雷布(Rebhun,2007:111)在描述巴西东北地区的状况时说,“人们声称情感和经济是完全分开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被问到如何判断某人是否爱你时,他们描述的都是经济行为。比如分享食物、金钱、衣物、信用、就业机会,分担劳动,一起照看小孩,等等。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把这些行为打上经济的标签。”
在大众认知中,亲密关系和经济交换似乎是两个“敌对世界”,一旦有接触,两个世界都会崩塌,事实上“钱和亲密同居在一起,甚至维持着亲密关系”(Zelizer,2005:28)。就像我在这章的引言中提到的那样,不止一位男性言之凿凿,认为女性的经济状况是离婚与否最强的指标。
人们不论考虑离婚,还是想方设法避免时,他们的理想关系模型都能映射出日本亲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战后早期,夫妻关系之所以成立,是和特定的雇佣模式密不可分的,更不要提做一个“好”丈夫或者“好”妻子。在当时,一个好丈夫需要非常努力工作,从而妻子要么可以专心做家务,要么只需做一点兼职工作。“脱节依存”不仅是常态,而且通常是稳固婚姻的证据。21世纪早期,两性都把这个模式当成反面教材。从前稳固婚姻的保证,现在变成了婚姻隐患。
如果离婚只是和女性薪资水平相关,过了某一数值就会引发离婚,什么也挽回不了,那么这样的模式难道不也挺好?这样的机制没有考虑到双方在结束关系时可能会感到的愧疚或者责任。我们已经在这一章看到,钱是必要不充分的离婚理由。人们想象钱在离婚中的角色时,他们不会具体描述婚姻是如何具体崩盘的;相反,他们注意到的是种种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包括婚姻未来图景、亲密关系风格、就业标准以及国家相关政策——这些政策让某种特定婚姻看上去更牢固、更好、更自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注意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契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解体,男性不再渴望或者有能力争取上一代人中更易得的稳定的终身职位。
因此,“钱”,对于当代日本离婚来说,是一个太单薄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把“钱”理解为日本亲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缩影,通过“钱”了解旧规范如何破裂,这个解释就能说得通。离婚之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某种魔力把女性从稳定的婚姻中撬出来,而是亲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让所有人脚下的土地斗转星移。
新型婚姻失败者
2003年酒井顺子出版了非虚构作品《“丧家犬”的呐喊》,深受读者喜爱。该作品用戏谑的口吻讨论离婚、污名以及亲密关系等话题。和英国小说《BJ单身日记》很像,这本书诙谐幽默且刻薄地给“丧家犬”提供了行动指南(酒井,2003)。
“丧家犬”指的是那些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酒井认为自己就是一只“丧家犬”,在书中陈述了种种或明或暗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用亲密关系状态来谴责评判当代女性。在她的陈述中,“丧家犬”是更有趣的一群人。在书中酒井批判了“被主流价值观洗脑的人,用婚姻状况将女性分成赢家和失败者的想法是愚蠢的”(Yamaguchi,2006:111)。“丧家犬”因为这本书而变成流行词汇,一大波媒体跟进讨论。我遇到很多人也喜欢讨论什么叫“赢家”,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上,什么叫“赢家”。
一个未婚年轻女士也说了和这本书相似的看法。她描述了“赢家”的通俗含义,同时也强调赢家概念本身的荒谬。据她描述,大众观念里女性赢家应在婚前有个好学历、好工作,然后和律师医生一类的成功人士结婚。最好丈夫上的是类似于庆应义塾一类的精英大学。(如果读者对日本学校不熟悉,可能没法立刻理解其中的语气。这位年轻女士是在讽刺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自视甚高。)女性赢家结婚并有两个完美小孩之后,就不应该工作了,而是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家庭的母亲。
整个“赢家”定义的问题在于,婚姻决定一切,只有嫁得好,嫁给一个“赢家”丈夫,女性才是“赢家”。就像酒井在书中讥讽的那样,婚姻质量或者稳定与否,都不是“赢家”标准的一部分。酒井认为,未婚或者离婚与大众观念相反,是勇敢、自信、理性的证据。《“丧家犬”的呐喊》启发读者重新审视用亲密关系定义“赢家”“失败者”的鄙视链。
《“丧家犬”的呐喊》出版时,书中对于亲密关系鄙视链的讽刺与大众观点的变迁不谋而合,人们开始反思亲密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着怎样的影响。如果说在传统规范中,相比于未婚,已婚的人是“赢家”,那么在当代辩论中这种联系就没那么明确了。在日本,选择不婚、离婚、丁克的人群数量日增,越来越多的人在从前的标准下是失败者,但现在却不一定。原因在于,标准在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话里人们对于离婚愈发理解、认同的态度上。中青年对离婚的态度和老一辈人形成鲜明对比,离婚比很多其他选择好,而且也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般让人抬不起头。
我第一次听人说离婚比没结过婚好的时候,差点以为听错了。悦子三十多岁,活泼聪明也豁达,但不幸的是,她丈夫五年前去世了,她成了寡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想要给她介绍对象。(事与愿违,我丰富的离异知识没能转化成牵线搭桥的技能。)有一次,悦子和我在厨房里一起准备晚饭,一个朋友建议她去见某个男人,那人是个律师!听上去不错吧?我并不认识那个男的,但我认识这个朋友,而且听上去这个男的不错,至少可以见一面。
悦子并不十分情愿,解释说她觉得那个男的说不定很奇怪。他已经47岁了,却从没结过婚。悦子觉得从没结过婚比单身更可怕,这个男的肯定有问题。她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他结过婚然后又离了,看上去就正常多了,那至少意味着他可以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并且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从来没结过婚”可能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过亲密关系,单身如此之久,他可能是脾气太糟了,且不肯作出改变。悦子同意见面,但并不感到兴奋,他们见了一面之后便没了下文。悦子的直觉和偏好说明在各种关于亲密选择的讨论中,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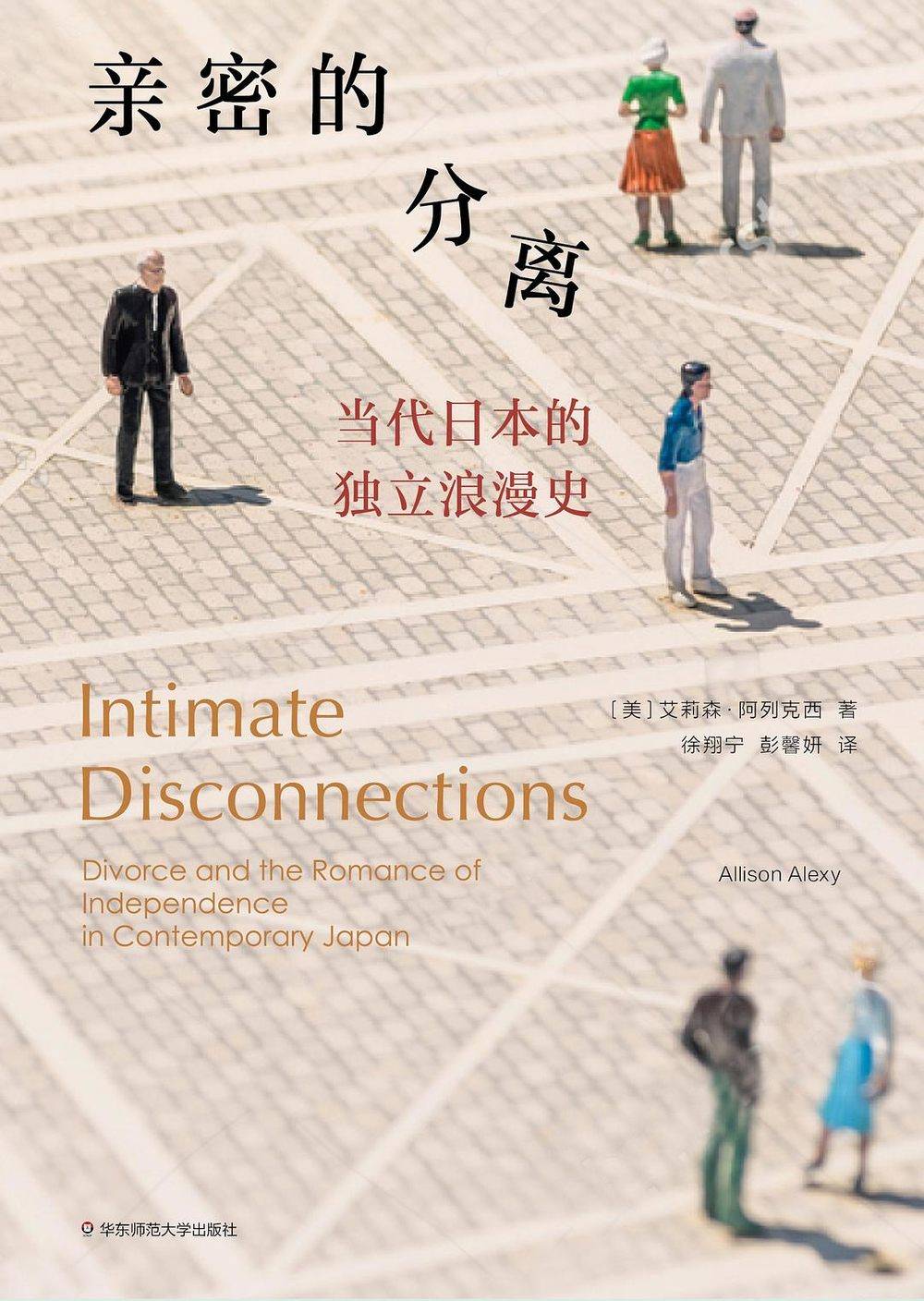
作者:艾莉森·阿列克西
译者:徐翔宁 彭馨妍
丛书:薄荷实验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本文摘编自《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作者:艾莉森·阿列克西,译者:徐翔宁、彭馨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