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第七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一书中,作家博尔赫斯给我们构思了一个他笔下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之一。在一次骑马事故后,富内斯卧床不起,在许多个失眠的夜晚,富内斯发展出了一套他自己的古怪的列举系统:
为了替换七千零十三,他会把它说成(例如)马克西姆·佩雷斯;替换七千零十四的,是火车;替换其他数字的是……硫磺、俱乐部、鲸鱼、气体、大锅、拿破仑、奥古斯丁·德·维迪亚。为了替换五百,他会把它说成九。每一个词都有一个特定的符号、一种特殊的标记……我尝试去解释这种语音不关联的狂想曲恰恰是一个列举系统的反面。我告诉他说,365意味着三个一百、六个十、五个一——是一种以神秘的蒂莫西或肉毯“数字”所不可能完成的分析。富内斯并不明白,或者他也不想明白。
格奥尔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写道,如果金钱将现代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问题”,社会金钱是否仅仅是一场失眠症患者的幻想呢?如果金钱本质上是一种数值现象,那么当我们将某些金钱说成肮脏的或者干净的,家庭的或者慈善的,小费或者工资,我们是和富内斯一样疯了吗?
对经典理论家来说,金钱的“数理特性”使社会生活充满了“测量和权衡”,充满了一种“可进行数值计算的理想”,这必然会削弱个人、社会和道德的特殊性。所以,历史学家也告诉我们,美国人是如何在19世纪末用一种“定量伦理”回应社会剧变的,那成了“他们的价值危机的标志”。罗伯特·韦伯(Robert Wiebe)观察到,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权衡、计算和测量他们的世界”。货币经济助长了世界的灰暗,仅仅给客观的、定量的计算留出了空间;匿名的数字无情地擦去了个人的标记。
但是富内斯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们经常调动金钱的社会词典,以创造词汇、句子、段落、整本书,这发生在他们巧妙地处理他们的货币的过程中,标记一些金钱以专款专用,依据金钱被赚取的方式来区分金钱,为特定的交易指定特殊的使用者,为官方货币的独特用途发明新的名称,或者将非货币的物品转换成交换的媒介。当然,数量会导致一种差别,人们关心他们的交易中涉及多少金钱。但是它是哪种金钱,是谁的金钱,这些问题同样也会有重大影响。
这些差别不是不稳定的、空想的,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理性货币体系来说亦非孤例,在该体系中,金钱的标记被认为并不存在。金钱的社会分化是普遍的。不仅在经济的黑暗而奇异的角落,也在我们看得到的任何地方,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重塑了金钱。不仅个人,组织甚至政府也区分出了多种多样的法定货币或其他货币。如齐美尔所说,因此多元货币并非原始生活的奇特残余,在原始生活中,金钱仍然保留着“神圣的尊严”或者“特殊价值的品质”,但多元货币事实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
面对货币化时的标记
事实上,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人们发明了日益复杂和广泛的标记系统,这正是因为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在美国不断得到巩固,工业资本主义繁荣兴旺,消费主义迅速发展,以及政府为实现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法定货币所做的努力。现代消费者社会不仅把花钱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经济行为,还把它变成了一项动态且复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金钱应该用来买什么,什么时候买,又以什么频率买?金钱的来源要紧吗?谁可以适当地、自由地花钱,谁又需要指导、监督和限制?
同时代的社会观察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预计金钱将会进入更社会化的、更商业化的交换中,但他们对那些后果的评估却是错误的。由于遭受知识色盲(intellectual color blindness)的影响,齐美尔的精辟论述没能捕捉到丰富的新社会色调,而这种色调已经出现在货币经济中,人们即兴想出了很多将金钱个人化和差别对待金钱的方式。在色盲只看到灰色阴影的地方,正常视力的人却看到了整个彩虹。不过,标记金钱的人们更胜一筹:他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光谱,以替代那些由政府和银行所提供的光谱。
对金钱的标记甚至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最脆弱的领域,这些关系和交易可能尤其易受美元理性化的影响,包括家庭内部的交易、礼物赠予和慈善,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会受到影响。金钱焦虑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美国家庭的内部,从礼物交换到慈善捐款。就单从这儿,我们应该已经能发现国家均质化货币的标准化和去个人化的效果。
相反,我们发现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在金钱进入家庭、礼物交换和慈善捐款之中后,个人和组织发明了一系列广泛的货币,从家用开支补贴、零花钱,到礼物形式的金钱、礼品券、汇款、小费、一分钱银行的存款、母亲抚恤金和食品印花。他们将表面上同质的法定货币分为不同的种类,并且创造出了缺乏国家背书的其他货币。
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会仔细地,有时甚至会热情地区别和分开他们的金钱,将用来购买食物的钱与用于支付租金、学费或用于慈善捐款的钱分开,这笔钱也同样区别于用于葬礼、婚礼、圣诞节或娱乐活动的资金。
妻子们、丈夫们和孩子们在标记安排上的意见不总是会达成一致,家庭成员们会争论如何定义、分配和规制他们的金钱。我们已经看到一位妻子的钱是如何从根本上有别于她丈夫的或者她孩子的,不仅仅在于数量,也在于这笔钱是如何获得的,有多经常获得,是怎么使用的,甚至被保管在哪里。
争论不是总能友善地得到解决:为了保护各自的钱,女人们、男人们和孩子们经常撒谎、偷窃或者欺骗彼此。因此家庭建构了金钱的不同形式,由强有力的家庭文化以及夫妻间和亲子间变化着的社会关系所共同塑造。它们同样也被阶级所影响:中产阶级家庭内部的美元与工人阶级家庭内部的美元不是精确的等价物。
家庭、密友和商业同样也将金钱重塑为可能性质最不同的形式:一件寓有情感的礼物,表达的是关心与喜爱。是谁给的礼物性质的金钱和是谁收到的,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怎么提供的,以及是怎么花的,这些都至关重要。礼物性质的金钱挑战了货币中性、客观和可交换的概念,作为一种有意义的、非常主观的、不可替代的货币在流通,而且受到社会习俗的严密规范。在圣诞节、婚礼、洗礼或者其他宗教的和世俗的活动中,现金变成了一种高贵的、受欢迎的礼物,几乎无法被认定为市场货币,并且明显有别于其他家庭内部的通货。
礼物赠予者和礼物接收者经常就金钱形式的礼物的标记发生争论。特别是在涉及陌生人之间的交换时,礼物形式的金钱就变成了充满争议的货币,象征着特定社会关系的不平等。
例如,小费是极具争议的一类金钱,部分具有支付性质,部分则具有礼物性质,小费有时被定义为表示感谢,但其他时候则会被当作一种侮辱性的施舍而被拒收。此外,给穷人的金钱在礼物、小费、正当权益和服务费支付之间不断达至不稳定的平衡。一笔特定的转让是被算作服务费支付、合法权利,还是一份酌情决定的礼物,都深深地影响着有关各方,以至于各方都在自己的范畴间竖立了看得见的边界,并为边界的定位展开了斗争。
当权威机构介入对金钱的标记时,一种不同类型的货币出现了。大量机构和组织开始关心所谓的不称职的消费者。在20世纪早期,它们便开始进入了这些需要依靠的人群的标记系统。对于穷人来说,公立的和私人的福利权威们开始深入参与到了创造慈善货币的过程当中,这些货币是为教授他们的客户如何合理使用金钱而设计的。
社会工作者为穷人所做的事情类似于其他机构为规范消费模式所做的努力,如监狱、教养院或孤儿救济院,还有许多工作场所;企业生活区,或者甚至是福特汽车公司。福特著名的1914革新——一天5美元和利润共享计划,区分了工人的常规工资收入和基于公司利润的有条件的补充收入。这一安排使得员工的利润分配取决于他们正直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使用额外收入。
在大量权威机构强制实施货币的相关证据的存在之处,我们总能发现反标记和异议。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见到阻力,还有其他场景下的替代性货币的出现。说到慈善货币,毕竟,穷人保留了他们自己的金钱区分系统,这使得现金救济变成了一种有争议的、竞争性的、复杂的金钱交换。
家庭生活、礼物交换和慈善不大可能处于现代经济生活的边缘位置。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是创造中心,积极并持续参与了标记过程。事实上,金钱的革新和分化在这些微妙的社会互动领域是特别积极、精细、明显的。人们在创造意欲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金钱上投入了很多精力,这些关系表达了亲密,但也带来了不平等;表达了慈爱,但也代表了权力;表达了照顾,但也体现了控制;表达了团结,但也导致了冲突。重点不在于这些社会生活的领域在勇敢地抵抗商品化,相反,而是它们在欣然地吸收金钱、改变金钱,以使自己符合更多价值观和社会关系。
当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越来越多地开始管理经营家庭经济和礼物经济的重要部分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突出的货币性别化。类似地,求爱实践中随性别标记的金钱已发生了深远改变。但是性别涉及许多其他社会环境:办公室、学校、教堂、偶然的社会聚会,等等。在每一种环境下,我们都有理由预见男性和女性对金钱形式和实践的设计。显然,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性别工作。采用并行方式,我们必须探索年龄、种族和族群性是如何定义金钱的使用、意义和分配的。
市场货币的社会基础
那么,市场货币是什么样的?是否真如经典理论家所描述的,至少市场货币可以像同质的、无色的货币一般恣意漫游?是否可能存在黑白分明的世界货币地图呢?是,但也不是。
无疑,从18世纪到20世纪,为了使交易正规化和常规化,减少经济当中的社会关系困难,在市场环境的重要领域,人们发明了很多货币策略,诸如支票、单一价格(one-price)商店、付款指令(money
order)、自动转账,以及各种各样的信用卡。齐美尔或许有知识色盲,但他依然可以看到:经济生活的货币化有利于商业关系的扩张,有利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市场。
然而,问题在于经典思想家们太过聚焦于标准化市场的例行常规,以至于他们犯了两个基本错误。首先,他们未能意识到在市场货币的发明过程中所包含的充满困难的社会过程。对市场货币的标记不是现代市场经济自发的、无法抑制的产物。相反,如美国的案例所显示的,在创造一种中央化的、同质的、统一的法定货币的过程中,政府付出了巨大而持久的努力。
其次,通过假设其必然性,经典思想家们将市场货币绝对化了。由于相信只存在市场货币,他们没有看到新货币的发明,没有识别出现代社会中品类繁多的货币。他们没有捕捉到一个逐渐增长的悖论:当金钱的物理形式和法律地位变得更加标准化时,法定货币在许多生活领域的使用都变成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社会过程,这也使得法定货币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区分日益精细。
当社会工作者们或家政学家们热心地设法将齐美尔的想法付诸实践,塑造理性的消费者,将家庭金钱或者现金救济定义为无异于工资的,而且可以如同普通支付一样被匿名而自由地花销的金钱时,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努力一如既往地失败了,就像创造一种不同种类的货币一样,就像市场货币在一套陌生的社会关系中一样。比如,把家庭金钱当作工资,不仅会被视为一种侮辱,也会被视为对家庭稳定的一种直接威胁。
另一方面,“自由的”现金救济并不适用于社会工作者与其案主间已确立的社会关系。因此,虽有市场自由一说,但社会工作者却仍在继续限制并指导其案主的标记系统。然而,金钱的同质化也遭遇了失败,因为社会工作者所做的这些努力的目标人群(案主)对标记金钱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让我说得明确些:金钱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在竞争性的市场当中。事实上,阿瑟·努斯鲍姆(Arthur Nussbaum),一位法律史学者,已经指出了美国人在货币试验上的“非凡天赋”。今天,美联储已经意识到了国家货币供给的构成部分,不仅包括现金、货币、活期存款,以及旅行者支票,同时还包括其他金融资产中的隔夜回购协议、欧元、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份额、储蓄债券、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以及流动的国库债务。
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乔尔·库尔茨曼(Joel Kurtzman)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货币和类货币,例如私自发行的数十亿美元的信用卡货币,住房抵押的信用额度,或者像通用电气信贷公司这样“所谓的非银行财务机构”借给个人和公司的钱。库尔茨曼观察到,“计算市场上存在多少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变得显而易见”。
然而,特定的市场交换已经发展出了几套例行化的交易,以至于事实上,电子货币转账、直接银行存款、计算机化的家庭购物,或者自动电话购物都受到了明确的规范,但却很少或根本不涉及付款人和收款人的个人联系。
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指出,在一个“无现金社会”,大多数人用信用卡付款,人际间的纽带和对特定他人的信任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卖家不再依靠买家,而是依靠非个人的中央电子债务清算公司。这些重要的交易在很多方面都符合社会学有关货币化的经典理论。但是,在更加复杂的、较低例行化程度的社会互动领域——无论是在市场还是非市场中——对各类货币的创新、讨价还价和竞争都是习惯性的。不管怎么样,这些复杂系统的所有参与者们依靠的都是对与他们互动的行动者的一般化的信任。
事实上,本书的论点对更宽泛地分析不同类型的市场的变异具有启示意义。最近,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挑战了新古典主义关于单一的、自主的且可以自我维持的市场模型,正如社会学家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提出的,社会科学家们主张市场活动是“高度社会性的——和亲属关系网络或者联邦军队一样都是社会性的”。社会层面上的变异的市场不仅在价格上有变化,还被购买者和生产者之间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情境所塑造。因此,当一些市场达至某种程度上的标准化的时候,新的市场正在被持续不断地创造出来,而其他市场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恰如怀特指出的,即使是在范围明显狭窄的专业的剧院市场,也有市场的子集——百老汇音乐剧或戏剧、餐馆剧院、非百老汇戏剧和音乐剧,准备多种剧目定期更换演出的剧团——每一个都有独特而鲜明的特征。
举个例子,许多形式的剧院想要生存,只能通过它们对高度专业的顾客的吸引力,或者借助于富有的赞助者对它们的支持。同样地,传统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必须区分外部和内部的、专业和非专业的劳动力市场;许多经济学家也在继续对由种族、族群和性别所塑造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区隔做出区分。
近来东欧的变化凸显了市场创新的普遍流行和重要意义。例如,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ery)对苏联经济崩溃的分析,不仅扩展到了苏联各联邦共和国,也扩展到了区域、地区和单个的大型组织。
汉弗莱证明,苏联远未形成一个单一的、相互联系的市场,当地新的经济结构由当地的老板控制,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或者借助各种各样的受限制的优惠券、食品卡和订单运行,这些票证并非由中央发行,而是由区域、地方甚至是工作单位发行。这种交换关系是不完整的、特殊化的;例如,食品卡专为特定的产品设计,只发给一个特定城镇或区域的居民,且不包含游客;优惠券甚至更受限制,仅仅会被分发给某些类别的人——一个工厂的工人、退伍军人、幼儿的母亲——只能用来购买特定的产品,有时还仅限于在一家特定的商店使用。事实上,公司之间临时创造的信用——很明显,这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所有尝试。
在东欧和其他地方,市场的直接扩张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经济转型过程,其包含了对多种多样的货币的发明创造。社会学对这种转型的恰当理解,应该能最终挑战和重新解释大规模的经济变迁与变异。这种理解也应该可以用来阐明一些经济现象,如收入再分配、储蓄率、对通货膨胀的应对、基于各种消费者变异的总支出,以及一系列个人消费者行为所导致的重要的宏观经济差异的其他相关现象。
当然,本书最终没能提供一份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陈述。但是,通过聚焦于大规模过程中的小规模对应物,本书展示了区分、创新和竞争是如何成为花销和储蓄过程中的内在构成部分的。总而言之,标记是经济过程的核心所在。
人们如何以及为何标记
标记如何运作?人们如何区分各种各样的金钱?我们已经看到此中的技术千差万别。金钱标记有时候是物理标记,如19世纪铭刻着誓言的爱情信物或者由家庭主妇巧妙创造的礼物性质的金钱。有时候人们也从空间上区分金钱,使用各种各样的家庭金钱容器——贴上标签的信封、不同颜色的罐子、长筒袜、储蓄罐——或者指定的机构账户,如圣诞俱乐部或度假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可以仅凭不让金钱流通就区分了各种金钱,例如把美元钞票粘在墙上或者一家新商店的柜台上,通常这样的钞票上面会写着一位朋友留下的令人感到愉快的好运祝福,或者这样的钞票会成为一位收藏家的收藏品。
通常,人们会通过约束金钱的使用方式来对金钱进行标记:孩子的收入被指定用于合理的特定采购,只能花在孩子的娱乐或者衣服上面;礼物性质的金钱通常会被用于特定的物品或活动;现金救济的使用范围经常只限于社会工作者们同意的预算支出。
人们也会通过为货币指定特定的使用者对金钱进行区分:每周的零用钱是给孩子的,不是给成年人的;零花钱是一种女性货币,而不是男性货币;小费对于服务员来说是能接受的,对于律师来说却是不能接受的。
人们还会通过链接金钱的某些来源以选择使用方式,以此来对金钱加以区分:妻子的收入留给孩子教育之用,而丈夫的收入则用来支付按揭贷款;遗产的使用方式可能有别于挣来的收入或者意外收益。人们还会通过创造不同的分配体系对货币进一步加以区分:例如,家庭收入、礼物性质的金钱或者现金救济的计算和分配,是基于迥异的家庭原则、情感指南和福利哲学的。最后,人们不仅标记了法定货币,还在许多情况下将选定的实物转变成了货币(香烟、地铁券),也创造了新的受限制的货币(礼品券、食品印花)。
标记有多顽强?一美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补贴而是成了礼物呢?或者把慈善货币变成家庭金钱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一种特定的标记形式的持续时间与一种特定金钱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直接挂钩。许多类型的标记事实上被例行化了,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比如,机构中的代币);有些标记如此深地铭刻着道德和情感的意义,以至于所涉钱款不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或者不能被不同的人所使用(如遗产);但其他标记却是不稳定的和短暂的(彩票中奖)。尤其在微妙的社会互动领域,创新是持续的,因为人们会不断创造新钱以界定麻烦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
这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多样性最终是一种情感的自我欺骗吗?金钱的创造力和试验只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是用来掩饰货币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计算的和腐蚀性的这一现实的吗?抑或是标记至多是一种富人的奢侈,它们消失在穷人的绝望经济之中?毕竟,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社会关系的创造力与权力及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是很难调和的。
有证据表明,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无疑,金钱是推动不平等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毫无疑问,家庭金钱、礼物性质的金钱和慈善金钱的账户表明独立货币已经一再强化了女人、儿童和穷人的依赖性。货币转移的各种方式标示了有关各方的平等或不平等,正如它们标示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度和持久性。
但是这些货币的历史也证明了,无论多么无力的人,都会设法质疑占支配地位的标记系统,他们会通过定义、维持、有时甚至是改变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法,重新定位他们有限的资金的使用方式。回想一下有关丧葬保险的争议:尽管有来自社会工作者们的批评和限制,保险购买人仍然坚持认为死亡金钱的标记是一个基本的、无可争议的经济决定。
事实上,所有经济形势下的人们都如此深切地关心着其金钱的合理区分,以至于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地去维护或改变标记系统。家庭金钱有别于服务支付,福利支票有别于监狱津贴,这些都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对家庭货币、礼物性质的货币以及慈善货币的界定经常引发激烈的公共辩论,这些辩论不仅出现在家庭内部或福利办事处的范围内,也出现在大众媒体、报纸社论和杂志文章里。
多种多样的金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和意义的强有力的明显标志。但是它们又不仅是如此而已,它们直接影响着社会实践。人们不仅对他们的各种金钱想得或感觉不一样,而且对各种金钱的花费、储蓄或者赠送的目的和对象也都不一样。更甚者,一些群体——如福利工作者们——意图建立完整的改革程序,推广一个标记金钱的特定系统。
金钱是独一无二的吗?
对金钱的标记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进程,无论我们将它仅限于法定货币的使用,还是包含发明或转换其他物体作为交换媒介的过程。人们区分、标记、分隔着所有类型的事物——时间、空间、食物、时尚、文学、语言——以此定义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并表达不同的象征系统。
例如,充满活力的有关消费的新文学研究最近已经表明,消费主义不止催生了标准化品味和实践,它还创造了赋予社会和个人生活多种多样的现代意义的全新方式。随着20世纪初期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数量成倍增加,美国人并没有被简化为一个仅由可以互相交换的消费者所构成的民族。事实上,人们把他们的新物品——比如汽车、收音机、洗衣机、衣服或者化妆品——变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物品,并将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融入了个人化的关系网络之中。
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原子化的消费模式下,商品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质量和价格而被购买,但从凡勃伦到布迪厄的消费理论家们,却与此种模式渐行渐远,他们把商品当作社会群体的符号、世界不断变化的线索而加以研究。他们记录了最充分的分析,考察了商品的获得所起到的阶级位置的文化标记的作用,包括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确认的人们的“文化资金”。
历史学家们记录了消费品的这种积极的、复杂的和有意义的分化。如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所指出的,“无防备的”消费者,正在被改写为消费者文化形成过程中创造性的参与者,而不是由大规模的商业入侵所造成的被异化的受害者。这一点更普遍。人们一再利用商品,同时将商品当作他们社会排序的标记,当作其他共享的集体身份的标志,也当作他们个体性的信号。
我们可以思考一些具体的例子,看人们是如何把购买的商品变成有意义的私人物品的。举个东欧犹太移民在世纪之交的例子。他们购买一套崭新的衣服或一架钢琴,或者选择一件名牌产品,或者安排一次夏日度假,都不只是经济交易;但是,在一战前的几十年间,安德鲁·亨恩兹(Andrew Heinze)对纽约下东区的犹太移民的研究证实,这些奢侈品和活动变成了这些犹太移民新美国形象的象征性建构的核心。然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化的故事,而是一个复杂的创造犹太式美国主义的文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大规模销售的商品经常被融入传统仪式活动的庆祝当中,比如安息日、光明节或逾越节。
如亨恩兹写到,美国犹太人为了开创“一种拥有新产品的有意义的生活”所做的积极努力,不仅是复杂的也是有争议的。比如,物质商品对上层阶级的德国犹太人的象征意义,就不同于对东欧犹太人的。
举例来说,詹娜·韦斯曼·约瑟利特(Jenna Weissman Joselit)对1880年至1950年犹太家庭文化的生动描述,展示了在世纪之交时,富有的德国犹太裔的家庭改革者们劝告穷人主妇们,朴素整齐的家庭装饰是重要的,而与此同时,廉租公寓的住户却“偏好维多利亚晚期客厅家具的‘豪华颜色’、‘涡卷装饰和蛇发女怪之手’”。约瑟利特观察到,“传教式家具的重要性对于移民消费者没有一点吸引力,他们想要他们自己的沙发和英式橡木饰面的餐具柜,因为这种餐具柜有分量、有颜色,还有坚固的线条……可以成为一件实在的物品”。
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历史学家丽莎贝斯·科恩(Lizabeth Cohen)关于不同族群的产业工人对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众文化的各种不同反应的报告。尽管工人阶级只有有限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来为消费项目和活动买单,但是他们的小额购买行为通过具体说明的关注而得以被清晰地标记。
例如,芝加哥的意大利人会用他们新买的留声机播放卡鲁索或者其他流行的意大利歌曲,以在他们的家中保持意大利的文化之声的生机盎然。少数族裔的工人在他们当地的食品杂货店购物,当犹太裔妇女可以买到符合犹太教教规的肉或者犹太哈拉面包的时候,意大利裔的妇女则在这里发现了莴苣菜、蒲公英叶和各式各样的意大利面。甚至当她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族群性会将她们的经历歪曲为“叫喊和嘲笑的语言,而这些语言通常是无声电影的配音”,这反映了社区的族群特征。科恩观察到,邻里商店和戏院“以当地的,尤其是族群的文化调和了标准化的产品”。收听广播也是一样的,因为不同群体都会用电台来广播族群的新闻和信息。
消费品被不同族群与宗教信仰的群体、不同阶级、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人群所做的标记,与金钱的分化并行不悖,人们通过将物质占有和活动私人化,来理解他们的个人和集体生活,由此记录了标记的普遍性。在这方面,婚礼仪式、礼物馈赠或家庭开支的专款专用是对消费和交换的一般区分的例证,这种区分是基于阶级、种族、年龄、宗教、性别或区域来实现的。
但是金钱的例子却是独一无二的。鉴于现代生活的工具化和理性化,金钱站到了舞台中心;经典的社会理论学家们一再指出,金钱是主要的利刃,其对先前一种聚合在一起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悲惨的肢解。金钱看起来像是在一个分离的领域、一个自由区中运行,独立于任何有意义的影响或限制之外。很明显,即使是消费者文化的分析者也在金钱面前停了下来,就好像社会区分的商品无可避免地要使用一种中性的、标准化的货币来购买一样。
抛开理论上的建构,金钱事实上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商品:金钱是更加可替代的、明显流动的、高度可转让的,连接着相距甚远和不同时空中的人们。毫无疑问,相比于其他物品,要将金钱私人化更加困难。因此,如果现代生活的理性化是普遍性的,那么这种普遍性恰恰应该出现在金钱当中。而实际上取而代之的却是,对现代金钱持续的、强烈的和广泛的区分,这为反对一种均质化和工具性的社会生活模型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未来的货币
金钱什么时候不再重要,我们已经有结论了吗?我们可以听到齐美尔幽灵般的耳语:“所以你找到了一些涟漪。潮流还是朝着我的方向在大力涌动。等着看吧,金钱会使这个世界祛魅。你注意到了吗?电子转账正在将所有的金钱转变成一种单一的、全球的、无形的‘兆字节’货币。你听说过吗?
1999年,欧盟计划引入欧洲货币单位(ECU),一种单一的欧洲货币以取代所有欧盟国家的货币。货币不仅会变得越来越同质化,而且也会变得势不可挡。只要简单地看看你的周围:货币正在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血液、婴儿、器官、恋爱关系、丧葬。”
当代的社会观察家们回应着齐美尔的幽灵,警告我们注意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和他的合作者所描述的与日俱增的“市场暴政”。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论述道,在过去的20年里,市场的逻辑越来越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家庭和社区中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之中。鉴于团结、利他主义和情感这些领域依然继续存在于美国人的生活当中,沃尔夫非常担心近些年来市民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在逐步淡化,这是由于“市场以一种美国人从未经历过的方式,在经济领域,同时在道德和社会领域都变得更具有吸引力”。
诚然,法定货币的形式已经改变,金钱的使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正在选择放弃对多元金钱的标记。
确实,银行现在依靠自动转账,但是特别的“俱乐部账户”依然存在;圣诞节、光明节和其他节日中的金钱,每周或每月都在被通过计算机化的转账自动分隔。即使福利系统正在试验电子福利支付,但是它依然没有抛弃它的限制。计算机化的标记实际上更可能实现对福利的规范、监督和区分。借助于新的国际化货币,标记的范围可能扩大,标记的技术会发生变化,但是分化依然存在。
事实上,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激增,人们创造和分隔新货币的能力正在提高,其速度甚至比国际货币任何的标准化过程都要迅速。如果本书的分析是正确的,人们将会利用这个能力,实现异常多样的货币创新。
将社会完全转变成为一个商品市场的设想只不过是个海市蜃楼。金钱还没有变成自由的、中立的、危险的社会关系破坏者。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当然,一些事会变得标准化和全球化;但是随着远程连接的猛增,对于所有地方的个体来说,生活以及选择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对货币进行标记是人们理解他们复杂的、有时混乱的社会联结的方式之一,这给他们各式各样的交换带来了不同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期望标记的新形式会随着社会变迁一起增加。当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更为突出时,人们会分隔、区分金钱,给金钱贴标签,装饰金钱,使金钱个人化,以满足他们复杂的社会需求。就像富内斯和他的特殊数字一样,为了我们的多元货币,我们将会持续创造新的名字,也会不断定义新的用途,指定不同的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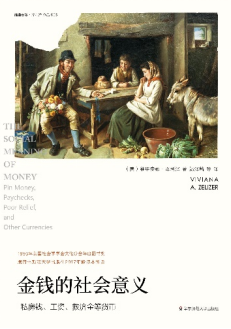
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
译者:姚泽麟 等
书号:978-7-5760-0275-1
定价:65.00元
丛书:薄荷实验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