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ID:pic163),作者:蒲潇,内容编辑:百忧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年里,吴恩惠陪同两百余名陌生人去医院看过病。
这些患者中既有空巢老人,也有独居青年。吴恩惠帮他们梳理病情、拿药、取报告,也会陪他们做检查,甚至做手术。在医院期间,她充当了他们的“临时家人”。
当独居成为常态,陪伴似乎就变成了一种稀缺品。根据统计,我国已有超过1.25亿“一人户”,人们开始习惯于一人住、一人食、一人游,但独自就医还不太容易。
根据医院规定,在大部分有创检查和手术之前,患者和家属必须共同签字。遇到疑难杂症需要前往大城市治疗时,来自小镇的居民们面对迷宫般的医院,也容易手足无措。还有不少年轻人,即使对看病的流程很熟悉,也不愿承受独自就医的孤独。这个背景下,陪诊员的职业便应运而生。
近几年,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关于陪诊员的信息。有不少人说这是轻松自由、月入过万的高薪职业,吴恩惠看到只能苦笑。她全职做陪诊员一年,每个月大概也就4000到5000的收入,还不太稳定。
每天在医院接触生老病死,在拥挤的人流中穿行绝对谈不上轻松,但吴恩惠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医院和患者间的一座桥梁。涉及到就医的都是挺紧急的问题,只要有患者需要,她就会一直做下去。
以下是吴恩惠的自述:
令人伤心的科室
在医院,会遇到很多让人难过的事情。
我陪很多人做过大大小小的手术,其中有不少是人流手术。这些女性大多很希望当母亲,但由于胎儿停止生长,不得不做手术终止妊娠。她们的伴侣和亲人都没能一起陪同面对这个令人心碎的时刻,具体原因我不过问。唯一主动告诉我的女性,是阿兰。
记得来医院的当天,阿兰扎着低马尾,带着金属圆框眼镜,穿着宽松的休闲服,脸色有些苍白。那次手术做了2个小时,她出来之后非常虚弱。由于宫缩,阿兰的肚子疼痛难忍,呕吐了很久。这是很多人做完人流手术都有的反应,所以我提前准备了呕吐袋,又让她喝了些温水,然后趴在我腿上休息了一会儿。做完人流手术的女性,几乎都是如此虚弱。我曾看到一个女孩做完手术后就一直哭,不知是药物还是情绪原因,眼泪止也止不住。
在医院休息了1个多小时,阿兰的疼痛稍微缓解了一些,但还是没有一点食欲。我带她去附近喝点粥,在餐厅里,阿兰和我聊了很多。
她是山西人,老公在北京的部队,自己一个人刚刚从老家来到武汉上班,入职还不到一个月。最近阿兰才找好房子,就得知腹中的胎儿停止生长,需要进行人流手术。在武汉人生地不熟,就找到了我陪她去医院。
阿兰那天几乎没有动筷子,后来被我硬是劝着才抿了几口粥。人在经历悲痛时,安慰的语言往往都是苍白的,陪伴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

我陪诊的患者,在各个科室的都有,但神经内科是个让人格外伤心的地方。
每次来这里,总是人满为患,很多人看着岁数不大,也是坐着轮椅过来的。在我的陪诊经验里,有不少神经内科的患者病都很难确诊,经常陪着他们检查了一大圈,到最后都没发现问题在哪里。还有的患者已经肌肉萎缩,无法行走,总是发抖。我能明显感觉到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但更令人难过的是,这类病很多是治不好。
我曾在这里陪诊过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60岁老人。老人退休前是一名装修工人,来医院的那天他穿着衬衫和西裤,看上去干净体面,总是看着我微笑,不太说话。这天,老人的儿子由于不放心,也跟了过来。他告诉我,自从一年前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老人逐渐忘记了回家的路,在家里时不时会陷入一种停滞的发呆状态,可以半小时都一动不动。他的反应很慢,而且肢体也不太协调,连杯子都不能够握紧。医生说他的病是不可逆的,没办法治好,只能用药物减缓它恶化的速度。
我还遇到过一位来错科室的老奶奶。她大概80岁左右,因为头疼独自跑到骨科来看病。她走路都走的不太稳,杵着拐杖颤颤巍巍。医生对她说,她来的科室不对,应该去看神经内科。医生还问她:“你这么大年纪,你家属呢?应该让你家人带你过来,要检查也要家里人陪着。”奶奶听力似乎不太好,医生反复问了多次后,她才很无奈地说:“我家里没人,就我一个人怎么办?”医生也没有办法。老人只得起身离开诊室。她走路很慢,看上去很虚弱,有种碰一下就会倒的感觉。

当时我排在这位奶奶的后面,等着帮一位客户开药。看到奶奶还在门口,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决定帮帮她,就让奶奶先在原地等下,我去机器上给客户缴费,顺便帮她看一看神经内科的号。
难得的是,平时一号难求的神经内科还有当天的号,我激动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老人的身影,又回到那个骨科医生的办公室,也再没有人见过她。
那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就这样消失了,我却时常在脑海中想起她,这件事一直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疙瘩。
临时的家人
需要陪诊的病人,很多是因为家属有事无法脱身,不得不自己一个人来到医院的。我要做的不光是陪人看病,也会去做一些他们朋友、家人会帮他们做的事,相当于扮演患者“临时家人”的角色。
有一位阿姨是从外地来的,身高不到一米六,据说因胃病一下子瘦了几十斤,背着一个与她体型不相称的大包,看起来就很沉。
帮阿姨下单的是她的女儿,当天因为有面试,不能陪妈妈来看病。女儿本来想取消面试,被她劝阻了,她不想影响女儿的前程。她还有一个儿子,最近和媳妇准备换房,当天去了另一个城市看房子。阿姨非常体谅孩子,即便儿女都没能前来陪同,她也一点没有不开心,还一直和我强调孩子们懂事。
看完病当天,阿姨还要回到老家。由于堵车,时间很赶,我一路帮她背着包送到了汉口站。没想到送别之后,我快上地铁时又接到了她的电话:阿姨没赶上火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连忙赶回去帮她办理改签,又重新送她到检票口,阿姨在临别前对我说,“我觉得你对我比我女儿对我还要好。”这次,我在检票口目送她上了火车才离开。
渐渐的,我的老客户越来越多,每周大约会有十几单,但很难比这更多。陪诊是个体力活,常常一个星期忙下来,有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但有时候,我会感到我的付出是挺有价值的。

有一次,一名白血病患者要做骨髓移植手术,让我帮他办理住院,顺便取一下核酸结果。办理住院的手续并不复杂,我想他一定比较虚弱,才需要我帮忙办理,就问是否需要我去接他,可以顺便帮他买点吃的送过去,但他都一一拒绝了。
后来见了面,才发现患者是一位个子非常高大的男士。他让我打电话联系他的妹妹,将转诊的事情交接给她。后来我见到他瘦瘦小小的妹妹,才知道原来妹妹就是哥哥的供体,要移植骨髓救哥哥。
妹妹刚出院,原本是能帮他办手续的,但哥哥心疼妹妹,就让我代劳。
陪诊师的工作中,最让我紧张的是做代问诊,因为总会遇到各种没听过的专业名词。因此每次代问诊之前,我都会详细询问客户的基本病史,提前了解这种疾病的相关情况,积累各种医学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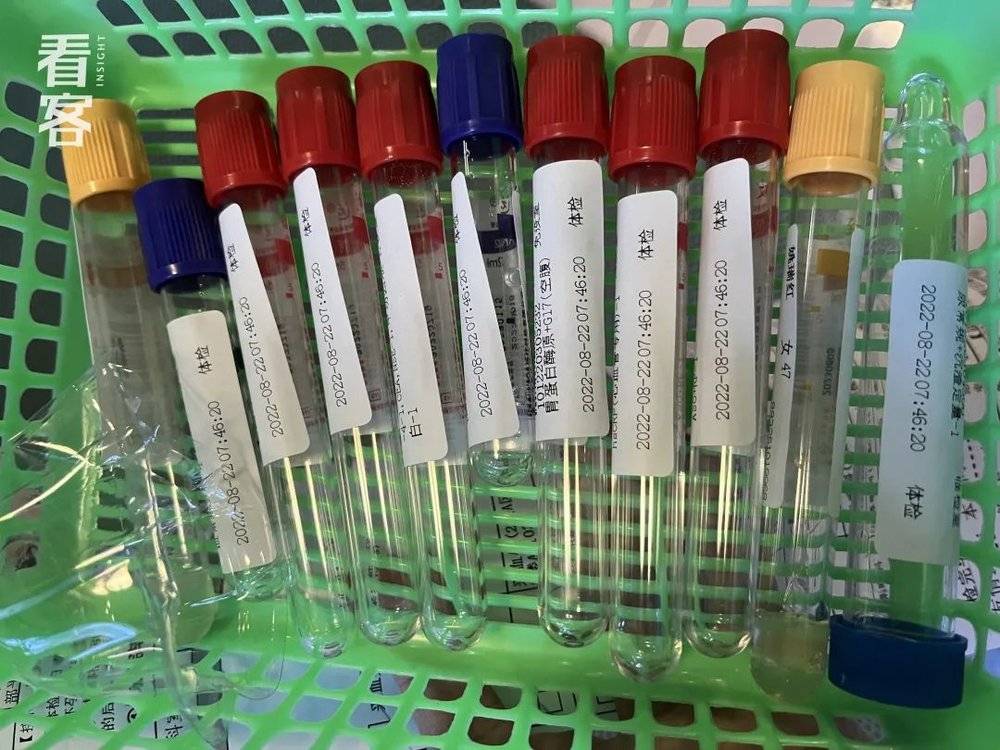
有一次,一位在外地的女士让我帮她预约检查,暂时不打算看病。但报告显示,她的子宫里有长达6厘米的强回声区域,这要么是囊肿,要么是瘤,我怕耽误病情,建议直接帮她代问诊。
医生看完报告就说,这个是子宫肌瘤,应该直接手术切除。“子宫里长了这么大的肌瘤是很危险的,会有出血等症状。长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像一个气球越吹大,还会有裂开的风险。”
我将这些情况告诉这位女士后,她在电话里有点懵,好几秒钟都没有说话。我安慰她说,不一定是很坏的情况,可以来武汉做手术。幸好,第二天,她就过来办住院了,病情没有被耽误。
鱼龙混杂的行业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花3小时往返于各大医院之间,习惯了门诊部不太清新的空气和嘈杂的声音,习惯了住院部浓烈的消毒水味。然而在一年前,我都还不知道有陪诊员这个职业的存在。
去年6月,我陪咳嗽的家人去医院做胸部CT检查。从早上等到下午5点还没检查上,没想到周围还有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仍在等待做检查。
老人们独自看病的场景对我的触动很大:一些独自看病的老爹爹比较着急,他们走路颤颤巍巍,对很多情况都不太清楚,到处找工作人员问,又一直盯着医院的显示屏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回到家,我在网上搜了搜,发现原来真的有“陪诊师”这个职业的存在,便决定自己也试一试。

刚开始时,看着汹涌的人潮,这么多的楼层和科室,我也有些茫然。给亲戚朋友提供陪诊服务、在自助机旁帮人挂号缴费……我用2个月时间摸清了陪诊师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开始去医院附近给路人发传单。
武汉的医疗虽然没有北京这么好,但还有一些科室是在全国排名靠前的。我会优先把传单发给手上有文件袋或病历资料、背着大包小包、拿着片子的人群,他们可能是来自外地的患者;还有那些年纪较大的患者,他们通常不太习惯使用线上挂号系统,都很可能需要帮助。
陪诊师在武汉的认可度也没有那么高,有不少人出于各种顾虑不愿收传单:有的说自己经济条件一般不舍得这个费用,有的担心我是骗子,还有的认为我就是黄牛或者医托。他们说话通常挺难听的。这种质疑让我一度有些沮丧,也只有自己回家慢慢消化。
我能明显感受到,这几个月行业的热度变高了。网上有关陪诊师的账号变多了,报道也越来越多。有人把它包装成轻松挣钱,月入过万的行业,这是一种误解。
我做陪诊半天199元,全天299元,常规跑腿一次100元,在本地几乎都是这样的收费标准。不少客户会下跑腿单让我帮忙预约检查,但跑一次就需要一个下午。

大医院的检查资源极度稀缺,很多患者又需要同时检查多个项目,我必须分别排很长的队去了解每个项目最快能约到什么时间。为了想办法把这些号约到同一天,一个检查我至少要排队预约两次。
若是和患者约陪诊时间,我也都会建议他们将看病时间约在早上,这样方便他们将很多检查在当天处理完。虽然这意味着,我几乎每天需要5点半起床,花一个半小时到达医院,然后开启在各个科室和各医院奔波的一天。
做这行之后,我似乎总在和时间赛跑,每次都是踩上单车蹬的飞快:有时一天要去的两个医院离的太远,路上的时间很赶;有时上一个陪诊的患者超时,但下一个患者的陪诊时间也不容改变。就这样一直忙到晚上回家,也仍然需要不停的回复新老客户的信息,直到半夜。
若是抱着发财的目的,那可确实选错了行业。虽然我整天忙忙碌碌,但现在的工资只能勉强覆盖日常开销。
大医院的人流似乎永远不会减少,患者排了几小时的队,见到医生可能聊不了几分钟,可医生一天里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休息的间隙,因此在做代问诊时,我会尽量把最重要的事放在前面说,尽可能减少医生的工作量。
但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勇气和医生说自己是做陪诊的,往往会说是患者家属。
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行业,有些人是凭良心做事的,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最近医院的厕所门上贴上了不少黑色的陪诊广告,旁边有时还贴着违法的代孕广告。若是搞得医院反感我们,然后去打击这个行业,对很多患者来说也徒增麻烦。
陪诊师的工作总是周而复始地接待新的患者,但总有几名患者始终让我挂心。例如那对做骨髓移植手术的兄妹,我仍时不时会去询问他和妹妹的状况。但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的信息那位患者迟迟没有回复。
他一直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不会看到信息不回的。心里总隐隐有些担心,但又觉得应该不是我想的最坏的那种情况。我对自己说:可能是他看到了一时没回,就忘记回复了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ID:pic163),作者:蒲潇,内容编辑:百忧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