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互联网时代,与其说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智能手机,倒不如说是完全依赖于智能化的电子产品:哪怕近在咫尺的一个目标,恨不得都要用GPS导航步行前往。而千禧年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有GPS作为辅助,英国伦敦出租车司机上岗前仍旧需要严格的培训——司机需要记住伦敦市中心查令十字街火车站方圆十公里范围内的25000条街道,以及其中所有景点、酒店、警局,甚至理发店、小餐馆、酒吧的位置和开业状况,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成功通过考试的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大脑在大量记忆资料的锤炼下,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与普通人相比明显增大,灰质增多。也就是说,这场大脑的极限运动最终真的改变了人类大脑结构。
但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越来越依赖那些外延的电子设备来减轻我们大脑的负担——信息囤积者由此诞生。想想你邮箱里那些未读的邮件、云存储中的各种资料、手机里来不及分类的照片和视频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Charlie Warzel,编译:Jichang Lou,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防疫隔离最严格的时候,通常是在我晚上无聊的时候,我会打开手机的相机胶卷回顾疫情开始前的生活。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种健康的疫情生活,但是看到以前正常生活时的照片,会让我对那样平凡的生活极为向往。看看我。在一个餐馆里!与朋友在看演唱会!参与社会活动,尽情展示自我!
先撇开照片的内容不说,单是打开相册对我以前的生活进行“马赛克化”这一体验,就让人感到一丝说不出的喜悦(当我打开“所有照片”时,我的手机可以同时显示45张照片)。
有些时候我会在我相册中的26,224张照片中搜索几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我的手机会很慷慨地将它归类为“最近项目”),而这个快速翻阅的动作,会使这种“马赛克感”更为强烈。

我注意到,当我在快速滑动而没有看清单独的照片时,我可以通过区分色块来对某张特定时期的照片进行寻找。比如说,我在纽约居住的那段时间所拍下的照片普遍更为昏暗,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照片都是在我铁道旁阴暗的公寓里拍下的。
在2015年下半年的那段时间,这种马赛克就转为红棕色系,这是我的狗佩吉进入我生活的标志。而当我在2017年搬到蒙大拿州之后,它就会变成蓝绿色系,因为我曾多次笨拙地尝试把我的新家、山峦和蓝天拍入一张照片。
对我们所有的照片进行翻阅实际上是一种奇怪的、值得反省的,甚至“痛快”的体验,以至于人们甚至为此写过歌曲。“除了按照年月顺序,只有痛苦”,这是歌手兼作曲家凯西·马斯格雷夫(Kacey Musgraves)描述自己最近相簿的方式。

而且,是的,这些档案可以记录下时间流逝所带走的爱和亲人。它也是一种实用的日记本或文件整理工具。在一次浏览中,我曾萌生出一种假想:一位历史学家能否只通过浏览一个人的相册,就写出他的人生故事?
概括我们的人生并不新鲜;但是我们进行这一概括时所囊括范围的大小和进行概括的便捷程度是全新的。正如作家德鲁·奥斯丁(Drew Austin)在《连线》(Wired)一书中所说:“通过不断给我们灌输‘个人信息井是无底洞’这一想法,谷歌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信息囤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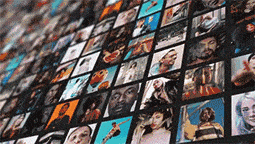
奥斯丁提出,在谷歌所提供的许多服务中——尤其是需要用户创建谷歌账号的Gmail——储存了大量用户私人信息,而且能够被轻易地搜索到。当Gmail在2004年启用的时候,它向我们提供了解决当时电子邮件各种问题的强大工具——例如回收站,满足了删除邮件以省下储存空间的需求,并解决了难以找到以往邮件的问题——而这些工具也同样改变了我们对电子邮件的使用和看法。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这是在Gmail启用10周年之际其创始人对电子邮件状况的描述:
“电子邮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它让人们的社交习惯变得非常糟糕。现在流行一种24/7文化,人们期待随时能得到回复。就算现在是星期六的凌晨两点也没关系——人们会觉得你此时同样在回邮件。人们不再出门度假。他们逐渐成为了电子邮件的奴隶。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不能被计算机算法解决。它更像是一个社会问题。”
Gmail的创始人在社会问题这点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依然觉得,他并不能因此就逃避责任。这是一个由于我们所用的强大工具而恶化的问题。无限的储存量和轻松的搜索功能,彻底改变了我们与个人信息的关系。
就像奥斯丁所说的:它“使我们能够随意地,甚至凌乱地处理我们的数据......而不是用一个可读的系统来组织我们的数据,或者知道东西在哪里,它可以全部进入一个看似混乱的堆积。”
它也会造成信息囤积。“由于担心我们可能会删除一些我们最终会需要的东西,我们会谨慎行事,将其全部保存起来。”奥斯丁写道。这样,你就得到了有26,000张照片的“最近项目”和深不见底的邮箱。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人给三个月前的邮件写回信的奇怪现象。当然,我们这一可悲的“成规”也不只是因为储存空间和搜索引擎的强大,但是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些强大的功能,电子邮件也不会成为像今天这样的“祸害”。
奥斯丁认为,在社会层面上,充足的个人数据存储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其中存在一种倾向:我们杂乱无章、组织不力的信息被个人化为一座座孤岛,而不是为它建立公共基础设施。互联网有过多的可公开获取的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被互联网归档。
我们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公共信息,但如果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代际之间)的个人信息传输却减少了呢?如果我们的数字传家宝变得无法被近亲获取,我们会失去什么?如果杰出人士不把遗产中的云数据捐给大学档案馆,我们会失去什么?
我自己就是一个信息囤积者。我最近不得不将我的谷歌存储空间升级到100G,而且我正准备购买一个更大的套餐。我的收件箱是一场灾难:将近20万封邮件,有已读的,有未读的,可以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我创建的最后一个标签是什么?“暑期实习申请”。
我的相册则是我个人生活的大杂烩,其中夹杂着2734张截图——主要是我过去的自己显然觉得可能值得回味的推文或文章段落。在我的各种存在云上的笔记应用程序中,我存储了无尽的无用清单和思考,复制粘贴的片段和链接。这都是为了把我每天面对的大量信息卸载到一种“外接记忆”中。
在理论上,这是令人兴奋且有用的。在实践中,我并不相信这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更高效,甚至更有见识。偶尔,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停顿下来思考我读过的重要的东西,而只是把它归档,以后再考虑。我的“外接记忆”的另一个影响是,它促使我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数量进行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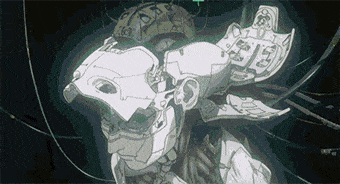
那个时代的记忆,现在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那么它们是否会因为我只能靠大脑来访问它们而更加珍贵,更加不可磨灭呢?还是说它们不那么可靠,更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
在同一采访中,萨卡萨斯讨论了他用手机记录两个年幼孩子生活的经历:
“他们成长得如此之快,而你想记录他们成长的情况。然而矛盾的是,我本以为对他们的成长的视觉记录能使这些记忆更容易保留下来,但是,它们反而让我对事物溜走的感觉更强烈。”
在疫情期间浏览我的相机胶卷,也使我感到时间和自己溜走得速度更快了。这是一种忧郁情绪,但它不仅仅是一种悲伤的感觉。因为这种体验的核心也是一种意识的知觉。我不断地评估自己和我的生活(一件好事!),同时也把自己从一些时刻中抽离出来,以记录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现在拍的照片比疫情前要少,而且我拍的那些照片也变得有些莫名其妙。我甚至在社交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我所拍的似乎是我在安静时刻的快照,即使这些地点并不适合拍照。大多数照片并不是真的要分享的。对我来说,手机照片所注重的更在于拍摄这一动作,而不是我用它们做什么。
相反,它们是为了给相机胶卷中近乎无限的滚动添加色彩。它们可能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还在这个世界上。它们是用来镶嵌、用来装饰的。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这绝对是我能够拍摄和保存无限多的照片的结果。
参考文献:[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502424/
原文/newsletters.theatlantic.com/galaxy-brain/623d45efdc551a00208acf88/data-hoarding-google-health-effect/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Charlie Warzel,编译:Jichang L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