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湘人彭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不是一本很容易看进去的书,它看上去既不像文学批评,也不像阅读札记,更不像人物传记,确切地说,它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孙德鹏天马行空的联想和仿佛梦呓般的个人感悟,也很可能吓退一部分读者。
一些文字会时不时跳上前,成为阻碍我们继续阅读的拦路虎,比如第三章“记忆”的开头:
“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唯一的入口在梦中。确切地说,我想是破晓时分的梦。
起初我梦到一片荒原,像南英格兰威塞克斯的乡间模样,多雨、泥泞,偶尔点缀些绵羊之类的软弱生灵,人烟稀少。不远处,有哈代小说中的古老街道,都是百年的宅院,除了人的离去,眼前的一切都凝结了。
黄昏的景色很美,有一种粘稠感,但缺少生气。可是,只要我们在这条接到上站得足够久,就有机会与哈代先生攀谈,他会告诉我们身处某一国度但偏远地区意味着什么,或许,他还会告诉我们怎样走出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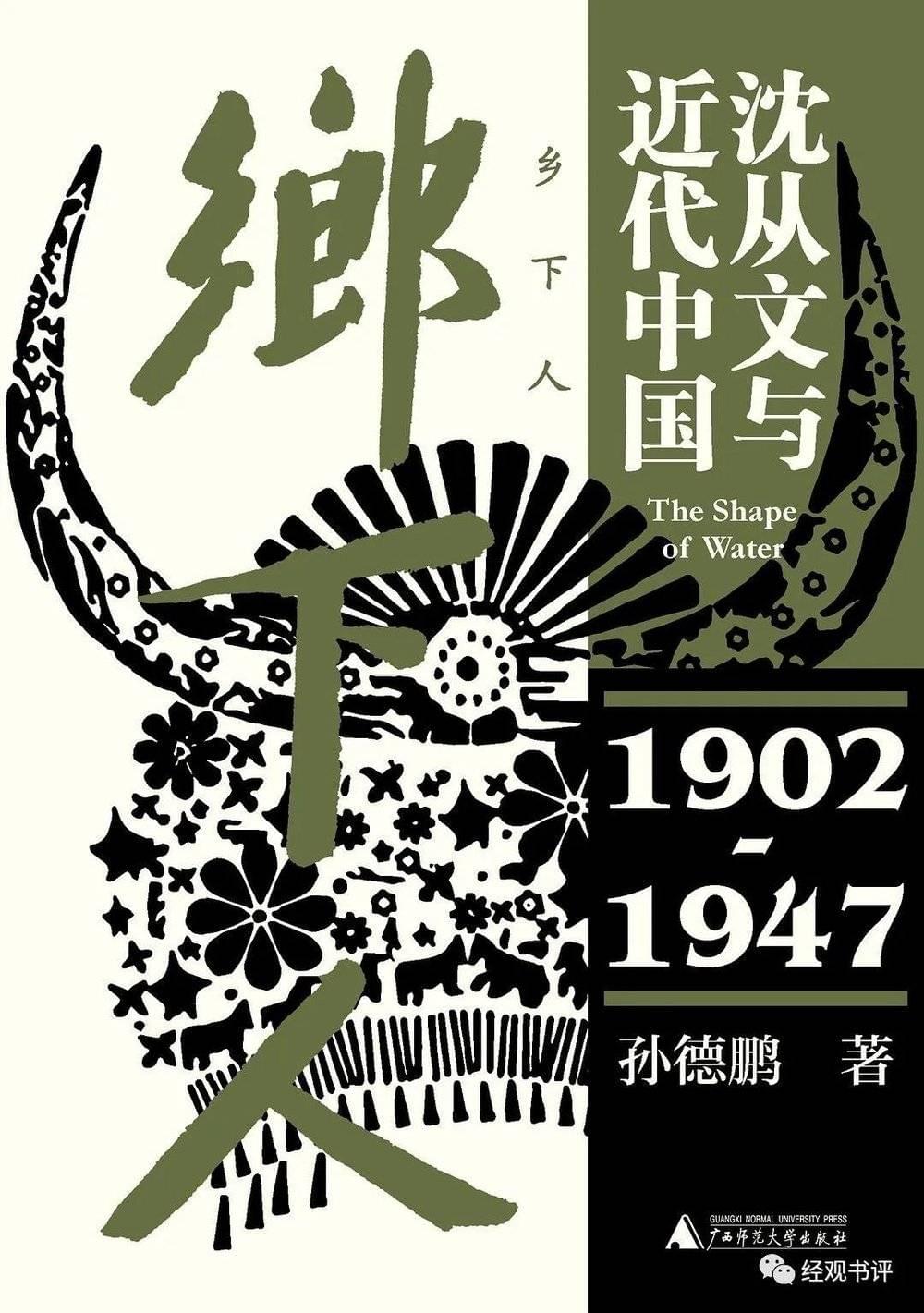
孙德鹏/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不用再举例了。这些像意识流一样有感而发的句子,充斥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的字里行间。它们像许多漫无边际、毫无规律和方向可言的云,飘在喜欢的人那里,会成为好看的风景;而在不喜欢的人那里,则会成为痛苦的源泉,以及笼罩整个阅读过程的阴云。读者在书页间跋涉得那么辛苦,难道是要作者来聊自己的梦吗?而这一切和沈从文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作者的某些叙述,有些个人化了。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有可称道之处。哪怕即使是它的弱点和不足,也在告诉我们:沈从文的传记可以有另外的写法,不一定都必须如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或者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那个样子。
他专列一章,花大量的笔墨分析沈从文和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中的乡下人形象,试图讲述“乡下人”代表更普遍的人性,但如果拿掉该章,对全书也没有影响。或者,如果换一个角度,比较沈从文和其他民国作家、学者、知识分子在乡下人思想和创作上的异同,或许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有更多帮助。
书中一再强调沈从文“乡下人的情结”,这不是作者孙德鹏的发明,已是很多沈从文的研究者的共识。但孙德鹏希望借助“乡下人”这个意象,来讲述近代中国的诸多问题。
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很多新的思想观念进入中国之后,沈从文正是以此来认识他的湘西,他所身处的世界。“在进化主义的语意场中,似乎没有乡下人的位置,他们被遗忘了。在都市知识人眼中,他们不足以成为改变国家的力量,也不足以成为善恶的主体。与国体问题、政体问题的重要性相比,他们还来不及去思考乡下人的处境。避开时髦理论,真正把乡下人的生活植入历史记忆的,是一位自称乡下人的作家。” 孙德鹏在书中如此写道。
和一般研究者不同的是,孙德鹏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沈从文的文本世界里徜徉。他坚信,沈从文走了不同的路,“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文本中,隐藏在那些有温度、有质感的故事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里看到沈从文作品的大段摘录和赏析,因为这是作者孙德鹏看重的。
在这本书的所有章节里,最难忘的是第三章:“记忆”。孙德鹏敏感地抓住了沈从文和他所处时代任何其他人的不同,就是他带着独特的记忆走上了文坛。作为来自湘西的“乡下人”,无论何时何地,沈从文都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他的笔也始终和乡下人站在一起。
沈从文说: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孙德鹏说:
“从保存人类记忆的角度来看,沈从文与奥德赛拥有一样的孤独旅程,面对相似的身份危机。他们共同的旧方式是借助旅程,通过让他人揭开自己身上的秘密来重拾记忆。”
孙德鹏也看到水对于沈从文写作和经历的深刻影响。在第三章“记忆”里,有一个部分“拜水”,是集中讲述这个问题的。湘西多水,多对水的崇拜。而水,也是沈从文灵感、经验和智慧的源泉。他所写的故事,也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他文字中的气氛,是水带给他的。孙德鹏用了一个词,比喻沈从文文体的特点,叫“液体性”。孙德鹏写道: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整个世界仿佛是被浸润在水中的样子,如此才值得人们记忆,如他所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某种程度,沈从文用他的笔保存了近代湘西的记忆。打开沈从文的书,仿佛能看到湘西从沈从文所有书页中走出来:
“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妈,王嫂;他是樵夫贵生,侦察兵熊喜,他是老实人自宽,他也是山大王刘云亭;他是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他是转过身谦卑面对云麓大哥,四处寻找九妹的那个人;他是他生活的时代,也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度, 他不停地超河流走去,乘坐的桃源划子也旧了,有两千年那么旧,像一张被江风,被岁月摧残的脸。”
在近代中国,不仅沈从文,许多人也都深受乡村影响。他们有的以启蒙者自居,乡村时常是他们居高临下俯视的对象。也有人则认为,乡村是封闭,保守,蒙昧的象征。但所有的观念,都和沈从文心目中的乡村并不一致。
在《乡下人》这本书里,孙德鹏通过对沈从文众多作品的梳理,提炼出许多个关键词,各列一章来阐述沈从文“乡下人的特征”:小兵、统领官、初出茅庐、都市、落伍、村姑、山路、诡道、新与旧、乡评、食色……。有些关键词很好,展开的内容也好。但有些关键词,如果换一换,也许更好。
比如“村姑”这一章,换成“爱情”,也许主题会更集中,也更能提炼出沈从文湘西世界最核心的精神气质。就像《边城》里,翠翠与傩送一生都没有向彼此表明心意,那是沉默的爱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还有《夫妇》里的爱情,一对年轻乡下人是一对夫妇。新婚不久,一同回娘家,走在路上,天气太好,两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边看山上的花。风吹,鸟叫。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做的事情,而这在外人的眼里却被看成伤风败俗,他们被人捉了奸,直到最后被释放。
还有《从文自传》里写到的,沈从文见证了一个卖豆腐乡下男子的爱情。他和一个女子的尸体在一起睡了三天,最后被发现,要被处死了。临刑前,年轻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作这件事?”他笑了笑,当沈从文是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又自言自语轻轻说:“美得很,美得很。”沈从文永远记得这个微笑;而沈从文自己,也是乡下人追求到爱情、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写给张兆和的情书,连同那句著名的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流传到今天……还有妓女的爱情。这一点,作者孙德鹏也提到了,只是他把它放在“食色”一章里。
孙德鹏以沈从文《小砦》中的妓女桂枝为例,写道:
“历史上不乏红颜祸水的歧视,人们斥责女性的堕落,让她们为国族的衰败担责。妓女自然被塑造成母性形象的对立面,指向疾病与死亡,而不是生育、抚养、仁慈等柔美气质。她们没有任何清白的征兆……沈从文的‘桂枝’自然不是什么文明的裹尸布,她和沈从文小说中的众多女性一样,都是隐匿的受害者。”
沈从文见过无数“桂枝”这样的年轻女子,他带着悲悯的心情写下:
“好几次在渡船上见到这种女子,默默地站在船中,不知想些什么,生活是不是在行为意外还有感想,有梦想。谁待得她最好?谁负了心?谁欺骗过她?过去是什么?未来是什么?唉,人生。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广宽泛,无边无岸。”
岂止是妓女,岂止是女子,整个湘西,在沈从文的眼里,人本来都是大海,宽广深厚,无边无际。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对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研究,还可以再深入。近代中国文学史以及思想史其实更复杂,而沈从文也不是唯一被边缘化的人(不管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关于近代中国,也不是只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那同样是一个各种学说思想争鸣、一较高下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更深入了解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以便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以及近代中国的乡村变迁。
但同样也想谢谢孙德鹏,不管是对于这本书的不满,还是对于这本书的意犹未尽,是他让更多人想继续行走,继续在沈从文和近代中国的路上探访下去。
那么,在出发之前,让我们再重温一遍沈从文说过的话: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湘人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