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沿着价值链生产和交易的:一个产品从构思到最终销售给消费者被分解成一系列任务,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市场推广、批发和零售等等,这些任务被分配给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完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李靖恒,原文标题:《全球价值链:中国出口背后的跨国公司》,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过去40年里中国出口的神奇现象: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世界高科技出口第一大国。作者邢予青是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将其劳动服务和零部件与跨国公司的品牌和技术进行捆绑,形成最终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与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贸易形式不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边界是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决定。这种新形式的贸易正在挑战着传统的贸易理论和贸易统计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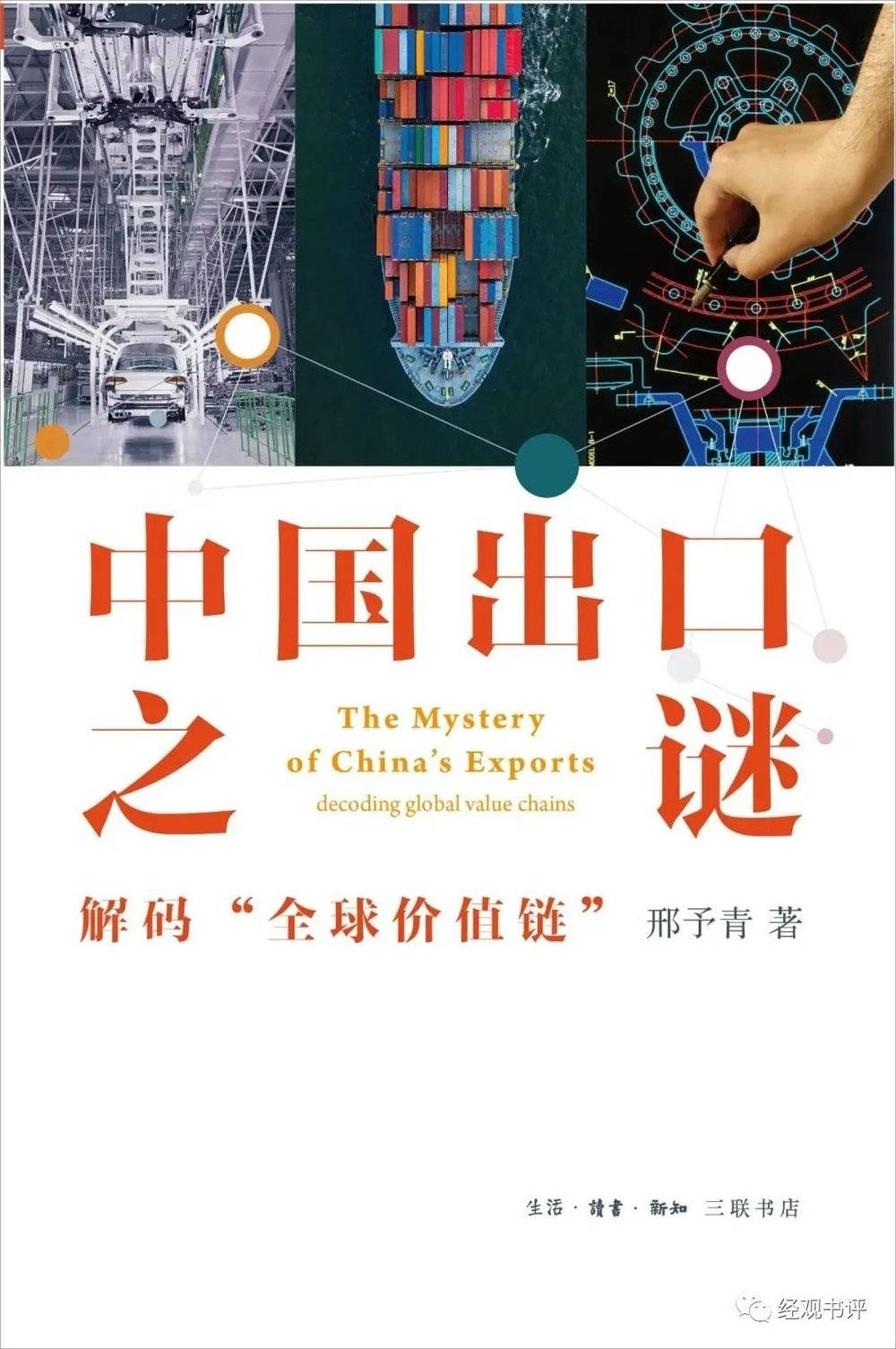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7月
一部苹果手机上的任务链
2008年6月,苹果公司时任CEO史蒂夫·乔布斯在旧金山发布了iPhone 3G。当时,这部手机因其新颖的设计给邢予青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观察到,这部手机的背面印着一句话:苹果公司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通常,按照世贸组织原产国规定,中国出口的产品往往印着“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邢予青认为,乔布斯之所以一反常规使用“中国组装”而不是“中国制造”,是因为他想强调,iPhone是由苹果公司设计的,而中国企业只是将进口的零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而已。
2009年,一份欧盟的研究报告也吸引了邢予青的注意,这份报告称,2007年中国高科技出口产品排名世界第一,年出口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等27个国家。然而,当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3500美元,只能算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直觉上,邢予青认为欧盟的这份研究报告的数据存在一定问题。
于是,邢予青萌生了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奇迹的想法。全球价值链是一种新的商业运作形式,它是由多个国家参与开发、制造,最终向国际市场上的终端用户提供制成品的一种新的生产和贸易方式。
苹果手机的生产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典型案例。参与iPhone 3G制造的有9家公司,分别位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和美国。其中,日本东芝公司提供了闪存、显示模块和触摸屏;韩国三星公司生产了应用处理器和动态随机存储器;德国的英飞凌公司提供了基带、摄像头模块、射频收发器、GPS接收器、功率IC射频功能。总的算下来,一台iPhone 3G的生产成本一共为178.96美元。其中,中国的组装服务费用为6.5美元,仅占3.6%。
如今,世界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沿着价值链生产和交易的。一个产品从构思到最终销售给消费者被分解成一系列任务,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市场推广、批发和零售等等。这些任务被分配给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完成。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演进,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定区别。19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不同国家各自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每个国家都能从中获益。李嘉图用“英国的布换葡萄牙的酒”这一著名的例子阐释了比较优势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他的学生俄林发展出了资源禀赋理论,也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资源禀赋理论考虑到了劳动和资本两要素,比只考虑单一劳动投入的比较优势理论更接近现实。资源禀赋理论表示,各国在需要密集利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生产上有比较优势。例如,劳动力相对资本更丰裕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具有优势。
然而,一些新的贸易现象也在挑战着新古典贸易理论。比如,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北北贸易”。于是,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新贸易理论。通过引入规模经济,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对同类产品既有进口又有出口,比如美国从日本进口汽车,同时又向日本出口汽车。由于存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消费者偏好差别,各国能够从产业内贸易中获益。
然而,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等都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并且向美国出口大量的高科技产品?
1980年,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额仅为182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出口额达到了1.58万亿美元,30年间的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中国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3.9%。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到2009年,中国出口份额达到了9.6%,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18年,中国出口份额增长到了12.8%。
在出口总额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截止1990年,中国出口的产品一半以上属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此时的贸易产品还相对符合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而到2018年,中国出口产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制造品出口占比达到了93.2%。从以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升级到以机械和运输装备、电信设备、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等高价值、高技术为主的出口结构。
随着经济发展,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并不奇怪。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2007年,中国就已经成为第一大高科技出口国,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达到了6542亿美元,又差不多翻了一倍。而同期,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却下降了三分之一。日本和德国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温和增长。这实在是很难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来解释。
于是,许多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和媒体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中国出口的奇迹。比如,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或者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有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汇率制度的角度来谈。邢予青认为,这些理论实际上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出口的谜团。
邢予青提出,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有关中国出口的一系列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在全球价值链中,货物贸易被任务贸易取代。目前国际市场上的大部分制造品,实际上是位于不同国家的公司协作生产的产物。而在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暗含的假设是,一个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都发生于一个国家内。
而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是跨国公司。国际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要么贴着国外的品牌,比如苹果手机和耐克鞋,要么在沃尔玛等零售业巨头的平台上进行销售。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能够将其低技术含量的劳动服务和零部件,与跨国公司的品牌和技术进行捆绑,然后将最终产品销售给全球市场的消费者。
在中国出口中,高科技产品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一。然而,大部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际上都属于加工贸易。所谓加工贸易,指的是利用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制成品,然后再出口到海外市场。进口的零部件往往包含着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比如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索尼游戏机等。
在1997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80%以上都属于加工贸易出口。到200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90%。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加工出口占中国高科技出口的比例一直在80%以上,之后有所下降。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还可以发现贸易统计上的问题。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统计是以产品跨境来结算。一件商品从一国海关运出,其金额被计为出口,反之计为进口。然而,这样的统计方式有一个隐含的假设:一件商品的出口总值都是在这个国家创造的。这个假设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相符合,但是不符合全球价值链贸易。
在国际贸易统计中,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顺差等于出口减进口。1980年,中国对美国有2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00年,中国对美国有273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到2018年,贸易顺差飙升到4195亿美元,占到了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一半。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邢予青指出,用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和解释中美双边贸易平衡,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大部分中国出口的商品是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入美国市场的。在这些产品中,不仅包括中国国内的中间产品,还包括国外制造商的零部件。加工贸易的产品中,往往包含了巨额的外国附加值。
比如,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中,就包含了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厂商零部件的增加值。而在最终的贸易统计中,这些增加值全部被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从增加值的角度看,中国到美国的苹果手机的出口额被高估了。
200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了1130万台iPhone 3G。如果以传统的总值计算,中国对美国产生了约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如果按照增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仅有7300万美元。
传统的贸易统计不但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几十年里,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主要从事品牌营销、产品设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将零部件制造和最终产品组装完全外包给世界各地的公司,成为了“无工厂制造商”。这些无工厂制造商将研发、设计、品牌、供应链管理服务等无形资产的收益嵌入在最终商品中,他们往往获得了最终产品增加值的最大份额。然而,根据货物跨境的出口统计方法,这些无工厂制造商从海外销售中获得的收入不会被记录为美国的出口。
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价值405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和手机。而事实上,苹果公司2018年在华销售额是519.4亿美元,其中没有一美元被计入了美国到中国的出口。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耐克、高通、AMD等其他跨国公司。
贸易历史:一部“分”与“合”的故事
如果从更长跨度的历史来看,中国出口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瑞典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是保罗·克鲁格曼的学生,他在《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一书中提出,在1990年前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开启了全球化第二次加速过程,他将其称为“第二次解绑”(second unbundling)。
这本书的名字“大合流”与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相对应。在《大分流》一书中,彭慕兰尝试研究了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何在18世纪后,中国与西欧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世纪初,蒸汽革命使运输成本急剧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成本大幅下降。1819年,蒸汽船第一次横渡大西洋。1820年以后,英国蒸汽船的运载能力和运输效率持续提升。在1820年到1870年期间,伴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国际贸易数量快速增长,鲍德温将其称为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
伴随着贸易快速发展的是工业革命。整个19世纪,工业化的浪潮从英国扩散至比利时、法国、瑞士、普鲁士等许多欧洲国家,也扩散到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19世纪中期,化学、电力和内燃机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工业实力超过了英国。
不过,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在地理上集中在“北方国家”,包括北大西洋经济体和日本等国。鲍德温认为,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过程中,虽然商品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了,但是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动的成本却没怎么下降。其结果就是,市场变成了全球性的,而工业生产则形成地区集聚。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却经历了“去工业化”。例如,18世纪时,印度的棉纺织业无论从质量、数量还是出口量都是全球的领导者。而到19世纪末,印度超过百分之70的纺织品需要进口来满足。1750年,中国和印度(当时包括巴基斯坦)占据了全球产出的73%;183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一半以上;而到191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仅有7.5%。
在1990年前后,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从根本上降低了思想交流的成本,全球化迎来了第二次加速过程。通信技术的突破发展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外得到协调。发达国家的企业这时发现,如果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离岸至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益。
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也可以称为“全球价值链革命”。这一过程重新划分了知识的国际边界。目前,行业竞争的边界越来越多地由国际生产网络的边界决定,而非国家边界。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了起来,引发了知识的“由北向南”的流动。
在“旧全球”化的过程中,北方国家发生工业化,南方国家去工业化。而“新全球化”反转了这一趋势,北方国家制造部门附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快速下降,这些部门的工业岗位数量也减少了。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出急速增长。
在1990年到2010年期间,G7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的制造业份额从三分之二跌到了二分之一以下。而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波兰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份额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在2010年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
新全球化也改变了贸易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北北贸易”主导着全球贸易,这些贸易很多都属于产业内贸易,也被称之为“往返贸易”。而大概在1985年左右,发达国家与周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往返贸易所占比重开始突然上升。这种“南北贸易”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内,尤其是电器和电子行业。
然而,20世纪末以来的“新全球化”目前遇到了挑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反全球化”的浪潮。邢予青认为,沿着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任务分解得越细,分散的国家越多,价值链也越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声称,中美贸易“不公平”,美国对华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在贸易摩擦中,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对华为等科技企业的制裁,也开启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脱钩。
甚至连一向相对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们也对全球化提出了质疑。2010年,保罗·克鲁格曼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人民币升值,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者保罗·萨缪尔森认为,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可能就是美国失去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是对全球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2019年12月以来的新冠疫情也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再一次的冲击,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疫情引发的国内生产中断,导致了全球很多产品的生产受到影响。比如,湖北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中心,由于武汉疫情,全球汽车产业运行一度中断。
同时,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医疗用品的生产离岸或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疫情爆发时,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限制医疗用品的出口,依赖进口的国家暴露了过度依赖全球价值链的风险,美国、日本等国家因而纷纷采取措施开始引导医疗产品制造的回流。
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困境,19世纪的第一波“旧全球化”曾经也遭遇到了逆转。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简要介绍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兴衰。罗德里克表示,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是全球化的致命弱点。
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100年里,世界经历了第一波全球化,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学说大行其道,1820年到1875年,欧洲各国的贸易壁垒和关税不断减少。其中1846年被视作英国税务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英国废除了拿破仑战争时代设立的谷物进口税,这标志着实现了自由贸易。
不过,在罗德里克看来,虽然大家都觉得19世纪是自由贸易的时代,但是当时只有英国推行贸易开放政策的时间稍长。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对自由贸易三心二意,只有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内才真正施行了自由贸易。美国在1861年到1865年经历了南北战争,对进口加工品征收了很高的税。在北方取得胜利后,为了保护北方处于萌芽时期的制造业,林肯总统对进口工业品施加了平均45%的关税。因此,19世纪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
鲍德温也介绍,在经历了1846年到1879年这30多年的自由贸易之后,1879年到1914年期间,现代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德国首相俾斯麦引领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风潮。俾斯麦在统一了德国之后,宣布恢复对外国的高关税,他表示:“别国的过量生产和德国的过度消费降低了德国的价格水平,阻碍了工业的发展。”这一期间,德国的关税翻了两倍至三倍,其他国家的关税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引领第一波全球化的英国已经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再单方面托举起世界的贸易体系了。美国更是在1930年推出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将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面对30年代的大萧条,各国也都想求助于贸易壁垒来摆脱经济困境。1929年到1937年,世界贸易量减少了一半。随着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全球加速滑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在,一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会告诉你,通过自由贸易,参与贸易的国家都可以获益,关税会导致“扭曲”和“福利损失”。教科书也会告诉你,自由贸易在一国之内会产生“分配效应”。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不过,教科书还会声明,总体上获益的部分会超过受损的部分,如果存在一定的机制来补偿受损的人群,那么大家都可以从中受益。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更复杂。罗德里克介绍,很多研究都表明,自由贸易带来的一部分人群的短期损失,会演变成长期甚至是永久性的损失。比如,美国低技术工人的失业有时会变成长期失业。而且,随着贸易变得更越来越自由,废除贸易壁垒的经济效益也变得越来越小,重新分配的效果却越来越大。
从19世纪初到现在,全球化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跌宕起伏,用于理解国际贸易的理论也层出不穷。到目前,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确实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机会。不过,分工、贸易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很多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没能被理解的问题也为全球化的进程埋下了隐患。《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这本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出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理解全球化提供了思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李靖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