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多数知名高校宣布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引起人们的关注。高等教育发展到底需要怎样的评价标准,关系到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培育和学术建构,不能不予以重视。调整原有评价排名之后,我们又如何有效衡量未来的高校建设?本文指出,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首先需要回归常识,在认识世界一流大学共性的基础上,理顺研究氛围及治理结构等多方面的逻辑。我们推出本文,以供读者参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原标题为《回归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的常识》,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其实,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既然它是世界性的,就总存在一些共性,否认共性仅强调差异性,也就不存在“世界”这样的限定词,甚至是否为他者认可的“大学”可能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因此,论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治理,首先就必须理清楚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甚至是常识性的问题。
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到如今英美知名大学的特征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大致包括如下方面:培养一流(高层次拔尖)人才;学术底蕴与基础扎实的学科与研究支撑;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相对充裕的科研经费以及其他有形资源的支撑;具有前瞻性视野、善于审时度势和掌握灵活策略来获取资源且有效将其利用的领导与治理制度安排。
上述几个方面存在一种彼此勾连、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前者为果,后者为因,缺失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办不成一流大学。整个连环的最终结果是一流的人才与科研成果,但它的首因是资源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获取和有效利用资源的领导与管理制度安排。但最终结果与首因之间,也存在一种有机关联,因为制度的设计目的即价值预期总要关联到人们如何理解一流人才和高水平成果,以及资源如何有效利用才能达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此就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审视一所大学是否能够成为一流,在理念层面,上述各个议题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的演绎逻辑,彼此之间存在派生关系,前者衍生出后者;但是,在操作层面上,却是一种反向的实践逻辑,因为没有后者为前者提供支撑,一流大学就永远停留在水月镜花的理念层面上。由此,我们不妨看看世界一流大学在上述各个环节中的共性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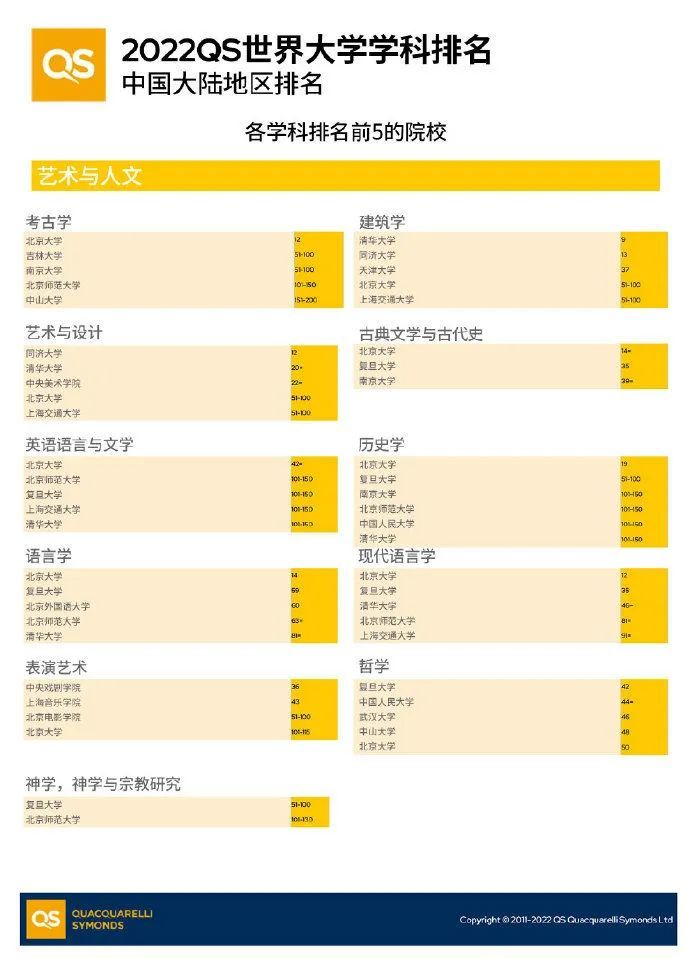
(一)良好的研究文化与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基于经验与事实不难发现,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尽管承担水平程度不一的本科人才培养任务,但高水平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更符合一流大学的特征。美国众多私立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品质很高,但它难被公认为是一流大学;很多州立大学本科质量一般,但因为有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而跻身世界一流;唯有少数兼顾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私立大学,以其全方位的优质表现而少有争议地处于金字塔的塔尖。
研究生教育的层次本身并不是一流大学的标识,毋宁说它代表了一流大学所特有的研究资源、氛围与文化。它会让所有人包括本科生受益,正如我们所领悟到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轨迹呈现如下特征:中世纪以教师讲授为主,到了德国则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与研究一体化模式,即把教师的研究作为人才培养手段,而进入现代,则是强调学生参与的教、学、研融和模式,当下国际知名高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教、学、研、创共融共生,所以我们才看到斯坦福和MIT不仅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还涌现出大量高层次创业人才。研究在如今世界一流大学中已经成为人才培养过程甚至溢出教学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不仅仅是研究生的本分,也是本科优秀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一: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特征之一是,它一定拥有良好的研究氛围与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
(二)学术底蕴深厚与基础扎实的学科支持。卓越研究生与本科人才培养,需要借助丰富的研究资源与良好的研究氛围。学科与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单元,也是其得以实施的底层结构。本科专业需要学科提供课程资源,而学科建设则主要靠研究实力与基础来支撑。学科水平固然不能与研究水平直接画等号,但是,没有研究水平,学科乃至大学肯定难称一流。那么,究竟如何衡量研究水平?就目前而言,我们似乎对各种论文发表、引用以及ESI的位次等情有独钟,但是,这种指标化的最大误区在于它并没有反映科学研究活动的实质。
衡量科学研究质量存在三个价值维度:是否是特定领域中的突破,如重大发现,它代表智力性的贡献;是否带来产品、技术、方法、手段以及工艺上的创新,它反映为知识应用与转化的贡献;是否通过研究培养出一批高层次的人才。可以说,纵观全球,没有基础领域重大发现的如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不能够承担最前沿领域研究的大学,很难号称为世界一流大学。ESI等指标从来不是这些一流大学的追求目标,而不过是高质量成果的自然外溢。在应用研究领域,一流大学也表现极为突出,它不仅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外在高回报的社会福利,而且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受到启发而产生新问题,进而拓展为新的研究领域。
简言之,一流大学的科学研究更多应该是开山凿石,而非仅仅铺路。数量巨大的论文成果,如果没有开拓性的重大发现与技术突破,是否是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且不说,充其量就是铺路石。
结论二: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二,它专注于重大发现与重大应用难题的突破,而非简单数据表现。
(三)雄厚的师资力量。高水平的研究自然需要有高智力与一心向学的教师来承担,一流大学中的教师的确是教学者,但他们是卓越学者型的教师。美国19世纪下半叶尚处于初创期的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迅速崛起,就在于它们能够从全美乃至欧洲遍揽世界最为著名或最有潜质的科学家与学者,求精而不求多,并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
进入20世纪,这种揽才方式渐成制度乃至传统,它推崇实力至上,以准市场化的方式撬动知识和思想市场的开放,因而,不仅促成了全美最为优质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而且吸纳了全球最优秀人才的加盟。如今我们频繁谈论一流大学内部的学科建设话题,所有探讨如果偏离了卓越人才智力资源发挥这个核心,所谓一流就根本无从谈起。一流的大学一定是国际高水平人才汇聚的中心,这才是我们常言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外籍教师与留学生数量多少仅仅是标,而质量才是本。
结论三: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三,它的核心在于拥有最为卓越的智力资源。
(四)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与相对充实的研究资源。卓越的师资力量需要有相对优厚的经济待遇提供稳定工作与生活保障,需要有良好的研究设备设施以及经费资源提供研究支持。大致观察一下众多世界一流大学的经费来源渠道,不难发现其共同的特征是经费来源渠道极为多样化。政府固然是高校经费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大学得以维持其运行的更多经费源于其他。
以哈佛大学为例,2016年度其收入来源中来自联邦政府(包括竞争性研究合同拨款)的仅为26%;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2017年度可支配性收入中来自联邦、州与地方仅占24%;牛津大学2016/2017年度经费收入中,政府资助为14%,研究合同经费占41%。我国的清华大学(2016)与北京大学(2015),政府财政拨款(不包括科研经费与学费)分别为31%和45%。经费过度依赖政府以及渠道的相对单一,弱化了高校的财政弹性,甚至束缚住了手脚,约束了高校自主发展的空间。因此,如果没有相对充裕的经费,在资源管理与使用上没有足够的自我掌握空间,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恐怕步履维艰。
结论四: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四,它具有多渠道经费来源与经费使用的相对自主。
(五)领导体制与治理结构。回溯历史,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都带有时势造英雄的意味。没有一代思想家如费希特、洪堡、施莱尔马赫等人的开创性办学理念以及亲力亲为,恐怕不会有当时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而没有受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启发而主导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创办与改造的众多传奇校长,如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芝加哥大学的哈珀、康奈尔大学的怀特以及进入20世纪后的MIT校长康普顿、副校长布什,斯坦福大学被称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特曼等,恐怕也不会有如今依旧处于鼎盛期的众多美国研究型大学。因此,特定时期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想、开拓实践的意志、纵横捭阖的领导策略对一流大学建设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他们不仅塑造了研究型大学本身,甚至影响政府政策导向,缔造了一个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传统。对外不遗余力争取资源,不断吸纳卓越人才;对内尊重学术自主与自由,为富有好奇心、勃勃雄心的人才创造事业发展机遇与空间,是具有卓越领导力与号召力的传奇校长共性特征。因此,如果从实践逻辑角度来审视,一个具有开创性且深谙和尊重学术规律、拥有强大外部公共关系协调能力的领导核心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首因,也是围绕上述事项确立有效治理结构的首要环节。
因此,化繁为简,回归常识,在当前双一流特殊境遇中,我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的关键点在哪里也就一目了然,即领导体制是核心。
结论五: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五,有远见与高效的领导核心与相应体制是关键。
最后,或许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领导不是专断、治理不是管理,目前普遍流行的规划导向、绩效取向、指标关注所体现的是管理活动的逻辑,而未必符合学术组织运行的逻辑乃至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或许能够达到数量提高的目的,但是,对真正的学术创新却可能有巨大的隐患。一流大学所谓的善治,应该是管理逻辑服从学术活动规律,而非凌驾其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阎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