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xtquestion(ID:gh_2414d982daee),翻译:Vicky,审校:Jiahui,编辑:EY,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你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可以肯定地说你拥有意识。意识是一种魔力,它让你知道自己清醒地活着,知道你就是你,而非别人。意识,是冬日里松木的冷冽清香,是蓝色带给人的纯净忧郁,是初吻的青涩回忆,也是一场卓越的表演带来的震颤——是所有可量化的体验,那样丰富多彩而又不可言喻,正是这样的体验赋予生活生存的意义,像是一根丝线,穿梭在时光之中,将一个又一个瞬间编织起来。
但是,我们也许都非常熟悉意识的感觉,要解释意识为什么存在或是其背后的物理和生物原理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古老的问题,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可是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仍未找到肯定的答案。纵观历史的长河,探讨意识的本质大多数时候是哲学家和诗人们涉足的特有领域。它一直没有被当成一个合理的科学论题,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相关实验太难了,在当时几乎不可能。但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一情况改变了。神经科学家们开始推进相关科研,以了解意识相关现象背后的神经机制。
这其中有两位神经科学家,虽然生于不同年代,但都对阐明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便是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和阿尼尔·赛斯(Anil Seth)。达马西奥现年77岁,曾出版过《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和《万物的古怪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等书籍,他在这些书中探究了感觉、情感和决策的神经基础。赛斯现年49岁,他阐释了感知体验背后的大脑机制,尤其是视觉和自我体验,并因此在神经科学领域留名。
去年晚些时候,两位科学家都出版了新书,进一步深入拓展他们对大脑和意识的探索。在《做你自己:一门新的意识科学》(Being You: A New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一书中,赛斯提出了一个理论:“可控的幻觉(controlled hallucination)”。该理论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体验是大脑在一个预测系统的支配下创造出来的,这证明意识与身体内部密切相关。在《感与知:让“心”有意识》(Feeling & Knowing: Making Minds Conscious)一书中,达马西奥试图揭开意识神秘的面纱。他认为,身体与精神的互动过程,是从包括疼痛和饥饿在内的原始感觉演化而来的,是由内脏深处的化学反应产生的。
我们邀请到两位神经科学家进行了一次线上视频对话,请他们分享各自对意识的看法、互相提问,并让他们打赌我们最终能否解决意识——这个神经科学领域最难的问题。
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你们各自新书的标题。安东尼奥,你新书标题里面的“感与知”是什么意思?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我认为人类没有感觉,就不会拥有意识。内稳态感觉,比如饥饿、口渴、疼痛或是幸福是天然且自发的意识,否则它们对我们而言就不具有任何价值。而“知”实际上来源于“感”。这种本能的知觉帮助我们管理生活。比如,如果你感到疼痛,便会基于这种感觉采取行动,它会告诉你想要活下来,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这就是我想要在书中用尽可能少的笔墨阐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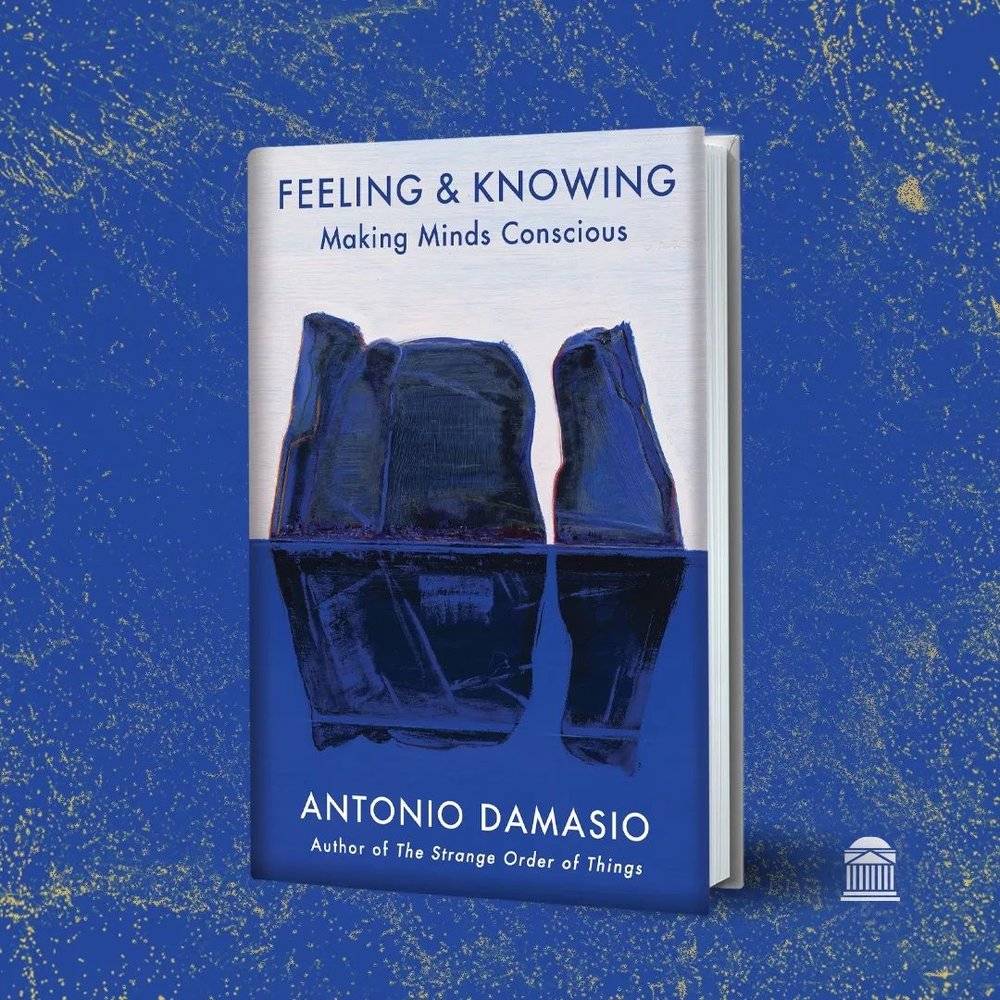
问:阿尼尔,你新书标题中的“做你自己”是什么意思?
阿尼尔·赛斯:长期以来,我的工作主要聚焦两个方面: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一方面来说,视觉是可供测试的最简单形式;然后是自我和情感,后者很大程度是受安东尼奥研究的启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理解做自己意味着什么。童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呢?”,“我死后会发生什么?”,“我的世界跟别人一样吗?”。我想,这些是大家都会问到的基础问题,随着我们渐渐长大,通常又会忘却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让我们不再发出此类的疑问。所以,我想让大家重新关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上做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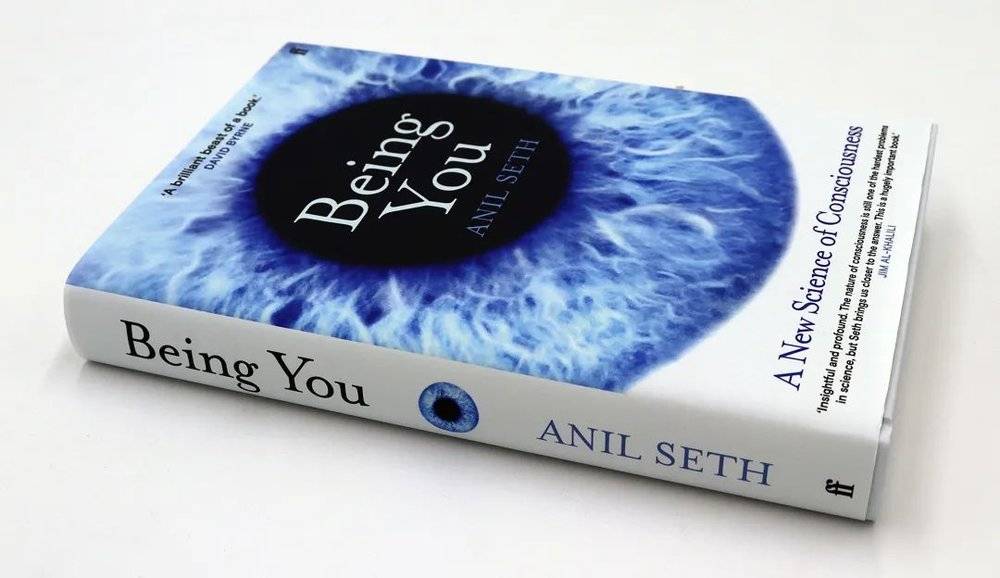
问:很显然,有一点是你们两位都同意的,那就是:意识是一种具身化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有生物意义的躯体才能拥有生存于世那些不可言说的体验。这种心灵与物质关系的再定义相对较新,安东尼奥对此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你们在各自新书中,却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了这种具身化的观点。身体在意识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达马西奥:如你所知,《感与知》这本书是应我编辑的要求而写的:创作一本书,以一种简短精悍、易于理解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在新书中讨论的许多观点,与我之前写的《万物的古怪秩序》一样,但有一点是新的:感觉和意识的混杂性。我的意思是,跟视觉这种直接的感知类型不同,这类感知大多是单向的。而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是通过身体内部信号与神经系统信号混合产生。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意识大多仅依赖神经系统的处理,而并非如我所提出的,是神经与身体交互处理的结果。
赛斯:我的最终结论与安东尼奥相似。我还同意其它的一些观点,比如我们作为生命系统,意识是根植于我们的本质之中的,根植于最基础的生物层面的必要性,让我们得以日复一日的生存下来。但我在《做你自己》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观点:我认为感知体验中的所有事物,包括自我和世界,都是基于大脑做出的多种预测,我称之为“可控的幻想”。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外部世界,还是在身体内部,我们从未感知过客观现实的“真实性”。相反,我们的大脑从身体内部和周遭环境中接受信号,然后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预测,以判断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然后,这种从上至下的预测会不断被大脑更正,因为大脑接收到了更多感官预测的误差信号。这一观点历史悠久,19世纪时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当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 von Helmholtz)认为,视觉感知是大脑做出最佳猜测的过程,是大脑对于外部环境的推断。

达马西奥:阿尼尔,你刚刚所说的话,即便你的预测机器没有马力全开的运作起来,意识仍然会出现。假如你有一种评估体内信息的方式,那么无论有没有进行预测,你都会有意识。所以,我在想预测成分在意识的实际体验中增加了什么呢?
赛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的假设是,无论是与世界还是自我相关,意识的内容都是由从上至下的预测来承载的。所以,预测不仅仅是丰富了意识体验,更是生成了这些体验。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大脑中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最小的预测系统?
对我而言,这个系统涉及大脑编码其世界和躯体的生成模型,该模型能够生成有关感官信号的预测,而这些感官信号可以根据感官数据进行校准。那么,意识体验是否需要此类生成模型,又或者其他更为简单的脑身互动形式就足够了,就便是经验之谈了。安东尼奥,我感兴趣的是你会用怎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些概念,描述基于大脑的预测和生成模式。比如说,你用“图像”一词来描述信息的感官模式,这些信息是“最丰富的心智组成部分”。这也许会跟我刚刚的观点有所共鸣?
达马西奥:我毫不怀疑预测在我们的心理活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们是意识生成的必要条件。
安东尼奥,你刚刚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你提到感觉是意识的核心,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意识。阿尼尔,你同意吗?
赛斯:我也相信感觉和情感对生命调节和意识体验的过程来说极为重要,但是我想确认我理解了安东尼奥的意思,他说感觉是“自发的意识”,因为我知道该领域有很多关于有些情感是不是或者可以是无意识产物的讨论。我认为,从概念上来说,意识流露背后可以调节身体和引导我们行为的预测控制机制尚且留有一定空间。
达马西奥:为了避免混淆,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区分感觉和情感。我对“感觉”的定义相对严格,我认为“感觉”主要是与给定有机体中生命调节的状态相关。我所说的“内稳态感觉”,包括饥饿、口渴、疼痛和幸福感等,就是突出的例子。感觉是主观的体验,但我认为情感却大不相同。情感是体现在我们脸部和身体上的行为合集,同时可以被他人察觉。情感是公开的,喜悦、恐惧和愤怒都是突出的例子。所以说,有可能拥有无意识的情感吗?我认为不可能。
赛斯:是的,我在书里写道,我认为有一系列的情感可以被认为存在于感觉和认识之间的过渡区域。举例来说,根据您的定义,悲伤是一种“合格”的情感,但是我相信它也可能存在于感觉的领域。这是一种非常内在的东西,可能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被表达出来。但是,失望却更有可能是实打实属于情感领域的,因为它要求大脑的期待值高于实际结果,这种转折更为复杂。我们人类也会感到悔恨。我们甚至可能有预期后悔的情绪,这为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的层级,也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水平。
问:你们认为这些更为复杂的情感状态代表更高或更复杂的意识“层级”吗?
赛斯:我个人非常怀疑这种标签化的做法,也就是把意识标记为更高和更低的层级。这其中当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除非我们同意,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比蚂蚁更有意识。我们漏掉了有关意识本质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为了让这个观察具体化,像对待气温那样对待意识,并且认为“有一个单一的意识尺度,占据从绝对零度到某个数值之间的范围,”,我认为这种类比太过了。当我们想到婴幼儿、成年人和其他动物中的意识可能性时,这确实很重要。婴幼儿和非人类动物也许在某些维度更缺乏意识,比如心理时间旅行的能力,又或许是类似悔恨的体验。但是,他们可能在别的方面更具有意识。也许他们感知环境的即时存在可能会更加生动。
通俗来讲,人们也会把诸如迷幻状态或是冥想状态之类的状态认作是意识的更高层级。但是,这是一种社会性解读,充满了道德和伦理价值。我认为意识是一种多维度的概念。
达马西奥:我完全同意阿尼尔。当人类谈论意识的更高层级或是对于外部世界意识的提高,这确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大家在谈论非常不同的概念,更为混乱了。

问:大卫·查默斯于1995年提出了意识的困难问题——物理基础为什么以及如何生成体验的。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一直困扰着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阿尼尔,你在书中表示,困难问题是理解意识的错误方式,并且认为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你所说的意识的“真正”问题上:解释为什么大脑活动的特定模式或是其他物理过程会映射到某种特别的意识体验上。安东尼奥,你如何看待“困难”问题的框架?
达马西奥:我认为阿尼尔对困难问题的描述非常嘴下留情。我就没有那么宽容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是制造困难的阻碍。我认为困难问题的框架使得我们无法通过生物学来解释意识,甚至无法就解释它的必要性达成一致,这可能是人们目前对泛心论着迷的原因。你同意吗,阿尼尔?
赛斯:我认为困难问题很好地将有关意识的常见直觉正式化了。但是我也确实认为它的框架阻碍了相关理解的进步。从表面上看待困难问题确实会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认同一些相对极端的形而上学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
泛心论(panpsychism)便是其中一种:该理论认为意识是根本且普遍存在的。对我来说,泛心论最主要的问题是其定义几乎不能产生任何可验证的预测,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某个问题取得循序渐进的科学性进展,那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非常徒劳无益的。
另外一个极端的形而上学立场是幻觉主义(illusionism),有些人认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意识并不真正存在,至少跟我们想的不同,根本没有所谓的意识“问题”。尽管我发现幻觉主义的极端说法与泛心论一样难以下噎,它还有一些更为温和的观点是有用的。比如,当我们解释意识时,我们可能对试图解释的到底是什么过于天真了。
问:安东尼奥,你能进一步说说为什么你认为困难问题是一种“阻碍”吗?
达马西奥:困难问题让解释意识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的。它并没有给你提供任何出路。我们拥有的每一点证据都证明宇宙的奥秘逐渐通过科学得到了解答。我看不出意识到底有何不同。我认为,我们现在能有意识,我能知道我在跟你说话并且能看见屏幕上你的面庞,你同样也可以,这一切成为可能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与情感相关联。它是一种感觉,彻头彻尾的感觉,是我的有机体内生命延续的感觉。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一核心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在大脑皮层以下的层级生成的。然后,它才被我们的大脑皮层所感知,主要是通过某些皮质下的结构,比如丘脑和海马体。意识过程的本质实际上比人们想的更简单。其实并没有什么困难问题。
问:人有可能拥有无意识的情感吗?我认为不可能。
赛斯:我同意你的部分观点。我认为,理解意识所面临的挑战有时比想象的简单。只需要将研究意识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对比,后者现在正向着拉格朗日点(Lagrange Point)*进发,目标是为宇宙中一些早期发生的事件进行观测,包括最初几个星系的形成。这样疯狂的科学探索,可以说是工程史上的壮举,因为要获得早期宇宙的数据是非常困难的,更别说要进行可控的实验了。回到意识上来,大脑要比宇宙更触手可及。它就长在人身上,大小刚刚好。我们可以给人注射麻醉剂,意识会消失然后又恢复。我们可以给人吃致幻剂,意识会发生变化,然后回归正常。在某些方面,研究意识是一件非常可行的事情。
*译者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加拿大航空航天局联合研发的红外线观测用太空望远镜,为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继任者。现已成功抵达第二拉格朗日点(L2)。
但是我也不认为会那么简单,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意识的相关数据是私密且主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的科学是不可实现的,只是相关数据会比较难采集。其次,不可否认,困难问题具有直觉性的吸引力:确实,意识似乎并不是那种可以通过物理过程来解释的事情。但实际上,一些现在看上去很神秘的事物并不意味着会一直保持神秘。我采取的办法是逐个攻克意识的属性,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可怕的大谜团。这意味着要去分解而不是解决困难问题。聚焦情感和感觉非常有帮助。
我强烈赞同安东尼奥的观点,即所有人类意识都有一个核心的情感基础:我们是通过或者因为活着的躯体,才能去感知周围的世界和身处其中的自己。但我们该如何进一步解读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只有生物才能具有意识?这种哲学立场被称为生物自然主义。有些人甚至会进一步说,所有生物都具有意识,即生物心理学(biopsychism),它是泛心论在生物学领域的体现。但我却看不到其中的合理解释。
我认为,相比寻常的科学解释,大家倾向于对意识科学抱有更高的期待。这是因为我们要试图解释自己。在量子力学或物理学领域,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成功的理论可能是违反直觉的。但不知为何,我们期望意识的解释是完全直觉性的。
达马西奥:我们都知道意识的作用:它让我们能够将感知、观点和计算与一个特定的有机体联系起来,这个有机体属于我自己。它将我的心智“置于”我的身体之中。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关键之处在于内稳态感觉的延续性,包括积极的、消极的还有中性的感觉,以及与它们自然相伴的事物:对生命有机体持续且自发的识别,将这个有机体认定为心智发生的“地方”,换言之,一种意识体验。
当然,我很清楚,还有许多细节尚未厘清,但我不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比如,为了产生感觉,我们需要外周神经、脊髓和脑干神经节(例如三叉神经节),还有脑干核心里的多种核(例如臂旁核)。我敢打赌,感觉的基础要素实际是从神经系统的这些组成部分产生的过程中获得的。

问:这为我接下来想问两位的问题开了个好头,请问你们是否愿意打赌,意识最终可以得到解释。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跟大卫·查默斯用一箱好酒打赌,赌科学家们能够在2023年前识别出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预计,21世纪末我们便可以解释意识了。安东尼奥,你刚刚说你敢打赌,我们将发现某些脑区生成了意识的基础要素。所以我在想,如果你在跟人打赌,赌我们是否能够以及什么时候解决意识的难题,你会拿什么做赌注?
赛斯:很多人打这种赌,输了很多瓶酒!
没关系,我确定要打赌!
赛斯:虽然大家都不爱听,但我会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看情况。有时甚至要看是哪一天。有些日子里,我早上醒来,意识似乎前所未有的神秘。其他时候,我听到学术圈的人说:“我们完全不了解大脑是如何生成意识的,”这让我很是生气。在了解意识与神经解剖学和生理学之间的关联性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科学进步,尤其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刚刚安东尼奥也已经解释过了。我非常乐观地相信,我们将会继续探索发现,了解更多。而我们对意识抱有的各种问题也会进化。我不觉得我们会顿悟,有人会说这就是答案,只需要做这一个实验,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各回各家了。
问:如果可能性和资金没有任何限制的话,你们会设计什么样的实验?
赛斯:科学总是与现有技术同步发展。其实不仅是意识相关研究,在神经科学领域我们仍然缺乏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以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去测量大脑活动,无论何地都可以同时进行测量。
以上三个目标,我们通常可以实现一个,有时可以实现一半。虽然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未来最有趣的一些实验可能是那些互相攻击的意识理论。我们目前已经发现了一些这样的理论。有一个叫做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lobal workspace theory),认为皮质网络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传播信息时便会产生意识。还有一个高阶思维理论(higher-order thought theory),认为意识就是脑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征其它脑区中的活动。
有些理论是以情感为基础,像是安东尼奥提出的。还有些是以预测为基础,我所提出的理论便是其中一种,跟安东尼奥的观点紧密相关。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发现可以裁定不同理论的实验。在物理学领域,当科学家们试图弄清楚相对论是否站得住脚时,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真正对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出了裁决。
达马西奥:阿尼尔,我同意你关于“好日子”和“坏日子”的说法。有些日子很美好,你会发现一个可能帮助解释意识本质的机制初见端倪;但当你感觉糟糕的时候,又会意识到要做正确的实验以验证该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非常复杂。之后又会有一些好日子,我们其实克服了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启发性的发现。比如,我们对于外周神经系统特征的了解就非常了不起。外周神经系统将身体各个部位的信号导向大脑,由此产生了内稳态感觉。我在这个方面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和思考。
又比如脊髓神经节,它将全身的信息传输到中枢神经系统,碰巧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们是直接暴露在血管中流动循环的分子中的。这些听上去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血脑屏障为我们的大脑皮层提供了极致的保护,让其与身体分隔开来:所以,许多分子无法进入大脑皮层。但是你瞧,在脊髓神经节中,所有这些神经元都直接暴露在血液循环的过程中。这实在是太令人惊叹了。
同样震撼的是,我们意识到外周神经系统中的大多数神经元都是由古老的神经元演化而来,它们与负责我们视觉和听觉的神经元完全不同。但这些更为古老的神经元却完全没有被隔离开来。它们没有髓磷脂来保护脉冲的传导,也存在非突触接触的可能性。我相信,神经系统和身体信号的直接混合产生了我之前提到的混杂性。这样的发现给了我希望,我们正在慢慢构建有关感觉的详尽生理学理论,并因此能够去理解意识。
问:我有一个关于灵魂的问题。
达马西奥:天哪。
问:没错,就是关于灵魂。不好意思,阿尼尔,你在书中提出,意识最基础的层级,也就是仅仅只是活着的体验,可以被称为是灵魂的回声。你用一章优美的文字描述了这一观点。你提到了印度教中的阿特曼(Atman)*,对我们最内心深处的本质进行了深思,将之更多视为呼吸而非思想。所以我在想,在你们各自的意识概念中,信仰灵魂是否拥有一席之地?
*译者注:阿特曼(Atman)是古印度梵文中灵魂的意思。
赛斯: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恢复这个概念。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你体内无形的本质,即便躯体消亡,它也可以存活,也许会跳进另外一副躯体中去,又或许会让自己重新实体化,等等。这种灵魂通常与理性和人格同一性相关,但是,还有许多其它关于灵魂的设想,它们与理智和思考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反而与躯体和身体新陈代谢的过程(比如呼吸)关系更为紧密。所以,是的,我认为灵魂确实是在意识概念中有一席之地的,但是更多是那种具身化的、生物意义的灵魂。
问:安东尼奥,你怎么认为?
达马西奥:我同意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说的,灵魂更多是被持续的存在感所捕捉到的,我前面也有提到这种存在的感觉。诸如饥饿和口渴的感觉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暂停一下,仔细观察我们心智中发生的事情,就会意识到“仅仅是活着的感觉”是持续存在的。当这种感觉消失的时候,“你”也会短暂消失,这就是你昏倒或被麻醉时的感觉——意识消失了。
问:这个问题更多是问你,安东尼奥。你既是一个神经科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历史上,这两个领域就意识这个话题争执不断。所以,我想问哲学是如何影响了你在意识方面的立场?
达马西奥:我实在太尊重这门学科了,我觉得自己还算不上哲学家。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哲学家相关的训练。当然,我热爱哲学。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哲学历史上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那么神经科学家们便不能恰当地研究意识。但是哲学家们并不总是会在日常研究中考虑到意识背后的神经科学。这很遗憾,因为神经科学发现了许多明确的事实,可以为相关研究做出贡献。
赛斯:大概20到25年前吧,做一个心灵哲学家,谈论意识,但却不真正参与到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去,是完全可以的。一位对意识感兴趣的神经科学家并不一定要了解哲学,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一切都变了,变得更好了。有些哲学家甚至开始做实验,要想做真正的意识神经科学家,你需要乐于接受从哲学的角度看问题,了解这个领域,并且愿意进行对话。神经科学和哲学之间有越来越深入的跨界,这对意识研究来说前途无量。实际上,哲学、神经科学还有医学和临床科学之间的跨界对话也越来越多了。麻醉师最近才加入其中,与其他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分享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取得进步?我会告诉你,这就是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
达马西奥:正是这样,我同意。
来源:https://nautil.us/whats-so-hard-about-understanding-consciousness-1387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xtquestion(ID:gh_2414d982daee),翻译:Vicky,审校:Jiahui,编辑: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