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译文(ID:stphbooks),原载于2021年第6期《外国文艺》,原文标题:《<沙丘>是“稀饭科幻”吗?》,作者:宋明炜,头图来自:《沙丘》剧照
电影《沙丘》上映之后,又一次掀起了有关科幻文学与影视的讨论。
硬科幻?软科幻?稀饭科幻?当科幻小说日渐挑战文学传统,科幻拥戴者及鄙睨者不自觉间将“科幻性”与“文学性”对立起来。
“这在科幻最初发生的时候,在雪莱、凡尔纳那里原本都不成为问题。”究竟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让科幻与主流文学相隔绝?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大批如阿特伍德、石黑一雄、纳博科夫、麦克尤恩等的经典作家触及科幻?对科幻的傲慢与偏见是否该被弃绝?如何走出科幻与文学两相对立的环套?
2021年第6期《外国文艺》特邀批评家、学者、作家宋明炜撰文解惑——《科幻作为方法:交叉的平行宇宙》。
文章梳理了科幻发展史,呈现科幻性与文学性的争论纠缠,站在文学事实与理论的最前沿提出了启发性十足的观点:科幻性与文学性并非二项对立,当下,科幻已脱离约定俗成的“类型”,变成一种更为普遍的认知、表现、生成世界的“方法”,在叙事深层次上影响着文学领域。另外,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奇观,科幻也成为为小说制造“惊奇感”的力量助推,唤醒了文学发展两个更早时期的精神……
以下为正文:
科幻小说的起源也许非常早;有的研究者——如英国科幻作家、学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将古罗马的希腊语作家卢奇安的讽刺小说《真实的历史》(周作人曾翻译成中文),看作最早的科幻小说,因为其中写到人们在太阳系的旅行。
此后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都有类似的作品偶尔出现,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旨在讽刺政治弊病、思维谬误或是直接对某种流行的写作方法加以讽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幻小说作为最直接体现“现代性”的文类,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和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也是最为广泛的认识,如去年离世的研究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美国学者保罗·K.奥肯(Paul K. Alkon)在两部著作中,就分别将科幻小说的起源放在大革命之后和工业化初期,将有关未来想象的小说起源放在法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期间。
如果将乌托邦小说看作科幻的“亲属”文类,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也是这个文类的起源背景之一,那时候各种真假难辨的游记开始将世界本身变成可以无限打开的“奇观”,地图上充满了不存在的岛屿、大陆、伊甸园以及种种想象中的珍禽异兽。虽然古典时代有《真实的历史》这样的“科幻”作品旨在反讽唯一“真实”的权威意义,但科幻小说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文类,无疑是在大航海时代、大革命时代与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发生并成长得枝繁叶茂。
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文类在美国获得新的文类意义,经过大萧条和二战,在战后进入了犹如超新星爆发一般的科幻“黄金时代”,它以一种通俗化的情节、类型化的叙述,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黄金时代的许多科幻经典之作,如《基地》《沙丘》建立的帝国想象、时空延伸、救世主意识都成为战后美国意识形态的具象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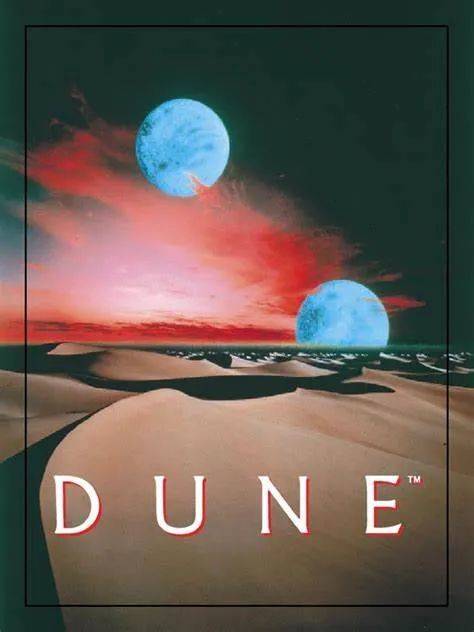
此后又经过六十年代的新浪潮和亚文化运动,科幻元素进入更广泛的美国文学之中,为一些挑战意识形态正统性、热衷于形式实验的小说家使用(如品钦、巴思、冯尼古特、阿特伍德,甚至纳博科夫,晚近在英美各有麦克尤恩、石黑一雄和朱诺迪亚兹这样将科幻作为主题——而非类型叙事——来写作的作家);当然充分类型化的科幻也成为美国的文化主流,为电影电视以及游戏工业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
至此,科幻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以至于当代学者如小伊斯特万·基切里-罗内(Istvan Csicsery-Ronay Jr.)认为科幻小说/影视/游戏如此流行,正在将各种文化产品构筑的世界镜像变成“科幻小说”。
以上用寥寥几百字来勾勒科幻的历史,像是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平行宇宙般的书写时空。这中间不能否认,西方有过威尔斯这样一手写狄更斯式写实小说,一手写科幻以及乌托邦想象作品的作家——晚近的女作家莱辛和阿特伍德也是如此,虽然她们写的已然是恶托邦科幻;而中国也有曾在青年时代热衷译介科幻、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之父的鲁迅。但大体上,在过去二百年中,人们可以为科幻写一部并不包括经典作家(如奥斯丁、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的平行历史。这是一种非主流的文学史书写。科幻作为一种类型,甚至可以独立在将所有其他类型视作总合的文学之外。
甚至,关于科幻是否是文学,也会引起讨论。在有雅俗(或高眉与低眉)之分的读者心目中,科幻是消遣读物,进不了文学殿堂;这种傲慢与偏见,在最近二十年已经日趋显得落伍。但另一方面,科幻性和文学性,在有些维护科幻独立地位的作家和评论家那里,有时候也竟然能够变成一组二项对立。
在国内科幻迷的心目中,科幻“出圈”既是机遇,也是危机。随着科幻小说的文学性越来越强——特别是一批极其优秀的女作家在近年写出“文学性”表达相当精彩的科幻作品,读者开始辨别“硬”“软”科幻(甚至出现“稀饭科幻”这样的说法)。这或许是必然趋势,因为当文类流行起来,越来越多参与进来的作家无论科学“点子”是否有趣、合乎逻辑,首先还是要做一个storyteller,讲故事的人,是所谓虚构作品的作者。
文学性的提高,恰好是这个文类在整体上强化社会关怀、提高审美自觉的表现;此外,本来就是打破界限的科幻,本不该自我设限。事实上在世界范围来看,在中国刚刚发生的科幻“出圈”现象,在美国和英国都早已在几十年前就发生了。
当科幻新浪潮在英国最先出现、随即冲击到美国科幻,乃至于后来不断在世界各地——从盎格鲁风和法兰西风国家到印度、西葡语系国家——出现各种形式的新浪潮变体。如美国本土出现“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出现亚裔科幻作家群体,如刘宇昆提出的在英语语境中具有反对西方中心意义的“丝绸朋克”(Silkpu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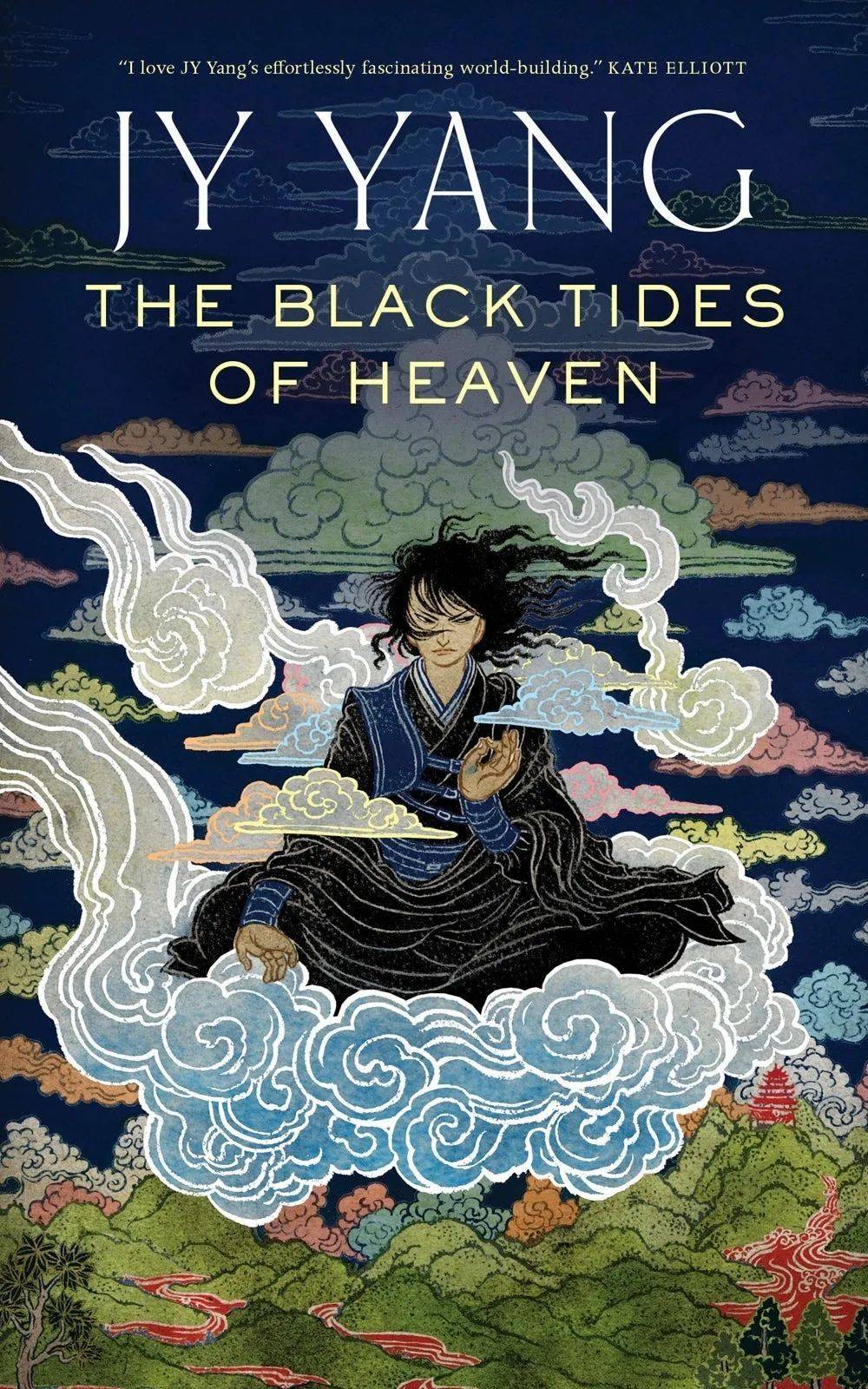
以上所述,其实只是陈述一个很明白的观点:科幻小说是文学,是比非科幻文学更多借助于科学思维的文学,其中科幻性与文学性并非二项对立,这在科幻最初发生时候,雪莱、凡尔纳、威尔斯那里原本都不成为问题;社会关怀和技术奇观融为一体。
历史上科幻与世界文学主流的平行宇宙关系,是美国文化工业内部制造的类型区别,在中国也有其他原因造成科幻与主流文学界过去的隔绝。但我认为,事情已经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幻不仅更具文学性,文学也更具科幻性。
仅以文学史的书写为例,正因为近年来学术界对以刘慈欣、韩松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科幻发生兴趣,导致《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科幻文学纳入其中,在此之前出版的《哈佛新编美国文学史》中也有多篇涉及科幻文学的章节。
在文学领域,我甚至持有一种更大胆的观点。科幻小说作为中国文学最新的前锋,已经开始影响所谓的“纯文学”。不仅有在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作家如骆以军主动借用科幻主题、科幻元素、科幻世界观来重新安排小说叙事,甚至在当代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王安忆笔下,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具有科幻性的时刻,如《匿名》中作者时而拉开镜头、进入外太空视野来反观人间。这并不是说科幻已经成为主流,但这意味着叙事上更深层次的一些变化比文类区分更重要。
我认为,与维护科幻的“纯洁性”或者反过来维护“纯文学”相比,认识到世界/世界文学的呈现与生成方式都正在各个层面获得越来越强烈的“科幻性”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过去二三十年,也正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个阶段看作一个政治、技术、文化转变的关键时间段,科幻从作为消遣读物、大众流行文化的边缘地位,在整个文化场域中转而成为各个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对象,甚至变成一些新型理论发生的基础(从技术美学到认知科学到文学理论到社会学、人类学、新的哲学学派等),这是一个科幻脱离约定俗成的“类型”,变成一种更为普遍的认知、表现、生成世界的“方法”的过程。
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新技术的出现,人类感知和沟通的方式从模拟转向虚拟,从线性逻辑转向空间化感知,从人本中心转向超越人类纪的非二项性思维,技术带来的变革也影响到承载着塑造自我与世界功能的讲故事的方法。如南希·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通过对网络文学、后人类“身体”、“非思想”(unthought)认知的研究,从传统文本研究转向了最激进的科幻思维,甚至认为人类用语言来构筑的文学时代或可能即将终结,未来的文学就像科幻小说那样,是借助于技术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过去的二三十年也许只是一个起点。文学性与科幻性的交融可能会在未来加速发生。
另一方面,过去作为文学最重要的“摹仿”传统,在面对这个时代种种奇观的时候,或许并没有足以制造“惊奇感”的力量。建立在摹仿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上的现代小说,虽然名为“新奇”(Novel本来的意思是新奇),但并不以制造“新奇”取胜,而是将现实“熟化”而后呈现给读者。
作为通向新奇宇宙的科幻,很可能在两个意义上唤醒了文学的两个更早时期的精神,其一是神话,对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 如非常早期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科幻的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即断言科幻为一个宗教消失的时代提供新的神话,而最近如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的地下世(Chthulucene),人类与怪物在残破的世界上相处共生,正是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自我认知的一种新型神话体系。
其二是在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曾制造了第一次全球化文艺风格的巴洛克。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问世之后,就有批评者谓之为“巴洛克”,大概是贬义,指的是形象大于思想,过于变异的表现扰乱了影像秩序。

巴洛克——以及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的新巴洛克文学、电影、哲学——是西葡国家开启航海时代重构世界版图时代的主导艺术形式,曾经广泛影响欧洲、近东、北非、美洲,并也影响到清代的中国。它是一种奇观美学,如巴洛克建筑;是一种对自身形式发生兴趣的元艺术、元文学,如巴赫的音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它也是一种对改变的兴趣大于秩序的物理学和科学思维。
巴洛克在科学上对应的是哥白尼革命,天体物理学失去了古典秩序,但还处在不能确定的时刻,还未在后来的牛顿物理世界重获整齐的秩序,伽利略观测到的四颗木星的卫星是难以安顿的“变化”,是宇宙的奇迹。
巴洛克兴盛时期有一百五十年,但此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始终是主导性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所压抑的附线。但我们很可能——在此时此刻——正处在一个新的巴洛克时代的起点:这个起点,除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各种新宇宙论、新物理学构筑的认知变化上,还更为具象地体现在许许多多的科幻奇观上。如完全没有秩序可言的三体世界(刘慈欣《三体》)、有与无之间处在永恒轮回的深渊状态的医院(韩松《医院》)、跨越了五百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任何体制控制和秩序约束始终抵抗的自由共生的伦理精神(米契尔《云图》)。

也正是《云图》通过六个时代、六个人物(包括后人类)的声音、以对文本自身高度自觉的六种文体,以及六次叙述上的中断和重新连接,在二十一世纪文学初期(2004年出版)呈现出新巴洛克的瑰丽风采,沃卓夫斯基兄弟(姐妹)改编的同名电影(2012年),从电影剪辑方式到成像过程,都具有范式转变的意义,而电影《云图》正与诺兰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其他科幻电影一样,也与沃卓夫斯基姐妹的电视剧《通感8人》和诺兰监制的《西部世界》一样,在从语法上修改影视的叙事——科幻作为方法,让平行宇宙交叉,创造新世界的奇观及其展开的方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译文(ID:stphbooks),作者:宋明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任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教授、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理事,Science Fiction Studies通讯编委。著有中文著作《中国科幻新浪潮》《批评与想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