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为凤凰卫视记者 陈其蔓
我赶到葵涌邨时刚过中午12点,社区内没有什么异样,居民进进出出,有的刚买菜回来,有的背着包正要出门。
当我穿过中心的休憩花园时,看到立法会议员陈恒镔正和同事一起举着喇叭向楼上的居民广播:非必要请勿出门;当前检测人数较多,大家稍后再下楼排队;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快速检测包,投递到每户的信箱中了,有需要请自取……

直到抵达我们采访目的地逸葵楼的楼下时,我依然没有太紧张。彼时,同一座大厦内出现16例感染新冠病毒个案,分布在11个不同的楼层,被专家形容为“超级传播”……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很平静:逸葵楼外的社区篮球场被改为临时检测站,居民在排队等候采样,大家很安静,队列秩序井然。

一位妇人推着轮椅上的老母亲来到检测点门口,却犯了难:进入篮球场要先下四级台阶。这里竟然没有设置无障碍通道,我和同事一起为他们想办法。这才发现,检测点没有工作人员负责指引,门口只有一名维持秩序的保安,对行动不便人士的特殊安排一概不知。最后,同事发现篮球场的后门有一道斜坡,这对母女绕路顺利进场。

这时,特区政府还未正式宣布围封逸葵楼,只要求大厦居民接受强制检测,随后可自由活动。但不少专家已发声,建议立即让大厦居民居家隔离,或全部撤离到检疫中心隔离。
整座逸葵楼有超过2500名居民,需要这么做吗?政府有没有能力做到?我的疑问很快得到了居民们的“答复”。在我采访到的逸葵楼居民中,没有一个人不赞同专家的话。他们甚至主动说,居家隔离也许还不够,能去检疫中心隔离最好,自己一定全力配合。
-“这样不会给你们日常生活造成不便吗?”
-“可是万一我身上真的携带病毒,肯定要远离社区啊,人不能那么自私的。”
疫情让社会面临难关,我却看到了身在其中的市民的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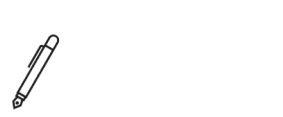
采访工作按部就班进行着,现场连线、采访、写稿,没有什么波澜。直到下午两点50分左右,那个女孩出现了。
我和同事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新闻连线做准备,突然,一个20出头的女孩跑到我们跟前,一开口就问:“你们是记者吗?”下一秒,她突然崩溃大哭,颠三倒四地说着:“我们家对面有两袋垃圾,没有人理我们,我们真的很绝望⋯⋯”我条件反射地想去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先冷静下来,结果,我刚伸出的手,她就后退避开了:“你不要碰我,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
原来,这个女孩家对门的邻居早前确诊新冠肺炎,已经被当局送往医院。但邻居放置在门口的两袋垃圾,一直没有人来处理。前一晚也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场,将确诊邻居的家人接走,送往检疫中心,但两袋垃圾还在原来的位置,确诊者的住所也并未消毒。
女孩一家5口提心吊胆,害怕对门“残留”在垃圾中的病毒会蔓延到自家来,尤其自己家里还有体弱的婴儿。女孩致电过两个相关部门,又与大厦保安反映,但近一天过去了仍未得到处理,焦急之下,她只好趁着下楼检测的机会向媒体求助。
在接下来的直播连线中,我将这件事复述出来,希望相关的负责人能看到。这也是我能为她想到的第一个解决办法。

结束直播后,我联络了一位熟悉地区事务的同事,请她一起想办法。她想到有立法会议员专责跟进公共卫生议题,且当天下午正在与特区政府卫生部门开会议事,立即向其反映了情况。同时,我们也联络了本地政党在当区的社区主任,为女孩提供紧急支援。
两个多小时后,女孩发短讯告诉我,垃圾已经被清走了,并且正在等待专人来对单位进行消毒,我和同事才放下心来。

随着越来越多消息传来,从要围封逸葵楼三天到五天;从楼内16例个案,到至少20例个案⋯⋯再加上与女孩的接触,消息接踵而至,让我们和同事后怕了起来:初抵达时,我们没穿防护服,还到处找居民采访,是否太松懈了?香港此前稳定安逸的一大段时间,也许真的让太多人都放松了警惕⋯⋯
连我们都怕了,身处其中的居民能不怕吗?
晚上,特区政府正式宣布将围封逸葵楼五天,全部居民需要禁足家中。
“逆行者”也出现了。首先是大批警察和工作人员来到楼下,拉封锁线、布置增设的采样点、为禁足居民准备晚餐⋯⋯一位协助检测的护士,已经一天一夜没合过眼了,早上换班回家休息了一会儿,逸葵楼有需要,又来值班了。
居民们也在“逆行”,白天在外上班,傍晚下班得知自家要被围封,没有逃避,去超市买好大包小包的生活物资,然后从容地回到逸葵楼下,走进封锁线,上楼锁门。
一切都是无声的,但是却让旁观者的思绪无法平静。
结束现场采访的第二天,我也去做了检测,阴性。
经过这一天,我已经明白,当我以为我们已经战胜了新冠病毒时,它卷土重来,提醒人类在它面前是多么渺小。
现场也确实也看到了一些差强人意的安排,但是我也认同有位议员接受访问时的一句话:事情已经发生,没必要再过多指责,人永远要关顾未来。
我并不是唯心主义者,但这一次,我还是愿意相信人的意志更强大,大象有力,而蝼蚁亦有慧,我相信香港市民的担当,我相信香港特区政府的进步,毕竟——希望在明天啊。
作者:凤凰卫视记者 陈其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