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三视锥动物,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负责把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进而引起神经活动。所以,当我们说“叶子是绿色”的时候,只不过是因为叶子反射了波长介于520和570纳米之间的光。同样,在面对一个红色苹果的时候,你身边如果有只会说话的猫,相信ta的答案肯定不是红色。
而文章涉及到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则和语言相对论有关,即,人类的观察与思考会受到其所使用语言的限制。这在目前学界仍存在极大的争议。比如在众多不同语言(母语)群体中,不论横向还是纵向对比,对于描述颜色的词汇多少均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为何今天的我们试图通过译本来理解希腊人眼中的颜色有多么困难的原因之一。究竟是“看”决定了语言的规模与格局,还是语言决定了“看”的主观性和选择性,还真不好说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Adam Rogers,原文标题:《如果没有命名颜色,它们还存在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用来描述颜色的词汇,与光的波长或是视网膜的生理机能同样重要。对于色彩的生成而言,我们谈论它的方式和我们实际制造或观察它的方式占据了同等的主要地位。
论及色彩,其相关物理原理是这样的:科学家能够测量光——波的长度和光子的能量。人眼看到的“紫色”光实际上原本并不是紫色的,直到你眼睛后方的某些基于血肉之躯的计算系统把它转换成了神经电信号。在此之前,它只是波长约400纳米的光波。哦,但是,说来不好意思,它也是能量约为三电子伏的光子。
假使我向你谈及“黄绿色”的光,我既可以称它为波长540纳米的光波,也可以说它们是能量为每摩尔222千焦耳的光子。它们是计算同一事物的不同度量标准。
波由光子构成,但光子也是由波构成的。它们真是一团糟,但现实就是如此。区别不在于数学或科学领域。区别存在于方法——和语言。
当人们测定人造光的颜色时,他们则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测量系统和另一组词汇。这即是“色温”(colour temperature),也就是你必须通过加热一个理论上的“黑体”(black body)才能得到这种颜色所需的开氏度。因此,它仍旧是能量,不过又换了个名字。
在火焰中或金属熔融时出现的蓝白色光是最热的,所以,鬼魅般的电子闪光灯的色温可以达到6000开氏度——然而人们把这种光形容成“清凉的”。1893年,白炽灯泡点亮了芝加哥世博会(译者注: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因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年而如此命名),直到最近为止,它仍旧为大多数人的住宅提供着光源,它的色温在2700开氏度到3000开氏度之间,这是一种偏凉的黄白色光,人们却反直觉地称之为“温暖的”。
光,以及我们感知到的颜色——或者说我们的技术能够看到的颜色——也可以用其他术语、以其他方式来描述。量子电动力学所描述的光子和电子的相互作用在谈及颜色时有它自己的说法;研究光如何与粒子和(物体)表面相互作用的科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特殊的术语。但他们谈论的都是同一件事。
这个想法的推动者之一是英国政治家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他想谈谈人们并不常谈起的颜色。
1858年,在格莱斯顿首次出任首相的十年前(他的任期长达四届),他就《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其他作品写作了一套三卷本的分析,题为《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发现,即荷马从不使用可能与英语中的“橙色”“绿色”或“蓝色”相对应的词汇。(荷马的失明可能与此有关,不过格莱斯顿否认了这一点——他甚至不确定“失明”这个词是否恰当,而且不管怎样,“吟游诗人并不会因失明致残,因为他们的作品既不是自己写就,也不需自己阅读。”格莱斯顿写道。译者注:荷马史诗最初靠口传记述)

事实上,荷马史诗中的许多色彩都很怪异。荷马使用了“purpura”一词——格莱斯顿将其译为“紫色”——来描述血液、乌云、海浪、衣服和彩虹这些完全不相干的事物。他把黎明描述为“如玫瑰色的手指一般”,尽管手指从来都不是玫瑰色的。格莱斯顿还重点提及了荷马反复说起的“酒暗色(wine-dark)的海洋”。格莱斯顿写道,荷马用了数个词汇来形容用作颜色表述的“酒”一词,其中有一个的意思是“暗沉的,但多半没有确定的色彩”,另一个则“在火焰和烟的概念之间波动,要么指黄褐色(tawny),要么指的是光而非颜色,并带有闪烁迸光的意味。”
格莱斯顿总结说,这就是一团糟,“它很难与‘荷马对颜色有着精确理解’的假设达成一致。”换句话说,也许古希腊人缺乏的不仅仅是描述蓝色和绿色的语言。也许他们没有那些词语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像格莱斯顿那样理解那些颜色。
没有生理学上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很少有人类缺少能让他们看到蓝色的基因。要说每一个古希腊人,无论男女,都有这种基因缺陷,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假如古希腊人看不到蓝色,那他们为什么要在工艺品中使用蓝色颜料?
更有可能的是,荷马用希腊语的颜色词来描述的是对希腊人来说意义重大的那些事物。教授们喜欢称这种重大意义为“突显”(salience),意思是“文化和个人重要性”。荷马所用的颜色词“porphureos”的词源是昂贵的皇家紫色染料泰尔紫(Tyrian purple),在希腊语中是“porphura”,它是从一种特定的地中海海螺中提取的。它之所以被高度评价,部分原因在于要一万枚海螺才能制造出一克染料。
从化学上来说,泰尔紫与靛蓝色(indigo)类似,色调应该介于暗红色到深蓝色之间,还掺有一些缺氧血液的色彩。对于希腊人而言,它是财富、贸易和帝国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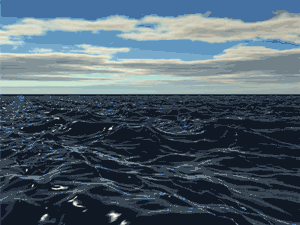
而且,谁能说奥德修斯看到的海洋果真是蓝色的呢?大多数人认为水的颜色反射了周围环境(通常是天空)的颜色。但有关水的颜色,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分子结构——H2O,也就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允许它与其他水分子形成化学键。水体中的每个氢原子都可以与两个氧原子结合,而不仅仅是一个。这些氢键以一定的频率振动,其频率刚好足以吸收红外线和红光,并反射蓝光。
当白浪和泡沫在风中或暴风雨中形成时,它们会散射周围的光线(这让它们看起来是白色的),阻止大部分光线穿透到足够深的地方,海水就不显出蓝色了。最后,海水变成了白色、灰色、黑色——甚至是酒暗色。
对于水——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事物——希腊人看重的是它的“明辉感”、“闪光感”,他们看重的是泰尔紫让织物如丝绸或天鹅绒般闪耀生辉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认为原色之一是“明辉闪光”(译者注: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颜色是世间各物体中流射出来的火,其微粒结构和视线发生反应,形成种种原色,包括透明、白、黑、明辉闪光、红)。
希腊人能看到蓝色,他们只是不在乎。
1879年,小说家兼哲学家格兰特·艾伦(Grant Allen)试图推翻格莱斯顿的假说。艾伦后来成为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先驱,但在此之前,他写过一本早期著作《色觉》(The Colour-Sense),作为著作的一部分,艾伦曾写信给“传教士、政府官员和其他在最不开化的种族中工作的人”。
抛开艾伦此处的种族主义不谈,关键点在于,他给了那些人一张有关颜色的问题清单去提问或回答。他们能区分多少种颜色,或者说,有多少种颜色名称?他们能区分蓝色和绿色,或者蓝色和紫色(violet)吗?他们有像淡紫色(mauve)或混紫色(purple)这样的“混合色”吗(译者注:英语中“violet”指光谱色的紫色,是一种单色,而“purple”和“mauve”均指红色与蓝/紫色混合而成的不同深浅的复合色,前两者在中文通译为“紫色”,此处为便于区分将“purple”译为“混紫色”)?
他们认为彩虹里有多少种颜色?他们使用多少种颜料?他们的每种颜料都有名字吗?他们有没有缺少对应颜料的颜色名称?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可惜艾伦整理的答案并不十分出名,也许只是因为他收集数据的方法杂乱且具有道听途说的性质。最后,艾伦断言,欧洲和亚洲的所有民族对颜色的感知和说法几乎是一样的。南北美洲的原住民也是一样。南部非洲的人们能(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看到所有颜色,但常常缺少表述紫色的词汇。
艾伦写道:“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莫桑比克人没有形容紫色的母语单词,但他学会了荷兰语里的这个词,并正确地使用了它。”几页之后,他又写:“即使是卑贱的安达曼岛民——他们多半是已知的最低等的人类样本——也用红色和白色涂抹他们的脸部。”
换句话说,格莱斯顿的假设是错误的。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颜色。词语的缺失——艾伦理论中的“语言的负面证据(negative evidence)”——并不能证明概念的缺失。
一种较新译本的《奥德赛》解决了这篇史诗的负面语言问题:它直接抹除了问题本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古典学家埃米莉·威尔逊(Emily Wilson)在她的新译本中为荷马的世界填满了色彩。
黎明依然如玫瑰色的手指一般,但是天空有时是古铜色的,特别是当皮洛斯人(Pylians)把黑色的公牛带到海滩上供奉给蓝色的波塞冬的时候。船头漆成了红色。大海有时是酒暗色的,但有时也是灰兮兮的,有时又泛出白来。
这是因为威尔逊知道,古希腊语中很少有词能与现代语言一一对应。古今文化差异着实太大了。威尔逊说,古希腊语中有一个词的含义类似于“妻子—女人”,但并不是指配偶或者仆人。“Dmoos”一词通常被翻译为“奴隶”,但它并不具有和“强迫终身奴役”相同的内涵。颜色也是一样。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翻译问题,而通过使用古怪的英语来假装我们得以贴近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是一种理论幼稚的表现,”威尔逊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有时试图用一些令人惊讶的词语来体现荷马式希腊语中那些令我们吃惊的颜色表述,比如在形容海洋时用‘紫色’、‘靛蓝’,当然也有蓝色,因为此处希腊语的原词涵盖了以上所有颜色。”
艾伦对于颜色的研究成果称得上晦涩,因此遭到了尼采和歌德等哲学家的忽视,因为他们的想法与格莱斯顿大致相同。一个人在缺少词语来形容某事物时就无法想象该事物,这一想法被证明是非常棘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和消防安全检查员,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

19世纪早期,法国神秘主义者安托万·法布尔·奥利维特(Antoine Fabre d’Olivet)试图在《圣经》中找到隐藏的意义,沃尔夫对他的研究着迷不已,他从中吸取了一个观点,认为希伯来字母不仅仅是一系列声音,而有着更深刻、更隐秘的意义。奥利维特认为希伯来语中有所谓“词根符号”(root-signs),沃尔夫为了寻找相应的证据,首先提出了语言学家后来所说的音位(phoneme),一种语言的基本声音单位——它如同乐高积木一般,是统一所有语言并描述其结构的“原子微粒”。
沃尔夫随后在阿兹特克语、霍皮语(Hopi)和玛雅语中寻找词根符号——他是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博学者。在白天做本职工作的同时,沃尔夫还能以大学教授都会羡慕的速度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他工作到很晚,用优雅的铅笔字写初稿,休息时还在他的机械式三角钢琴上叮叮咚咚地弹奏古典音乐。
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开始在耶鲁大学上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课,其时两人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理论。所有的语言都是彼此关联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文化的结果,而是文化的驱动力。语言本身指导并限制了它们的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
在20世纪40年代《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的一系列文章中,沃尔夫奠定了后来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的基础,即“语言相对主义”。他们认为,你所能说的限制了你所能想的。语法“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再现工具,而本身就是思想的塑造者,”沃尔夫写道,“任何人都无法自由地以绝对公正的态度描述自然,即使在他自认为最自由的时候,他也会受到某些阐释模式的限制。”
“语言支配思想”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核心论点。这句格言让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恼火了几十年。部分原因在于它很难测试。至少,要想想出一个实验来将语言从思想中分离开来,需要找到一些客观的、可测量的东西,它既要是一种在人类感知之外有着自身可验证、可量化现实的事物,也需要是一种完全人为发明的存在,一种语言为之创造词汇的认知构造。
换句话说,也就是颜色。
(原文/lithub.com/does-a-color-exist-if-we-dont-have-a-name-for-it/,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Adam Rogers,翻译:苦山,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