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我记得小学时候班里有个男生,平时说话丝毫没问题,但每次朗读课文的时候总是结结巴巴,当我心里跟着他一起念的时候发现,他总会在一些不应该停顿的地方卡住。有同学课后给他支招儿说,你应该在念眼前这几个字的同时兼顾后面的句子。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朗读是否有些许好转。
阅读障碍,又称失读症,自这个词语诞生至今,公众似乎很少质疑其究竟是否应该被算作一种病症,近年来,学界开始不断出现质疑声,其主流观点认为,并不存在什么阅读障碍,针对它的诊断在科学上是有问题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Sirin Kale,编译:Sue
1
1984年的一天,朱利安·乔·埃利奥特(Julian Joe Elliott)的上司邀请他共进午餐。当时,埃利奥特28岁,正在接受成为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吃饭的时候,埃利奥特的主管提到,他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测试一个孩子是否患有阅读障碍症。孩子确诊了,并开始参加一个名为Data-Pac的项目。Data-Pac是一种新的识字教学方法,把教师将与孩子一一配对,教他们如何读出字母组合。
埃利奥特问他的上司,如果这孩子没有患上阅读障碍症,那该怎么办?他的上司显得局促不安。他说,他还是会让这孩子参与Data-Pac。
埃利奥特觉得这很奇怪,但那时他还尚未出师,又知道些什么呢?1986年,他获得了教育心理学家资格,并开始执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经常需要诊断阅读障碍症。当时,大多数教育心理学家认为,阅读障碍是一种基于神经系统的学习困难。患病的孩子其实是聪明的,他们的阅读和写作困难不能以常理解释,比如智力低下、没有上学或家庭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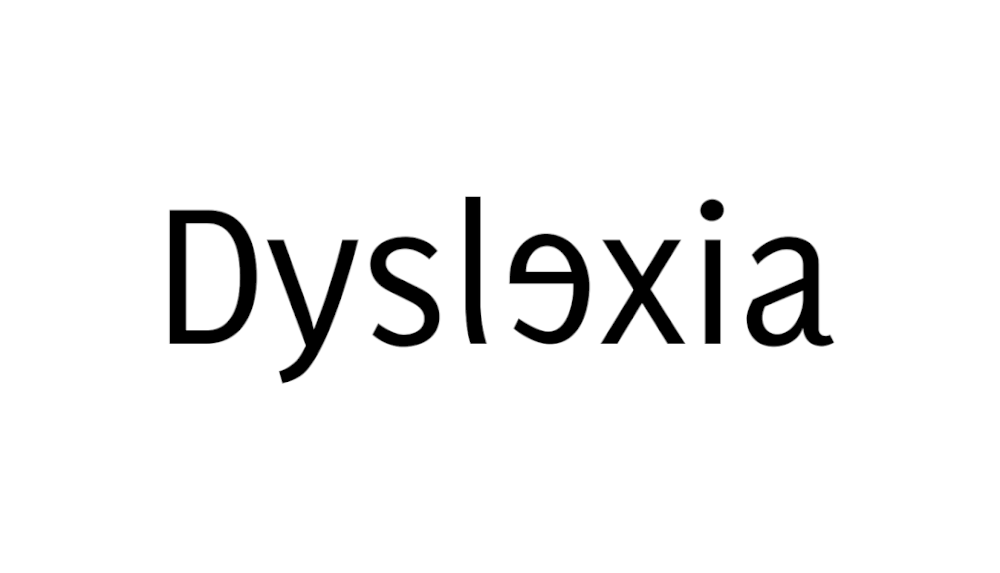
诊断阅读障碍的方法被称为差异模型(discrepancy model)。这个方法很简单:测试孩子的智商和阅读年龄,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比如智商达到平均值或以上,但识字率很低,那么这个孩子就患有阅读障碍症。埃利奥特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方法。他测试的阅读障碍症患童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确存在困难,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其识字困难的症状表现却不尽相同。
不过,那时埃利奥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医生,他把他的怀疑归结为冒名顶替综合征(译者注:imposter syndrome,指患有冒名顶替综合征的人无法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并总是担心有朝一日会被他人识破自己其实是骗子这件事。)的表现。
1998年,埃利奥特与人合写了一本供特殊教育教师参考的指导意见。这本书获得了《泰晤士报教育副刊》年度学术书籍奖的提名。但埃利奥特却坦言,关于阅读障碍的那一章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章很垃圾,真的。我还没有理解它。” 六年后,当出版商要求他更新第二版时,他下定决心要把阅读障碍这一章写好。他现在年纪大了,经验也更丰富了。他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阅读障碍的研究,并开始研读它们。
在他的研究中,埃利奥特发现了一篇令人震惊的论文。1964年,一位名叫比尔·尤尔(Bill Yule)的年轻研究员被派往怀特岛(Isle of Wight)。他在那里对数十名有阅读困难的学童进行了实地调查。毫无疑问,他研究的许多孩子都十分努力地学习阅读和写作。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尽管尤尔后来成为了当时顶尖的教育心理学家,但却始终找不到一种适用于所有孩子的指标模式,而这种模式应该能够汇总成一种叫阅读障碍的病症。在他看来,每个孩子的读写问题似乎都不一样。
埃利奥特记下了尤尔的论文,然后继续往这个方向研究。直到70年代,阅读障碍症一直是解释为什么聪明的孩子不能阅读的一种方式。但是从80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表明,智商与读写能力没有关系。(首批反对阅读障碍症模型的批评发表于1980年,而在整个90年代,更多的论文加入此行列。) 智力和阅读能力是没有联系的,这意味着阅读障碍不能再被定义为只影响聪明孩子的状况。任何智力水平的人都可能是阅读障碍症患童。
埃利奥特窝在书房里,脚边堆满了学术论文,他问自己:如果不能用智商来测试阅读障碍,又该怎么能测试呢?如果尤尔没有找到统一的诊断标准,一种能适用于他研究过的所有阅读障碍症患童的模式,那这还算是一种病症吗?如果不管孩子是否患有这种疾病,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正如他的上司多年前在午餐时承认的那样,那么诊断这种疾病又有什么意义呢?埃利奥特说:“这就是我意识到的。那全是胡扯。”
从那天起,作为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的埃利奥特就把挑战阅读障碍症的当成了自己的使命。他认为,一个阅读和拼写能力不足的人和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本质上没有区别,针对他们的教学方法也应该是没有区别的。他认为,阅读障碍症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术语,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埃利奥特认为,我们应该停止使用“阅读障碍症”这个词,同时,教育心理学家也不再需要去探究明摆着的事实:那个孩子读写能力不足。与之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帮助所有有读写困难的儿童,而不仅仅是那些被诊断患有阅读障碍症的儿童。
埃利奥特并不在意他遭受的争议。有时,人们感觉他反而很享受争议。埃利奥特经常收到恐吓信。一位专业教育阅读障碍症儿童的老师,在看到埃利奥特在一次活动上的讲话后这样形容他:“一个反派角色……我想到了恶霸这个词。”
英国阅读障碍症患童协会(BDA)的公关主管卡勒姆·赫克斯托尔·史密斯(Callum Heckstall-Smith)告诉我:埃利奥特就像一个“否认气候变化的人”。而当我提到埃利奥特时,自由民主党、BDA的主席艾丁顿勋爵(Lord Addington)表示:“他绝对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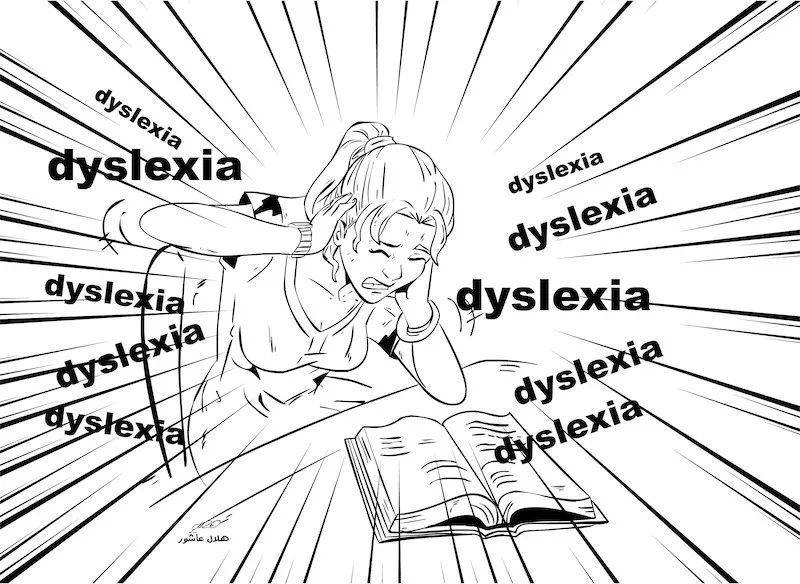
然而,虽然并非所有专家都同意埃利奥特的观点,但事实上,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教育心理学家的支持。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的西蒙·吉布斯教授(Simon Gibbs)说:“我认为,乔并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他和我的观点是,没有可靠的、快速的或简单的方法来诊断阅读障碍症。”
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教育学名誉教授格雷格·布鲁克斯(Greg Brooks)也同意这个观点。2004年,他核查了现有的所有关于阅读障碍症的定义。他说:“没有两个定义是一致的。早在遇到乔之前,我已经得出了和他一样的结论。”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教育心理学教授薇薇安·希尔(Vivian Hill)认为:“乔所做的只是告诉人们科学研究的结果。”今年一月,英国心理学会授予埃利奥特杰出成就奖,以表彰他在阅读障碍症方面的工作。
对埃利奥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准确性的问题,而且他还认为,目前的诊断体系加剧了不平等,因为贫困的儿童往往不太可能被诊断患有阅读障碍症。他告诉我:“阅读困难是真实存在的。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孩子有阅读困难。你知道吗?在贫民区,在公营房屋中(译者注:council house,指在英国,公营房屋是一种由当地政府开发的公共房屋),那里很少有人被诊断出阅读障碍症。”
2
近年来,埃利奥特和与其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在英国越来越有影响力。2018年,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和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地方政府宣布,将不再区分阅读障碍症儿童和有读写困难的儿童。当局出示的相关指导意见这样解释道:“人们普遍认为,阅读障碍的诊断在科学上是有问题的。”
相反,他们会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他们试点采用一种开创性的教育方法,其重点在于教孩子读写英语中最常用的100个单词,这些单词累计占所有书面英语的53%。2011年,在为期一年的实验研究中,该方法在斯塔福德郡的14所小学进行了推广。在一所学校,阅读落后的学生数量在8个月后减少了一半,从60%下降到32%。更大规模的相关研究表明,该方法能让阅读困难的发生率从20-25%降至3%~5%。
尽管早期的试点计划取得了成功,但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2018年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强烈反对。当年十月,BDA主席艾丁顿勋爵在上议院提出了这个问题。艾丁顿勋爵拥有世袭贵族爵位(译者注:hereditary peer,指世袭贵族,英国的一种贵族爵位。全英约有八百个持有世袭头衔的贵族。),他自2011年以来就担任Microlink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自2003年以来从政府获得了1.323亿英镑的合同,为包括阅读障碍症患童在内的残疾学生提供辅助技术。
在随后的辩论中,一位贵族质疑沃里克郡和斯塔福德郡是否“也曾告知当地居民地球实际上是平的,不存在全球变暖这回事”。焦虑的家长打爆了当地阅读障碍症慈善机构的电话,询问他们的孩子是否将不再得到帮助。BDA向《专业教育报》和《每日电讯报》发表声明称,这两个地方政府只是想削减成本。

去年年底,我在艾丁顿狭小的上议院办公室见到了他。他告诉我,当他读到关于这份新指导意见的报道时,就开始关注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这份报道是BDA带给他的。艾丁顿说:“我想,对,这在很多地方都与法律相抵触。”
他觉得,这份指导意见声称阅读障碍症并不存在。“如果你告诉我阅读障碍真的不存在,恐怕我每天的生活经验都可以告诉你,你错了。”(艾丁顿本身有阅读障碍症。)我说:“我并不觉得阅读障碍症不存在。”在我们的谈话中,艾丁顿说,在公关说客们取消他们的政策之前,他没有和有关地方当局,或者学校试点背后的研究人员谈过。他解释说:“我公开批评他们,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当我坐在这里,而且我在议会中有一席之地,我会遵循自己的判断。”
上议院的辩论,尤其是那句关于“地球是平的”的言论,在英国教育心理学界引起了震动。伦敦大学学院的名誉讲师乔纳森·索利蒂(Jonathan Solity)气愤地告诉我:“两地的地方政府都没有否认阅读障碍症儿童的存在,也没有表示被贴上阅读障碍标签的孩子不值得关注。他们只是想帮助所有有读写困难的人!”
正是乔纳森·索利蒂的研究为沃里克郡和斯塔福德郡公布的指导意见提供了基础。2019年1月,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的后续活动中,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团队为他们的案例进行了论证,近200名教育心理学家参加了活动,还有数千人在线观看。这是教育心理学这个小圈子的重大事件。
然而,到了2019年底,斯塔福德郡已经放弃了这项指导意见,而沃里克郡也在进行审核。(两个当局者都拒绝就本文与我交谈。) 这是英国地方当局有史以来第一次尝试抛弃阅读障碍症,而且失败了。但这也是一场罕见的公开小规模冲突。
过去20年来,这场冲突一直在英国各地的教室、演讲厅、专设委员会听证会和特殊教育需求法庭上悄悄地进行着。一方是由学术界和地方当局的教育心理学家组成的新兴团体,推动教育工作者放弃他们认为在科学上含糊不清和具有社会排斥性的阅读障碍症定义。另一边是阅读障碍症的倡导者,由一些学者和阅读障碍症儿童的父母组成,他们大力维护阅读障碍症,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已经帮助数百万儿童获得支持和理解。
双方都坚持己见,常把对手刻画成无情的官僚主义者,决心剥夺阅读障碍症患童的急需的支持,又或者是焦虑的父母,决心为他们的后代争取利益。珍妮丝·爱德华兹(Janice Edwards)在《阅读障碍症的伤痕》(The Scars of Dyslexia)一书中写道:“如果你想引起一场学术骚乱,只要对着一个挤满教育心理学家、各种教育‘专家’、政治家、教师和家长的大厅大喊‘我们来讨论阅读障碍吧!’。然后优雅地退场,看着混乱开始。”
当我把我正在写的那篇稿子告诉格雷格·布鲁克斯时,他发出了长笑:“你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可怕的争议,可怕的混乱。”后来,他发来电子邮件:“祝你好运……做好被丢臭鸡蛋的准备吧。”
3
人是不可能光靠自己学会读书写字的。与说话或走路不同,读写必须有人教才行。在英国,大多数人在7岁之前都能学会阅读和书写,约有20%的人难以达到这一水平,其中约有一半的人被认为患有阅读障碍症,但不一定确诊。
阅读障碍患者可能会在看一篇文章时跳过单词,或者把字母换来换去。写作时,他们有时会摸索着想用的单词,但又拼不出来,所以会选择较短、不精确的替代方案。对于有阅读障碍症的学生来说,书籍并不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而是一扇不断在他们面前关上的门。

阅读障碍症一词的原意是“文字困难”。这个词是由德国的一位眼科医生鲁道夫·柏林( Rudolf Berlin)于1887年创造的。因为当时鲁道夫注意到,他的一些病人在视力测试中阅读印刷文字时很吃力,这使他推测他们的阅读障碍可能由神经方面的原因引起。在19世纪末,研究人员将阅读障碍症定义为一种只影响智力正常的儿童的疾病。这种迷思一直持续到今天。
当比尔·尤尔刚从研究生院毕业,来到怀特岛时,学术界已经知道有一定数量的孩子患有持久的、无法解释的阅读困难症。在尤尔检查过的怀特岛孩子中,有3.7%的人符合上述标准。但这些孩子都没有相同的症状。从那时起,诊断阅读障碍症时遇到的弹性空间,就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
牛津大学的玛格丽特·斯诺林在《阅读障碍症简介》(Dyslexi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写道:“阅读障碍症这个概念的核心问题在于,它不像麻疹或水痘,不是一种具有明确诊断特征的疾病。”她建议,把阅读障碍症看成类似于高血压的疾病可能会更有帮助。高血压的诊断并没有精确的分界点,只有一个会令医生担心的范围。
整个20世纪下半叶,对阅读障碍的认识逐渐从学术期刊中渗透到公众意识中。1963年,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成立了文盲中心(Word Blind Centre)。那里汇集了一批语言治疗师和心理学家,首次尝试在英国系统化地提供阅读障碍症的治疗。
研究人员桑迪亚·奈都(Sandhya Naidoo)在1972年发表了对该中心的儿童的分析报告。报告发现,患者绝大多数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前牛津大学英国阅读障碍症档案馆的研究员菲利普·柯比(Philip Kirby)写道:“和现在一样,在较富裕的社会经济群体中,有较高比例的儿童被诊断患有阅读障碍症。”
随着人们对阅读障碍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加深,患者的家人们致力于为阅读障碍儿童提供法律保障。随着2014年《儿童与家庭法》(Children and Families Act)的出台,家长可以申请公共资金,将孩子送到专门针对阅读障碍症学生的私立学校就读。与之相关的案件由专门研究教育和社会关怀问题的法官负责的一级法庭进行监管。
有了确诊书,这些法律权利更容易实现。于是,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涌现,以满足持续增长的家长为孩子寻求阅读障碍诊断的需求。私立教育心理学家,辅导老师,律师……所有人都愿意为你的孩子诊断出阅读障碍,为他们争取权益,前提是你能支付得起他们的费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被诊断为阅读障碍症的孩子,与确诊的孩子之间出现了差距。2019年,一份来自研究阅读障碍症的多党议会小组(译者注,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全党议会团体是英国议会中的一个团体,由来自所有政党的议会成员组成。)的报告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诊断为阅读障碍的可能性较小。(大约50%的英国囚犯有读写困难,但其中几乎没有人被诊断为阅读障碍症。)
根据2019年的报告,对于被诊断出患有阅读障碍的孩子,近一半的受访家庭平均每年花费1000英镑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克服阅读障碍。私立的阅读障碍症学校往往位于较富裕的地区,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海伦·阿克尔阅读障碍症慈善机构(Helen Arkell Dyslexia Charity)网站上列出的13所阅读障碍症专科学校中,有一半以上位于英国最富有的两个郡——伦敦或萨里(Surrey)。没有一间学校位于英国最贫困的10个郡。
不管是阅读障碍症的倡导者,还是希望取消这个词的人都认为,这种不平等是一个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BDA的主席海伦·博登(Helen Boden)主张在英国所有学校配备专门的阅读障碍症教师,并对所有儿童进行阅读障碍症筛查。博登告诉我:“目前,那些不能为自己战斗的人只能听天由命。这是不对的。”

4
即使对那些有能力的父母来说,这个过程也是残酷的。克丽丝拉·戴维斯(Chrissla Davis)是一名护士顾问(NHS的最高级别护士),她的丈夫马克是一名保安。他们住在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的威伦霍尔镇(Willenhall)。
为了把他们12岁的女儿谢莉送进一所专门的阅读障碍症学校Maple Hayes,他们花了两年时间,还花费了他们大约1万英镑,这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克丽丝拉的情绪也几乎崩溃。送谢莉上学时,她有时会因为压力而哭。坚强的克丽丝拉说:“这把我们这个家庭搞得四分五裂。”
这一切都始于2016年,当时克丽丝拉和马克聘请了一名私人教师来帮助他们学习较差的女儿。这位教师建议对谢莉进行阅读障碍症测试。2017年10月,谢莉被一位私人教育心理学家诊断为阅读障碍症。测试花费了400英镑。对克丽丝拉来说,结果是可信的。谢莉经常告诉她妈妈她有多讨厌上学,而且还会假装生病不去上课。
2018年3月,沃尔索尔(Walsall)委员会任命的教育心理学家却告诉克丽丝拉,谢莉不是阅读障碍症患者,她需要专门的语言治疗。克丽丝拉说:“我告诉这个政府的教育心理学家,她错了。她把她的博士学位甩在我面前。而我说,‘我才不管你有什么学位。我了解我的孩子。’”
随后,学校与地方政府和戴维斯一家展开了一场三角搏斗。学校先最初告诉克丽丝拉,他们不能满足谢莉的需求,但后来又反悔说可以,这动摇了克丽丝拉的信心。地方政府对谢莉的阅读障碍诊断书提出异议,而戴维斯一家愿意为谢莉进入该学校付出一切。对克丽丝拉来说,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学校提供的教学方法,她还希望谢莉能和与她一样的孩子一起学习。在Maple Hayes,克丽丝拉希望她的女儿能感觉到自己是个正常人,而不是班上的笨蛋。谢莉讨厌上学,甚至威胁要打断自己的腿。
2018年11月,克丽丝拉和马克将沃尔索尔告上了特殊教育需求法庭。他们卖掉了家里的路虎来支付相关费用。在我们的谈话中,克丽丝拉把她在谢莉一案中用的巨形大文件夹摔在我面前。里面记录了克丽丝拉与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每一次谈判,从他们家第一次决定上法庭的那段时间开始,即2018年3月左右。克丽丝拉抄录下了与学校和地方当局官员长达数小时的对话。
2018年12月,法庭做出了有利于沃尔索尔的裁决:一所主流学校足以满足谢莉的需求。但克丽丝拉没有放弃。去年夏天,Maple Hayes让谢莉试入学,看她是否适合学校。克丽丝拉说:“她在那里重获新生。”
因此,2019年2月,克丽丝拉接受了《伯明翰邮报》(Birmingham Mail)的采访,向沃尔索尔施压,要求为谢莉在Maple Hayes的学习提供资金。最终,2019年4月,克丽丝拉胜利了。沃尔索尔同意报销谢莉在Maple Hayes的费用。他们每年要为她支付14,855英镑的学费,到她13岁时,学费会涨到20,115英镑。
2019年12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Maples Hayes遇见了克丽丝拉、马克和谢莉。星期六,学生们去骑马和上课。学校进行小班教学。孩子们学习阅读时使用了学校创始人内维尔·布朗博士(Dr Neville Brown)研发的一种形态学系统,该系统将字母与单个符号配对。这是一种非传统,但有效的教学方法,因为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喜欢用自然拼读法教孩子们读出单词。在Ofsted评级中,该校“杰出”。(Ofsted: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英国政府的一个非部级部门,向议会报告。——译者注)
那天早些时候,我和谢莉在学校露天食堂吃了午饭。谢莉吃着一大碗意大利面,微笑着告诉我,她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大有进步。Maples Hayes的97名学生都是由16个不同的地方当局资助上学的(在他们的父母和地方当局对簿公堂之后)。地方当局每年总共要向这所学校支付至少170万英镑,要知道,学校可不是慈善机构。

在带我参观了一番之后,布朗博士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宠物狗和栗鼠,并向我展示了学校用来识别有阅读障碍儿童的评估方案。但这就是科学家所质疑的那个模型。Maples Hayes的招生说明书甚至明确写出了学校的目标——帮助智商在中等至高水平的孩子学习阅读和书写。我给伦敦大学学院的薇薇安·希尔和纽卡斯尔大学的西蒙·吉布斯发去了一份Maples Hayes的评估方案。他们都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指出智商并不能用于测试阅读障碍。
就读于Maples Hayes等私立阅读障碍症学校的孩子们,他们原本在主流学校里举步维艰,现在却生机勃勃。这本身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在当地方当局的预算本来就难以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的情况下,还需要从中抽取大量资金资助学生上私立的阅读障碍学校。截至去年,14.9%的英国学童有特殊教育需求,这个数字是连续第三年增加了。
随着对特殊教育的需求增长,预算却在缩减。自2010年联合政府上台以来,沃尔索尔的预算已被削减了1.93亿英镑;斯塔福德郡县议会,即Maples Hayes所在的地方,同期削减了2.6亿英镑。吉布斯认为:“如果家长们想把孩子送到像Maple Hayes这样的学校是他们的权利,但地方政府不应该给予财政支持。”
5
每个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但有些父母比其他父母更有资本去这样做。如果你有钱,那么你在法庭上更容易获胜。而法律费用从1万英镑到3万英镑不等。一位专门处理阅读障碍症案件的律师说:“有人曾经这样跟我说,中产阶级的父母有更锋利的武器。他们了解,但不玩弄这个系统,他们能得到足够的信息,从而知道他们的孩子有权获得支持。他们对此志在必得,而且他们很有头脑。”
这位律师告诉我,他的业务以每年25%的速度扩张,他的团队每年接手大约100个阅读障碍症案件,其中败诉的只有两到三个。2018年,德比郡议会(Derbyshire)收到了来自《信息自由法》的请求。其公开出的数据表明,这位律师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迄今为止,在特殊教育需求法庭登记的119起上诉中,地方政府只胜诉了一起。律师说:“越来越多的家长上诉,法庭上的案件太多了。”
在特殊教育需求法庭上,站在这些律师的反方位置的是地方政府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们负责评估他们辖区内儿童的需求。在阅读障碍症患童父母设立的Facebook群中,他们往往被描述为小气的财主,拒绝为患童们提供帮助,而独立教育心理学家(报酬由父母直接支付)则更关心孩子的需求。
Facebook上的一篇典型的帖子这样写道:“我只是不想被搪塞,我想为我儿子的问题而战。”这位家长担心,地方政府的教育心理学家低估了她孩子在读写方面的困难。这群父母的反应是一致的:请来私家的教育心理学家,准备战斗。
但是,这些地方政府的心理学家要审核他们所在区的所有儿童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得不做出取舍,决定哪些儿童最应该获得额外的资源。希尔告诉我,她所处理的两个案件同时提交给了特殊教育需求法庭。其中一个涉及一位单身母亲,住在公营房屋,没有律师代理她的案件。希尔说:“一个孩子还不会说话,有严重的多重学习困难,需要全天候的照顾和上厕所时的额外支持;而另外一个孩子患有阅读障碍症。”
希尔说:“让我震惊又害怕的时,患有阅读障碍症的孩子得到了资源。而另外那位含辛茹苦的母亲得到的帮助,要少太多了。我觉得很奇怪,当地政府把阅读障碍症患童安置在昂贵的地方,却把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可怜的孩子放在一幢高楼的第十三层(西方文化认为数字13不吉利,译者注),和他的单亲妈妈一起。”

我与多位地方政府的教育心理学家进行了交谈,他们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虽然他们对此感到不安,但大多数人害怕引火烧身,即便是在匿名的情况下,也不同意我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看到了发生在沃里克郡和斯塔福德郡的事情,对由此产生的后果很警惕。有一位心理学家愿意对此发表言论。但当他的妻子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她把电话从他手中夺了过来,并挂断了。
最终,我找到了凯蒂,她是伦敦一个自治市政府的教育心理学家,她同意以化名登报。她说:“我所在的不公平的事时有发生,因为我们一半的人口非常富有,另一半则非常贫困。较富裕的父母会向私立教育心理学家和阅读障碍协会支付900英镑,让他们的孩子被诊断为重度阅读障碍症。尽管孩子的得分对该年龄段来说是正常的,但这对这些父母来说还不够好。”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所以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专业诊断书,只要你愿意给钱。他们可以负担得起律师的费用,然后只需在法庭上展示诊断书,就能获得特殊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地方当局每年常常要为这样一个孩子花费8万英镑。
独立教育心理学家一小时的评估费用在300英镑到900英镑之间。私立阅读障碍学校也会给他们送去潜在客户。这些学校会为家长推荐专门处理此类法庭案件的律师。希尔和吉布斯有时会审查由家长在法庭上提交的独立教育心理学家报告。
他们发现其中一些报告令人担忧,因为当孩子们在主流学校获得专家支持之前,这些报告就对地方政府的资源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他们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看孩子对教育干预的反应,然后再采取像强制他们进入专科学校这样的极端措施。
凯蒂认为,中产和中上层阶级的父母实际上是在“榨干特殊教育需求预算”。她认为,由于家长们在网上、在私人Facebook群组和Mumsnet等论坛上分享知识,对特殊教育需求体系的滥用正在恶化。她说:“我从事教育心理学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过大概70次这类案件。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贫富之间的差距。”
同时,她所在地方政府的教育预算也在不断削减。她说:“我们在不断地削减开支!这太不公平了。” 自2015年以来,英格兰的学校预算已经被削减了54亿英镑。
6
在1994年出版的《阅读障碍的伤痕》(The Scars of Dyslexia)一书中,特殊教育需求教师珍妮丝·爱德华兹(Janice Edwards)向我们讲述了她的一个阅读障碍症学生“约翰”的故事。约翰11岁,但他的阅读年龄只有7岁。他在主流学校的经历是暴力的,而且是创伤性的。约翰谈到一位老师时说:“T老师有一次重重地打我。她让我做一件事,我就是做不到,所以她说我很笨。”
在课堂上,约翰感到同学们在排挤他。他告诉爱德华兹:“我很愚蠢。他们都很聪明,通过了11-plus。(译者注,11-plus,指针对英格兰和北爱尔兰一些学生在其小学教育最后一年进行的考试,用于申请中学入学资格。)我连那些该死的题目都看不懂。我讨厌他们所有人。”
他发明了一些方法来隐藏自己的阅读障碍症。因为有时老师会叫学生们念花名册,约翰提前把所有的名字都背下来了。不幸的是,有一次当约翰被要求念花名册时,他把本子倒了过来,全班都嘲笑他,尽管他已经很努力了。
但在11岁被转到一所私立阅读障碍学校后,约翰进步很快。爱德华兹说,当他离开学校时,约翰甚至能够“阅读和理解莎士比亚”。

约翰的故事并不罕见。研究表明,多达20%的阅读障碍症患童经历过焦虑或抑郁。毫无疑问,一份确诊通知书能帮助他们在让人挫败的教育系统中稍稍减少恐惧。”
2019年,一位阅读障碍症患童的父母在对研究阅读障碍症问题的全党议会小组说:“当你的儿子尖叫着想自杀、想自残,并在六岁时反复逃跑,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蠢,这太难了。”阅读障碍症的支持者们常常认为,不管科学家们怎么说,这本身就是坚持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理由。BDA的主席博登说:“关于事情本身的学术争论是好的,但对我们来说,它永远都是关于人的。”
去年冬天,我参加了BDA在特威克纳姆体育场(Twickenham Stadium)举行的年度筹款晚会。当我站在大厅里时,看着晚会的人群到来。穿着闪亮鸡尾酒裙的妇女在身着黑色领带的男士的搀扶下,从Ubers中走出来。人群大多是白人,年龄在30岁以上,房间内的气氛很兴奋,氛围就像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在享受难得的远离孩子的夜晚。
当我们吃着烤羊肉时,一位又一位发言者上台分享自己阅读障碍症的经历。在被诊断出之前,他们认为自己很笨。随着他们被诊断出患有阅读障碍,他们被大家接纳,并进入了一个支持性的团体,那里全是和他一样的人,经历过一样的挣扎,并走了出来。
女团the Saturdays中的成员莫莉·金(Mollie King)说道:“我很幸运,在10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阅读障碍症。想到还有其他的孩子没能确诊,还和我一样觉得自己很笨,我就很伤心。”嘉宾们纷纷点头表示认可。一个18岁的女孩因为她的坚韧而获得了一个奖项。“我想让人们知道,阅读障碍是一种天赋。你不是笨,你是以不同的方式聪明。”她赢得了阵阵掌声。
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斯诺林是英国科学家中最著名的阅读障碍症的捍卫者之一。虽然她批评了埃利奥特的观点,但两人的观点有些相似之处。她说:“我认为乔·埃利奥特的直觉是对的。”
像埃利奥特一样,斯诺林对独立教育心理学家的做法感到震惊。这些专业人士由父母直接支付报酬,以诊断孩子是否患有阅读障碍。她说:“我认为这是一场骗局。不会有医生给出你不想要的诊断。”她也同意埃利奥特的观点,即阅读障碍症患者和非阅读障碍症的人,基本上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学习读写。
然而,在其它许多方面,斯诺林并不同意埃利奥特的观点。她指出,阅读障碍症有遗传性因素的影响。研究一致表明,阅读障碍症患者的后代,更有可能被诊断为患有同样疾病,或患有注意力缺乏症和计算障碍。这表明阅读障碍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处理语言和声音的部分大脑受到了影响。
最重要的是,斯诺林认为,埃利奥特对传统观念的批评是没有必要的。她说,阅读障碍症确实存在,而且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标签很有用。她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的儿子患有诵读困难症。斯诺林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认识的人因为这个问题而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那么我认为他们应该有一个标签。”她指出,贴上这个标签可以帮助人们向自己解释“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蠢”。
但埃利奥特依然不买账。他告诉我:“他们说确诊阅读障碍症是有用的。这样你就可以看着孩子的眼睛,告诉他们,你并不笨,这不是你的错。但那些没有阅读障碍症的孩子呢?他们是懒惰和愚蠢吗?我们应该对每一个不擅读写的孩子说,这不是他们的错。这句话并不需要一张确诊通知书。”
7
有的地方政府则抛开了阅读障碍症学术上的争论,但同样改变了对待有读写困难的儿童的方式。2019年,就在上议院对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进行猛烈攻击之后,剑桥郡(Cambridgeshire)悄然推出了一项几乎完全相同的政策,但它加上了一句重要的声明。尽管剑桥郡的政策并没有区分阅读障碍症患童和正常孩子,但却从来没有把“阅读障碍症”这个词从指导意见中移除。
剑桥郡只是顺其自然,没有卷入政治风暴。如果父母想说他们的孩子有阅读困难症,可以,但这不会影响其教学方式,也不会影响孩子们所能得到的教育资源。BDA甚至支持剑桥郡的做法。
三月,我拜访了剑桥郡议会的教育心理学家乔安娜·斯坦布里奇(Joanna Stanbridge)。她对工作充满热情,并帮助推广了这种新政策。她激情洋溢地说:“不能读和写,这是一种困难。每个人都需要有读写能力,尤其是那些没有特权的年轻人。”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会面。2019年11月,斯坦布里奇和她的同事柯尔斯滕·布莱尼根(Kirsten Branigan)邀请我参加剑桥郡特殊教育需求教师的培训课程。课上,这些教师可以学习如何识别儿童的读写困难,应采取哪些干预措施,如何为儿童量身定制这些干预措施,如何创建有利于阅读障碍的教室,以及如果这些干预措施不起作用,该怎么办。据信,剑桥郡约有1.7万名儿童和年轻人有一定程度的读写困难。
斯坦布里奇决定带我去一所小学。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位受益于新教学方法的低收入儿童。他从玳瑁眼镜后面悄悄地露出了笑容。他自豪地告诉我,他现在开始读“更厚的书”了。在这之后,斯坦布里奇带着我在剑桥郡最贫困的地区芬兰(Fenland)兜了一圈。
她说:“这里主要是农业区。”我们在狭窄的道路上飞驰。芬兰地势平坦,在大片灰色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和棕色的田野。“这里很偏僻。很多村庄根本就没有火车站。因为进出芬兰的交通工具不多,所以没有太多的通行需求。”
斯坦布里奇不是这种新教学方法的传教士。她的母亲是一名阅读障碍症的专业教师,斯坦布里奇打算追随她的脚步,成为一名教育心理学家。她在阅读障碍症问题上没有像保罗归信(译者注,Damascene conversion,《新约圣经》记载,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决定改信基督信仰,成为后世所知的外邦人使徒。)
那样的大转变,也不像埃利奥特对自己的书大刀阔斧地改来改去。而斯坦布里奇稳中有进,在读写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种慢慢改变,而不是像被苹果砸了的牛顿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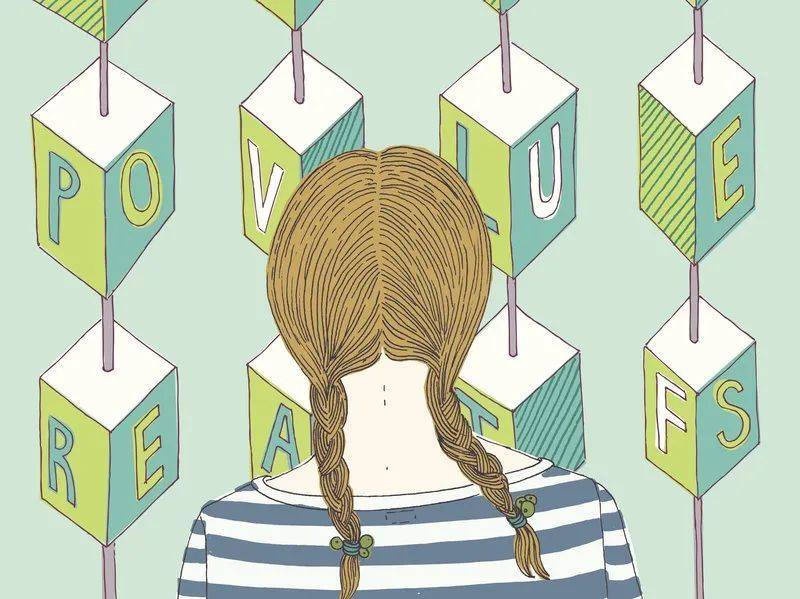
斯坦布里奇说:“在教育心理学家的世界里,阅读障碍症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他们到底有没有阅读障碍症?但我在想,我们应该怎么做?对策是什么呢?这可能是我180度大转变的开始。只是在想,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想,'他们有没有阅读障碍症呢',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
但如果改变真的要来,它也不会来得太快。剑桥郡仍然在付钱送孩子们去私立的阅读障碍症学校。无论改革与否,政府仍然有法律义务履行法庭的判决。如果你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孩子的居住地,80%都集中在剑桥市中心,或剑桥南部,这是郡内最富裕的地区。他们都不是来自芬兰的人。
这全国的缩影。在实施新政策的努力失败后,沃里克郡和斯塔福德郡每年花费约90万英镑将53名儿童送往私立阅读障碍症学校。用同样的钱,他们可以雇佣27名教师。
早在1976年,比尔·尤尔就以如下结论总结了他在怀特岛的研究:“应用‘阅读障碍症’这个标签的时代正在迅速结束。这个标签的作用是,把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在掌握阅读、写作和拼写艺术方面有很大困难的儿童身上,但是继续使用标签会挑动情绪,常常妨碍理性的讨论和科学的调查。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标签依然没有过时。这场阅读障碍的辩论,暂时看不到尽头。
原文:www.theguardian.com/news/2020/sep/17/battle-over-dyslexia-warwickshire-staffordshir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Sue在利维坦发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Sirin Kale,编译:S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