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脏兮兮的砖头在编辑部转了一圈后,整个屋都陷入了黑人问号脸和哈哈哈哈哈。
书名特别简单,且精准:《北京土语辞典》。
是的,这本书里的北京土话,就是特!别!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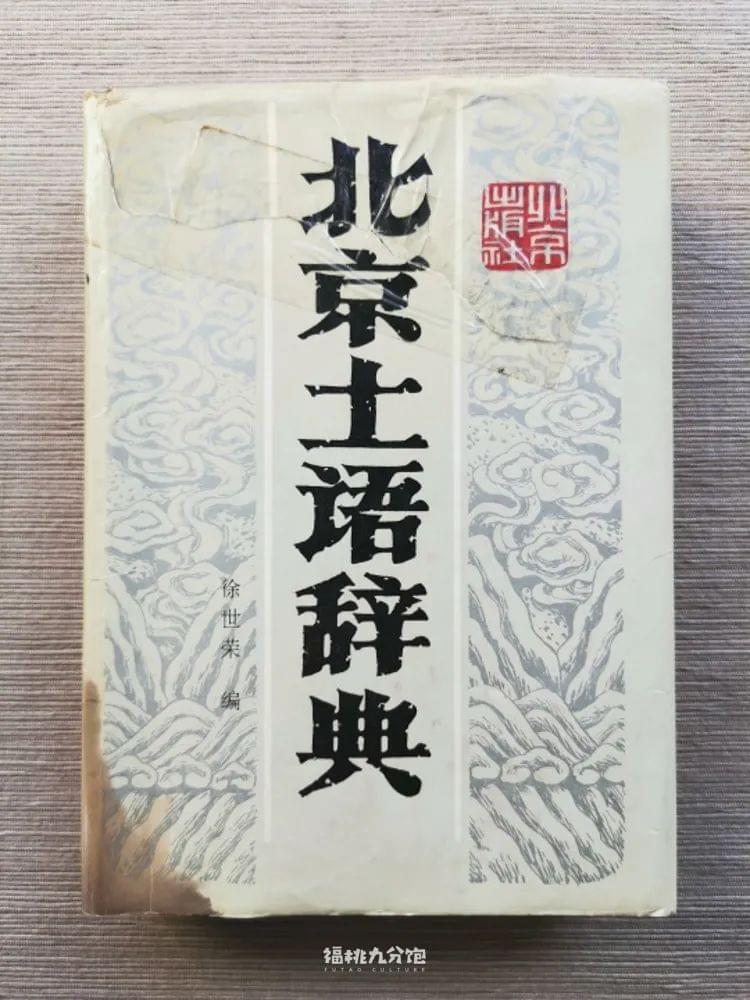 随便一翻,饱弟饱妹们就对北京人的吐槽天赋有了全新的认识。
随便一翻,饱弟饱妹们就对北京人的吐槽天赋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损人这件事上,北京话擅用比喻、象声,还自带引申义,能用一个词儿把一个人骂透,被骂者还浑然不觉,甚至有点儿……饿了。
是的,北京人犯起贫来,满口不离一个字儿——吃!
 当一个北京人在与吃无关的场合,突然吐出一句菜名儿,千万别以为是他饿了。
当一个北京人在与吃无关的场合,突然吐出一句菜名儿,千万别以为是他饿了。他们热爱不好好说话,脑回路里全是比喻,仿佛地球上任何东西,都能比作一种吃的。
北京到底是不是美食荒漠?听他们骂人,就知道了。
茄子
(qié zi)


 用来骂人,且什么人都能骂。
用来骂人,且什么人都能骂。北京人吃圆茄子,那玩意儿又黑又圆,像个蛋,怎么听都不是好词儿——
“我要是骗你,我就是个茄子!”
骂归骂,其实北京人可爱茄子了。炒茄丝、拌茄泥、炸茄盒、茄子干儿焖肉、茄子汆儿过水面,尤其烧茄子,是最讲究的家常菜,轻易不做。
老嫩合适的圆茄子切片儿,正反面打花刀好入味,过油一炸,搁酱油葱姜一炒,临出锅撒一把蒜末儿,嗬!

炸酱
(zhá jiàng)

 © 美食台
© 美食台 北京人要说一样东西“炸了酱了”,甭惦记了,肯定是没了。
北京人要说一样东西“炸了酱了”,甭惦记了,肯定是没了。只有一样财物被人私吞了,才说是被人“炸了酱”,好比三两五花肉,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炸了黄酱黑乎乎油汪汪一小碗儿,人家吃下肚里,你找都找不着。
还有一个词儿叫“软炸酱”,专指人表面温和,暗地里使手段谋财。
炸酱的火候,就是做人的火候,冷眼一看,无非四个字儿,鸟为食亡。
油脂麻花
(yóu zhi má huā)

 © 周末做啥
© 周末做啥 北京人从前爱吃麻花,不亚于天津人,“烧饼油鬼”过去少不了麻花。
北京人从前爱吃麻花,不亚于天津人,“烧饼油鬼”过去少不了麻花。可“油脂麻花”不是一种麻花,而是形容东西沾满了油渍,脏得都花了。
兔头兔脑
(tù tóu tù nǎo)


 其实是骂人形貌狡猾、轻佻、贼眉鼠眼。
其实是骂人形貌狡猾、轻佻、贼眉鼠眼。然而在餐桌上,老北京人对“兔头兔脑”的热爱,也不亚于成都人。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小酒馆“安乐居”,酱兔头就是最受欢迎的下酒菜,可惜如今不好找啦。
髭毛儿栗子
(zī máor lì zì)


 比喻男子头发长而乱的样子。
比喻男子头发长而乱的样子。您就脑补一下,北京摇滚协会副会长于谦老师留了个激流金属大长发,还烫。
 © 《脱口秀大会》
© 《脱口秀大会》锛瓜
(bēn guā)

 © 图虫创意
© 图虫创意 指的是说唱演员表演时偶然忘词或吃字。
指的是说唱演员表演时偶然忘词或吃字。比如,德云社著名锛瓜小能手孟鹤堂。

芥根头
(jiè gen tóu)

 © 图虫创意
© 图虫创意 北京人最爱的咸菜之一“辣菜”,就是芥根头切丝用盐腌,取其天然的辣味,喝豆汁尤其离不开。
北京人最爱的咸菜之一“辣菜”,就是芥根头切丝用盐腌,取其天然的辣味,喝豆汁尤其离不开。而没腌的芥根头,独有一股冲鼻的辣味儿,用来比喻一个人落落寡合,待人态度生硬。
切糕架子
(qiē gāo jià zi)


 切糕,是北京常见的点心。
切糕,是北京常见的点心。不同于以果仁为主料的新疆玛仁糖,北京切糕多以糯米蒸成,中夹豆沙、小枣为馅,便宜大块,要是馅料搁足,口感还真不错。
 © 满妈厨房
© 满妈厨房过去卖切糕的都是走街串巷,携带两样工具:一个木盘,盛着大块的切糕,还有一个活腿架子,有买主就停下,把盘子往架上一搁,现切现卖。
然而,由于架子是活腿的,立起来晃晃悠悠,所以北京人拿“切糕架子”比喻不牢靠的家具——搁切糕还成,人就别往上搁了。

 初来北京吃饭,尤其到老饭馆,大家都会时不时头一大。
初来北京吃饭,尤其到老饭馆,大家都会时不时头一大。明明菜单写的是汉语,老板说的是中文,合一块儿就不明白什么意思,点菜都不敢点。
此时,需要一只饱弟/饱妹拎起书本飞来帮你!
锅儿挑
(guōr tiǎo)

 ▲这个实在无法想象
▲这个实在无法想象 要是去吃面,师傅问你一句“锅儿挑还是过水儿?”别愣,说明这家店态度好,注重口味、认真负责。
要是去吃面,师傅问你一句“锅儿挑还是过水儿?”别愣,说明这家店态度好,注重口味、认真负责。“锅儿挑”和“过水儿”,其实是手擀面的两种吃法:
“锅儿挑”,顾名思义,从锅里挑起来盛碗里,加卤子加炸酱直接吃;“过水儿”,就是捞起面来过一遍凉水再盛了吃。
 © 迷迭香Rosemary
© 迷迭香Rosemary一般来讲,“过水儿”夏天吃得多,降低面条温度的同时,也让面条更加爽滑,尤其北京人夏天最爱的凉面,必须是过水儿。
 © 京城奇珍异物志
© 京城奇珍异物志“锅儿挑”则是秋冬天吃,捞起来直接吃,趁着热乎劲儿,饱腹又驱寒。
像炸酱面,夏天吃一般是过水儿,因为菜码儿都是时鲜蔬菜,小碗干炸一拌,吃个爽快,冬天再吃锅儿挑。
而打卤面,一般来说都是锅儿挑,不然面条过于光滑,就挂不住卤啦。
木须
(mù xu)

 © 《花木兰》
© 《花木兰》 北京人爱给平凡的食物起个雅称,比如“木须”指的就是鸡蛋。
北京人爱给平凡的食物起个雅称,比如“木须”指的就是鸡蛋。从前北京桂花多,也爱吃桂花,而鸡蛋炒出来,是桂花一样的金黄色,桂花别名木樨,所以炒鸡蛋就成了“木樨”,《北京土语辞典》作“木犀”,饭馆菜牌多写作“木须”。
这么麻烦的事儿,谁想出来的?
有一种说法是,过去北京太监多,一听“鸡”“蛋”二字就心疼,于是管鸡蛋叫“木樨”“桂花”“黄菜”,这个称谓才流传开来。
于是,北京最早的“木须肉”就是鸡蛋炒肉片;“醋溜木须”指的是炒鸡蛋和牛羊肉片一起醋溜;晋阳饭庄的“木须炒拨鱼儿”,自然也是鸡蛋炒的啦。
 © 美食台
© 美食台它似蜜
(tā si mì)

 © 《魔道祖师Q》
© 《魔道祖师Q》 要在老字号清真餐厅看到这道菜,放心点吧,羊肉。
要在老字号清真餐厅看到这道菜,放心点吧,羊肉。一种说法是,这名儿是回语音译,《北京土语辞典》里作“他丝蜜”。
 © 北京宏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宏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但还有传说,这道菜是清末伺候慈禧太后的御厨,因为长期没有新菜色,硬憋出来的:
用羊里脊肉,加甜面酱和白糖炒出来,慈禧随口一句点评“这菜甜而入味,它似蜜”,这才传开。
折箩
(zhē luó)

 © 图虫创意
© 图虫创意 折箩,其实不是个好听的词儿。
折箩,其实不是个好听的词儿。过去宴会剩下的菜,不分种类倒进一锅,又成了菜,这叫折箩——说句不好听的,整个一高级泔水,还不卫生。
 © 《我爱我家》
© 《我爱我家》可这种“高级泔水”也有人吃,甚至还有专门卖折箩的饭馆,收集大饭庄的剩菜卖:
过去穷人吃不起大馆子,可总吃得起大馆子的剩菜,也算沾沾光吧。
暴腌儿
(bào yānr)

 © 图虫创意
© 图虫创意 乍一听,以为是咸鱼咸菜咸蛋搁久了,暴晒之下盐霜都出来了,其实人家是新鲜的:
乍一听,以为是咸鱼咸菜咸蛋搁久了,暴晒之下盐霜都出来了,其实人家是新鲜的:把菜、蛋临时加盐腌制,很快就吃,也入了点味儿,原理跟四川的“洗澡泡菜”差不多。
 然而,也有一些与吃有关的北京土语,随着食物的消失、时代的变迁,日渐消亡。
然而,也有一些与吃有关的北京土语,随着食物的消失、时代的变迁,日渐消亡。下面这些词,如果你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听到,请一定一定告诉饱弟!
霜肠
(shuāng chang)

 © 大众点评
© 大众点评 河南小伙伴注意啦!北京的“羊霜肠”和开封的“羊双肠”不是同一个东西哦!
河南小伙伴注意啦!北京的“羊霜肠”和开封的“羊双肠”不是同一个东西哦!根据开封有名的“西门郑羊双肠汤”介绍,羊双肠最早也叫“羊霜肠”,以羊的大肠、小肠为主料,煮好后添汤吃喝。
想进补又口重的朋友,还可以加羊外腰和羊胎盘之类(噫),满满一碗,是下水爱好者的人生巅峰。
 ▲看起来可怕又好吃
▲看起来可怕又好吃© 雪鱼探店
然而北京的羊霜肠,不是做汤用的:
羊肠衣里灌入羊血和羊脑,下冷水凝固后,外皮发白,所以叫“霜肠”。
传说,老北京有一道“烩霜肠”,把生霜肠切段煮熟,加麻酱、辣椒油、淀粉连汤一烩,加蒜泥吃,充满北京黑暗料理的暴力美学。
可惜,在90年代这道菜已不多见了,所以饱弟现在还没吃过……
白板
(bái bǎn)


 白板,指的其实是牛羊尾巴根部两边的肉,适合炖着吃。
白板,指的其实是牛羊尾巴根部两边的肉,适合炖着吃。想一下,动物尾部脂肪最富集,肉质最肥最嫩,要是牛尾巴羊尾巴根儿,像炖羊蝎子一样来那么一锅,边煮边啃,那多美呀。
 © 有意思报告
© 有意思报告要知道哪家馆子有这菜,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饱弟去吃!
野鸡脖儿
(yě jī bór)

 © 寻找桃花岛
© 寻找桃花岛 其实,这也是个比喻——指的是短而根部发红的韭菜,从根到梢长出了白、黄、绿、红、紫五种颜色,像野鸡羽毛一样多彩,才有了这个名儿。
其实,这也是个比喻——指的是短而根部发红的韭菜,从根到梢长出了白、黄、绿、红、紫五种颜色,像野鸡羽毛一样多彩,才有了这个名儿。从前,这是北京冬令难得的时鲜,可如今好多老人想吃也找不到啦。
 © 北京农业
© 北京农业五月鲜儿
(wǔ yuè xiānr)

 ▲大概是五月值班的神仙吧
▲大概是五月值班的神仙吧© 《大闹天宫》
 能让北京人夸为“五月鲜儿”的,只有春末夏初上市的鲜桃。
能让北京人夸为“五月鲜儿”的,只有春末夏初上市的鲜桃。再怎么说北京水果平平无奇,平谷大桃也是永远的神——软桃多汁、脆桃滑腻,饱弟一个夏天吃桃都能吃饱。
 ▲呈青绿色,但桃尖微微发红的,才能叫五月鲜儿
▲呈青绿色,但桃尖微微发红的,才能叫五月鲜儿© 《大闹天宫》
不过,如今交通便利,四方水果北京都有,平谷的桃儿能从三月吃到十月,当年的“五月鲜儿”也不足为奇了。
漫大联儿浪荡着点儿


 啊?发大水啦?
啊?发大水啦?其实,这句话连《北京土语辞典》里都没有。
因为,这是老北京勤行(厨师界)的一句行话暗语,就像曲艺界、江湖人士的“春典”,用暗语交流,以防被外行偷听秘密。
这种行话,往往是有系统的,如油称“漫”,香油即香漫;糖称“勤”,红糖即红勤;酱油称“沫字”,黑酱油即“黑沫字”;盐称“海潮字”,只有同行才能听懂。
 © 《天下第一楼》
© 《天下第一楼》而像“漫大联儿浪荡着点儿”,就是“炒这个菜油加大着点儿”;说一句“漫大联沫着点儿”,就是要“这个菜油小着点儿”。
假如你在北京一家饭馆,真听到师傅们这么聊天,可得珍惜这家馆子——
这么说话的年轻厨师,大概是名门正宗的传人,要是老人家,只怕早过了退休年龄啦。
其实,看一个地方的人多爱吃,就看他们挂在嘴边的俗话有多少“吃”。
广东人,从小被妈妈念叨“生嚿叉烧好过生你”,从小学鸡百炼成铁嘴鸡,句句不离鸡。
上海人,哪怕吃酸吃瘪吃排头吃生活,只要肯吃劳肯吃硬,好好生活,照样吃得开。
这么一比,北京土话里的风物与妙喻,似乎也透露出一件事:
句句不离吃的北京,从来都不是美食荒漠呀。
参考资料:
1.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1990.4
2.周三金,《名菜精华》,金盾出版社,1995.3
3.唐济泉,《老北京的大棚厨子》,《名家谈吃》,成都出版社,1996
4.张佳玮,《蛋炒饭》,《孤独的人都要吃饱》,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