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初开始,“如何看待年轻人开始选择断亲”这个话题就在互联网上持续引起热议。所谓“断亲”,指基于血缘联结的亲戚关系逐渐淡化,表现为年轻人不愿意与亲戚往来,甚至与家庭疏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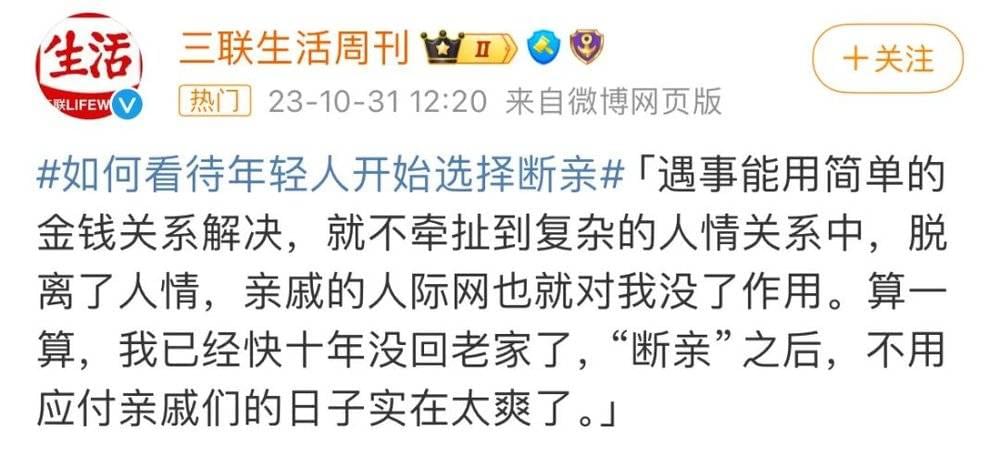
其实,“断亲”也不是今天才有,例如那个能让梨的孔融就曾提出“父母无恩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
不过,今天的“断亲”显然不同于从前,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数字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社交关系的转变。“断亲”现象为何发生?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未来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又该如何重构?曾师从费孝通先生的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的新作《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能给你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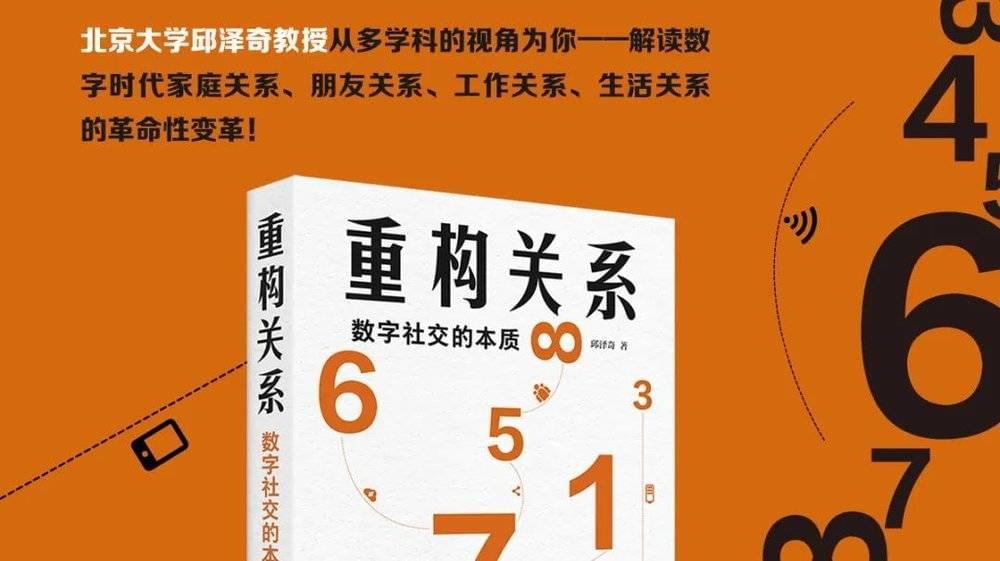
一、年轻人“断亲”,是大势所趋
家庭关系,是一切社会迄今为止最基本的初级社会关系。人类家庭在诸多方面,以前不是一个模样,现在不是一个模样,将来也不会是一个模样。
不同的社会里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亲缘关系,在特罗布里安岛上,子女是由妻子的长兄抚养和教育的。人们曾经以为异性婚姻是建立家庭的基础,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记载了特罗布里安岛特殊家庭关系。
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人因为爱情而选择配偶,浪漫爱情是通奸的代名词,是男性虚弱甚至患病的表现。配偶关系的缔结并非个人选择的后果,亲密关系也形成于配偶关系缔结之后。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人与物质的联系远远超过人与人的联系,家庭是优先围绕财产的社会组织,主流形态是几代人和多重亲属关系组成的扩大家庭,外国和中国皆是如此。
到了18世纪晚期,配偶选择才与浪漫爱情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基于爱情的配偶选择更加晚近。20世纪中叶,自由恋爱才成为法律保障的行为,直到80年代之后,才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随着浪漫爱情的兴起,家庭成为人们依恋父母、配偶、孩子的所在,家庭的主流形态也变成了由父母和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正是家庭关系的本质变迁。个体身在家庭,却从家庭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性,不再只是家庭决策的执行人。
个体自由意志的践行为自由恋爱提供了条件,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不再接受家庭的安排,变成了个体的抉择,也给扩大家庭的维系带来直接冲击,使家庭结构和人口规模朝更加有利于保障个体自由意志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为了更适应工业社会地域流动性的需求,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与人口规模的主流。
二、不只“断亲”,“家庭”都可能会消失
现在的许多断亲,指的是脱离大家庭,而把情感寄托于小家庭。不过,在书中邱老师指出,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初级关系的基础也面临挑战。
早在若干年前,人机融合就已成为热点议题,如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2045年,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泰格马克的《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等先锋文献探讨的场景或许距离我们还太远。
而随着人工智能向日常生活的渗透,人们对人机社会的想象不断丰富,且不说科幻类作品和文献,仅是一部更加接近于生活现实的英剧《真相捕捉》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如ChatGPT)进入应用,便足以让人们不断思考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影响。
数字时代,个体与家庭的关系越来越不确定。一个普遍的事实是,世界各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制度上为人的生存提供的保障越来越丰富,家庭对人的生存保障的影响力却越来越被社会的制度化安排所替代。从人出生之前到进入坟墓,越来越多的社会在提供近乎一切生活支持的保障。
一方面,当人只有生命来自父母,其他一切都由社会提供保障时,人对家庭的责任便不再有合法性,也没有了回报父母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父母只是带给人生命,却从子女那里得不到任何回报,父母也失去了坚守十月怀胎和担负养育责任的理由。
其实,不只是在数字时代,从工业时代后期开始,在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多地覆盖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时,婚姻和生养便已经变成人的自主选择。养育子女,不是文化和规则强制的后果,而是自我选择的后果。
数字技术只是将个体与家庭的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格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婚和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不育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事实。
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婚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生育率不断降低说明了,个体面对的与家庭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社会强制性,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个体选择的社会后果,家庭存在的确定性也变得越来越弱,家庭在个体社会关系中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小。
当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让生养不再完全依靠两性结合,家庭的初始社会意义即丧失殆尽,稳定的两性关系也将失去社会合法性,个体因此获得了实现自我完全独立的机会,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初级关系的基础也随之消失。
简单地说,在人的生活关系中,在经历了完全依附家庭、部分依附家庭之后,个体将可以不再依附家庭,即可以不再有家庭关系。是否建立家庭也不再是社会的制度安排,而是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关系由此展开。
三、“断亲”也“断我”,断不掉的“亲”才是真的“亲”
在数字社会之前,自我的形塑常常会透过个体参与的组织,经由组织信誉的保障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反过来,经由社会的认可,进一步形塑个体在生活关系中的自我。
而这背后,个体面对的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是相对连续的,如个体成长的物理空间、个体学习和接受社会化的社会空间都是相对连续的。连续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形塑了个体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认识自我的路径和方式,因此形成了自我对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相对连续的认知。其中,家庭等亲戚关系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背景。
人的流动性破坏了人所处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相对连续性,对人的自我认知构成重要影响。这一现象在工业时代劳动力快速流动的阶段就已经出现。
直到数字时代,自我和心灵更多基于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人与自我的关系不得不随技术迭代和场景切换而不断转换。每一次转换,都难以保证与上一场关系具有连续性,场景化的关系不再只是出现在与他人和社会之间,也会出现在与自我之间。
也就是说,个人连过去的“自我”都斩断了,更别说“断亲”了。不过,社会制度保障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体其实不是孤独的,而是有机会热闹的、温暖的,可能来自家庭的子孙绕膝,也可能来自远方朋友的八卦闲聊,还可能来自在画面和声音里出现的同伴或追随者。是否热闹和温暖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
对生活关系的重构,不是奔向自由与独立的欣喜,而是形塑人类新生活的机会。在一个让个体完全有机会也有能力“为所欲为”的时代,人们需要考量的可能不一定是个体面对的社会空间有多大,于己有利的异质性有多强。而是在面对无限的可能和无法积累的生活关系里,需要有一个怎样的心灵空间才能获得幸福,建构生活关系的积极性和包容性或许是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而这正是理性“断亲”的人们所渴望的。
观点资料来源:《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出版社(ID:pku-press),作者:小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