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们所知的世界,还有什么是可能的
1927年,一位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彻底颠覆了科学界。在那之前,经典物理学一直假设,当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已知时,就可以计算出其未来的轨迹。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证明,这种条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精确地知道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而且我们对其中之一知道得越精确,我们对另外一个的了解就越少。
这就是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又译测不准原理):在任一给定的时刻,某一粒子的位置越确定,其速度和方向就越不确定,反之亦然。五年后,海森堡因奠定了量子物理学的基础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一发现具有现代科学突破的所有特征,因此,当我们得知海森堡的同代人、阿根廷诗人兼小说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也知觉到,并且在他之前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哲学家们就已经预言过时,可能会感到惊讶。
虽然博尔赫斯在世时并未对物理学的革命发表评论,但他对悖论,尤其是希腊哲学家伊利亚的芝诺(Zeno of Elea)的悖论非常关注。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让我们承认所有唯心主义者都承认的东西:世界的幻觉性。让我们做任何唯心主义者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去寻找能证实这一特征的非现实因素。我相信,我们会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和芝诺的辩证法中找到它们。”
康德(Immanuel Kant)的二律背反是当我们的理性超越了我们通过感官所能了解到的界限,并对世界的本体作出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无关的判断时,必然会产生的悖论。他的第二个二律背反涉及空间的可分性,表明我们既可以推理出自然界的基本成分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物质,也可以推理出所有物质都是无限可分的,尽管这两种立场公然相互矛盾。
康德在提出二律背反时,受到了芝诺的启发。芝诺悖论旨在证明运动的不可能性。要从A点到达B点,旅行者必须先穿过两点中间的C点。但在此之前,他或她必须在A点和C点之间的中途越过D点,如此无限循环,旅行者事实上就永远不会移动。
在芝诺悖论和康德的二律背反中,观测行为所产生的知识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事实证明,我们在不确定性原理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明显的矛盾。虽然所有的观测都包含这种内在的悖论,但它只有在逻辑或物理世界被推向极端时才会显现出来。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他就致力于创作这样的极端场景。
1941年,博尔赫斯发表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故事讲述一名中国间谍余准(Yu Tsun)来到一名英国汉学家的家中。在那里,他们讨论了间谍的曾祖父彭㝡(Ts'uiPen)的一本奇书。这本书没有遵循单一的情节,而是旨在探索无数条故事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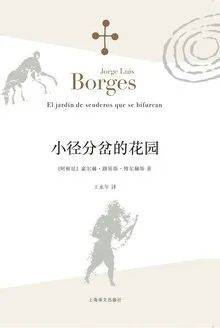
小径分岔的花园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著 王永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7月
这位名叫斯蒂芬·艾伯特(Stephen Albert)的汉学家说:“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Ts'ui Pen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由此,小说家Ts'ui Pen以这种方式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未来,而这些未来本身也在增殖和分叉。
博尔赫斯用大部分篇幅解释了一个复杂的观点,即许多不同的现实可以共存于迷宫般的时间线网络中。
小说中,艾伯特接着对余准说:“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
这个故事让读者去想象,除了我们所知的世界,还有什么是可能的。这就是博尔赫斯这篇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持久不衰的吸引力所在。然而我们有一个问题,也是余准最终不禁要问的问题:如果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那么是否真的值得做出任何选择?
虽然世界很多,但熵增不可挽回
《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有句题眼:“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在艾伯特的叙述中,Ts'ui Pen的一生主要致力于两件事:写书、盖迷宫。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东西。正如艾伯特必须穿越Ts'uiPen以笔绘就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一样(对语言着迷的博尔赫斯,为自己虚构的迷宫建造者起的中文姓是Pen,而它却是英文含义上的 “笔”),Yu Tsun也在艾伯特家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穿行。而日后的一代代读者,也反复游览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眼下,亲爱的读者,您正在我有关博尔赫斯的花园的导览之下漫游。
这种看似无穷无尽的“镜像之墙”效果是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个关键特征。如果博尔赫斯今天还活着,他可以把他的花园称为“多重宇宙”(multiverse)。我们的宇宙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而这些平行世界可能拥有相同的过去或相同的人物,这种在20世纪40年代看来天方夜谭的想法如今似乎无处不在。
不妨首先来借鉴一下科学家的研究成果。16世纪,佛罗伦萨思想家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提出了一个有许多世界的无限宇宙。四百年后,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和海森堡等人试图解释他们对量子物理学的发现。海森堡写道,原子和基本粒子“构成了一个潜在性或可能性的世界,而不是事物或事实的世界”。
休·埃弗雷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于 1957年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MWI,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根据这一解释,观测宇宙就是创造宇宙的多个副本。换句话说,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在某个现实中发生。
埃弗雷特本人并没有命名“多世界”。在他最初的论文中,它被称为“相对状态表述”(relative state formulation)。所谓相对状态,指的是观测者与被观测对象的状态之间有某种关联。在埃弗雷特看来,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是由于“坍缩”与观测(collapsed by observation)的状态“叠加”(superposition)所致,就像著名的薛定谔的猫的例子那样,在被观测到之前,猫既是活的又是死的。
相反,埃弗雷特想象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观测并不会产生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是每一种可能性都会产生不同的观测者。正如埃弗雷特写到的,“由此产生的叠加的每个元素都描述了一个观测者,他感知到一个确定的、具有普遍差异的结果”。
这似乎难以理解,但其他人扩展了埃弗雷特的想法,想象每种可能的状态都存在于自己独立的分支“世界”中——这就是“多世界解释”。
但要记住,在埃弗雷特最初的表述中,每种可能性并不存在于某个独立的空间。相反,所有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于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之所以不能同时感知到每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每一种“相对状态”都无法与其他“相对状态”相联系——作为观测者,我们只与单一的“相对状态”相关。构成你的粒子——以及构成你记忆的粒子——只能“调整”到你周围众多流体中的一种特定状态。
埃弗雷特语出惊人地表示,测量带来的不是坍缩,而是分裂(splitting)的宇宙。科普作家曹天元在《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中如此描述:“从宇宙诞生以来,已经进行过无数次这样的分裂,它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很快趋于无穷。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宇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在它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宇宙。有些和我们很接近,那是在家谱树上最近刚刚分离出来的,而那些从遥远的古代就同我们分道扬镳的宇宙则可能非常不同。”
埃弗雷特的“多世界解释”被科学界忽视了几十年,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科幻小说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他的多重宇宙中,任何事件的每一种可能结果,无论多么不可能,都有实质性的存在。我们化身无限个版本,经历着每一种可能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概念。
它构成了架空历史的丰厚土壤。曹天元写道,“也许在某个宇宙中,小行星并未撞击地球,恐龙仍是世界的主宰者。在某个宇宙中,埃及艳后克娄帕特拉的鼻子稍短了一点,没有让凯撒和安东尼怦然心动……在某个宇宙中,格鲁希没有在滑铁卢迟到,而希特勒没有在敦刻尔克前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在一个宇宙中,你点了鸡肉,但在其他地方你点了豆腐;在不同的世界里,希拉里击败了特朗普,而中国足球队成了世界冠军。
物理学家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其著作《隐藏的现实》(The Hidden Reality,2011)中列出了数学上可能的九种不同类型的多重宇宙。博尔赫斯钦佩的英国作家奥拉夫·斯塔普雷顿(Olaf Stapledon)在他的小说《造星者》(Star Maker,1937)中描绘了某个宇宙——当然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具有“奇特的时间形式”:“每当一种生物面临几种可能的行动方案时,它就会采取所有这些方案,从而创造出许多不同的时间维度和不同的历史。”
对斯塔普雷顿来说,多重宇宙是一个宏伟而复杂的地方,让人心胸开阔。
一些作家利用多重宇宙来探索人类走上歧途的另类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受到科幻迷的追捧,2015年还被亚马逊拍成电视剧——它以轴心国打败同盟国的时间线开头。
《高堡奇人》有一部书中书《蝗虫成灾 》(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在这部全美(彼时的美国,大部已经被战胜国德国和日本瓜分,外加一个两国之间的缓冲区)被禁的丑闻小说中,盟军赢得了战争。
书中人物朱莉安娜(Juliana)前往怀俄明州拜访隐居的作者霍桑·阿本德森(Hawthorne Abendsen),对霍桑说,他的书告诉人们出路总会有,因为存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恨,什么也不需要躲避或者逃避,什么也不需要追求”。
然而作者并不是一个人在写这本小说,他依靠的是通过《易经》占卜得到的信息。霍桑通过阴阳爻线一个个地选择,包括成千上万个选择,比如历史分期、主题、人物和情节等等,每隔几行就要求问一次神谕,因此他费了好多年才写完这本书。既然如此,《易经》难道就对一切了如指掌么?并不然,面对“谁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相,霍桑悲伤地回答:“我什么都不相信。”
这其实反映了迪克的世界观,因为在这位科幻大师看来,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在这本书中,他让那些爻辞和卦辞彼此矛盾,《易经》最终给出的是一幅幅无法确认的多重宇宙图像。《高堡奇人》和主流科幻非常不一样,那些科幻关注的是飞船、星云和外星人,而《高堡奇人》是一本关于人和人的关系的小说,“讲人们之间的隔阂、猜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别人是谁,都在互相打量,讲着暧昧的对话,陷入两难的困境”(韩松语)。
对书中之书《蝗虫成灾》,迪克笔下的人物议论说:“里面根本没有科学的成分。故事也不是发生在未来。科幻小说都是讲未来的,特别是科技比现在发达的未来。这本书两个条件都不符合。”这段评论用于描述《高堡奇人》也无比恰当,它并非科幻小说,而是架空历史小说。迪克精心地构建了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易经》是核心。它不仅为不同历史的转换提供了一个窗口,它还让我们——现实当中的读者,一睹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而迪克的书本身也是《蝗虫成灾》的变体。两本书重叠,似乎想通过算命,为不确定的世界带来新的确定性。
然而,就如同霍桑告诉我们的,看似能确定地算出未来命运的《易经》,又把人引向了更大的不确定。人人都生活在一个虚构的结构中,这是经典的菲利普·迪克。他作品中很多是由主观感知定义的宇宙,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客观地锚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构建的。而不论是哪一个宇宙,都遵循熵增的规律。
可以说,迪克一直乐之不疲地与“梦想自己是一只蝴蝶的哲学家又梦想自己是一名哲学家”的困境搏斗。这也正是博尔赫斯难以抗拒的游戏。在收入《沙之书》(The Book of Sand,1975)的短篇小说《另一个人》(The Other)中,博尔赫斯在波士顿北面的剑桥遇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另一个博尔赫斯认为他在日内瓦的罗讷河畔。
两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另一个人的梦,就像庄子的蝴蝶,或者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神秘的陌生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1916)中最令人不安的凄凉结局,在那里,所有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揭示为毫无意义的、短暂的、“怪诞而愚蠢的梦”。
世界并不虚假,但它始终为观测所限
博尔赫斯如何看待不确定?他的许多故事,都是围绕着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完全自足的物体、地点或人物展开。然而,这些叙事总是揭示出,如此实体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微观世界,而意味着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东西: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我参照的深渊。
在《通天塔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1941)里,博尔赫斯描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图书馆,“书架上包括了二十几个书写符号所有可能的组合(数目虽然极大,却不是无限的),或者是所有文字可能表现的一切”。故事的中心是这样一个对立性事实:用字母表来表达的语言中,没有任何真理是不会被某种字母组合记录下来的;而在浩瀚的排列组合中,要找到任何可读的东西都是天方夜谭,更不用说有用的东西了。
然而,这一困难并不能归结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数据问题,也不能归结为因规模庞大而难以管理的档案问题。如果你手头有自成一体的全部知识,那么你不仅几乎不可能分离出你需要的信息,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你需要什么。如果你偶然发现了一本书,它以合理的方式将单词和句子串联在一起,你将无法判断由此产生的文本的真实价值,因为你唯一的参考点就是其他同样不确定的文本。
博尔赫斯在1939年的文章《全能图书馆》(The Total Library)一文中,不仅强调了图书馆的规模,还强调了图书馆的矛盾性。他写道,“纵向的书籍荒野不断有可能变为其他书籍,这些书籍肯定、否定和混淆一切,就像一个谵妄的神”。
在博尔赫斯的故事中,可以获得魔法知识的领域或对象(图书馆、环形废墟、扎伊尔、沙之书、自己或他人的记忆等)往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让他笔下的人物开始疯狂而自我毁灭的探索。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完全的知识,也不是对获取知识的企图的全然放弃,而是完全知识的自我毁灭性质与其强大诱惑之间的鸿沟所导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引发了他的许多故事中令人不安的驱动性质。
博尔赫斯小说中的宇宙反映了日常阐释的问题。在解读文本时,我们并不是在进行无边无际的解读。但我们确实经常试图形成自足的、不被知识空白所穿透的解读。因此,我们通常将相关性视为与不确定性相对立的东西。
与此相反,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1942)、《通天塔图书馆》和《上帝的脚本》(The Writing of the God,1949)等故事中,我们瞥见了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的阐释和相关性概念。博尔赫斯在这些故事和其他叙事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唯我论的陷阱,即一种在文本中迷失自己的阐释,而不懂得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阅读与外部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里我们回到至关重要的观测问题。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博尔赫斯创作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场景。故事中的人物富内斯拥有完美的记忆力,他认为时间中的每一瞬间都是完全不同的,与之前或之后的时间无关。因此,他无法忽略细微的差别,无法将某一时刻的印象与下一时刻的印象联系起来。富内斯是一个能记住他所经历过的一切的人,因此他可以通过回忆“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南面朝霞的形状”或通过记忆重建“一整天”来打发时间。
将惊人记忆力的例子推向如此不可能的极端,博尔赫斯揭示了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核心悖论:不可能有纯粹的观测,不可能有不受时间影响的观测。一个观测者要感知一个实体,他或她必须能够将其与前后相继出现的印象区分开来;然而,为了将这些印象视为同一实体,同一个观测者必须能够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尽管相继出现的印象意味着差异。
观测的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运动悖论、二律背反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基础。因为在所有情况下,任何观测的发生都需要某种最低限度的运动、距离或速度——即伴随时间的变化,即使观测者假定一个不变的点或粒子,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
在正常的物理感觉层面上,这些必要的观测要素相互排斥的事实不会被注意到。只有在量子物理学高度集中、细化的层面上,或者在哲学虚构的极端情况下,这种相互排斥性才会出现。很可能,不确定性原理以及量子理论的奇特之处,就在于提醒我们,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不是虚假的,但它始终是我们所观测到的世界。
选择你的世界,克服倦怠,并爱上它
以我们的观测来看,今天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我们生活在多重宇宙的时刻。或者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多重宇宙的某一角落正在经历一个多重宇宙时刻。
2023年,《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在奥斯卡奖评选中大获全胜,得到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七个主要奖项,杨紫琼成为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亚洲女星。而这部多重宇宙史诗巨制只是近期众多情节依赖于多重宇宙而存在的漫画、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中的一部。
多重宇宙概念催生了与漫威影业有关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影,从《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Avengers: Endgame,2019)到《蜘蛛侠:英雄无归》(Spider-Man: No Way Home,2021)。它构成无数漫画的主题,为科幻作家源源不断地输入灵感,也启发了《探险活宝》(Adventure Time,2010~2018)、《瑞克和莫蒂》(Rick and Morty,2013~)和《星际迷航:发现号》(Star Trek: Discovery,2017~)等风格迥异的电视节目。
多重宇宙已经开始塑造我们的语言,影响我们的想象。这些多重世界的制造者还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终局之战》的联合导演乔·鲁索(Joe Russo)曾警告说,多重宇宙电影就像“印钞机”,电影公司永远不会关掉它。
2022年,漫威影业宣布推出“多重宇宙传奇”(The Multiverse Saga)系列电影和电视剧。无独有偶,2022年,华纳兄弟推出了一款名为“华纳大乱斗”(MultiVersus)的电子游戏,在这款游戏中,蝙蝠侠可以与兔八哥对战,《史酷比》(Scoo-by-Doo,1969~2019)中的维尔玛(Velma)可以与《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2011~2019)中的艾莉亚·史塔克(Arya Stark)对战。
在这种背景下,多重宇宙从一种讲故事的工具演变成了一种商业策略,成为众多娱乐公司循环利用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的手段之一。多重宇宙导致了影评人兼作家伊丽莎白·桑迪弗(Elizabeth Sandifer)所抨击的“万物漫威化”(Marvelization of all things):情感投入对于这些电影来说并不重要,大创意和视觉奇观非常重要。并且,很明显,它们都是男性电影。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抱怨:“漫威电影就是一部原型电影,没完没了地制作,一遍又一遍地让它看起来不一样。”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认为,这些大制作电影取代了真正的艺术作品:“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如果你想在大银幕上看点什么,大系列电影(franchise films)现在成了你的主要选择。”
电影公司计划斥资数十亿美元——比某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还多——大规模生产更多的多重宇宙是有原因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会花时间和金钱来消费它。多重宇宙的兴起是否意味着原创性的消亡?我们的文化是否走入了分岔的小径?还是说,多重宇宙开启了一种我们真正需要的故事讲述方式?
多重宇宙所颠覆的,不仅仅是线性叙事的理念,它也颠覆了身份、目的、成功或失败等概念。为什么这种无休止地传播无限愿景的方式会吸引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力呢?
不妨列举一下18至45岁这一主要人群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的事情:全球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乌克兰战争、右翼民族主义抬头、社交媒体武器化、对气候崩溃的预言越来越严重,最后是全球大流行病。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很容易觉得自己生活在最黑暗的时间线中。
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从大多数指标来看,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从未这么高。真正的骇人之处是一切似乎如此紧迫。互联网、社交媒体不间断地向我们发出可怕的警告,政治家、科学家和文化领袖告诉我们,每一项事业都需要我们全神贯注,我们必须不懈地紧急行动起来。然而,头绪如此纷乱,哪怕我们用一辈子来专注于一件事,时间似乎也是不够的。
二十一世纪使我们面对无处不在的各种危机、各种要求、各种风险、各种希望、痛苦和恐惧,它们牵引着我们,要求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如果被逼得太紧,人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一块漠然的石头,呆瞅着广袤而没有任何生命的宇宙——这似乎是个很诱人的前景。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不是绝望,而是厌倦。《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
在现实中,如何避免这种宇宙倦怠?在所有可能性(无论好坏)的重压下,在不确定性和失败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一个人如何继续坚持下去?答案是:进入多重宇宙。
对于科波拉和斯科塞斯来说,多重宇宙大片可能代表着大众文化的黑暗时间线。然而,在最佳状态下,这类作品仍能给人带来惊喜和启发。2018年,当《蜘蛛侠:平行宇宙》(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上映时,好评如潮。它的成功并不归结于任何一个全新的角色,而在于帮助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角色的新面貌。
这部电影向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展示了有多种方式可以从英雄身上看到自己,即使你并不像蜘蛛侠最初的白人少年化身彼得·帕克(Peter Parker)。漫画评论家扎卡里·詹金斯(Zachary Jenkins)写道:“今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蜘蛛侠。这不仅仅是关于代表性的问题,而是关乎给孩子们表达自我的选择。”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多重宇宙,这样人们才能想象还有什么是可能的。
14岁的非裔拉丁混血少年迈尔斯·莫拉莱斯(Miles Morales)之所以对有色人种的年轻观众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个蜘蛛侠有可能成为他们的蜘蛛侠。这正是多重宇宙叙事的一大好处:在打破普遍和单一的同时,它们允许更小、更个人、更偶然的意义出现——这些意义不是基于普遍的吸引力或必然性,而是由群体创造并为群体服务。
对于我们为什么生活在多重宇宙的时刻,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它的兴起与我们保持多种身份的需求相吻合。我们常常过着好几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家乡的生活、异乡的生活;国内的生活、国外的生活;现实的生活、虚拟的生活。因此才有了《洛基》(Loki,2021~)这样的电视剧,剧中的反英雄有无数种表现形式,包括男人、女人、孩子、鳄鱼和总统。
也因此才有了《瞬息全宇宙》这样的移民电影,导演之一丹尼尔·施纳特(Daniel Scheinert)评论道:“整个移民故事就是一个多重宇宙的故事,因为你存在于三四个世界中。”
正如《瞬息全宇宙》的主角伊芙琳(Evelyn)跨越多重宇宙,从不同的现实中获取技能一样,现代人也越来越像看似不可调和的自我的混合体,不过这些自我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包含多种版本。我们是一切,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无处可去。我们不扎根于一处,也不属于一处;我们跨越世界,甚至经常跨越文化。
尽管有以上特点和好处,多重宇宙概念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终极批评是,它最终会导致无意义。文学评论家斯蒂芬妮·伯特(Stephanie Burt)在《纽约客》上问道:“如果所有可能的结局都实现了,那么一切的后果又是什么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的余准之问:如果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那么是否真的值得做出任何选择?多重宇宙谬误容易将抱负视为彻头彻尾的幻想,助长犬儒主义,破坏维系社会的纽带——至少,它反映出我们想象力贫乏,对实际居住的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改造能力有限。
在《瞬息元宇宙》中,乔伊(Joy)在多重宇宙中被推得太远,一下子看到了所有地方的一切,这让她产生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动力。多重宇宙的自由给乔伊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空虚。用韦蒙德(Waymond)的话说,“她看得太多了,失去了任何现实感,失去了对客观真理的信仰”。乔伊迫使伊芙琳接受越来越多的多重宇宙自我意识,这导致伊芙琳的行为越来越像乔伊,变得更加愤世嫉俗和残忍,因为“什么都不重要”。
然而伊芙琳必须超越这种宇宙虚无主义,发现一个充满同情和接纳的地方。在韦蒙德看似天真的善意刺激下,伊芙琳从愤世嫉俗走向宇宙慷慨,找到了一种给予每人所需的方法。正是这一点,让《瞬息全宇宙》成为我们的多重宇宙时刻的标志性影片。伊芙琳和乔伊共同面对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倦怠和精疲力竭的感觉,尽管问题最后并未消失,她们还是一起渡过了难关。
博尔赫斯也一直在坚持思考宇宙的意义。虽然《小径分岔的花园》谈论的都是选择和环境,但它对“不可避免”这一概念十分感兴趣。余准一直在讨论如何实施他知道是可怕的行为。他说:“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
在博尔赫斯看来,决定论甚至叙事本身的限制都是个人允许自己做出可怕行为的途径。但是,岔路花园提供了一线出路。它不认为历史不可避免(因而也反对暴力不可避免),而是将万事万物、所有故事的相互联系视为跨出暴力循环的一步。
也因此,《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多重宇宙中看到的不是无意义,而是更深刻的意义。看似不可避免的战争暴力才是真正的幻觉;真实的是可能性、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及最重要的,你身边的人。
在二十一世纪,博尔赫斯笔下的岔路花园已经成为一个窗口,让人们可以在这里窥见一个超越了当下持续不断的争斗的世界。多重宇宙并不是只能催生消灭共识的认同政治,也不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借口,让他们不去努力把事情变得更好。
就像存在主义一样,它要求你选择生活在你所能接触到的众多世界当中的一个,并爱这个世界,尽管它有缺陷、偶然性和不完美,尽管它有各种方式可以变得更好(而实际上并没有)。你不得不爱你选择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它是唯一存在的。相反,你热爱这个世界,是因为它可能与众不同。
今天的多重宇宙叙事要求我们寻找连接、爱和仁慈之处,这些地方存在于偶然中,而叙事的主人公往往因为简单地接受了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免于虚无主义。在《洛基》中,目睹无数个自己陷入狭隘的自我毁灭的野心中,主人公被迫正视自己野心的病态,转而开始关注身边的人。
在《瞬息元宇宙》中,韦蒙德的最高呼声就是“要善良,尤其是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而最终指引伊芙琳的就是善良,甚至是对女儿想要退出家庭(和宇宙)的悲悯接纳。她必须冒着永远失去女儿的风险,以打开女儿选择留下的可能性。尽管伊芙琳在多重宇宙中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活,她最终还是接受了她原来的宇宙,并重建了破碎的家庭。在多重宇宙的无限旋风混乱中,爱依然存在。
今天的这一代人正在经历意义的探索——即未来本身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过去那种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即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努力改变,不对我们的努力抱有任何期望。这是一种既接受希望又接受失败的态度,适合于走向一条漫长的道路,它通往一个不可能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未来。
于此,多重宇宙的一切都是礼物。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我们的可能性。唯有可能性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