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说出口的,我们绝不该使之沉默,它必须被书写”,约恩·福瑟(Jon Fosse)时常引用这句德里达的名言。10月5日,这位64岁的挪威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因他的作品“为无可言说之物发声”。
对福瑟而言,文学性之所在,或者说形式与内容相融至不可分离之处,即这种“书写的声音”。它来自于无可言说的沉默,其本身也是一种沉默:它并不言语,但我们可以透过小说叙事者或戏剧人物说出口的话来听见它。它是“来自远方的无声之声”。
福瑟因戏剧知名,但在23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红、黑》后的十余年时间,他涉足散文、小说、诗歌,却对戏剧敬而远之。他承认对戏剧抱有偏见:剧场里只有“文化”而无“艺术”,只有“一种文化共识、对报纸和电视也在讨论的话题的喋喋不休,或是徒劳的现代主义形式发明”。剧场太嘈杂了,太多事件,太多话语,它们紧紧抓住自己的表意功能,无法超越自身。
人们常说福瑟的戏剧是“极简”的。这种极简首先体现在以视觉为基础的表意系统的节约上。“我不是个视觉的人”,他说。写作时,他“聆听”,“看不到任何面孔,也看不到别的什么”。这样的创作模式更接近诗而不是戏剧,因为戏剧是视觉的,布景、着装、人物常常是一系列具体细节的总和,为观众制造罗兰·巴特所谓的“真实效果”。
福瑟的戏剧建立在对景观的拒绝上:台词和舞台说明很少有关于时间和地点的提示(越到后期越少,比如《我是风》:“场景发生在一艘想象的船上,因此无须过分具象呈现”),对话甚少参与视觉的建构,他笔下的人物没有面孔,也很少有名字,重复着简单的姿势和动作,“他们是声音”。
法国著名戏剧导演克劳德·雷吉(Claude Régy)将福瑟的戏剧搬上舞台时,演员常常显出疲惫麻木的状态。他们如梦游般徘徊,用空洞的声音念出台词。按法国学者樊尚·拉菲(Vincent Rafis)的说法,演员们“被迫远离阐释,被迫将自己交托给言辞,而不是主观干预。换句话说,他们被迫被言说,甚至被书写,因此被阅读”。演员的肉身化作声音装置,“打开一个空白的空间,如空白的纸页一样”,无损地还原文字符号。福瑟的戏剧是向文本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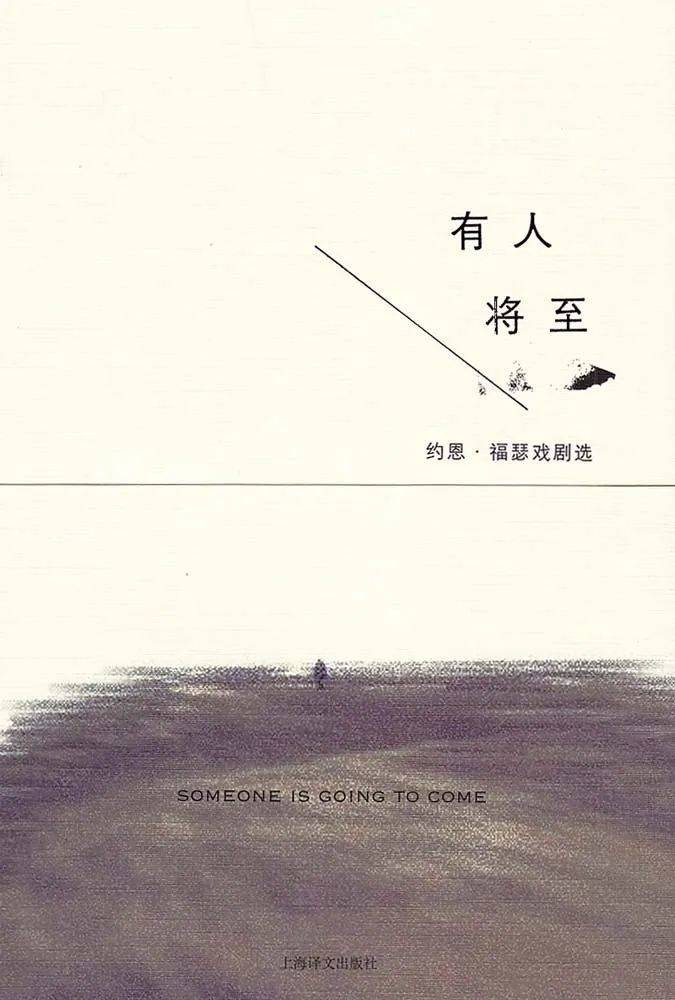
《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挪威) 约恩·福瑟/著 ,邹鲁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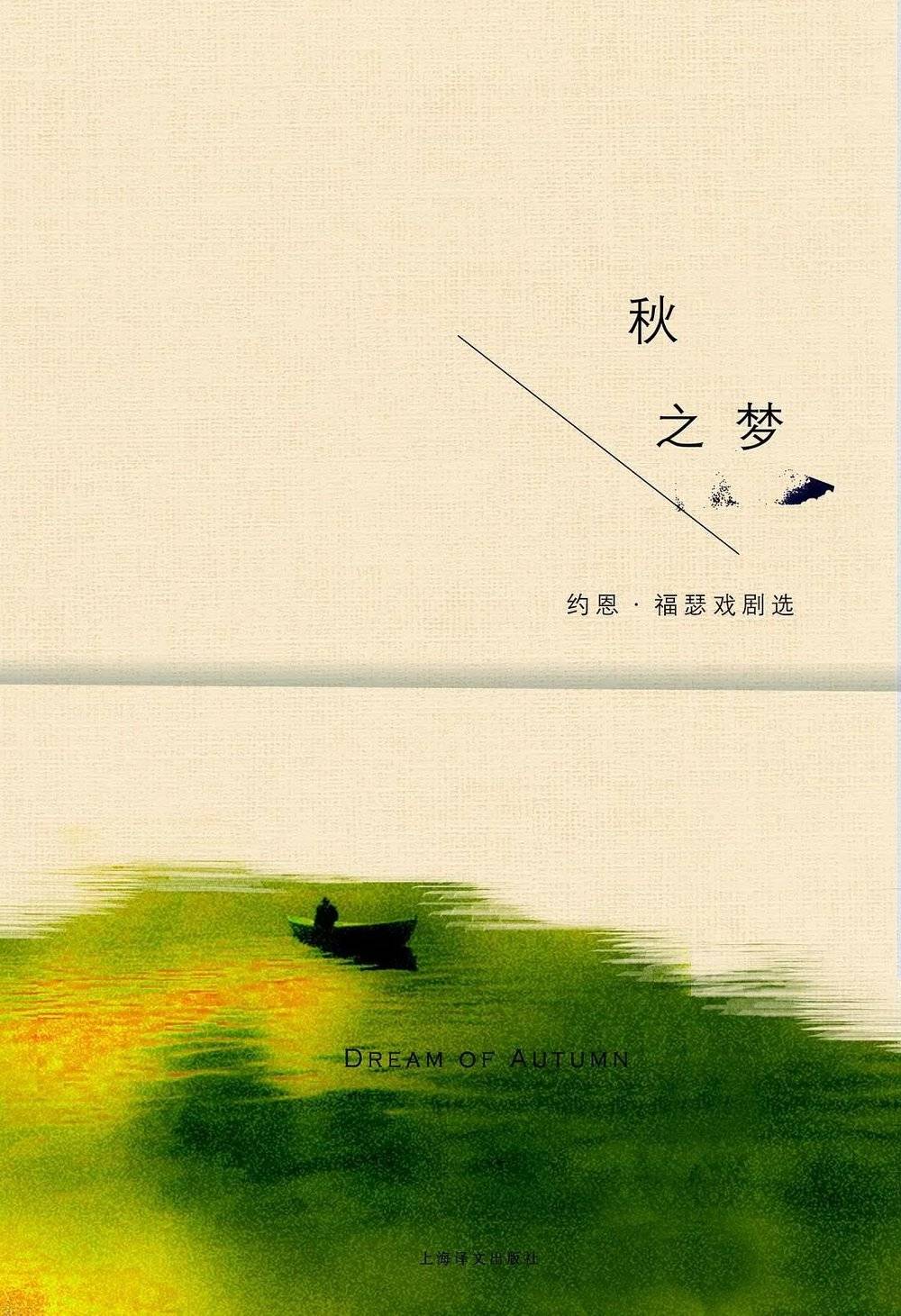
《秋之梦:约恩·福瑟戏剧选》(挪威) 约恩·福瑟/著 ,邹鲁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4月
福瑟戏剧的台词通常都是些日常话语,词汇贫乏,语法简单。台词充斥两种相反的运动。一种是语义链的突然断裂,一个话题刚起头便被打断,分出一条岔路,或是干脆是意义相反的两句话的并置,有时变成一种虚假的因果关系的断言(如在《有人将至》的开头,女人说:“这里是如此与世隔绝/一定有人会来的”)。
台词以断断续续的自由诗行的形式陈列,没有标点,于是句与句、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明确,有时甚至碎落成无意义的残片(如《儿子》中的一段话:“母亲/我会变成什么/如果你/父亲/是呀”)将逻辑碾压的支离破碎的不只是角色的主观臆断,更是超越心理层面之上的更深邃的神秘。
而这些断裂随后都会汇拢到另一种更本质的运动中:句子的重复和循环。重复的意义时常是不确定的,在对白中,角色相互重复对方的话,有时形成不断靠近、相互交融的气氛(如《秋之梦》开头,男人和女人的重逢),有时(或者大多数时候),在重复中渐渐渗入细微的变化,同一性开始崩裂,显出对话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人将至》是个典型的例子)。
每个角色(通常是创伤性角色,经历自己或亲人的死亡)自己也在不断重复自己说过的话。被锚定住一般,他们一遍遍回到同样的话语中,好像盲人不断地触摸同一块墙面,这种强力的偏执中又带着意志的虚弱:他们迟疑着、质询着,前进一些又退回原点,每次的重复都洗刷掉一点词语的原意。在厚度不断积累的同时,意义变得愈发单薄,好像一个个不断放大的特写镜头,最后只留下纯粹而空白的强度。对白的机器就这样不知倦地运转着,细微的变化慢慢转成崩溃,在崩溃的碎片中再度浮起残渣,进入下一轮的循环,在一轮轮的循环中渐渐下沉至未知的深处。
对福瑟而言,语言首先“是其自身,如同石头、树木、神与人”。他说他像演奏自己乐谱的音乐家一样工作,在语句不断的重复所制造的变奏和对位中,语言从传递意义的功用中脱离,获取了肉身:一种精心编织却又充满即兴的音乐。在这种音乐中,沉默是重要的有机成分。台词的自由诗之间充斥着“沉默”“短暂的沉默”“极短的沉默”的舞台指示,这些沉默不只是所指也是能指,构成了音乐的基底和动机。
在有声的语言之间藏着另一种语言:“重要的是之间的东西,是人物之间,文本的不同元素之间的空隙和裂缝。它更多地通过安静,通过没有说的话而不是说出口的话表达”。诗句漂浮在沉默之上,它们成了有声与无声之间相互转化的一道道边界。
如法国学者玛丽昂·舍内提埃(Marion Chénetier)所说,福瑟的戏剧制造“一种紧密编织但有空隙的沉默,似乎唯一的作用是确保一种语言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的特点在于,它绝不会被间隔它的沉默所中断,而是与沉默合二为一。因此,沉默被感受为语言的基质,是它的来源,而语言则是沉默的延续,甚至是对沉默的深化或质疑”。
本质上,福瑟的戏剧是一种语言情境,故事内在于语言,且由语言召唤而出。《有人将至》中,一个男人和女人住进一栋偏远的海边小屋,决定自此遗世孤立,但女人突然担心起“有人就要来了”。于是,她一声声恐惧的呼喊(抑或是,她的恐惧中也夹杂着希望他者到来的欲望)如一声声连祷,最后,他们的房门前真的响起了脚步声。
而在《一个夏日》《我们永不分离》《死亡变奏曲》等剧中,经历至亲死亡的主角追溯创伤,他们的话语召唤出过往。《一个夏日》里,年老女人的独白与过往场景中的对话相交织的同时也相互渗透,过往的对话是独白内容的客观化呈现。舞台在语言的腹中。
因此,福瑟的戏剧不存在从开头到结局的曲线,故事的发展不在人物的行动中,而在语言前前后后周旋的节奏之中。许多学者将这种运动方式与海浪联系在一起(海也是福瑟剧作中的核心意象),玛丽昂·舍内提埃将之命名为“状态戏剧”:“始终在运动,但整体视图却暗示了静止”。
剧中的人物处于一种恒常的不安状态中,这种不安关乎存在的本质,类似海德格尔的“畏”(Angst)(福瑟曾称自己深受《存在与时间》的影响):在《一个夏日》中,女人的丈夫阿瑟“终于得到这/梦寐以求的房子时/他却突然感到/不安了/一种黑暗/到底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他自己也/不太明白/突然淹没了他”。
这种不安时常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相关,在《我是风》中,两个主角的其中一个说:“那些他人的声音/那些万事万物的喧哗与躁动/把我压垮了/把我封闭起来”。他无法忍受他人,但也无法忍受自己:“如果我独自一人/那我能看到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也只有自己,而我不想看到也不想听到自己”。他“不喜欢自己是一片虚空”,如果只剩下一片虚空,他“会变得沉重”,就像一块石头往下沉。于是,他“无法独自一人/也无法身处他人之中”。在《有人将至》中,“单独在一起”这句矛盾修辞贯穿全剧,主角二人无法相互沟通,却也无法离开彼此。
不安状态要么一直持续下去(如《有人将至》中一样,矛盾始终处于潜在状态,无法爆发),要么以死亡结束(如《一个夏日》和《我是风》),但死亡并不会在舞台上得到直接的展现,且理由不明,不受主角的意志左右(《我是风》的开场便说:“我不是想这么做/我只是就这么做了”)。人物都是被动的,情境似乎与过去和未来都隔绝开来,什么也无法改变。
平滑的舞台生出多层褶皱:不同的时间共聚在同一个空间中。过去的人、现在的人、不存在的、存在的被赋予了同一种虚弱的强度,他们都处在生死之间,如同鬼魂,时常处于静态,躺着,坐着,望向窗外(《名字》里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人/你一定要能够去想象/所有死去的人/所有未出生的人/所有活在当下的人是如何作为人而存在的”)。
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重复同样的动作和对话,仿佛这一切是梦境的凝缩,仿佛时间从来都是静止的。人物“不是在虚空中对话”,而是“在与他们周围创造的虚空对话”。
《死亡变奏曲》的开头,年老女人说:“深深地/陷入/黑夜……陷入黑夜/陷入接近透明的无限/戛然而止/这令你觉得/你明了了/世间所有需要明了的一切”。走入语言的深处,进入前语言的黑夜,主体性将被剥夺。
《一个夏日》里的年老女人说:“我觉得自己变得空虚/就像雨和黑暗/就像风和树木/就像远处的大海/现在我不再觉得不安了/现在我觉得空虚而又冷静/现在我是一片黑暗/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现在我什么也不是/而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哦不知怎么我好像在向外发着光”。
剧中的角色只有一个身份的空壳,他们的台词可以互换,彼此是彼此的重身。他们的主体性被布朗肖所谓“语言的无名性”所替代,这种无名性不指向作者的意识,也不指向观众,而是指向一种冗长而无止尽的、位于生死之间的语言流。把福瑟剧作搬上舞台的雷吉坚持认为,福瑟剧里所有的对白都是表象:所有的对白都是独白,是无人言语的语言在喃喃自语。
自七岁的一次濒死经历后,福瑟开始写作。他的写作与死亡相关,也与神秘主义相关:在濒死时,他从外面看到自己,在一种光芒中,很平静、很快乐。他说自己是诺斯替主义者,他寻求的是一元的、无差异的超语言:“来自远方的无声之声”。这种超语言在沉默的黑暗里放光,光芒沾染在可读的台词中。
奇妙的是,这些客观的、无感情的词语的流动,在麻痹观众理智活动的同时,带给观众强力的情感体验。如同一场催眠,一场大型的祷告,观众从日常空间中抽离进入意义边缘的文学空间中,被施以一种平和的暴力,以及暴力所拥有的悲剧效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杜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