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由来自卡罗林斯卡学院的50名医学专家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将开会投票决定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根据往年的获奖情况,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经常在非常基础的分子生物学发现和实际治愈人类疾病的发明之间循环。而去年奖项授予了偏向基础研究的古基因组学,这意味着今年临床进展很可能成为关注点。
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有着许多热门候选者,包括CAR-T细胞治疗、mRNA技术等等。而目前正在改变糖尿病和肥胖症治疗格局的GLP-1类药物,同样被外界预测为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最近几年,这些基于GLP-1的药物似乎无处不在,它们帮助了许多人安全地控制糖尿病和减肥,一些新的临床研究显示,它们还可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甚至有望用于戒烟戒酒。许多研究人员指出,GLP-1类药物的开发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不是今年,那么可能也不会等太久。
那么,接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GLP-1类药物获得诺奖,获奖者将是谁?
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GLP-1类药物的畅销,并非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从发现GLP-1激素,到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的旅程漫长而曲折,跨越了40多年时间,涉及学术界和制药行业的数百名研究人员。已经有一些科学大奖授予了三位科学家,他们参与了对GLP-1激素的一些最早见解的解析,从历史来看,诺贝尔奖更倾向于表彰基础研究,而且一个奖项最多授予三人。这一点也一直饱受争议,批评者认为,这将由一群人做出的发现个人化了。
对于GLP-1类药物而言,从发现GLP-1、解析其作用,再到开发成药物,每一步都是如今GLP-1类药物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必要条件,而其中哪一步最困难,最具创新性,这很难说。而且,这一过程也充满了运气的成分,例如,发现靶向GLP-1受体可以大幅减轻体重。
著名科技媒体STAT采访了大量科学家,确定了一个在GLP-1类药物中发现了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名单。

对GLP-1的结构和功能的早期认识是由麻省总医院的 Svetlana Mojsov、Joel Habener 和 Dan Drucker 以及哥本哈根大学的 Jens Juul Holst 提出的(从左至右)。
鱼内脏和大鼠器官:发现者
那是1979年的夏天。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科幻电影《异形》刚刚首映,在科德角海岸外,一艘深海拖网渔船正在寻找另一种黏糊糊的生物——美国琵琶鱼(鮟鱇)。
此时,年轻的医生 Richard Goodman 驱车两小时前往码头购买了这些鱼,然后使用手术刀将它们切开,从内脏周围的粘性组织中取出青豆大小的肉块,把它们放入液氮瓶中,而这每个都是内分泌学家的金矿——成千上万份制造代谢激素的mRNA。
就在几年前,科学家们提出了革命性的新技术——重组DNA技术,用于分离基因并研究它们的工作原理,各地的生物医学研究实验室都争相学习这些新方法。Richard Goodman 在麻省总医院工作的实验室是将这些技术应用于激素研究的顶级实验室之一,其领导者为 Joel Habener。
该技术从mRNA逆转录出DNA,然后对其进行测序,将其拼接到细菌基因组中以创建生物分子工厂。该技术的出现让过去需要半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加速到了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不过,这一技术需要大量的mRNA。
Richard Goodman 对一种叫做生长抑素的激素很感兴趣,这种激素在大脑和胰腺中产生。但大脑产生了太多的多肽类物质,而胰腺更简单,除了生长抑素,只有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等几种物质,而且只在一种细胞——胰岛细胞中产生。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身上,胰岛分散在整个胰腺中,从中收集足够的mRNA进行实验非常耗时耗力。于是他转向了鮟鱇,这种鱼的胰岛细胞集中在布罗克曼体中,大到足以被人眼看到。
很快,Richard Goodman 就培养出了拼接了鮟鱇DNA片段的细菌,并使用放射性探针进行筛选,以识别携带生长抑素基因的细菌。在他成功完成这项工作后不久,一位对肠道肽感兴趣的博士后P. Kay Lund来到了实验室。利用 Richard Goodman 构建的含有鮟鱇DNA的细菌文库,P. Kay Lund首次确定了胰高血糖素前体的基因序列,胰高血糖素是一种提高血糖水平的激素。
事情到这里才真正开始。
1982年,他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1】,发现胰高血糖素前体基因实际上编码了三种多肽——胰高血糖素,以及两种在肠道中表达的新激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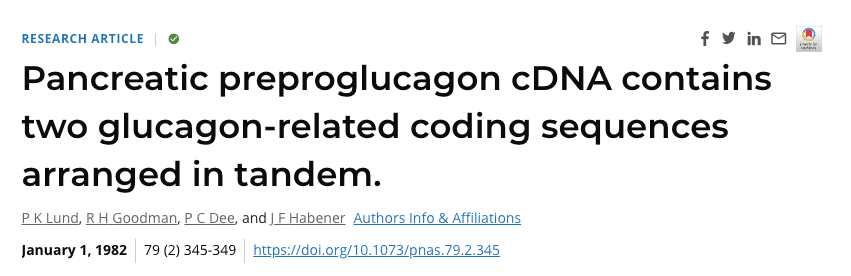
一年后,Chiron公司的 Graeme Bell 领导的研究团队在 Nature 期刊发表了两篇论文【2、3】,他们从哺乳动物和人类中克隆了胰高血糖素前体基因,并对其进行了测序,将两种在肠道中表达的新激素命名为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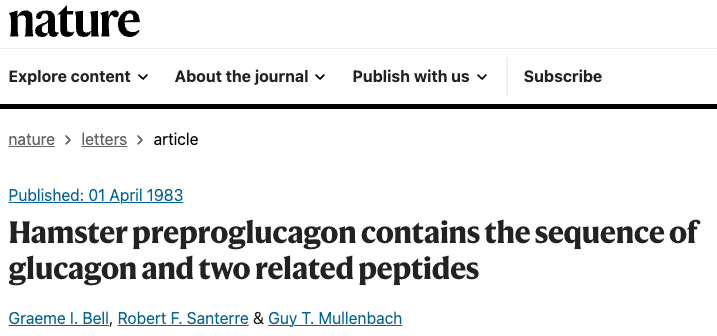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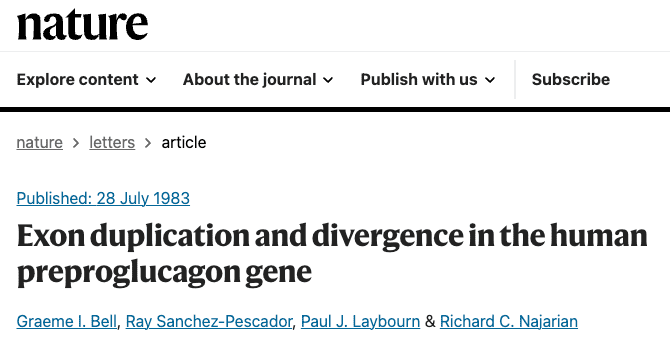
Richard Goodman 认为自己对GLP-1的贡献“微不足道”。在分子生物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一直在识别新的基因和多肽。他认为,真正意义深远的事情是迈出下一步——GLP-1到底是做什么的?
1983年,Svetlana Mojsov 加入了麻省总医院内分泌部门,她是一位研究胰高血糖素的化学家,对GLP-1很感兴趣。作为一位多肽合成专家,她猜测GLP-1的活性结构实际上是完整分子的一个较小的截断片段——GLP-1(7-37)。在一系列在小鼠上进行的艰苦实验中,她发现了这种截断片段天然存在于肠道中。
我们在吃糖时,胰岛素水平比直接注射葡萄糖到血液时更高,这表明我们的肠道分泌了刺激胰岛素的物质来应对进食。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名为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的激素。但事实证明,GIP并不是全部。Svetlana Mojsov 认为自己发现的GLP-1(7-37)是所谓的“缺失的肠促胰岛素”。就在她准备将这些发现写进论文时,Joel Habener 实验室的博士后 Gerhard Heinrich找到了她,他有更多关于基因序列的数据,并希望将他们的发现结合起来。1986年9月,他们合作在 JBC 发表了这篇论文【4】。
与此同时,Svetlana Mojsov 向另一位负责解开GLP-1之谜的 Joel Habener 实验室的博士后 Dan Drucker 提供多肽和其他试剂,Dan Drucker 在细胞系实验中发现了GLP-1(7-37)。1987年2月,Svetlana Mojsov 、Gordon Weir 和 Joel Habener 在 JCI 发表论文,发现GLP-1(7-37)能够刺激大鼠胰腺的胰岛素分泌【5】。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 Jens Juul Holst 团队在 FEBS Letters 发表了一份报告【6】,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是一名胃肠外科医生,自从他在医院看到接受减肥手术的病人胰岛素激增和血糖下降以来,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缺失的肠促胰岛素。当看到GLP-1的发现时,他立刻开始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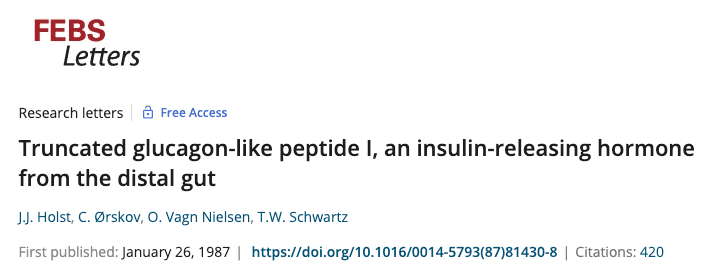
然而,Jens Juul Holst 团队的第一次实验失败了,他们从新发现的GLP-1基因序列中合成了GLP-1,并将其滴入一只从活猪的分离胰腺时,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他向一位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到哥本哈根的同事Thue Schwartz,在芝加哥大学,他发现了一种叫做胰多肽的激素,它有一种相当独特的裂解模式。他猜测GLP-1可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因此,他们开始独立地研究了GLP-1(7-37)片段。
从上述两个团队收集到的所有数据来看,GLP-1尤其是7-37片段开始变得很重要。如果它确实是一种能够增加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分泌的激素,那么它就有可能用于治疗糖尿病。重要的测试他在人体内的效果。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率先做到这一点的并不是这两个团队。
据 Jens Juul Holst 的描述,1987年夏天,他和帝国理工学院的内分泌学家 Stephen Bloom 一起参加了一个派对。或许是因为喝多了,也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团队的研究进度已经遥遥领先,Jens Juul Holst 畅谈了GLP-1的治疗潜力。
几个月后,也就是1987年12月,Stephen Bloom 团队证明了GLP-1已经通过了第一次重大测试。他在《柳叶刀》发表论文【7】,证实了GLP-1(7-36)是一种人类肠促胰岛素,并揭示了其在人体中的生理作用,能够迅速刺激胰腺产生更多胰岛素,从而降血糖。

研究人员很快发现,GLP-1是一种寿命非常短的物质。血液中的酶在几分钟内就能把它消化掉。因此,需要大量的GLP-1来治疗糖尿病。然而,在 Svetlana Mojsov、David Nathan,以及 Jens Juul Holst 和 Michael Nauck 领导的第一项GLP-1治疗糖尿病的临床试验中,高剂量GLP-1会导致恶心和呕吐。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开发出看起来和行为都像GLP-1的分子,但要比天然的GLP-1存在的时间更长。
吉拉毒蜥和饥饿大鼠:开发者
对于主导这个新兴行业头几十年的那一代生物技术高管来说,GLP-1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想法。一些人试图把它变成一种药物,但都失败了。
1980年夏天,一位名叫 Jean-Pierre Raufman 的年轻胃肠病学家来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他渴望得到一个有趣的奖学金项目。他和 John Pisano 搭档,后者是一位有点古怪的生物化学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收集毒液而闻名,他从当地的业余动物学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毒液。
Jean-Pierre Raufman 采集了大约20个最有趣的样本,包括蝰蛇、眼镜蛇和吉拉毒蜥,吉拉毒蜥是一种原产于美国西南部的大型黑色有毒蜥蜴。他的工作是这些毒液滴入豚鼠胰腺的培养皿中,然后测量细胞分泌的淀粉酶的含量。这个想法是为了找到可能改变人类生理的物质。在看到吉拉毒蜥的毒液刺激淀粉酶的大幅增加后,Jean-Pierre Raufman 开始专注于揭示其毒液中到底有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合作者发现了几个新的多肽和激素,并在不知名期刊上发表了这些研究结果。
1983年,Jean-Pierre Raufman 在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小实验室。由于没有获得来自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资助,研究进展很慢,直到他的领导把他介绍给了 Rosalyn Yalow(她因发明了胰岛素放射免疫分析法,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她的实验室里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研究员——John Eng,擅长分离多肽和使用新技术确定它们结构的,他认为吉拉毒蜥的毒液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1991年8月,他们在 JBC 期刊发表论文【8】,从吉拉毒蜥的毒液中提取了一种名为Exendin-4的由39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这种多肽是全新的,但又似乎很熟悉,它的形状几乎完全像GLP-1。但不同的是,GLP-1在血液中不到一分钟就会被降解,而Exendin-4则能够持续超过两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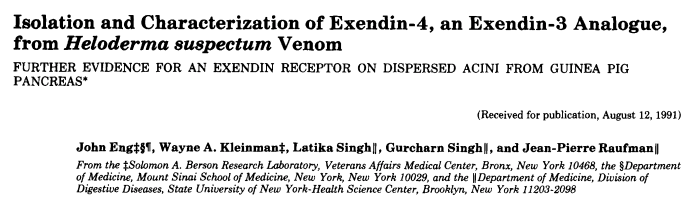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重磅糖尿病药物。但在90年代初,他们发现自己有点超前了。
他们在学术会议上展示这样研究,感兴趣者寥寥。他们所在的单位也不愿利用部门资源申请专利,John Eng 只好自己完成了专利的撰写和申请。他还尝试吸引当时知名糖尿病药物开发公司的兴趣,包括礼来、百时美施贵宝、赛诺菲和诺和诺德。但全都被拒绝了,因为没有人想把从致命的蜥蜴嘴里提取出来的东西注射到人体内。
但好在,John Eng 还是说服了一个小型生物技术初创公司Amylin公司继续支持这项研究。1996年,Amylin公司获得了 John Eng 的授权,开发了合成的Exendin-4,也就是艾塞那肽。三年内,该公司发现,糖尿病小鼠使用艾塞那肽一周后,血糖水平可以正常化。进一步的临床试验表明,它能够有效且安全控糖。2005年,艾塞那肽获得了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糖尿病。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也是全球第一款GLP-1类似物药物。
随着艾塞那肽作为糖尿病药物上市,使用者们发现,这种药物还有减肥效果,他们将这种药物称为Gilly,向它的来源——Gila monsters(吉拉毒蜥)致敬。该药物的灰色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将它作为一种时尚减肥药供应,这也预示着将来的司美格鲁肽热潮终将到来。
对于长期从事GLP-1研究的人来说,他们认为艾塞那肽的减肥效果总体上并不那么显著,特别是考虑到大量使用该药的人出现了恶心和其他肠道不适,再加上它会显著降低餐后血糖水平。因此,艾塞那肽这种GLP-1类似物可能不是制药公司的终极目标。
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显示,GLP-1受体激动剂是治疗糖尿病的一种可行方法。此时,诺和诺德已经开始了GLP-1受体激动剂的临床试验,该药物被命名为利拉鲁肽。诺和诺德公司内部的科学家认为它可能比艾塞那肽更好,尽管他们正在测试它作为糖尿病的治疗药物,但在公司内部,他们已经在讨论其减肥效果。
在诺和诺德旗下的学术中心哈格多恩研究所,一位名叫 Ole Dragsbæk Madsen 的细胞生物学家给小鼠注射了由胰岛细胞制成的肿瘤,以研究这些细胞是如何成熟并启动胰岛素基因表达的。随着小鼠年龄的增长,肿瘤也越来越大,这些小鼠开始吃得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瘦,就好像肿瘤在释放一种足以致命的食欲抑制剂。当他检查这些肿瘤时,发现这些来自胰岛细胞的肿瘤产生了大量的GLP-1。
诺和诺德的研究人员 Lotte Bjerre Knudsen 看到了这些数据,她认为GLP-1似乎既能抑制食欲,又能促进胰岛素分泌。所以想到了为什么不使用一种药物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呢?那是在1995年,由于科研进入死胡同以及公司组织结构变动,研究计划停滞不前,直到两年后,她的团队终于想出了一个可行的设计方案——通过添加长链脂肪酸,让其抓住白蛋白这种血液中最丰度的蛋白质,使GLP-1类似物躲过酶的降解。但这种结合必须是可逆的,这样药物才能找到到达胰腺GLP-1受体的路径。
使用这种方法,他们开发了利拉鲁肽,2000年作为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注射药物进入临床试验,并最终在2010年获得FDA批准上市。而早在1995年,Lotte Bjerre Knudsen 团队就发现,除了增加胰岛素分泌外,GLP-1还能使小鼠吃得更少。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Stephen Bloom(右)首次发表了GLP-1和食欲抑制之间的联系的论文。诺和诺德的Lotte Bjerre Knudsen(左)开发了利拉鲁肽和司美格鲁肽
此后的一系列研究证明了GLP-1的减肥效果是通过大脑介导的,这是一种与它对血糖的影响不同的机制。当诺和诺德开始测试 Lotte Bjerre Knudsen 团队开发的司美格鲁肽时,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现了,利拉鲁肽被证明可以减少一个人15%的食物摄入量,而司美格鲁肽可以减少高达35%的食物摄入量。
2014年,FDA批准利拉鲁肽作为减肥药物上市 , 2021年,FDA批准司美格鲁肽作为减肥药物上市。现任诺和诺德首席科学顾问的 Lotte Bjerre Knudsen 表示,根据她的团队进行的小鼠研究,司美格鲁肽更强的减肥效果可能是因为其化学结构使其更容易进入大脑,特别是进入与饱腹感信号有关的区域。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清楚了,司美格鲁肽作为减肥药上市后,产生了爆炸性的需求,其2022年的销售额超过120亿美元,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双重靶点和多重靶点:创新者
司美格鲁肽的火爆让人惊叹,但实际上,它已经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制药公司正在迅速从GLP-1单靶点转向多靶点,以期达到更大的减肥效果。
礼来公司(Eli Lilly)的开发的GIP受体和GLP-1受体双重激动剂替尔泊肽的3期临床试验成功,在为期72周、每周一次的治疗后,帮助肥胖者体重减轻了22.5%,这一效果超过了司美格鲁肽。目前该药物正在等待监管部门批准作为减肥药物上市。
此外,礼来公司还在开发一款三重激动剂Retatrutide,在近期完成的2期临床试验中,在为期48周、每周一次的治疗后,帮助肥胖者体重减轻了24.2%,这是迄今为止药物减肥实现的最好效果。
这些减肥药开发的下一个前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Matthias Tschöp 和 Richard DiMarchi 的工作。

Matthias Tschöp(左)、Richard DiMarchi(右)开发了第一款双重激动剂和三重激动剂减肥药物
1999年,年轻的德国医生 Matthias Tschöp 前往礼来公司申请博士后奖学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抑制食欲的激素瘦素(leptin)被发现,似乎是一种很有希望的肥胖治疗方法,这促使他离开医学界,转而学习药物开发。然而,当他到达时,瘦素在试验中开始令人失望。
他和他在礼来公司的同事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激素——胃饥饿素(ghrelin,也叫生长激素释放肽),它被认为是瘦素的反面,因为它会增加饥饿感。但阻断胃饥饿激素似乎也不是一个有前途的方法。从这些实验中,他开始思考,针对一种激素可能不足以治疗肥胖症,我们需要结合几个信号。
2003年,刚刚成为辛辛那提大学副教授的 Matthias Tschöp 接到了来自多肽研究专家 Richard DiMarchi 的电话,Richard DiMarchi 此前是礼来公司的高管,他刚刚离开礼来,成为印第安纳大学的化学教授,他也想开发结合多个药物靶点的肥胖症治疗方法。此后,他们开始了长达20年的合作,Richard DiMarchi 制造新化合物,Matthias Tschöp 进行生物测试。
他们从一份超过12种可能成为潜在靶点的肠道激素清单开始。他们锁定的其中一种是胰高血糖素(Glucagon)。胰高血糖素可以提高血糖,它已经是一种用于治疗葡萄糖突然下降的药物。治疗代谢疾病的传统思路是阻断胰高血糖素,而不是刺激胰高血糖素,因为它会提高血糖。但小鼠实验表明,胰高血糖素有增加能量消耗的作用,从而导致体重减轻。
将胰高血糖素这种机制与GLP-1抑制食欲的效果结合起来,可能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减肥方法,而GLP-1也可以抵消胰高血糖素提高血糖的效果。因此,他们开始研制靶向GLP-1受体(GLP-1R)和胰高血糖素受体(GCGR)的药物。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仅仅是在一个机制上添加另一个机制的问题,而是必须确保单个分子在激活这两种受体时具有同样的效力。
2009年7月,他们在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期刊发表论文【9】,首次报道了靶向GLP-1受体(GLP-1R)和胰高血糖素受体(GCGR)的双重激动剂具有更好的减肥效果。

此后,他们继续探索其他组合,他们确定的另一种激素是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GIP类似于GLP-1,它被认为也是一种“肠促胰岛素”,一种触发胰岛素分泌的肠道激素,但基于GIP的产品作为糖尿病的候选药物令人失望。
2013年10月,他们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发表论文【10】,证实了靶向GLP-1受体(GLP-1R)和GIP受体(GIPR)的双重激动剂比现有的仅靶向GLP-1受体激动剂更有效。在小鼠、猴子和人类中,该双重激动剂还能降低血糖,增加胰岛素分泌。激活GLP-1受体可能是打开了释放额外GIP能量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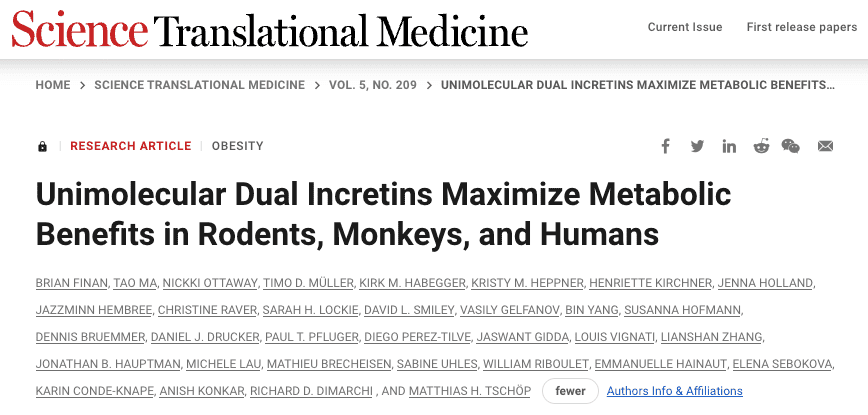
下一步,他们要开发同时靶向GLP-1受体(GLP-1R)和胰高血糖素受体(GCGR)和GIP受体(GIPR)的三重激动剂。
2014年12月,他们在 Nature Medicine 期刊发表论文【11】,实现结果显示,三重激动剂在小鼠上的减肥效果超过了双重激动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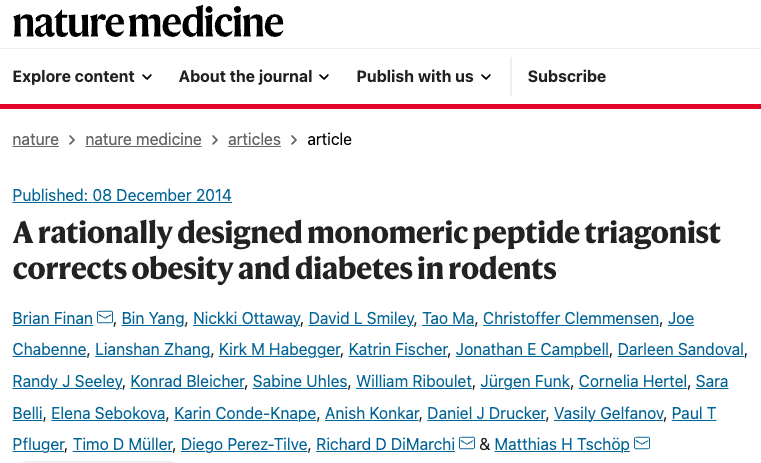
参考链接
1.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79.2.345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302716a0
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304368a0
4. https://doi.org/10.1016/S0021
5. https://www.jci.org/articles/view/112855
6. https://doi.org/10.1016/0014-5793(87)81430-8
7.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87)91194-9
8. https://www.jbc.org/article/S0021-9258(18)42531-8/fulltext
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hembio.209
10.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translmed.3007218
1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761
12. https://www.statnews.com/2023/09/30/weight-loss-ozempic-nobel-prize-scienc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生物世界 (ID:ibioworld),信息来源:STAT,编译:王聪,编辑:王多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