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每个时代都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读,常读常新。陶渊明的作品至少有两篇,一是《桃花源记》,一是《归去来兮辞》,是永远不能道尽的。
如果说,《桃花源记》是渊明社会政治理想的结晶,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渊明道德人格实践的记录。
桃花源旋开旋闭,幽眇难寻,真所谓“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归去来兮辞》由仕而隐,乐天知命,一切实实在在,读之即在目前。
前者系念社会,后者关乎自身。前者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后者标志着一种道德人格新范型的出现,在中国士人生活史和精神史上具有永恒意义。
如果要理解陶渊明的人格,寻找中国知识者道德人格的高标,就不可不读《归去来兮辞》。
为贫而仕,有什么可掩饰呢?
读《归去来兮辞》,必然会先碰到老问题:陶渊明为什么做彭泽令?又为什么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
据《归去来兮辞》序,归结起来有三点:做彭泽令以救穷,再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质性自然”的个性与虚伪的官场发生冲突;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
此外,在有关陶渊明的史传中,还有鄙视督邮事。渊明自述作彭泽令的始末以及去就的原因,应该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 石涛《悠然见南山》
渊明毫不掩饰为贫而仕。
口腹之需是人的第一需要,有什么可掩饰呢?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往往高尚其出仕的目的,称大济苍生呀,为国效劳呀,为民着想呀,非常动听,但不便说出口的是口腹之欲,身家性命。
中国士人的最早代表,或者说是士人的原型孔子,最先赋予知识者“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和崇高理想。但过分强调“谋道”,以至鄙视“谋食”,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之其中矣”。
一面鄙视“谋食”,甚至看不起樊须的学稼,一面又说“学也,禄之其中矣”。可见终究忘不了禄,终究不能不“谋食”,而禄便是最佳的谋食之道。关于“谋道”和“谋食”,孔子说起来有点吞吞吐吐,忸怩作态。其实,君子必须谋食,谋食为了更好地谋道。
只知“稻粱谋”者,固然是燕雀之志,然而世上也几乎不存在只谋道而不谋食的君子。
关于出仕的目的,渊明比孔子坦率得多。
他在五十多岁时回忆早年行役之苦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又回忆初次踏入仕途的原因:“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至于《归去来兮辞》序,交代因贫而仕的原因更真切具体。戮力劳作,所获仍不足自给,五个孩子待哺,瓶无储粟,饥寒交至。他又是个读书人,拙于生计。
亲戚朋友见其困顿如此,纷纷劝他出仕。他本来已经厌恶官场,十年间,多次由仕而隐,现在饥饿又一次逼着他踏进官场。仕而隐,隐而仕,反反复复,摇摆不定。
在某些人看来,他的仕隐不定未免是“二三其德”,不是君子行为。比如,日本学者冈村繁就怀疑渊明去就不定,是否“怠懒”,“见异思迁”,“虚荣心”等等缺陷。
其实,类似这种评论首先是漠视人性的存在。人为万物之灵,但“食、色,性也”,或者如渊明所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属于人道之首,人不管如何标榜志向高尚,衣食总是不可须臾或缺。
谋道固然是鸿鹄之志,谋食亦非燕雀专擅。试想“幼稚盈室”,五个孩子面黄肌瘦,甚至妻子也有怨言,作为父亲,难道能视若无睹,无动于衷?“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那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衣食无虞时才有的舒泰闲适。
倘若满室幼稚饥冻之声不绝,为父亲者,即使铁石心肠也化作百转愁肠矣。
渊明数次由隐而仕,犹如宿疾,反复缠绵,至作彭泽令之前尤甚,主要原因都是出于救贫的无奈。
性格刚强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违背“性本爱丘山”的素志,求个长吏做做。至于他如何求官,如何请托无门,内情不知。但可以断定,在“求之靡途”时,必定深感耻辱,痛苦不堪。
八十余天彭泽令,告别一生中最后的迷茫
我历来认为:要理解古人和古代作品,必须具备对古人的人文关怀,即与古人心心相契,互相照面,设身处地感受古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五情七欲。因为人情人心,可以超越时空,相通三世。
你读《归去来兮辞》“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等语,自然会想象自己若处于与渊明相同的境遇,会是怎样的焦虑和痛苦。
随后,你会自然地同情并理解渊明为何忍受耻辱和痛苦,赴任彭泽。你会看到,他在江边与儿子、亲友告别,冒着风波之苦,至彭蠡湖口,恰遇风潮激荡,江水湖水相激,怒涛拍打岸崖,声如雷鸣。这时,他远眺烟波阻隔的彭泽县,又生悔意,终当归去的念头,不禁涌上心头。

△ 黄慎《陶渊明诗意图》
义熙元年三月,渊明作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不久辞职归田。到了这年的八月,又去作彭泽令。
短短半年之中,辞官、做官如此频繁急遽,以至有人以为这是见异思迁。
殊不知,看似反复无常的背后,是性爱自然的素志与出仕以救穷二者的严重冲突,哪里是“虚荣心”呢?渊明作彭泽令,岂止没有荣耀感,有的是难耐的屈辱和痛苦。
我们不知道渊明在彭泽任上的情况。唯一可知也可信的一件事是郡里的督邮来县巡查,他耻于束带见之,即日挂冠而去。此事容后文评论。
为什么只做了八十余天彭泽令,就急匆匆归去?
他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质性自然”,遇上外力的非要“矫厉”,硬要变自然为虚伪,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痛苦?矫厉自然的本性,其情形正如龚自珍笔下的病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繁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于是,原来自然生长之梅,皆成病梅矣。
渊明生性喜爱自然,自然不愿被腐败的吏治矫厉。结果是深感心灵的痛苦,这痛苦比饥冻虽切还要难受。假若为了口腹之欲而役使良知,那就意味着抛弃自尊和自爱,与只知为“食色”生存的畜生相差无几。
渊明坚持平生之志,不愿违己,不愿口腹自役,这是他最终退出官场的根本原因。耻见督邮和程氏妹之丧皆属次要。
渊明为彭泽令八十余天,告别了一生中最后的迷茫,接着迎来彻底的觉醒。之前,他已有多次的迷茫与觉醒,摇摆于仕隐两端。
《归去来兮辞》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喻出仕是“迷途”,是“昨非”。
诚然,渊明年轻时有过济世之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从这少数几句诗,大致能看出他年轻时也有“尚志”的怀抱。
不过,大济苍生的声音,在陶集中实在很微弱,好像是偶尔的内心独白。相反,田园情结和隐士情怀,却是触目皆见。向往归隐,才是渊明性格的鲜明底色。

△ 文征明《桃源问津图》
在他作彭泽令之前的十年中,归隐田园的情怀,常常挥之不去。
晋安帝隆安四年,渊明为桓玄僚佐,从京师建康还江陵,还未到寻阳,阻风于规林,既叹行役之苦,又念家中老母,顿起归隐之念:“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暗下决心辞别仕途,纵心园林。
隆安五年七月,渊明由寻阳赴假还任所江陵。傍晚,挥手作别前来送行的朋友。
秋月初升,凉风吹过江面,天宇清明,星光闪烁。一叶孤舟,逆水而行,夜已深,还在艰难地前进。此情此景,再次触发诗人的归隐情怀:“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渊明自作江州祭酒至任彭泽令的十余年间,始终一心处于仕隐两端的痛苦中。越到后来,归隐之念越来越强烈。
辞官彭泽是他“性本爱丘山”情性的最终胜利,是人生中最关键的转身,一次意义非凡的道德人格的实践。
从此,他坚守田园,如扎根山崖的劲松,不论狂风或雷霆,都吹不倒、劈不断。陶渊明归隐田园,影响了后世无数知识者的处世行为,成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高标。
一个短命的陶彭泽,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政绩却获得了永恒
渊明作彭泽令仅仅八十余天,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他在彭泽有何政绩?留下什么“标志性的建筑”?史无记载。依常理推断,八十多天不可能建树了不起的政绩,也不会有“形象工程”。
他作彭泽令原本就是为一点俸禄,一是养活孩子,一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即为以后的隐居积累本钱,并非为树立自己的形象,让后人追念遗泽。
多种陶渊明的史传只记了他做了二件事。一件是“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另一件是“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前者写渊明喜酒,是风流;后者写渊明仁慈,是德性。假若渊明在彭泽任上真有打击豪强、削富济贫的改革大手笔,史传中恐怕早就大书特书了。
以此判断,他与彭泽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许,他只是在公田上经营经营,在廨舍中喝喝酒,或者跑到乡下劝农,说一番“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大道理。可是,在他之前之后,作彭泽令者多矣,后人却只记得陶彭泽。

△ 石涛《带月荷锄归》
一个很短命的陶彭泽,只存在八十多天,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政绩,却获得了永恒,居然成了中国职官史上的“天下第一县令”。
原因在于渊明辞官彭泽,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次道德人格实践,标志着一种道德人格新范型的出现。
奥秘在于人格魅力往往胜于事功。
事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一定的历史、政治条件下的产物。此时代之事功,有可能成为彼时代之恶果。彼时代之“伟人”,此时代或许称为“独夫”。
人格之美则从人性的根基上产生并升华,具有美善的崇高品质,必然超越功利,超越时代,获得永恒。
渊明之前,“士志于道”是士阶层(知识者)普遍信奉的古老传统。
士阶层的最早最伟大的代表孔子,是“士志于道”的传统的创立者。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把“道”作为士的终极追求目标,“谋食”、“忧贫”不足与言士。那么,“道”是什么?“道”即仁义。“士志于道”,即志于仁义。
由孔子创立,经曾子、孟子等先儒充实、完备的中国士人的人格,以仁义为旗帜,以尚志为品格,以任重道远为己任,以除恶扬善为担当,以朝闻夕死为标榜,影响中国士大夫文人至深至远,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价值、最壮观的部分。
然而,士的欲使“天下归仁”的宏伟理想,与其自身地位的低下,从一开始就两不匹配。
居于社会最高层的是贵族阶级中的最有权势者,是他们主宰天下,而不是贵族阶级中最卑微的士。虽然士是知识者,是思想者,“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但没有资格直接施政于民。他们必须先取信于权势者,才能对政治发生实际影响。
非常尴尬,士不过是权势者的附庸,若权势者不用士,士就什么也不是。孔子曾经自比藏于匮中的美玉,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孔子自比待价而沽的美玉,是士人真实处境的非常形象贴切的象征。美玉藏于匮中,固然仍是美玉,但无人知晓,也毫无作用。美玉只有在交易场合,而且只有善贾,才能显示它的真正价值。
士的处境尽管非常尴尬,但为了弘道达义,必须把自己沽出去。这是“士志于道”的首要条件。
所以,作为权势者附庸的士,就始终存在一个出处进退的大问题。对此,孔孟都有影响深远的言论。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甚至把出仕看作“农夫之耕”,不可离弃。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最能说明出仕对于士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和迫切。但“有君”是否一定能弘道?不一定。
如果遇上鄙视仁义的昏君或暴君,士的欲使天下归仁的理想不仅变得一分不值,自身也处于险境。结果是:要么融入封建专制政体,成为食利者;要么坚持孔孟倡导的弘毅人格,踽踽独行;要么急流勇退,“卷而怀之”;要么被无端猜忌迫害,身家性命不保。
东汉中后期的党锢人物,可能是将先秦儒家所赞美的刚毅人格范型发展到极致的一群。
当时,君主昏庸,宦官擅权,政治黑暗到极点。李膺、陈蕃、范滂、杜密等为代表的士大夫,高扬儒家的刚毅人格,以天下是非风教为己任,激烈批评朝政。
结果,昏君震怒,前后两次逮捕党人,李膺、陈蕃、范滂等皆死狱中,连累者六七百人,天下善士,一时殆尽。东汉党锢之祸,典型地证明封建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不能容忍儒家志于道的弘毅人格,邪恶与正直势不两立。
通过回顾儒家人格范型在历史上的遭遇,可以更清楚地显示陶渊明的独特人格与“士志于道”传统人格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新的人格范型的意义。
由官场转向田园,不为五斗米,而为人身自由折腰
毫无疑问,渊明年轻时受到传统的“士志于道”的儒家人格的影响,但“性本爱丘山”的隐逸情怀终究是他的人格底色。之所以如此,应当从东晋末年的时代及士人的生活史、精神史两方面解释。
东晋末年吏治腐败,渊明看得很清楚。
《感士不遇赋》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饮酒》其六:“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
《饮酒》十二:“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
《饮酒》其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渊明年轻时就有隐逸情怀,与晋末的时代有关。从士人的生活史、精神史方面而言,东汉党锢人士惨遭专制政体的打击,深刻影响了后世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加上汉末以降政治的极端险恶,以及老庄哲学的推波助澜,形成崇尚隐逸的潮流。渊明早年就深受这一潮流的洗礼。

△ 石涛绘《遥遥望白云 怀古一何深》
后来出仕,主要不在“尚志”,而是为生活所迫。“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使为王事奔波,却常心系田园。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东汉党锢人物那种与邪恶势力殊死战斗的精神。
几次短暂的归田,既没有孔子“三月不见君则皇皇如也”的六神无主,也没有孟子比喻的农夫耕田失去农具后的失落感。最后弃彭泽令如敝屣,与专制政体彻底决裂,完成了人生中最关键的转身。
陶渊明由官场转向田园,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道德人格实践。
一是彻底摆脱了封建专制政体的附庸地位,确立了卓然不凡的独立人格。
如前所述,“士志于道”,要想实现政治理想与体现自身价值,必须成为封建专制政体的一员。士人必须栖身于君主威权的阴影下,才有可能看到人生的光明。
但这光明其实是虚幻的,光明掩盖之下是难言的耻辱。这样的读书人往往成为专制政体的附庸和工具,口腹自役,很容易丧失独立的人格。
或许是孔子、孟子亲历权力对独立人格的胁迫,痛感人性在欲望面前容易萎靡退缩,因此一再强调遭逢厄运和困境时,必须高扬刚毅人格精神。
正因为专制体制与独立人格两者存在难以相融的矛盾,所以到了魏晋,一些思想家设法统一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许多名士一面做官,一面不理官事,将仕隐统一,鱼与熊掌兼得,不无得意地咏唱“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这种人生策略看来很圆融,其实虚伪至极。凡是直道之士,必然难容于专制政体,深感痛苦。因为专制政体的本质是不人道的,邪恶的,是腐败、枉法、黑暗的策源地,入于其中,很难洁身自好。
“既欢怀禄情”,是丧失羞耻心,是食利者的情怀。“复协沧州趣”的所谓趣味,也决不是真隐士的啸傲山林,远离俗世,不过是假隐士的标榜。
渊明耻于亦官亦隐,毅然逃禄而隐,再次确立了士人的独立人格,指明依附专制政体或亦官亦隐之外,还有归隐一条路,能真正保持人的良知与真性。
二是追求自由精神的可贵。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向往和追求自由,属于人的本性。魏晋是自由精神高扬的时代,“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成了追求自由,放任情性的一面旗帜。
可是,真的越名教意味着放弃名位和官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渊明说的“口腹自役”,“违己交病”,乃是精神自由与官禄享受二者冲突引起的痛苦。
要自由,还是要“五斗米”?一般官僚难以放弃“五斗米”,宁愿损失自由或降低自由度,经受专制政体的“矫厉”。“怀禄情”和“沧州趣”实际上难以调和,若要“怀禄情”,必然会全部丧失或部分丧失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渊明却不,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为人身自由折腰。他懂得,物质有价,自由无价,丧失自由,比饥冻虽切更难忍受。渊明辞官归隐所体现的追求自由的精神,不仅在古代难能可贵,而且具有当代意义。
三是保持自我本真。
虚伪,乃是专制政体与生俱来的痼疾。一个以奴役人民为目的的专制政治体制,必然不存在正义和公平,必然导致吏治的腐败。虚伪,成了升迁的通行证;正直,反倒是官场的驱逐令。
渊明拒绝被“大伪斯兴”的官场矫厉,要保持“质性自然”,保持“任真自得”的生活状态,从思想渊源上说,既得之于儒家,也得之于道家。
四是安顿生命于自由朴素的田园。
为了自由和保持本真,渊明以富贵为敝屣,情愿选择贫困,躬耕田园,这是渊明道德人格最有实践意义与不可企及之处。
魏晋隐士不少,但像他那样,与妻儿、亲知在一起,躬耕田亩,经受劳动的艰辛,收获艰辛的回报,在自然、宁静、孤独中安顿生命、安顿身心,这在中国士人生活史和精神史上最具开创意义。

△ 袁耀《桃花源记》局部
在渊明之前,知识者的人格犹如一个苦魂,身上刻着“士志于道”的印记,或者徘徊在专制政体的高墙之外,不得其入;或者在高墙之内苦斗挣扎,忍受口腹自役的痛苦。
陶渊明却从高墙内毅然决然地冲出来,喜看出岫的云,高飞的鸟,篱边的菊,樽中的酒,欢乐地歌唱:“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而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何疑。”在归田之初大声表达对即将开始的自由生活的憧憬。
虽说过于理想化,贫困不久将会像大山一样压迫他,但他抛弃富贵,不信仙乡,尽情享受田园的宁静平淡,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依然激动了后世千千万万的读者。
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能反思自身的人格孱弱、猥琐或堕落,面对渊明的道德人格高标,生出一份愧意,进而师其人格之万一,那么,庶几读懂了《归去来兮辞》,读懂了陶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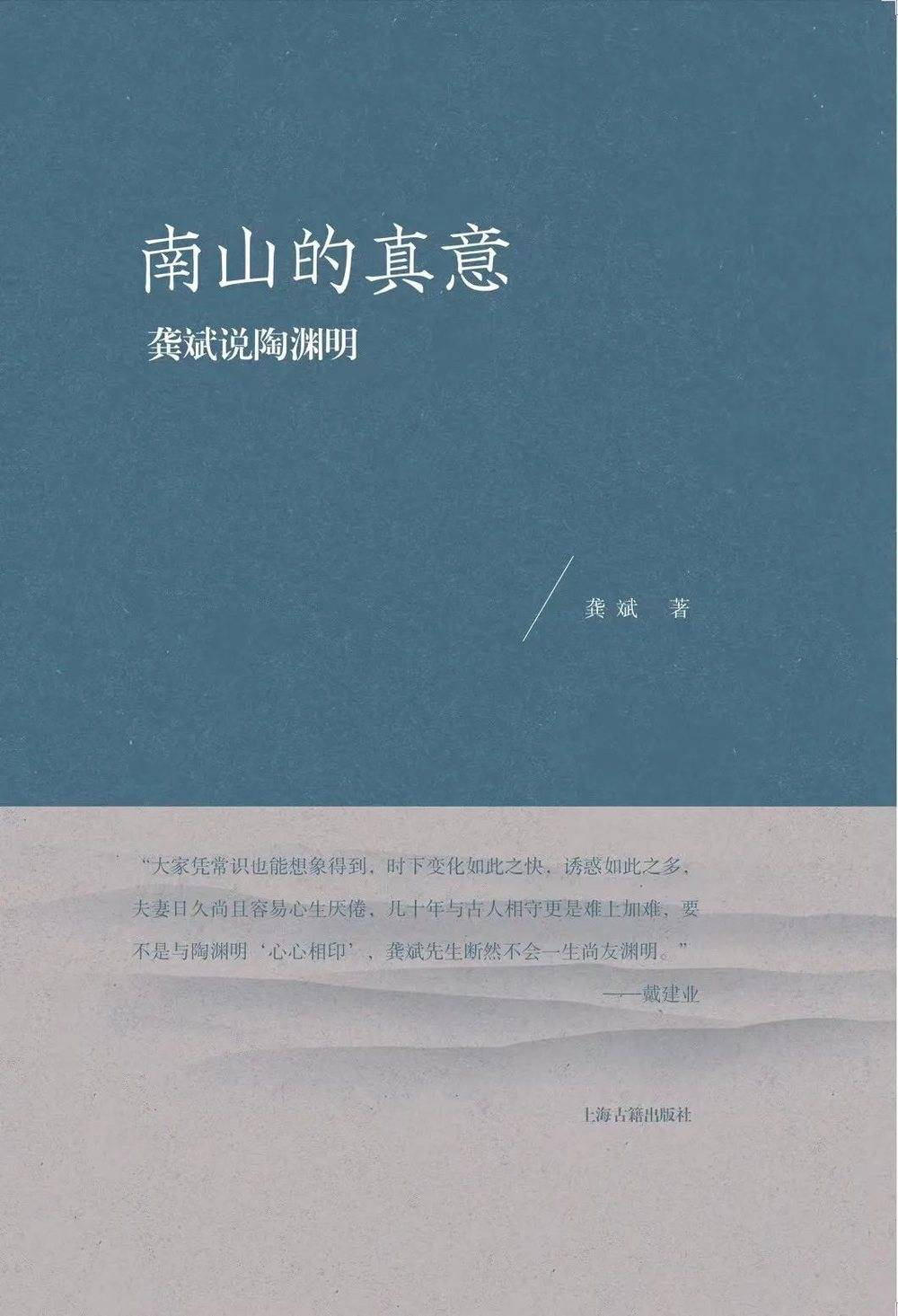
《南山的真意》
副标题: 龚斌说陶渊明
作者: 龚斌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 2023-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内容摘编自《南山的真意:龚斌说陶渊明》,作者:龚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