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eesayso(ID:gh_7504995ab922),题图来自:《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国家统计局在6月公布的5月青年失业率达到20.8%。
青年失业率主要指16-24岁之间人口的失业率情况。这一数据从今年1月以来持续上涨,也是自2018年公布青年失业率以来的最高值,总量达到600多万人。
这意味着目前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3300多万青年人口中,2600万已经找到工作,而600万仍旧处于失业状态。
青年失业率本身有摩擦性失业的短期影响,但同样是经济波动起伏的反映,一方面摆脱不掉新冠疫情的后坐力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悄然发生的人口模式转变存在本质关联。
就业质量和结构矛盾则是青年失业率之上,更为深远的人口代际问题。
美国人口统计学家珍妮弗.D.朔巴在其今年出版的专著《80亿人口——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中,就以变动不居的全球人口模式为背景,分析了青年失业率及其背后运转不停的代际矛盾。
当“青年失业”成为人口议题之一
首先,我们应了解:21世纪的故事,与其说是人口呈指数级增长的故事,不如说是关于各方面差异扩大的故事。
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历史新高,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同比变大。21世纪的世界人口仍在增长,出人意料的是,其中98%的增长发生在尼日利亚一类的欠发达国家。
在这50年中,不少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面临生育率下滑的处境,而美国是例外,直到最近它的生育率仍接近更替水平。时至2020年,日本已经跌至第11位。据预测,205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的生育率将超越俄罗斯和墨西哥。这意味着全球人口重心将发生明显的地理转移。
回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入学率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把握了青年型人口模式的中国成为历史上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时至21世纪的今天,2021年中国64%的人口处于劳动年龄段。工作人口多,被抚养的人口少,这种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但人口年龄结构没有显示出:中国正在走向老龄化。
实际上,处于劳动年龄的年轻人口相对饱和,即将迈入老年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生育率呈现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人口模式正在从成年型人口结构转变成为老年型人口结构。
历史上,青年失业率上扬不止一次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3年前。2010年的突尼斯,26~30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据了该国人口最大比重。同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来到一个加油站,在政府大楼的街道前引火自焚。这是在针对于大楼里的市政官员。
当天,布瓦吉吉平日贩卖水果和蔬菜所用的秤被市政官员没收,他不断抱怨,结果被警官人身攻击。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在布瓦吉吉身上,身为长子的他没有稳定收入,推车卖农产品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这场悲剧成为一场抗议的导火索,而不能忽视的青年人口膨胀趋势是被等待点燃的燃料。
突尼斯的人口趋势发展导致布瓦吉吉同年龄段的人群面对就业竞争比最近任何一代人都激烈得多,而工作机会却寥寥无几。这一起发生在突尼斯的青年失业问题并非个例。
时间倒回1975年的伊朗,15~24岁的年轻人有660万,占15~64岁成年人口的37.7%。尽管每年都有大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但他们却大多投身石油开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国王统治下的伊朗25%的收入用在了武器装备上,而不是建设经济,在经济发展失调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分配失调,数百万人失业,庞大的城市青年群体承受着这份人口压力。
如果再次拉长时间的刻度尺,我们会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后排兵的德国,年轻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最高值,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劳动力市场。
这些年轻人没有工作,对未来不抱希望,他们一直希望有人能针对现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政策,并能做出郑重承诺满足自己的心愿。从当时的人口统计角度来看,此时的局面真可谓糟糕透顶:工人数量达到峰值,经济却一片萧条。
从1918年至2023年,随着世界各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不同地域青年失业问题或低频或高频不断发生,已然不再特殊,但伴随着其而来的阴霾仍成为悬在每个人心头的恐惧。
或被失业引发的青年抗议
2010年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后,其同年龄人群以此为契机发起抗议。他们与自己的父辈不同,与布瓦吉吉同龄的年轻人都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很难成婚或建立自己的家庭。
警察和其它官员天天上门骚扰,让他们感到厌倦;腐败的政客无视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满腹抱怨。此地区身处相同境况的年轻人高达6400万。
亨里克·乌达尔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年轻人占人口35%及以上的国家,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比年龄结构接近老年型的发达国家高出150%。虽然人口趋势这一单一因素不会引发革命,但会加剧潜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因此在伊朗爆发。1930年,受德国的经济萧条困境影响,超过18%的选民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助其成为了德国第二大政党。希特勒曾经承诺要恢复德国的荣耀,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共鸣,更是吸引了大批前途渺茫的年轻人。
这是因为反对现状的成本很低,德国年轻人将赌注押在了独裁者希特勒身上,助长了战争的爆发。因此,当我们专注于青年就业问题的回应,实际上也呼应着对未来社会态势的判断。可以设想:如果每年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都在增长,那么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失业率将会飙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不接受教育,靠什么打发时间呢?
人们根据发生在突尼斯的内乱创造了两个重要概念:相对剥夺感和机会成本。相对剥夺感指代与上一代相比,生活并没有达到相同水准,这也意味着年轻人对生活的期望没有实现,因此他们拥有了反抗的动机。
但是,犯罪题材的电视节目告诉我们,动机只是一部分原因,机会是另一部分原因。机会成本指代做某事所要放弃的最大成本。劳动力资源丰富,相反工作机会极少,因此年轻人拿起武器的机会成本变低。
如此,动机和机会结合起来,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相互作用。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戏剧般出现过,背景截然不同,但本质上与青年人对未来发展预期息息相关。以上这些例子都与暴力相关,这致使各国政府面对青年问题时每每颇感紧迫。
如果我们跟随朔巴,将目光投向青年失业导致的暴力反抗现象背面,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靠什么打发时间”的问题。
抗议背后的代际矛盾
在不同的国家,成年的标志大致相似: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和家庭,不再依靠父母;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年轻人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丧失时,就会引发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革。
经济动机并非背后唯一的驱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在政治上遭到排斥或者被掌权的老一辈忽视的感觉,以及改变现状的想法,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青年动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是由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刺杀者点燃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青年波斯尼亚”的一名革命者,他希望遥远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采取行动对抗奥地利以赢得独立。
而在当今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新加坡,当地对住房保持着严格限制。不少年轻人痛苦地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搬出父母的房子,这种情况下约会也会感到十分尴尬。
但此地也未爆发抗议。所以相对上一辈而言徒增的生活成本未必会激发反抗,但政治意见无法被上一辈接纳或成为抗议的导火索。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18~21岁的年轻人被征召参加越战,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他们这个年龄可以上战场,却没有资格参加投票,因而感到强烈不满。
除此之外,这群年轻人还有一种普遍的疏离感,对性别、种族和社会现状感到愤怒。活动人士要求国会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1971年,这项提案通过。
这种政治氛围随之弥漫开来。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人为了反对战争和争取公民权利进行过示威游行,1968年,法国大学生也参与其中,要求对僵化的大学体系进行改革。此前10年,法国大学生数量从17万增长到50多万,仅巴黎就有13万人之多。
最终,游行四天内罢工人数增加到900万。1968年发生的事件揭示了人群所处的人生阶段和历史时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政治影响。
正如科兰斯基所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自我感觉非常不同,怀有强烈的疏离感,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一切形式的权威中就囊括了与青年人政治诉求不适配的政治权威。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缩小代际来进行民主协商。
2018年,年轻的国家尼日利亚成功将担任总统的最低年龄从40岁降至35岁,众议院任职年龄从30岁降至25岁。此时,尼日利亚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8岁,这一政策变化给予部分尼日利亚年轻人参与政治竞选的机会。尽管如此,青年参政或政治意见被接纳也并不意味着实现民主的机率稳步增加。
青年地位决定立场
青年意味着人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段,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而言,随其而来的影响力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青年易于制造麻烦、煽动冲突,力求通过重大变革来改变现状;另一方面,青年是革新者,是争取权利和进步的驱动力量。地位决定立场。
阅读文献资料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特别是青年男性,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但如果认为这部分人全都存在问题,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这会将大批青年所做的积极贡献排除在理性讨论之外。
因此,政策制定者所持有的合理的政策目标应该关注青年的机会,这里主要指工作机会。且不能用人口统计当做借口掩盖不作为的后果。
不要责怪青年,应该把重点放在腐败、低效的体制和法治薄弱等因素上。这些问题显露出来则是治理不善的标志,意味着此地商业投资环境受限。另一方面过度吹捧青年人口红利也可能会导致其它问题。
无论什么情况,人口结构转型期的过渡都充满阵痛。在年龄结构比较大的国家,仍有不少青年在寻求独立,却没有机会实现。哪怕是在富裕国家,青年的生活也会受到是否拥有政治和经济机遇的影响。
作为人口议题的发力点之一,“青年失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始发阶段已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每年毕业季到来,涌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口仍会增加。与此同时,以应对老龄化,退休年龄推迟政策已开始实行。
老龄化的世界即将到来,我国也已进入到人口结构转型期。到2050年中国大陆20岁至69岁年龄段人数将减少8.9%,台湾地区将减少14.9%。这或意味着代际之间的立场、意见将出现更多样、更复杂的发展态势。如何将转型期危机转化为机遇,将取决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人口统计数据则提醒着政策制定者应当意识到该有所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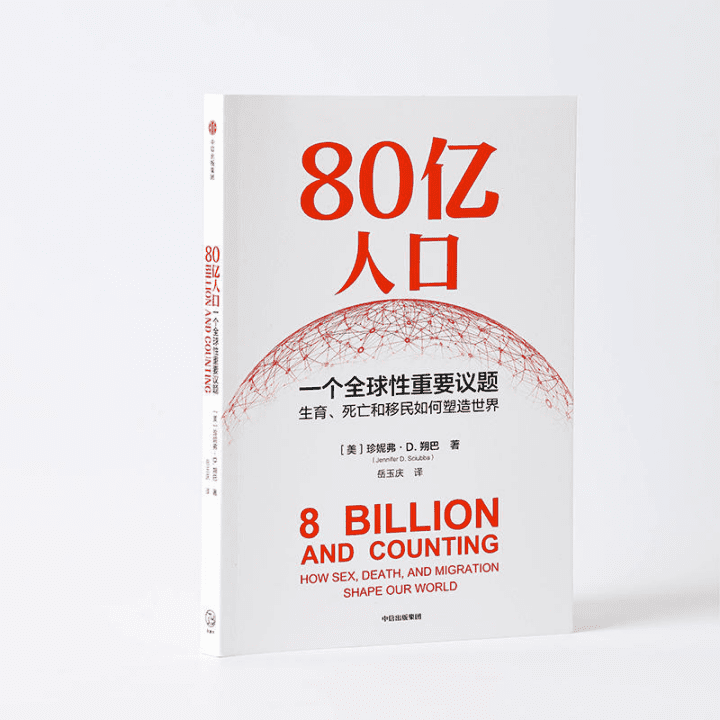
《80亿人口——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
珍妮弗.D.朔巴 著,中信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eesayso(ID:gh_7504995ab922)

